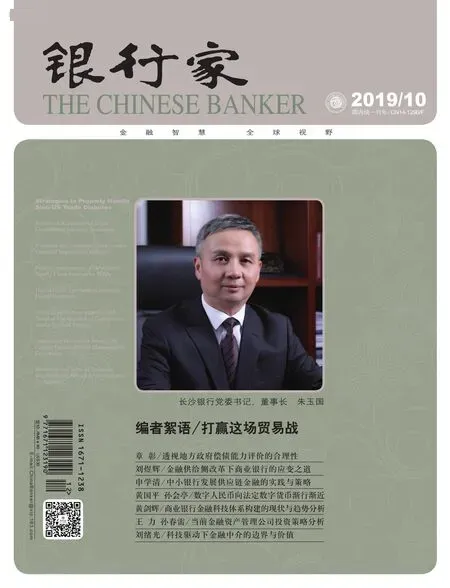父子集(39)
臣服人格與叛逆人格 王青石
前天穿梭在車水馬龍中,看著被無數(shù)個面孔填充的北京,一個念頭忽然出現(xiàn)在我腦中——我們所有人對“現(xiàn)實”的既定印象都來自童年時代,世界觀的成長只是對這種既定印象一遍遍的刪刪改改。
在我們眼中,公眾場所的陌生人就像一些隨機的人形程序,我們很少意識到他們也有私人空間、真實如你我的主觀意識、只有他們自己才了解的成長經(jīng)歷,以及不為人知的家庭體驗。
人腦具有自我欺騙性,其體現(xiàn)之一,即當(dāng)人被自己的主觀認知所框住時,他會逐步加深對自己主觀想法的深信不疑。打一個比方,如果一個健康孩子從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每天灌輸“你有××疾病”這一概念,那等到他成年后,任何人都將很難逆轉(zhuǎn)他把自己當(dāng)病人對待的狀態(tài),哪怕他連一次癥狀都沒有出現(xiàn)過。
所以容易被我們沖動判定為錯誤的事物,往往只是與習(xí)慣性思維背道而馳而已。
也因此,假設(shè)決定論不成立,而具備主動性的性格可以獨立于客觀條件存在,那獨立于客觀因素(即習(xí)慣產(chǎn)生處)的性格其實只會有兩種:臣服人格與叛逆人格。或者說,當(dāng)一個為我們留有選擇余地的事件發(fā)生,而我們的思維已經(jīng)有效忽略掉此前所受到的來自各種消息源的耳聞目染與親身經(jīng)歷,從而完成了一個盡量“正確”的決定時,這個決定與絕對客觀條件或理想狀態(tài)下的最佳決定的偏差便出自性格的作用力。
詩意而言,性格就是攔在我們與上帝之間永不可逾越的幾厘米。當(dāng)一個人屈從于外界因素的作用力,這種心理出自臣服人格,當(dāng)一個人嘗試扭轉(zhuǎn)外界作用力,則是叛逆人格。
綜上所述,只要有性格存在,就沒有人的思想是永遠正確的,因為性格的定義正是與絕對無誤的偏差。
閱讀傳統(tǒng)書籍與閱讀商業(yè)化公眾號的區(qū)別便在于此。漫畫、新聞與科普類除外,支撐著公眾號的多數(shù)文字素材皆是通過闡述、維護一個立場來做文章。然而立場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具備主觀性,雖然有時這種文章會靠特定辭藻為自己生造一個客觀面具出來,但本著吸引流量、誘導(dǎo)傳播的目的,絕大多數(shù)在非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里立足某種立場的網(wǎng)絡(luò)文章都無異于精神辣條——入口挺香,營養(yǎng)沒有,過量食用還會壞了胃腸。
并非傳統(tǒng)書籍就清高在上,但考慮到當(dāng)代在線讀物通過高瀏覽換取廣告收益的特殊價值,閱讀傳統(tǒng)書籍相比之下顯然是更純粹的閱讀、汲取信息的體驗。
同樣道理在人際關(guān)系方面也具有探討意義。
“人際離合是一種根據(jù)腦中激素起伏進行的周期性運動。”這句話我很早就從微觀社會學(xué)課上摘抄到自己文中,但現(xiàn)在來看依然值得思考。如果我們把離與合的傾向分別視作叛逆與臣服的話,那么依據(jù)理論,世上所有人都是游走在對不同事物的叛逆與臣服之間的,是這種來回游走維持了個體與個體、以及個體與概念間的平衡。
在任何自然的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中,不存在絕對的臣服型人物與叛逆型人物,所有人都是這兩種人格的混合體,只是每個個體的調(diào)配比例不同。依此方法,人依照天生性格與后天經(jīng)歷可以粗略分作四類,如下:
生來是臣服型人格,后天環(huán)境也使其一直處于臣服狀態(tài)。這種人在面對挑戰(zhàn)性事件時斗志偏低,但生活中非常溫順, 做事也往往偏于安穩(wěn),擅長忍讓與規(guī)避風(fēng)險,較為容易滿足。我給他們的標(biāo)簽是“幸福小職工”。
生來俱備臣服型人格,卻因后天所迫而要反復(fù)參與斗爭、革新運動或激烈競爭。這些人非自愿地成長、生活在競技場或高強度壓力下,很少能靠一己之力掙脫韁繩(先天人格所致),所以會不安,會頻頻感到沮喪,會容易出現(xiàn)精神問題。形容他們的詞匯包括優(yōu)柔寡斷、不上進、任人宰割等。我給他們的標(biāo)簽是“董事長家只想搞園藝的少爺”。
生來叛逆型人格,后天際遇也縱容了他們生性的野蠻生長。這類人常常懷有英雄情結(jié),好勝心強,且享受自信的狀態(tài), 他們?nèi)烁衽c思考能力相較于大眾都更為獨立,潛在缺點是內(nèi)心多疑與病態(tài)自負。我給他們的標(biāo)簽是“有個性有想法的小領(lǐng)導(dǎo)”。
生性叛逆,卻因后天環(huán)境而常年生活在臣服的狀態(tài)中。這群人習(xí)慣將內(nèi)心真實想法隱藏較深,嚴(yán)重者會因此感到壓抑, 容易不擅社交,并常會因自我懷疑與自卑而感到不開心,他們與第二種人一樣容易產(chǎn)生精神問題。我給他們的標(biāo)簽是“反骨仔與滿腹怨氣的小市民們”。
注意,我在上述總結(jié)中所提到的“后天環(huán)境”通常指代“成長環(huán)境”,理由參考本文第三段。人一生的習(xí)慣往往是在成長期形成的,這對于在未來幾年里準(zhǔn)備養(yǎng)育小孩的朋友來說,興許非常重要。
近兩三日所想,大抵如此,隨性一寫,用以記錄。
2018.5.16
在天賦異稟的人生中得到滿足感,是當(dāng)務(wù)之急 王青石
魚離了水不能活,我離了圈子比脫水之魚還慘。更慘的是,意識到這件事花了我一年多時間。
2018年6月6日,夏初,很平淡。我站在籃球場上,對面那個2005年生的孩子生龍活虎地用花式運球戲耍我,晃得我頭暈?zāi)垦!獮橥怀鲂Ч掖瓪忸l率甚至像放慢了八倍。“打得好,可以的。”喝水休息時,我抱著最后一點尊嚴(yán)對他說:“你這個技術(shù)特點頗有托尼帕克的神韻,是你應(yīng)該不知道的一個球員,我上學(xué)時候他很強。”
“我知道托尼帕克啊,看過他carry的很多比賽。”小孩大汗淋漓,一本正經(jīng)跟我說。
我略驚到。“你怎么可能看過啊,我2009、2010年開始看球,那時才是帕克巔峰。”
“對啊,我2010年開始看球嘛。”他仍一臉正經(jīng)回答我,正經(jīng)中夾雜一絲深藏不露的欠打。

我不想再說話,默默喝水。
海外久居后歸國的人都有過這種感覺:在回家后第一個醒來的早上,你會覺得那些大洋彼岸的時光是夢,是一夜間燃燒殆盡的腦細胞,沒有真實發(fā)生過。
我2010年出國,2017年回國,這場夢持續(xù)了七年。
當(dāng)我睜眼醒來時,我的房間確實仍模樣熟悉,街對面匯佳幼兒園的早操音樂仍一點兒都不悅耳,書柜上那只初二在昌平抓娃娃抓到的黑猩猩公仔仍一臉兇相,兩只大綠眼珠子瞪著我。
我坐起身,不確定目前什么情況。打開朋友圈,看以前總一起下館子、在湖邊搞音樂的學(xué)弟阿樊都畢業(yè)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圍在他身邊、對著鏡頭笑,有人穿著畢業(yè)禮服,有人穿著便裝,照片里羅切斯特的太陽光仍很明亮。
一群還沒醒來的家伙,而已。
不知從何時起,我變得只會寫意識流文字,雖說大學(xué)時誤打誤撞投出過幾篇受歡迎的稿子,也因此獲得了一些關(guān)注者,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是很被我現(xiàn)在的囈語連篇所吸引。我時常為此苦惱,但能改善的有限。
當(dāng)生銹感日益加劇,我就在夜里聽聽小老虎、Itsogoo這些人的音樂。他們的歌詩性很足,文字營造的空間感特別棒,只是普通聽眾很少有這種去體會詩句、營造更多維遐想的興趣,所以他們的歌有兩三百條評論都算很不錯了。
“小老虎的音樂啊,我覺得比國內(nèi)平均水平超前了十年左右吧。”在一個音樂交流群里,有天我這么感慨道。
“真能裝啊,幾年還能聽出來。”某個素不相識的酸民立刻諷刺我,我沒回復(fù)。
混跡過的許多獨立音樂人微信群,一般都有幾百號這種人,他們很暴躁,生活里一定沒少受委屈。可以說他們都是一些雖無意、但最終還是把對音樂的熱愛變成鳥籠困住了自己的人。
鳥籠嘛,這個星球就是個百鳥園,每個人都有一個或安好、或傷痕累累的喙。
在家這一年里父母沒有讓我去實習(xí)或上課,我大部分時候就自己在房間里寫歌、錄歌。不過一如高中那些粗糙的、最終石沉大海的惡搞小視頻一樣,這些歌并不會成為我行路的指南。我一直知道,如果一個人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為了點亮前路、賦予他力量,那這種創(chuàng)作思路本身就不利于創(chuàng)作。
創(chuàng)作是生活的調(diào)劑,但最好獨立于生活。生活是溫飽、柴米油鹽與定期去醫(yī)院體檢;藝術(shù)創(chuàng)作則是顱內(nèi)閑置空間的一套利用方法論,后者是較為不必要的。
藝術(shù)生大多都家庭富裕,人們會覺得這是社會公不公平、窮人富人選擇平不平等的問題,其實不然。任何人一旦躋身衣食無憂階層,他的孩子都會更容易被藝術(shù)性的事物吸引,這是一種自然傾向。并非說家境普通的人就不會喜歡美的事物,他們的審美能力同樣與生俱來,只是不會像富人家孩子一樣更容易看見美、感受美——因為后者所要思考的正事(吃穿住用行)比前者少得多,也就是說他們顱內(nèi)可支配于精神需求的閑置空間要大得多。
站在上帝視角去看,會發(fā)現(xiàn)這不過是自然規(guī)律而已。一個社會的階層差異貧富有別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和道理,一如女人在男權(quán)社會中與男人同樣重要一樣,低階層、中產(chǎn)和高階層的兼容是確保社會能健康運轉(zhuǎn)之關(guān)鍵,抹除階層間差距的想法本身并不切實際。要知道,從古至今地球生命形式的繁衍、延續(xù)都是植根于叢林法則之上的。
所以我從中應(yīng)悟出的就是,創(chuàng)作當(dāng)愛好就好,縱然我天賦異稟。
8月即將重返美國,在這之前的時間大抵還是會無趣的,但不妨趁閑繼續(xù)折騰。
2018.6.08
神都是單獨一個人 王青石
“生命到了最高等階段,為什么他們都是單獨一個人?神都是單獨一個人,耶穌是一個人,釋迦摩尼是一個人……無論圣經(jīng)還是佛經(jīng)里,都沒有談?wù)摴陋殹?赡懿徽務(wù)摴陋毜臅r候,就是最大的孤獨。”在接受VICE中國采訪時,科幻作家韓松坦然說道。
時值2018,七月已有落葉了。
我站在奧體公園一座橋上,看見那些在十年前奧運落幕后就未再延伸過的公路之外,許多被操縱的交通工具正沿著北四環(huán)匆忙駛來、或駛?cè)ァ0氩[起眼,朦朧視野中的深灰色是混凝土,淺灰色是鳥巢體育館,水立方是一坨棱角分明的泡泡。
身旁熙來攘往的游客穿著符合自己審美的服飾,并癡迷于使用蓋著一層汗?jié)n的手機鏡頭。他們聚精會神舉著自拍桿,甚至沒有看路,險些就同我發(fā)生不雅觀的碰撞。
還好只是擦肩而過。
本科畢業(yè)后什么正經(jīng)事也沒做的一年馬上就結(jié)束了,離家七年初次回國久居,本以為會重拾些許歸屬感,不料卻恰好相反:在與家鄉(xiāng)人群打過足夠多的交道后,我最大感受竟是一種強烈的不合群,一種遠超脫于“寂寞”定義的形單影只感。我難以融入同齡人們的興趣點,許多話題要避諱,也時常要掩飾對他們諸多看法的嗤之以鼻。
我先前一直強調(diào)“文化鴻溝”“中美夾縫人”等地域相關(guān)的、使我們成為異類的因素,其實現(xiàn)在回頭一看,許多同樣橫跨兩個文化、隸屬于北美留學(xué)圈或移民圈或什么圈的人,總還是能找到歸屬的——哪怕只是屬于一個不大的群體。所以我會問自己,也許失范感和留不留美的因果關(guān)系從來不是那么強烈,人在任何環(huán)境中都有權(quán)利去擅自活成一名失范者。
大抵,只是在豐衣足食的生活里看見天花板的蒼蠅,無傷大雅,不過在我偶然聽到韓松有關(guān)天選之人的孤獨那句話后,還是隱隱受到了震撼,我在歌詞里提及過人站得越高,會越膨脹,卻沒有考慮到越膨脹,越孤獨這件事。我想這是一個循環(huán),某種意義上人所處的地帶越高,他便越自大,也就越容易感到一絲沒有同伴的凄涼。
在這種看似茅塞頓開的瞬間,最需一缸寒透脊髓的冷水浴。
Alina是我大學(xué)時關(guān)系甚好的學(xué)妹,昨天她同我講了前些日在西安拜訪幾位80后隱士的見聞。據(jù)她所說,畢業(yè)于西安美院的那幾位朋友已在終南山上住了五到十年不等,平時就飲山間泉水,食自己種的、養(yǎng)的。閑暇時,他們會喝茶、把玩中國的傳統(tǒng)樂器,其中一人是一名作家,另一人則精通于制造古琴,他們以此賺些小錢,并維持與社會的往來。
“吃穿夠用,經(jīng)濟不算富裕,精神無比富足。”她說。
我認真思考了一下這種生活是否值得向往,并斬釘截鐵得出結(jié)論:我只想做個城市人,步行范圍內(nèi)要有便利店,出急事去醫(yī)院不會被路程耽誤,周邊必須要有數(shù)家可不停換著吃的餐廳,這都是基本需求。
深山有其詩意,但生活向來不是詩。
而他們孤獨嗎?必然,他們只是不介意,否則也不會住這么久。Alina說他們租的那間山居只要4000元人民幣,租期是二十年。可能這種生活對尋常人是修煉,但對他們而言卻是再好不過的、消磨歲月的方式。就像南美許多雨林部落后人仍相信的——萬物皆有靈且共通,由西方世界引領(lǐng)的現(xiàn)代生活方式卻鼓勵人們阻斷自己與生俱來的通靈能力,在這個物質(zhì)財富就像毒品的時代,總得有人去堅守與萬物的關(guān)聯(lián),那種原始且渾然天成的、魚與水的關(guān)系。
物質(zhì)財富則確實會像毒品,人們總是想要,卻不會因為得到它們而感到真正的快樂。我清楚記得那位雨林部落長老在紀(jì)錄片里一字一頓說道:“真正的快樂只會源于靈魂。”有趣的是,這是一句字面上連小學(xué)生都能看懂的話,地球上卻鮮有人把它當(dāng)一回事,或許因為毒品帶來的短暫亢奮與致幻已攪拌了他們的感知力,或許他們只是生來愚笨。
無論怎樣,我是說,既然四十、五十多歲的人都還在網(wǎng)絡(luò)上感慨自己“依舊在尋找生命的意義”,那我們有什么理由焦躁呢?雞湯總說,相比于對終點所能給予的垂涎三尺,不如以路本身作為意義。我近來愈發(fā)全身心感受到這句話的深奧之處了,卻難以表述這種神奇的感覺。必須承認,世上最美妙的感覺的確令所有語言蒼白,在上帝的左手前,文學(xué)、藝術(shù)家也只能做謙卑的學(xué)徒。
大致如此吧。我希望此刻的平和感來自這一年無數(shù)思緒的沉積,而不是方才喝的那兩瓶東方樹葉烏龍茶。
2018.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