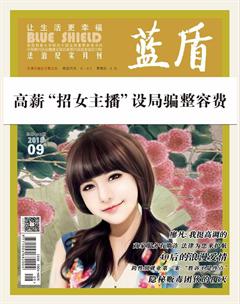不肯去與已成功

我們的生活,已經被—連串結果導向的“成功”所定義。
端午節期間,我帶父親去了一趟舟山。和碼頭上煙火漫天、熱鬧喧囂的沈家門相比,普陀山給人遁入空門、歲月靜好的感覺。
在島上,漁船轟鳴的馬達聲沒了,隨之消失的是那些在大城市里司空見賃橫沖直撞的摩托車和三輪車,以及悄無聲息但速度極快的電動車。
這里唯一允許的機動車是官方提供的旅游巴士,但你幾乎聽不到喇叭聲。有人說,島上最大的聲音,不過是從馬路邊上喇叭傳來的誦經聲,海浪拍打沙灘的聲音。
去往旅店彎曲陡峭的山路上,散布著剛剛抵達、拖著大包小包的游客。偶爾有幾個騎著漂亮自行車的年輕人錯身而過,向碼頭疾馳而去,車座車框上,都摞著五顏六色的行李箱,有人告訴我,他們是給離開的客人送行的跑腿小二。這些騎車人很少按鈴。
我不僅暗暗為這些嚴苛規矩叫好。海天佛國,圣地有了圣地的樣子。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現事情并沒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
比如,旅游巴士價格不菲,而且是固定路線。如果游客去景點之外的地方,或者想在中途下車,都是不允許的。雖然島上各個景點之間距離不是很遠,但步行的話,也不近。特別是腿腳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行動有障礙人士,會面臨很多麻煩。
同樣的邏輯也在游客這一端應驗。
在島上,無論是在法雨寺的大雄寶殿,還是某個偏殿里的天王,很多人“見佛就拜”。我有不少信佛的朋友,很敬重佛教徒的虔誠。但我無法把那些在大佛面前虔誠禱告的香客,和那些在齋堂里肆意浪費食物的人聯系在—起。他們的高聲喧嘩,甚至淹沒了和尚們的木魚聲。
佛寺似乎看出了這種臨時抱佛腳的功利信仰觀,在宣傳欄里貼出文章,告誡人們不要執拗于錯誤的導向,認為自己的布施會帶來直接的后果。但就像沒有太多人會留意什么是‘普陀三寶”一樣,宣傳欄“敗給”了可以拍照曬朋友圈、高達33米的南海觀音大佛。
網絡時代,我們的生活,已經被一連串結果導向的“成功”所定義。花幾塊錢購買一瓶水,空中也會飄來一句“微信支付已成功”。一天下來,我們能收集到十幾個甚至幾十個“成功”。這是我們所謂的小確幸嗎?
似乎也不全是網絡的錯。“我開始了解教育哲學的根本差異,中國側重最終結果,美國則關注獲得最終結果的過程。”來舟山前,我看到一篇《紐約時報》的報道,記錄了一個美國老師在舟山中學教學的感悟。
我在旅店旁邊和一個島民交淡。他說,島上許多居民都購置了一批日本淘汰下來的二手自行車,車結實,基本上騎上幾年不會有問題。他挎著腳下那輛依然貼著“兵庫縣水上中學”紅白標識的內三飛變速自行車,特意強調:“騎得很舒服啊。”看來,從一個目的地抵達另一個目的地,過程還是很重要的。
因為地理關系,普陀島和日本島頗有淵源。普陀山的第一座佛教寺廟就和日本人有關。在康有為題過詞的紫竹林里,曾經有一個不肯去觀音院,這是普陀山最早的佛教寺廟。
841年,日本和尚慧鄂從五臺山請了觀音渡海回國,在杭州灣口遇海浪而置像于某洞東側,于是蓋了個不肯去觀音寺。
以我粗淺的理解看,“不肯去”三個字,以一個現代語境聽起來頗有情緒化的否定詞,記錄了當時渡船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狀態。為何不肯?后來如何?問題看似沒有答案,但卻被禪意地解決了:僧人把這種看不見的三個字,化成一座物理的寺廟,得以容納觀音真身,以及千萬后來者。如此觀自在,不是心隨境轉,而是心能轉境(星云大師語),心能造境,正是觀世音的智慧。
從不肯去觀音院出來往回走,我發現步道前方有一群人圍在—起。走近一看,一個大和尚正把一個瘦個子男人逼在墻角,他們中間隔著一個香爐。據現場圍觀的人講述,那男子在現場非法兜售佛珠,被管院的師父撞見了。“你跑不出我的掌心,還是乖乖跟我去好了!”那男子雙手合十,放在胸前向大和尚連連鞠躬,臉上露出求饒的表情——他是不肯去啊。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