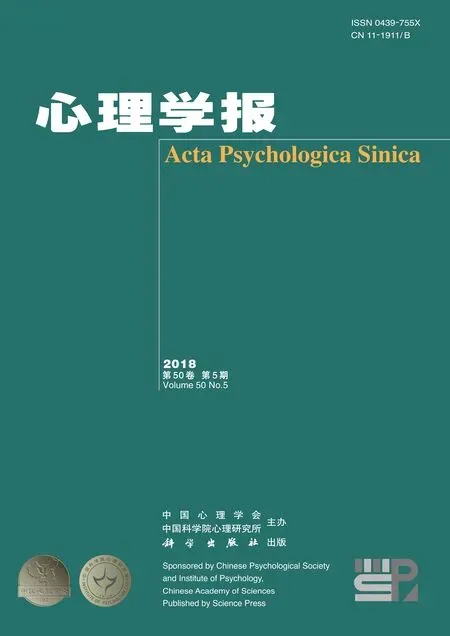對水稻理論的質疑:兼新論中國人偏好整體思維的內外因*
汪鳳炎
(南京師范大學 道德教育研究所,暨 心理學院,南京 210097)
整體思維,也叫整體觀或有機循環論的整體思維,認為世界(天地)是一個自組織的有機整體,整體包含許多部分,各個部分自身也是一個個小的整體,各部分之間有密切聯系,因而構成一個整體,想了解各部分,必須先了解整體(張岱年,成中英,1991,p.8,p.20)。Nisbett等人對整體思維下了一個更心理學化的定義:一種將背景(the context)或場域(field)視作一個整體(as a whole)的傾向,包括將注意力放在關注客體與場域之間的關系,以及偏愛以這種關系為基礎來解釋和預測可能發生的事情(Nisbett,Peng,Choi,&Norenzayan,2001)。為什么西方文化更加偏重個人主義和分析思維而東亞文化更加偏重相互依存性和整體思維?Talhelm等人挑戰以往跨文化心理學和文化神經科學主要基于畜牧業與農業生態差異基礎上解釋東亞文化與西方文化差異的觀點,提出了用以解釋中國文化內部水稻區和小麥區個體心理差異的新假說——“水稻理論” (The Rice Theory),它的核心觀點是:耕作類型可能會引起文化差異,因為種植水稻與種植小麥有重大差別:稻田需要大量用水,不僅灌溉時要與鄰居協調用水時間與用水量等,而且修建、維護灌溉系統不是一個家庭能夠完成的,同時,種植水稻勞動量大,讓人們相互依賴與合作,結果,水稻文化塑造了人的相互依賴性,長期的水稻種植史導致生活在水稻區的人們更傾向于整體思維和集體主義;小麥易于栽培,不需人工灌溉(僅靠降水即可),播種和收割小麥的勞動量僅為水稻的一半,所需勞動量小,不需與人合作也可獨立完成,這樣,種植小麥讓人們彼此獨立,結果,小麥文化塑造了人的獨立性,長期的小麥種植史導致生活在小麥區的人們更傾向于分析思維和個體主義。Talhelm等人認為,“水稻理論”是應用于水稻種植區的文化,而不僅僅是應用于種水稻的人,這樣,只要你生活在因漫長的水稻種植史所形成的水稻文化地域,或者,生活在因漫長的小麥種植史所形成的小麥文化地域,即便你從未親自種過水稻或小麥,照樣能夠繼承水稻文化或小麥文化。依“水稻理論”,生活在小麥區和水稻區的中國人雖都是整體性思維、都偏重相互依存性、都看重忠誠/裙帶關系(holistic-thinking,interdependent,and loyal/nepotistic),但生活在水稻區的南方人在這三方面都要高于生活在小麥區的北方人,所以,中國水稻文化與小麥文化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南方的水稻文化更傾向于東亞文化,北方的小麥文化看起來更像西方文化(Talhelm et al.,2014)。正如朱瀅所說,Talhelm等人勇敢挑戰已有的東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比研究,用水稻農業與小麥農業的差別來解釋中國南北文化的差異,視角頗新穎,但水稻理論能否成立有待檢驗。這不僅是他們測量的結果需要重復驗證,而且他們所用的測量任務較單一,僅限于量表測量,缺乏更為嚴格的行為實驗和神經科學的證據(朱瀅,2014,2015)。Hu和Yuan (2015)認為,Talhelm等人(2014)的研究中忽視了一些與研究結論有關的關鍵數據,即將以大豆和玉米為主要農作物的地區也歸類為小麥產區。但在中國北方,玉米和小麥是同等重要的糧食作物,甚至在有的省份玉米比小麥更為重要。并且,同小麥一樣,玉米在各省的種植面積也同水稻呈負相關。也就是說,在對中國人心理的影響程度方面,種植玉米和種植小麥同等重要。此外,種植小麥所需要的勞動量遠遠低于水稻,種植玉米所需要的勞動量介于種小麥和種水稻之間但更偏向于水稻。這也說明小麥和玉米應該分別與水稻進行對比。Hu和 Yuan 據此認為,宜將“水稻 vs 小麥”理論改為“水稻 vs.非水稻”理論,相應地,原先的推論也需要修改。因為從“水稻vs.非水稻”理論將會推導出:種植水稻的東亞或東南亞與不種水稻的世界其它地方人的心理不同。這一推論與當今認為西方與非西方二分的心理差異的主流觀點不符。一些非西方國家,如阿拉伯人、東亞人、俄羅斯人,以及非洲與南美洲的農民,相對于西方人來說都是整體思維,多持互依我(Henrich,Heine,&Norenzayan,2010)。同時,據“水稻vs.非水稻”理論,一些種植小麥或玉米地區的人理應更像西方人,但他們卻表現出整體思維。所以,無論“水稻vs.小麥”還是“水稻vs.非水稻”,可能都只是表面現象,水稻、小麥、玉米與大豆在不同地區的生產成本(production cost)不同,而生產成本可能才是背后的決定性因素,今后的研究宜重點考察不同農業的生產成本,而不是農業本身。Roberts (2015)與 Ruan,Xie和 Zhang (2015)也撰文指出水稻理論的不足,下文有引用,這里不贅述。本文以整體思維為切入口,從中國文化心理學角度,結合考古學、歷史學、古典哲學和文學文獻等方面的證據,秉承先“破”后“立”的研究思路,先詳細揭示水稻理論解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古人偏好整體思維的緣由時存在的兩個矛盾,隨后就中國人偏好整體思維的內外因提出新解釋。
1 “水稻理論”解釋中國人偏好整體思維的緣由時存在兩個矛盾
依據“水稻理論”解釋中國人偏好整體思維的緣由時存在兩個矛盾,它們證明“水稻理論”解釋不通:
1.1 南宋之前的多數中國人雖長期生活在小麥區,但他們的思維方式卻主要是整體思維
中華文明主要是建立在農耕文明的基礎之上。考古學研究表明,長江流域自古以來主要種植水稻。在江西萬年縣仙人洞發現了距今10000年以前栽培稻谷的硅石標本,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遺存。水稻在新石器時代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區已普遍種植,在距今5300~4200年間的長江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已取代采集狩獵成為長江下游地區的經濟主體(趙志軍,2011)。《史記·夏本紀第二》中有禹“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的記載(司馬遷,2005,p.38),證明在公元前1920年前后(Wu et al.,2016)中國先民確實已會種水稻。
不過,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發源地之一。考古發現,在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主要糧食作物是粟(古稱“稷”,俗稱“小米”,中國北方俗稱“谷子”)。粟與黍耐旱,適合在貧瘠、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區生長。在磁山發現粟的標本,使磁山被確認為是世界上粟的最早發現地,且將黃河流域植粟的記錄提前到距今 7000多年。夏代豫西、晉南、陜西等地的主要糧食作物仍主要是粟與黍。與夏朝類似,商朝的糧食作物仍主要是粟,故夏朝和商朝屬于“粟文化”。至今華北仍為粟的主要產區。至于小麥,它原產于西亞或阿富汗。在甘肅青海東部地區距今5000年到4500年前的馬家窯文化遺址中開始出現,此后在黃河中下游地區距今 4500年至4000年的遺址中也有少量發現。到了距今3500年前后的商代前期,在黃河中游地區,小麥顯著增加,成為北方地區的主要農作物之一(王巍,2016)。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告麥”的文字記載,說明小麥早在商代便已是河南北部的主要栽培作物。《詩經·周頌·思文》中也有小麥、大麥的記載,表明西周時黃河中下游已遍栽小麥。
比較可知,中國先民種植小麥比種植水稻的時間至少要晚 5000年(10000-5000=5000),種植小麥比種植粟的時間至少要晚 2000年(7000-5000=2000)。鑒于粟與黍的生長習性和小麥有許多相通之處(如三者都耐旱),在勞動方式與勞動強度上,種植粟與黍和種植小麥之間有較大的相似性,可以歸為小麥種植類型。中國南方人種植水稻的歷史雖比北方人種植粟、黍和小麥的歷史要早、要長,不過,自先秦以來,直至北宋滅亡前,中華文明的核心圈都位于主要糧食作物恰恰是粟、黍和小麥的中原和關中地區。所以,綜合《論語·雍也》、《論語·顏淵》、《論語·微子》、《史記·平準書》與《漢書·食貨志第四上》中有關“粟”的記載以及唐代詩人李紳《憫農二首》里“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與宋真宗趙恒《勸學詩》的“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 (黃堅,2007,p.14),可以大致勾畫出自先秦至北宋中國北方以粟作為主要糧食的證據鏈。假若“水稻理論”能成立,那至少北宋及其之前的多數中國人因長期生活在小麥區,應該具有彼此獨立、傾向于分析思維的特質,若果真如此,多數中國古人的自我理應更傾向于彼此獨立而非相互依存,他們的思維方式理應更傾向于分析思維而非整體思維;同時,從時間上看,中國古人至多是在南宋開始才能以整體思維為主。可事實卻是:南宋之前的多數中國人雖長期生活在小麥區,但他們的思維方式卻是整體思維而非分析思維,且至遲到春秋戰國時期他們已將整體思維運用得爐火純青(汪鳳炎,2017),所以,在《管子》、《老子》、《文子》、《周易》、《莊子》、《孫子兵法》、《黃帝內經》與《呂氏春秋》等名著中有大量運用整體思維去分析、論述和解決問題的文字。
1.2 目前無足夠可靠證據證明種植小麥的中國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
中國幅員遼闊,從北至南跨越了北溫帶到熱帶的諸多溫度帶,這些溫度帶上的地理生態、生活方式都有明顯差異。同時,因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311年)和 1127年的“建炎南渡”,包括士大夫和世族大家等社會精英在內的大批人口為避戰亂曾兩次從中原遷往長江中下游及長江以南地區,結果,自南宋至清末,中國南方地區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地區成為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 (也叫“中原文化”)的重心所在,其受到中原文化影響的程度要高于北方地區,而北方地區則屢次被文化相異的少數民族政權所統治,中原文化對其的影響反而在中原人口南遷、漢胡民族融合的歷史發展中逐漸減弱(葛劍雄,2013,pp.104-129;馬欣然,任孝鵬,徐江,2016)。這導致中國北方人和南方人在家庭供暖方式、身高、飲食習慣、方言與性格等方面都有一定差異。例如,北方人身高普遍高于南方人;北方人多以面食為主食,南方人多以米飯為主食;等等。
不過,盡管Talhelm與馬欣然等人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調查數據作依據,卻不能由此輕易得出如下結論:與種植小麥的中國北方人相比,生活在水稻種植區的中國南方人具有東亞文化的一些特點:集體主義傾向較北方地區更強烈;更傾向整體思維,更高程度的互依型自我構念,以及更低的離婚率;與種植水稻的中國南方人相比,種植小麥的中國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有更高程度的個人主義;更傾向分析思維;有更高的離婚率。” (Talhelm et al.,2014;馬欣然等,2016)。理由至少有四:(1)問卷或測量若想獲得可靠結果,一個基本前提是其背后的理念要科學,如果理念有偏差,按它編制出的問卷或量表必有偏差,由此得出的結果與結論自然也易出現偏差。依費孝通的研究,中國人的行為特色并不是個人主義,也不是集體主義,而是自我主義(1998,p.28)。楊中芳(2001,pp.107-145)也建議,為了避免由簡單的跨文化比較而歪曲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方式,應放棄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這個表層特征的探討。但Talhelm與馬欣然等人的研究恰恰采納了費孝通與楊中芳所批判的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理念來研究中國人。(2)Ruan等人(2015)在詳細分析 Talhelm 等人(2014)的實證方法后,發現原文存在著樣本偏差、測量誤差、模型設定錯誤等問題,由此認為 Talhelm等人的研究高估了水稻種植在塑造文化心理和創新性方面的作用。馬欣然等人的研究采用的是方便取樣,被試總數較少(只有745人),南北方被試數量不均衡(北方被試 454人,南方被試291人) (馬欣然等,2016)。(3)假若說隨著中國傳統文化體系重心的不斷南遷,自南宋至清末,較之北方,南方受到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體系浸潤更深,那么,自清末民初以來,南方先是得革命風氣之先、后是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受儒學影響反又式微,與此相反,北方尤其是華北受帝都北京的影響甚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反而更加保守。與此相一致,當年主要生活在北京的滿清皇室成員幾乎都主張帝制,主張復辟帝制的袁世凱也是北方人,而新文化運動時,“打孔家店”的代表人物吳虞、陳獨秀、胡適等都是南方人,“辛亥革命”和“八一南昌起義”都發生在南方,主張革命的孫中山與毛澤東都是南方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最早設立的四個經濟特區都在南方,現在以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為代表的南方經濟總體上較之北方要發達,中國大陸地區人口和人才流動才呈現明顯的“孔雀東南飛”態勢。正由于此,較之北方,當下南方尤其是東南沿海和沿江地區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發達,富裕起來的南方人往往既傳統又現代,從而更講誠信,待人更慷慨、更寬容,人我界限、公私界限更清晰。一項在江蘇(代表發達地區)、新疆和廣西(代表發展中地區)三地投放問卷1200份、收回有效問卷1149份的調查結果也表明,在關于當前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精神到底由哪些元素構成的多項選擇中,“市場經濟中形成的道德”占40.3%,“意識形態提倡的社會主義道德”占25.2%,“中國傳統道德”占20.8%,“受西方道德影響”占11.7%。這說明當前中國倫理道德總體上處于市場經濟中形成的道德占主導的狀態;意識形態倡導的道德與傳統道德在社會生活中雖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二者之總和才略高于市場經濟形成的道德所產生的影響;西方道德對當代中國人的道德生活雖有一定影響,但影響并不像人們感覺或想象的那么大(樊浩,2009)。因此,僅根據南方人對誠實的朋友更慷慨,對不誠實的朋友更寬容,對內外圈子即朋友和陌生人之間的邊界也更為清晰(馬欣然等,2016),似無法認定南方地區集體主義傾向較北方地區更強烈。(4)較之南方人,北方成年男子(尤其是東北三省的成年男子)常有“大老爺們心態”,在當下女子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經濟更獨立的背景下,它極易提高離婚概率。Talhelm等人(2014)文中的圖2數據也顯示,黑龍江、遼寧、吉林三省的離婚率相對最高,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不過,“大老爺們心態”不是個人主義,因為它有明顯的性別歧視色彩,缺少平等觀念(費孝通,1998,p.28)。同時,Ruan等人(2015)在文中提供了一組與 Talhelm等人完全相反的離婚率數據:Ruan等人以專利數(一個衡量創新的指標)為參照,發現自1995年至2011年,水稻省份專利數的增長高于小麥區,與此相吻合,水稻省份的離婚率也幾乎年年高于小麥省份的離婚率。所以,無論中國北方是否有比南方更高的離婚率,都不能將之作為推測中國北方相對于南方而言在文化上更像西方的證據之一。
綜上所論,因中國北方人與西歐人生活在差不多相同的緯度上,故二者在身高上很類似,即都普遍長得高大;且都以面食為主食。除這兩點相似外,目前沒有足夠證據顯示中國北方人和西方人有更多心理與行為上的相似點。即便中國北方人和西方人都愛吃面食,但在做法/吃法上仍有較大差異:中國北方人的面食主要以面條、餃子、饅頭、包子、餅、窩窩頭等為主,但幾乎不烤面包;西方人的面食以面包為主,卻幾乎不做成中國北方的面食。目前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自小生活在小麥區的中國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也無足夠證據證明中國北方人就更傾向個人主義,更擅長分析思維,而生活在水稻區的中國南方人就更傾向集體主義,更擅長整體思維(汪鳳炎,2017)。退一步講,即便Talhelm等人(2014)持下列說法,仍說不通:中國人無論生活在小麥區還是水稻區,都是整體性思維方式,只是整體性思維所占的比重不同:生活在水稻區的中國南方人的整體性思維的比例高于生活在小麥區的中國北方人。因為對于中國古人而言,無論是生活在小麥區還是水稻區,整體思維與分析思維都是“有”和“無”的問題,即中國南北方要有整體思維就都有整體思維,要無整體思維就都無整體思維,而不是“多”和“少”的問題,即不可能存在“生活在水稻區的中國南方人的整體性思維的比例要高于生活在小麥區的中國北方人”的現象。理由是:對秦漢之后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思維方式產生深刻影響的先秦“諸子百家”的創始人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幾乎都來自小麥區: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是今山東曲阜人;孟子是今山東鄒城人;荀子是趙國人。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是今河南周口市人,莊子是今河南商丘人。兵家創始人孫子是齊國人。法家的先驅管子是今安徽潁上縣人,子產是鄭國人;法家學派的開山者李悝是戰國初魏國人、商鞅是衛國人、申不害是今河南人、慎到是戰國時趙國人;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子是韓國貴族。墨家的創始人墨子相傳為宋國人,后長期住在魯國。名家的代表人物為惠施和公孫龍,前者是宋國人,后者是趙國人。陰陽家的代表人物騶衍(即鄒衍)是齊國人。縱橫家的創始人鬼谷子的籍貫不詳,相傳是戰國時楚人;縱橫家的代表人物是蘇秦和張儀,前者是戰國時東周洛陽人,后者是戰國時魏國人。雜家代表人物呂不韋是今河南省濮陽人。醫家代表人物扁鵲是戰國時期勃海郡鄚(今河北任丘)人。但是,這些產自小麥區的中國大哲并未顯示出繼承小麥文化后擅長分析思維的特點(Talhelm et al.,2014),反而更擅長整體思維,也就是說,生活在小麥區的中國北方人在思維方式上以整體思維占絕對優勢,且無論在所占比例和使用水平上,均絲毫不低于也不遜色于中國南方人。正由于生活在小麥區和水稻區的中國古人都偏重整體思維而少分析思維,才導致中國古典思維方式的一大弊病是“缺少分析思維” (張岱年,成中英,1991,pp.13-14;汪鳳炎,鄭紅,2015,pp.627-628)。近現代中國人不是從種植小麥而是從西方學會使用分析思維的。Roberts (2015)也認為,Talhelm等人將各省作為獨立樣本測量其文化特質,沒有控制不同省份之間的歷史關系。實際上,農耕方式和文化價值觀既可能是從傳統文化中繼承的,也可能從現當代文化中引進的。從傳統文化中繼承的文化特質和從外來文化中獲得的文化特質之間會存在虛假相關,即高爾頓問題(Galton's problem)。這就意味著Talhelm等人研究中的數據可能由非獨立的點組成,夸大了水稻種植和集體主義之間的相關性。
2 促成中國人崇尚整體思維最可能的重要外因和內因
中國先人為什么最終選擇了偏向整體思維?因時間久遠和商代之前缺少文字記載等原因,上古人寫作時又無在論著上署真實姓名的習慣,這個謎可能永遠也無法徹底破解了。根據現有證據,促成中國人崇尚整體思維最可能的重要外因和內因分別是,古人從治水經驗中獲得靈感與啟發以及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的提出與被認可,下面分而論之。
2.1 促成中國人崇尚整體思維最可能的重要外因是從治水經驗中獲得了靈感與啟發
從外因上看,中國人偏向整體思維是多種外因長期共同交互作用的結果。例如,中國的社會生態主要由有利于農業生產的較肥沃平原、丘陵與能通航的河流構成,所以,中央集權統治較易施行;農耕方式要求人們相互協作,而灌溉系統又要求中央集中管理,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睦便顯得重要;中國人在經濟、社會行為和政治生活中必須照顧到周圍的同輩和上司,這種社會實踐有利于中國人養成整體思維的習慣;中國的世俗哲學強調自我與他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Nisbett,2003,pp.32-39;尼斯貝特,2010,pp.29-33);漢語是整體定位法,文無標點,也不分段,意義在網絡中被決定,整體決定部分,對整體了解越多,對個體也就了解越多;重視關系(包括人際關系)超過重視實體、強調整體尤其是關注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偏向綜合而疏于分析的文化基因(張岱年,成中英,1991,p.197,pp.212-213)。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利于培養中國人的整體思維。
在上述諸種外因中,若一定要用排除法尋找一個最可能的最重要外因,與其說是水稻種植方式成就了中國人的整體思維,不如說中國古人偏好整體思維是從遠古先民治水經驗中獲得靈感與啟發的結果。因為治水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治水領導本人與族群的興衰存亡,從而深刻地影響到其思維方式。具體地說,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對農業而言,氣候是關鍵因素之一,但中國文明的搖籃——黃河與長江中下游地區——受梅雨天氣和臺風的影響較大,造成這兩個地區極易發生旱災與水災,“據水利部統計,從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中國發生過1029次大水災,一片汪洋,生靈殆盡;發生過1056次大旱災,赤地千里,餓殍遍野。” (宋健,1996)。這讓先民對水患和治水經驗刻骨銘心,流傳下來許多治水的傳說和故事,其中尤以“大禹治水”最為著名。據《史記·夏本紀第二》記載:“當帝堯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 (司馬遷,2005,p.37)。可見,當時洪水形勢嚴峻,受災人數眾多,百姓深受其害。傳說禹領導人民疏通江河,興修溝渠,發展農業。在長達十三年的治水歲月中,三過家門而不入,最終治水成功(司馬遷,2005,pp.38-57)。由于殷商之前的中國歷史缺少文字記載,《史記》中記載的“大禹治水”是否真的僅是傳說呢?吳慶龍等人的研究表明,公元前 1920年在黃河流域的確發生了一場大洪水,這場大洪水是由一場強烈地震引發的堰塞湖的潰決引起的,潰口流量10倍于黃河歷史時期最大洪水(1843年,3.6萬方每秒)。這個考古發現對認識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的歷史過程以及中國人偏好整體思維都具有重要意義(Wu et al.,2016)。因為若想成功治理如此大的洪水,治水領袖就需綜合考慮整個黃河流域的水文環境、氣象條件、生態環境以及當時所能動員的人力、物力、財力等因素,進而運用整體思維統籌規劃。事實上,細讀《史記·夏本紀第二》中記載大禹治水的記載(司馬遷,2005,pp.37-57),就能真切認識到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秘訣就在于他在長年的治水實踐中直觀、真切地看到了天人密切相關理念、順應自然和通盤考慮(整體思維的雛形)在成功解決復雜問題時的重要性,進而做到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合理疏導,“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道九川。” (司馬遷,2005,pp.38-52)。與此相反,禹的父親鯀治水時因缺乏天人合一、順應自然和通盤考慮的理念,只知在局部進行“湮”和“障”,卻不知著眼全局并做到“因勢利導”,結果,“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司馬遷,2005,p.38),致使治水失敗。并且,鯀與禹父子倆都是黃帝的后人,禹因治水成功而成為舜的接班人,為其兒子啟從原定繼承人伯益手中奪取帝位、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王朝夏朝打下了良好基礎(司馬遷,2005,p.62;夏征農,陳至立,2010,p.2054),而鯀因治水失敗落個被流放羽山并客死羽山的下場(司馬遷,2005,p.38)。
鯀與禹父子倆治水經歷的一成一敗構成了鮮明對照,對當時乃至后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產生了深刻影響,這從《尚書·周書·洪范》的如下記載中得到明證:“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 (王世舜,2012,pp.143-145)。由此可見,即便到了商末、西周初年,箕子仍是從鯀治水失敗而禹治水成功的事例說起,用它們作為自己立論的基礎,這表明鯀治水失敗與禹治水成功這兩件事對時人的影響之巨!
2.2 促成中國人崇尚整體思維最可能的內因是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的提出與被認可
從常理心上講,人只要進行思考就須依靠一定的思維模式(劉承華,2002,p.69)。一個人或極少數人具有或偏愛整體思維,它不可能成為中國人的思維偏好,一定要多數中國人都具有或偏向整體思維,它才能成為中國人的思維偏好。而要讓多數中國人都具有或偏向整體思維,不可能是天生的或通過種水稻就能于無意中形成的 [畢竟黃河流域種水稻的歷史只能追溯到新石器晚期(距今約4000年),比種黍、粟和麥的歷史要短得多。并且,雖然根據《孟子·滕文公下》與《周禮·夏官司馬第四·職方氏》的記載,在秦代之前,水稻在中國北方的種植范圍較廣,但由于氣候條件所限,北方種水稻的面積比種粟與麥的面積要小得多,水稻始終沒有在北方糧食作物中占主導地位(何凡能,李柯,劉浩龍,2010)。]只能是先經文化精英將之提煉成一種或幾種蘊含此思維模式的學說,然后再通過榜樣示范、文化熏陶與教化而成。事實上,“整體”是一個近代名詞,在中國古代一般稱作“一體”或“統體” (張岱年,成中英,1991,p.8),今人所說的整體思維在中國古代更多地是被叫作陰陽觀/思維、五行說/思維與陰陽五行說/思維,所以,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的成熟過程,也正是整體思維逐漸成熟和應用范圍不斷拓寬、應用頻次不斷增加的過程。這從一個側面證明基本上沒有這種可能:因中國人先普遍崇尚整體思維,然后才提出并認可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為了讓讀者能較完整而清晰地體會整體思維在中國的成熟過程,下面對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陰陽五行學的演進過程作一簡明扼要的闡述。
具體地說,起初運作整體思維時,因缺乏成熟的理念和可操作模式,全憑個人深厚的人生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故它只被像大禹和周文王這樣具大智慧的精英所掌握,連被堯手下眾大臣公認才華過人的鯀都未能掌握(司馬遷,2005,p.38)。稍后,先人主要從長期治水經驗中逐漸清晰地意識到生存離不開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進而在天(自然)人關系上孕育出中國傳統文化里的一個基本思想模式:“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國起源很早,其文字記載至少可追溯至《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楊伯峻,1990,p.1457)。從“天人合一”思想出發,《老子·二十五章》更明確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陳鼓應,2009,p.159),不但將天、地、人三者構成一個整體,而且明確主張“道法自然”是天道、地道和人道共同遵守的法則。不過,“天人合一”雖是中式整體思維的根本特點(張岱年,成中英,1991,p.21),但此理念太過簡略,其中“天人相類”又顯牽強(王利器,2009,pp.115-117),“道法自然”有時太過玄妙,有時又流于機械,二者都不易操作。在此基礎上,先人逐漸建構出了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
陰陽學說的演進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梁啟超,1921;徐復觀,1961a)。陰陽概念最初指日光的向背:背日為“陰”,向日為“陽”。此時“陰”與“陽”只是以有無日光作基準所形成的現象,并非獨立性的實物,也不屬意象或抽象概念,不具有哲學意蘊。據《國語·周語上》記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 (徐元誥,2002,p.26)。據此可知西周末年的伯陽父已開始將陰陽看作天地之二氣,此時陰陽本身已成為實物性的存在(徐復觀,1961a),并首開用陰陽二氣的矛盾變化來解釋自然現象的先例,也標志著陰陽學說的雛形已成(關煜平,2001)。其后,《老子》聲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陳鼓應,2009,p.225)。首次將陰陽兩字相連屬成一名詞,表示兩種無形無象的東西,這表明陰陽二字意義的巨變始自老子(梁啟超,1921),并肯定陰陽的矛盾勢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夏征農,陳至立,2010,p.2267),這進一步充實了陰陽學說。再往后,《易傳》的作者首次引進陰陽觀念來解釋《易經》,并對陰陽學說有意識地作了系統性建構:將陰陽二氣套進《周易》的“—”與“- -”兩個符號中,以陰陽作為構成萬物的二元素,能很方便地說明宇宙創生過程與萬物在此過程中形成統一的有機體(徐復觀,1961c)。《周易·系辭上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周振甫,1991,p.234)。這表明《易傳》的作者將陰陽作為宇宙創生萬物的兩個基本元素,及由此二元素之有規律性的變化活動而形成宇宙創生的大原則或根本規律,并以之貫注于人生萬物之中,而作為人生萬物的性命。陰陽學說至此發展完成(徐復觀,1961c)。《系辭》的基本部分是戰國中期的作品,著作年代在老子以后,惠子、莊子以前(周振甫,1991,p.19),這意味著陰陽學說至戰國中期已發展完成。與此同時,陰陽概念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已運用于中醫領域,《黃帝內經》進一步發展了陰陽學說,將其作為中醫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故《黃帝內經·素問》中有大量這方面的記載。因《黃帝內經》的基本內容寫成于戰國后期;迄于漢代,陸續有所補訂(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傳統醫學》編輯委員會,1992,p.286)。這表明至遲到戰國后期,中國古人已在中醫領域將陰陽學說運用得爐火純青。此后,《周易》被尊為“六經之首”、《黃帝內經》被中醫尊為醫書之祖,二書所推崇的陰陽學說就成為后世中國古人用以認識事物、解決問題的工具。從思維方式上看,陰陽學說實際上是一種陰陽思維:中國先哲看到一切現象都有正反兩方面,將“陰”與“陽”視作創造萬物的兩種相反相成的基本元素或動力,并用陰與陽來統稱宇宙萬物中相反相成的一對對概念,然后認為陰陽雙方的矛盾運動構成事物的發展變化,這是萬物不斷發生變化的內在根據(徐復觀,1961a;Yang,2006)。這表明,陰陽思維主張世界是普遍聯系的,其中蘊含整體思維;陰陽思維又強調事物都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包含著既斗爭又相互聯系、相互轉換的發展運動,故而其中又蘊含辯證思維。
在孕育出陰陽學說的同時,中國古人也逐漸孕育出五行學說。“五行”概念最早見于《今文尚書·周書·洪范》所載“洪范九疇”中的第一疇:“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王世舜,2012,p.146)。由此可見,五行學說中的五行并非指水、火、木、金、土五種具體物質形態,而是指五種抽象的物質功能或屬性,分別用水、火、木、金、土來作形象表征,事物經過這種屬性歸類,就全部納入五行模式之內。所以,Needham (1956,p.244)認為,“五行是處于周而復始、永恒式循環運動中的五種強大力量,并不是五種被動、靜止的基本物質。”關于《洪范》與五行的作者和產生時代,現在的共識是:雖然《洪范》的主體內容是商末、周初的作品,箕子是《洪范》的最主要作者,但《洪范》原本中的五行與五行學說中的五行名同實異,二者有本質上的不同(梁啟超,1921;徐復觀,1961a,1961b,1961c;劉起釪,1980;李學勤,1986)。在商末、周初的《洪范》原本中,第一疇或只稱“五行”,若標出細目,也只會稱“辰、太白、熒惑、歲和填”等五行星,絕不會標“水、火、木、金、土”,因為當時還不知道這五項是五行。后來天文學者借用它們分別作為五行星的代稱,“五行”才和金、木、水、火、土結合起來。把金、木、水、火、土與“五行”相結合的完成時間,也即寫入《洪范》第一疇的時間,大致不晚于春秋時期(劉起釪,1980)。與此同時,春秋時產生五行相勝思想。戰國時代,“五行”說頗為流行,并出現“五行相生相勝”理論。“相生”指相互促進;“相勝”即“相克”,指相互排斥。由此可見,五行并非是靜止與孤立的,而是以五行之間的相生與相克來探索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協調平衡的整體性與統一性(劉長林,1982,pp.83-88)。因此,五行學說實際上是一種五行思維:它先用五行來表征宇宙萬物,然后認為五行之間存在相生相克的關系。這表明,五行思維也主張世界是普遍聯系的,其中蘊含整體思維;五行思維又強調不同事物之間存在相生相克的關系,其中也蘊含辯證思維。五行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已運用于中醫領域,《黃帝內經》更是進一步發展了五行學說,并將其作為中醫的又一個重要理論基礎。這意味著,至遲到戰國后期,中國古人已在中醫領域將五行思維運用得爐火純青。此后,因《洪范》成為其后近三千多年來中國各王朝統治者所重視和奉行的統治大法(劉起釪,1980)、《黃帝內經》被中醫尊為醫書之祖,這樣,《洪范》與《黃帝內經》所推崇的五行思維同樣成為后世中國古人用以認識事物、解決問題的思維工具。
陰陽與五行原互不相干,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的誕生和演變原先也有較大差異。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的另一個重要演變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齊燕方士以“術數”為基礎,將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逐漸合流,生出陰陽五行說(梁啟超,1921;徐復觀,1961c)。陰陽五行說最初是在社會低級迷信中醞釀出來的,將五行從雜多的社會迷信中提出來以建立新說,引起世人的注意者,始于陰陽家鄒衍(徐復觀,1961c)。鄒衍開始以五行與陰陽相附合,并新造出“五德終始說” (司馬遷,2005,pp.1839-1840;徐復觀,1961c)。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被秦始皇采納,為他稱帝和采取“水德之治”提供理論依據(司馬遷,2005,p.169;徐復觀,1961c)。于是陰陽五行說在秦代受到思想界的追捧。到了漢代,陰陽五行說得到西漢時的大儒董仲舒的鼓吹,結果,《洪范》不但被抬高為“陰陽五行說”的經典(《洪范》本身不說陰陽),而且陰陽五行說形成了更完整的架構,產生了更大影響(徐復觀,1961c)。稍后,班固寫成《漢書·五行志》,可說是陰陽五行說的集大成。演變至此,陰陽五行說的大局已定(徐復觀,1961c;劉起釪,1980),最終將陰陽五行擴大而為解釋自然現象和人事變遷的法式,這樣,無所不在的陰陽五行便統一了宇宙萬物和社會(Boorstin,1992,p.21)。可見,秦漢以降的中國古人推崇陰陽五行說的外因,與鄒衍、秦始皇和董仲舒等人的鼓吹密切相關。至于秦漢以降的中國古人喜愛陰陽五行說的內因,則是因它融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二者之長于一體,較之單一的陰陽學說或五行學說擁有更加嚴密的內在邏輯性和系統性,這樣,蘊含在陰陽五行學說中的陰陽五行思維模式不但吻合中國古人所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而且是一種同時兼顧整體思維、辯證思維和循環思維的既開放又封閉的思維方式:說它開放,是因為它面向宇宙萬物敞開胸懷,容納宇宙萬物;說它封閉,是因為它自成一個封閉體系,循環不已。這樣,陰陽五行思維模式便能圓潤地解釋宇宙萬物的生、長、病、死,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在中國人心中,它成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解釋原則和宇宙人生的公式(劉承華,2002,pp.70-71),并通過教化、模仿等方式為廣大精英(包括政治精英與學界精英等)與普通民眾所認可與推崇,結果,陰陽五行說成為中國古人尤其是自漢代以降至清代中國古人的思想律,是中國古人對于宇宙系統的信仰,二千余年來,它有極強固的勢力(顧頡剛,1982,p.404)。這導致中國古人習慣用整體的、動態的、自調自適的陰陽五行模式來解釋、研究各種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劉承華,2002,p.71),中國古代漢族的天文學、氣象學、哲學、政治學、史學、化學、算學、音樂和中醫等等,都是在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陰陽五行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夏征農,陳至立,2010,p.2267)。
可見,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為廣大中國古人如何運用整體思維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思維運作方式,對中國古人運用整體思維而言可說是如虎添翼了,其后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讓整體論和整體思維在秦漢之后的中國人心中牢牢扎根,成為中國乃至東方自然觀和思維方式的基本特質。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在西方,整體論作為一種哲學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有人明確提出整體論(holism)這一范疇,以此彰顯“在自然界中,通過創造性進化而產生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趨勢”(段偉文,2007)。這表明,古希臘時雖有樸素的整體論思想,卻未及時發展出類似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的學說。同時,由中國古典哲學家提出的整體論讓人看到的是由單一物質組成的無縫隙的整體或是由幾種物質水乳交融而構成的整體,這樣,對中國人而言,世界是復雜的,萬事萬物是相互聯系的,復雜性與相互依存性意味著要了解一個事物而不顧其背景是注定要失敗的,并且,中國古典哲學的目標是追尋道與和諧而不是發現真理與追求自由,思想不能用來指導行動,這種思想就是無益的,結果,中國古人喜歡從天道中尋找人道,從人道中發現天道,這進一步促進了整體思維的發展。與中國古人不同,由古希臘哲學家提出的整體論讓人看到的是由互不關聯的物體所形成的集合,而其中的物體又是由微粒組成的,由此生出世界到底是由原子還是由連續不斷的物質構成的爭論,這種爭論在古代中國從未出現過;古希臘人又熱衷于追求真理,向往自由、不愿受約束,認為世界在本質上不復雜,人們應該做的就是了解物體的特質,以便歸類并尋找規律(Nisbett,2003,pp.18-19;尼斯貝特,2010,pp.16-17)。這是導致古希臘最終未能形成整體思維而走向分析思維的重要原因之一。
3 結論
綜上所論,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1)“水稻理論”因缺少文化生態效度,用它解釋中國人偏好整體思維的緣由說不通。
(2)先人從長期的治水經歷尤其是從鯀治水失敗而大禹治水成功的一反一正事例中汲取經驗與教訓,看到了天人合一、順應自然和通盤考慮在成功解決復雜問題時的重要性,是促成中國人崇尚整體思維最可能的重要外因;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的提出與被認可,為中國人如何運用整體思維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思維運作方式,是促成中國人崇尚整體思維最可能的重要內因。
致謝:
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外審專家和編委會提出的寶貴意見!論文在修改過程中充分采納了這些寶貴意見!Boorstin,D.J.(1992).The creators: A history of heroes of the imagination.New York: Random House,Inc.
Chen,G.Y.(2009).Lao Tzu Zhu (Revised Edition).Beijing,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陳鼓應.(2009).老子注譯及評介(修訂增補本).北京: 中華書局.]
Duan,W.W.(2007).On holism: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and science.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3),1.
[段偉文.(2007).整體論研究: 哲學與科學的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學報,(3),1.]
Fan,H.(2009).Ethics and Morality in China: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n analysis in terms of philosophy of mind.Social Sciences in China,(4),27-42.
[樊浩.(2009).當前中國倫理道德狀況及其精神哲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4),27-42.]
Fei,X.T.(1998).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Beijing,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費孝通.(1998).鄉土中國.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Ge,J.X.(2013).Unity and division: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history.Beijing,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葛劍雄.(2013).統一與分裂: 中國歷史的啟示.北京: 商務印書館.]
Gu,J.G.(1982).Politics and history under the theory of Five Phases.In Debate on ancient history (the fifth) Volume II.Shanghai,China: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顧頡剛.(1982).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見 古史辨(五)下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Guan,Y.P.(2001).Comments on scientific value of the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ies.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34(4),35-38.
[關煜平.(2001).簡評中國古代陰陽五行思維模式的雙重價值.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4),35-38.]
He,F.,Li,K.,&Liu,H.(2010).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e in ancient China.Geographical Research,29(12),2289-2297.
[何凡能,李柯,劉浩龍.(2010).歷史時期氣候變化對中國古代農業影響研究的若干進展.地理研究,29(12),2289-2297.]
Henrich,J.,Heine,S.J.,&Norenzayan,A.(2010).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33,61-83.
Hu,S.H.,&Yuan,Z.G.(2015).Commentary: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wheat agriculture”.Frontiers in Psychology,6,489.
Huang,J.(2007).Xiang Shuo Gu Wen Zheng Bao Da Quan.Changsha,China: Hunan Renming Publishing House
[黃堅.(2007).詳說古文真寶大全(熊禮匯 點校).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Li,X.Q.(1986).The silk book “Five Elements” and “Shang Shu – Hong Fan”.Academic Monthly,(11),37-40.
[李學勤.(1986).帛書〈五行〉與〈尚書·洪范〉.學術月刊,(11),37-40.]
Liang,Q.C.(1921).The origin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Eastern Miscellan,20(10),70-79.
[梁啟超.(1921).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東方雜志,20(10),70-79.]
Liu,C.L.(1982).Philosoph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Neijing.Beijing,China: The Science Press.
[劉長林.(1982).內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法.北京: 科學出版社.]
Liu,C.H.(2002).Culture and personality: A comparis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Hefei,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劉承華.(2002).文化與人格: 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一次比較.合肥: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
Liu,Q.Y.(1980).A study on the age of “Hong Fan”.Social Sciences in China,(3),155-170.
[劉起釪.(1980).<洪范>成書時代考.中國社會科學,(3),155-170.]
Ma,X.R.,Ren,X.P.,&Xu,J.(2016).The difference of collectivism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and its cultural dynamics.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4(10),1551–1555.
[馬欣然,任孝鵬,徐江.(2016).中國人集體主義的南北方差異及其文化動力.心理科學進展,24(10),1551-1555.]
Needham,J.(1956).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I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2).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isbett,R.E.(2003).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New York: A Division of Simon &Schuster Inc.
[理查德·尼斯貝特.(2010).思維版圖 (李秀霞 譯) 北京:中信出版社.]
Nisbett,R.E.,Peng,K.,Choi,I.,&Norenzayan,A.(2001).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08(2),291–310.
Roberts,S.G.(2015).Commentary: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wheat agriculture.Frontiers in Psychology,6,950.
Ruan,J.Q.,Xie,Z.,&Zhang,X.B.(2015).Does rice farming shape individualism and innovation? Food Policy,56,51-58.
Si,M.Q.(2005).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Beijing,China:Zhonghua Book Company.
[司馬遷.(2005).史記.北京: 中華書局.]
Song,J.(1996-05-21).Transcend Suspecting to the past and get out of confusion.Guangming Daily,p5.
[宋健.(1996-05-21).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1996年5月16日在夏商周斷代工程會議的發言提綱).光明日報,p5.]
Talhelm,T.,Zhang,X.,Oishi,S.,Shimin,C.,Duan,D.,Lan,X.,&Kitayama,S.(2014).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Science,344,603-608.
The Committe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of Encyclopedia of China.(1992).Encyclopedia of China -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Shanghai,China: China Encyclopedia Publishing House.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傳統醫學》編輯委員會.(1992).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上海: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Wang,F.Y.(2017).On the mission of China’s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today’s world.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4),126-133.
[汪鳳炎.(2017).論我國心理學研究的時代使命.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126-133.]
Wang,F.Y.,&Zheng,H.(2015).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5th ed.).Guangzhou,China: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汪鳳炎,鄭紅.(2015).中國文化心理學 (第 5版).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Wang,L.Q.(2009).Wen Zi Shu Yi (2nd ed.).Beijing,China:Zhonghua Book Company.
[王利器.(2009).文子疏義 (第2版).北京: 中華書局.]
Wang,S.S.(2012).Shang Shu.Beijing,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王世舜.(2012).尚書.北京: 中華書局.]
Wang,W.(2016-01-12).The silk road before the Han Dynasty- The early Eurasian cultural exchanges as seen from archaeological.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p4.
[王巍.(2016-01-12).漢代以前的絲綢之路——考古所見歐亞大陸早期文化交流.中國社會科學報,p4.]
Wu,Q.L.,Zhao,Z.J.,Liu,L.,Granger,D.E.,Wang,H.,Cohen,D.J.,… Bai,S.B.(2016).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Science,353(6299),579-582.
Xia,Z.N.,&Chen,Z.L.(2010).Cihai (6th ed.,Compact Edition).Shanghai,China: Shanghai Lexic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夏征農,陳至立.(2010).辭海 (第六版縮印本).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Xu,F.G.(1961a).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and the establish time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1).Democratic Review,12(19),480-485.
[徐復觀.(1961a).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的問題(上).民主評論,12(19),480-485.]
Xu,F.G.(1961b).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and the establish time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2).Democratic Review,12(20),504-509.
[徐復觀.(1961b).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的問題(中).民主評論,12(20),504-509.]
Xu,F.G.(1961c).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and the establish time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3).Democratic Review,12(21),529-538.
[徐復觀.(1961c).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的問題(下).民主評論,12(21),529-538.]
Xu,Y.G.(2002).Guo Yu Ji Jie.Beijing,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徐元誥.(2002).國語集解.北京: 中華書局.]
Yang,B.J.(1990).Chun Qiu Zuo Zhuan Zhu (Revised edition).Beijing,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楊伯峻.(1990).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 中華書局.]
Yang,C.F.(2001).How to understand Chinese.Taibei,China:Yuan-Liou Publishing Co.,Ltd.
[楊中芳.(2001).如何理解中國人—文化與個人論文集.臺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Yang,C.F.(2006).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self:Towards a person-making (做人) perspective.In U.Kim,K.S.Yang,&K.K.Hwang (Eds.),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 (pp.327-356).New York: Springer.
Zhang,D.N.,&Cheng,Z.Y.(1991).The tendency of Chinese thinking.Beijing,China: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張岱年,成中英.(1991).中國思維偏向.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ao,Z.J.(2011-05-10).Chinese rice-growing agriculture originated ten thousand years ago.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p5.
[趙志軍.(2011-05-10).中國稻作農業源于一萬年前.中國社會科學報,p5.]
Zhou,Z.F.(1991).I Chang Yi Zhu.Beijing,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周振甫.(1991).周易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
Zhu,Y.(2014).Testing the rice theory.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37(5),1261-1262.
[朱瀅.(2014).檢驗“水稻理論”.心理科學,37(5),1261-1262.]
Zhu,Y.(2015).Re-talk of the test of the rice theory.Psychological Research,8(3),3-4.
[朱瀅.(2015).再談檢驗“水稻理論”.心理研究,8(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