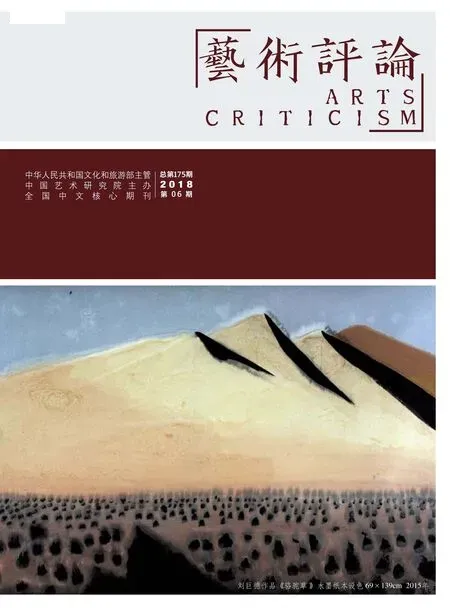中國民族歌劇表演藝術的本體回歸
李梓郡
[內(nèi)容提要] 中國現(xiàn)當代歷史在它涌動的長河中見證了中國歌劇從孕育起源到發(fā)展演進的動態(tài)軌跡,也見證了其表演藝術在艱苦曲折的探索中博采眾長、兼收并蓄的生命脈動。回顧中國歌劇的歷史印記,探尋其藝術發(fā)展革新的社會生態(tài)與文化追求,在歷史制高點上找到中國歌劇表演藝術審美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最佳契合點,實現(xiàn)中國歌劇發(fā)展在當代跨文明、跨文化、跨民族語境中具有世界史意義的藝術碰撞與交融,實現(xiàn)“古今”之間、“中外”之間的跨越式變遷,真正躋身為世界歌劇藝術中的一個具有東方特色的原創(chuàng)歌劇類型。
關于“中國民族歌劇”的討論向來充滿爭論,無論就其定義、概念而言,還是就其內(nèi)涵、外延而論,在學界都有不同的聲音發(fā)出。而對中國民族歌劇及其他中國歌劇類型進行學理性研討,對當前我國歌劇藝術的創(chuàng)演發(fā)展都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基于此,學界也是積極搭建各種對話平臺來將此論題的討論引向深入,如2016年11月25至26日在于北京大學盛大開幕的“首屆北大歌劇論壇”,主題即是定義“中國歌劇”,旨在用歌劇的世界發(fā)展史與中國“民族歌劇”概念兩相參照,對“中國歌劇”這一概念是否成立以及如何確定其內(nèi)涵外延進行研討,并圍繞這一主題從歌劇的劇本創(chuàng)作、作曲、演唱、導演等具體視角,對“中國歌劇”的資源、特質、形態(tài)和理論建構預期等問題進行全方位的審視和討論。這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們對于中國“民族歌劇”這一特殊歌劇類型本體問題的再思考。
再與2011年首屆中國歌劇節(jié)、2014年第二屆中國歌劇節(jié)以及剛剛落幕不久的第三屆中國歌劇節(jié)歌劇論壇的情形相聯(lián)系。這三屆歌劇節(jié)上議論最多、獲獎最多、受眾最廣的多部歌劇作品,無一例外都是以歌劇《白毛女》開山以來創(chuàng)演形制相一致的“民族歌劇”,涉《小二黑結婚》(山西晉城職業(yè)技術學院復排)、《洪湖赤衛(wèi)隊》(湖北歌舞劇院復排)和《白毛女》(中國歌劇舞劇院復排),幾乎所有參會人員在討論中國歌劇創(chuàng)演時,或有意或無意,不約而同地將研究對象鎖定于此。“民族歌劇”能成為三次大型歌劇活動討論的熱點和認識焦點,其實反映了一種時代情緒的需要,是中國歌劇藝術與生俱來的民族自覺和藝術本體回歸,這種自覺和回歸的需要一直沒有間斷,只不過在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由于西方文化思潮與藝術理念的強勢影響以及民族自卑心理的文化偏見持續(xù)干擾我們的判斷,本該建構本民族自有的文化邏輯和藝術審美的歌劇類型,卻造成了模糊甚至混淆的偏頗認知,從而致使對中國歌劇類型認識的問題裹足不前。基于以上現(xiàn)象和問題,本文嘗試予以探討。
一、對民族歌劇本體的解讀
近年來,從國家層面開始更多的關注中國民族歌劇,就所實施的傳播、普及和創(chuàng)新等種種行動看來,其目的和意義重在肯定、繼承、融合和發(fā)展。以《白毛女》為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創(chuàng)制思路,已然將中國民族歌劇本體界定得比較清晰。作為研究歌劇的學者,必須注重兼納“主位和客位”“廣義和狹義”的不同文化立場和傳承觀念。因為學術立場和界定出現(xiàn)任何偏頗,都將直接影響到歌劇傳承類型“被歸類”“被過濾”“被規(guī)范”“被整合”的過程和結局。
一直以來,創(chuàng)作民族歌劇要以“中”還是以“洋”為本體的問題,在認識和實踐上,大家都是有不同意見的。一種是主張以“洋”的方法做基礎,為了學習這種方法,作曲家掌握了大量西方音樂題材以及歌劇體式創(chuàng)作手法,在這個基礎上有的附著中國故事,有的附著中國語言,有的抒發(fā)中國情感。那么這種以西方創(chuàng)制為主要依據(jù)的認識和實踐就引發(fā)我們的思考,是否真正諳傳“民族化”值得商榷。此外,還有一類立足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作曲家向民歌、戲曲和其他傳統(tǒng)藝術形式學習,但終究因其不夠深入戲曲音樂本體研究,僅限于曲調(diào)上做文章,仍然達不到戲曲音樂的表演真諦,缺乏把握戲劇藝術的張力與沖突,徒有抒情之意,但無戲劇之本,成了空泛的抒情體表演。
因此,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無論主張以“中”為本體,還是以“洋”為本體,都存在流于表面而不能深挖到實質的問題,這與異質文化的碰撞、吸收及交融的狀態(tài)有關。一般而言,外來的藝術概念、藝術類型等在跨文明、跨文化的雙語境接觸中,會產(chǎn)生一系列復雜的演變環(huán)節(jié)和碰撞過程,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不同文明間的思維概念的翻譯都存在一種無奈的對應。這也是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歌劇藝術的跨國、跨文化交流來看,誕生于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歌劇藝術,在其全力擴展的過程中因各個國度藝術樣式的不同而被發(fā)展成多樣的、各具特色的歌劇形態(tài)。不僅歐洲不同國家之間產(chǎn)生了以各自文化母體為本的相應改造和融合,在歐洲之外,文明跨度更大的國家之間的歌劇藝術移植和重構,更是需要強調(diào)文化本體屬性的民族特點。
如出生并成長在意大利的著名作曲家呂里卻成為執(zhí)掌法國歌劇專門權利的大師,他完全可以將純正意大利歌劇引入法國,可以形成法國的意式歌劇經(jīng)典。但是,最終在他手中產(chǎn)出的卻是眾多純正的法國文化本位的歌劇,就是因其將法國古典悲劇以及宮廷芭蕾等民族特征整合保留為本體性元素,充滿法國話劇中訴諸理性的抑揚頓挫的音色變化和朗誦風格的音樂化,很少有典型聲樂化的意大利式詠嘆。因此,法國才建立了在歐洲國家中第一個能與意大利歌劇相抗衡的歌劇實力和特色。在德國,作曲家舒茨將本國原有的藝術形式——唱劇,與意大利歌劇結合成為一種新型的、帶有德國民族特點的歌劇,在之后的發(fā)展歷程中,因不斷整合德國民間音樂以及豐富的民間藝術因素和底層民眾的生活與感情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和歡迎,并推動了當時一些民族作曲家對傳統(tǒng)意式正歌劇的改革。
而歌劇傳到了中國后,出現(xiàn)了保持西方歌劇本體的創(chuàng)演體系,我們稱之為“中國的西洋歌劇”,即所言的正歌劇;但更值得我們自珍的應當是以中國戲曲曲藝等民族藝術為本體原創(chuàng)的“中國的民族歌劇”。自《白毛女》開山的民族歌劇自覺將中國人民自有的民族情懷與特色作為本色,即以傳統(tǒng)戲曲及其表演模式等藝術精髓為基本音樂和選材對象,將西方現(xiàn)實主義原則、生活化表演與中國寫意美學、虛擬化表演在實踐中辯證統(tǒng)一起來,不偏不廢,逐漸形成以多元演唱技法兼善為主、歌唱與表演和諧統(tǒng)一的極具中國民族風格并適合中國大眾欣賞習慣和審美理念的綜合性舞臺表演藝術,這是中國藝術家在民族藝術本體上兼容西方歌劇技法,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新的原創(chuàng)歌劇藝術類型。
二、對中國民族歌劇表演藝術本體的認知
回顧歷史,在1942年毛澤東同志主持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直接影響下,隨著一種來自鄉(xiāng)土文化的表演藝術方式——秧歌劇的蓬勃發(fā)展,催生出劇目《白毛女》,其表演藝術確立了中國歌劇表演藝術的基本模式和定型點,采用中國傳統(tǒng)戲曲寫意美學、虛擬化表演藝術程式,與西方現(xiàn)實主義原則、生活化表演有機結合起來為總體的表演特色。這一模式基本定型后,一批沿著該創(chuàng)演路徑探索的新歌劇《小二黑結婚》《洪湖赤衛(wèi)隊》《江姐》等優(yōu)秀的作品,與之一同勾畫出民族歌劇表演藝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十多年文藝史上的壯麗詩篇。
新時期以來,隨著我們對西方文化思潮的再一次狂熱的接受和深化學習,在逐漸深入的對比碰撞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中西藝術思維及其模式的差異之大,幾乎是整個中西文化模式上的關于審美思維的根本差異。這決定了歌劇的審美方式、表演方式以及接受方式系統(tǒng)的差別。因此,這種思維與模式上的對比,更明確地告訴我們,西方歌劇藝術思維在本體上到底是什么,我們傳統(tǒng)的表演藝術——戲曲的藝術本體到底是什么,我們現(xiàn)代文藝要建構的“中國民族歌劇”這一原創(chuàng)的歌劇藝術類型在本體上又是什么。
具體可以作如是觀。西方歌劇的模式大體是一唱到底,舞臺表演以寫實為主,表演藝術的中心目的和主要任務是表現(xiàn)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可以看到西方歌劇是由一系列詠嘆調(diào)組成的、由主旋律統(tǒng)一起來的“人物形象中心”模式,這一特點可在西方歌劇的劇目多以人物名字直接命名就可以看出。相比中國戲曲的模式,大抵以多種板腔自由組成的成套曲式以及曲牌聯(lián)套體式等,唱白兼有,以“唱念做打”四功為表演特點,以虛擬化、程式化為主的舞臺表演,其表演藝術的中心目的以表達情感和宣揚道德故事為主,人物形象較為扁平化、臉譜化,這在中國傳統(tǒng)劇目名稱上以非人物的景、物等意象命名為主也可以得到印證。
由西方的表演觀念和中國傳統(tǒng)表演藝術模式的比較可以看出,雙方的文化審美心理有巨大差異,西方歌劇繼承的是古希臘羅馬戲劇以寫實和敘事為主的傳統(tǒng),尤其是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思潮中突顯“人”的價值的觀念,把人物塑造作為表演藝術的中心任務;而中國傳統(tǒng)表演藝術繼承的是幾千年來中國詩歌的“詩教”傳統(tǒng),通過豐富的言志抒情表達人際關系間的道德修養(yǎng)和承擔禮樂教化的任務,正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另外,從前述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西歌劇(戲曲曲藝)表演藝術的藝術思維在本源上就是雕塑藝術(空間造型)和書法藝術(平面線條)在中西藝術兩種完全不同的源起上的差異。
因此,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語境下,中國民族歌劇一方面繼承了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一方面廣泛吸收了來自西方的優(yōu)秀戲劇表演經(jīng)驗,主動接受著西方美學觀念的熏陶,逐漸開始走出了一條既符合中國大眾審美需要、又不失藝術高雅原則的自我探索之路。最終尋找到中國民族歌劇藝術適合自身發(fā)展需要的平衡點,這里面包含著在表演美學和技巧呈現(xiàn)方面的探索實踐中領悟到的理性認識,即要遵循適合具體文本演繹的需要而追求的寫實性與寫意性技法和風格的辯證統(tǒng)一;也包含著在跨文化語境中兩種不同母本的藝術體打開雙方的文化壁壘,在藝術質素自由選擇再重構的新藝術體中,追求既能跨文化又能在自我內(nèi)部充分展開多元藝術技法切換并兼?zhèn)浼嫔频母叩燃壦囆g修養(yǎng)。因此,我們看到中國民族歌劇表演藝術與西方歌劇藝術之間是一種從本質存在差異的“求同”,在此前提下尋求某種科學性、普適性的表演規(guī)則。中國民族歌劇表演藝術的這種基本關系決定了西方歌劇與中國傳統(tǒng)藝術“混血”后,生成了獨具特色的表演藝術觀念和理論。
(一)以中西聲腔詮釋人物性格
中國民族歌劇的發(fā)展扎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大環(huán)境之中,遵循了以中華文化為“母本”的藝術立場——與戲曲深結著同根之緣,而戲曲在中國千百年發(fā)展的歷程中對中國人潛移默化所引導的一種審美傾向,決定了民族歌劇自《白毛女》開始,就注定要從戲曲的表演藝術規(guī)律中探尋出符合民族歌劇自身發(fā)展所需要的表演方式。如藝術家們始終堅持“依字引腔”“字領腔行”的中國傳統(tǒng)戲曲歌唱理論的原則,以“字正”作為“腔圓”的前提,是一種符合中國民族歌劇表演藝術特點的正確審美態(tài)度。而緣起于西方的歌劇藝術在進入中國以后,觸發(fā)了中國的現(xiàn)代藝術生長,在“舶來”正歌劇的“父本”基因過程中,西方歌劇中對聲音表現(xiàn)的嫻熟運用的觀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人的聲音藝術美學,眾多歌劇表演藝術家都已系統(tǒng)接受了西方美聲演唱方法訓練,皆為有著扎實的聲音和呼吸運用的基本功的高素質演唱者。
以表演藝術家雷佳塑造的民族歌劇《白毛女》“喜兒”一角為例,在演唱《恨似高山仇似海》時,將中國傳統(tǒng)民歌和戲曲唱法中的吐字和咬字技巧發(fā)揮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路”和“恨”字,單純按照樂譜來唱,會唱得較為平緩,但雷佳在這兩個字的處理上,加上了倚音,如此一來將原本樂譜中即時語音形態(tài)的“平聲”變成了原本漢語發(fā)音中的“去聲”,如此一來,每一個字都準確而又清晰地放在了統(tǒng)一的聲線上,觀眾聽起來就覺得更加真實、自然。
此外,雷佳也敢于在民族歌劇表演中對美聲唱法進行準確運用。美聲唱法的呼吸主要采用橫隔式聯(lián)合呼吸,是一種同時運用胸腔、兩肋、橫膈膜、小腹以及腰部協(xié)同合作來控制呼吸的方法。這種方法既克服了胸式呼吸閥氣息過淺的弊端,又克服了腹式呼吸法氣息過僵、過死的缺陷。它充分調(diào)動了人體呼吸器官的綜合技能,打開了共鳴腔體,能夠較為靈活地控制聲樂的高、低、強、弱變化。比如她在演唱喜兒的所有唱段中不論高、中、低音都將聲樂保留在了高位置,支點穩(wěn),轉換自如,使得她的聲音由此而更加富有色彩。由此可見,我們看到的普遍現(xiàn)象是,“洋為中用”的方式自然被大家探索著運用到民族歌劇的演唱中來。
(二)以體驗演說表達人物情感
中國民族歌劇的表演藝術對于念白的拖腔式特別處理是其獨特魅力的因素所在,不同于西方歌劇對念白的不重視,按照對傳統(tǒng)藝術的接受和理解,通過念白對人物展開全方位的塑造和展示,給予觀眾一種完整的、到位的表演。而這種表演絕不是對劇本臺詞的解說,而是化身為劇中人物,用大量的生活體驗、模擬再現(xiàn)等方法來輔助自己的表演,再通過戲曲特有的念白手法來解說人物的臺詞,在抑揚頓挫的演說中將人物的情感表達清楚,進入觀眾心中。
例如,對2015年中國歌劇舞劇院版《白毛女》中“喜兒”的“80后”表演者蔣寧來說,在表演楊白勞帶回二斤白面時,喜兒的臺詞是“什么?是白面!”作為成長在新時代的青年人,用自己每天可吃到各種面食的不以為奇去表演整年吃糠咽菜、吃樹葉的喜兒在看到白面可以用來吃餃子時的驚喜和興奮,那么這樣的臺詞表演一定是失敗的。因此,她們表演的前期對角色的各方面特征展開詳細討論與分析,這時的下鄉(xiāng)體驗顯得尤為重要。
因此,中國民族歌劇表演藝術在表達人物情感、揣摩人物性格的藝術感知中,認為中國戲曲藝術中以人物與演員自身的間離效果產(chǎn)生的虛擬化重抒情的東方美學并不足以有效地表現(xiàn)出劇中人物的特點,而應該尋找與西方表演藝術的平衡,接通西方“斯坦尼”的體驗式表現(xiàn)手法,辯證地考量表達人物情感的最佳方式。這也是其表演藝術寫實寫意辯證統(tǒng)一在實踐和思辨上的具體展現(xiàn)和邏輯支撐。
(三)以虛實結合塑造人物形象
中國戲曲中的虛擬表現(xiàn)手法,在民族歌劇表演中得以良好的繼承和運用。在此基礎上,逐步將西方表演中的寫實主義規(guī)則選擇性引入,形成虛實相生的演繹方式。這一方式對人物的性格刻畫和角色塑造都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虛擬化手法可以使得舞臺上的演員在表演中來去自如,毫無掛礙,但是藝術必須要真實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這是任何時候都不能背離的規(guī)律和法則。因此,舞臺的假定性必須和表演的真實感結合起來,舞臺是空的,戲是假的,但是假戲必須要真做,讓虛擬的、看似遠離生活的表演實則充滿生活的質感和真實感。
對于表演者來說,舞臺上的動作無論怎樣變換和設定,都一定要符合生活的邏輯,“看山如山在,看水如水流”,當演員的表現(xiàn)和觀眾的生活體驗達到某種程度上的契合時,就可以引發(fā)觀眾的共鳴和聯(lián)想。在觀眾的默契合作中,逐漸呈現(xiàn)出劇情所要展現(xiàn)的故事和情節(jié)。如在民族歌劇《野火春風斗古城》中飾演“楊母”的歌唱家黃華麗,已經(jīng)將這種虛實相和的表演手法嫻熟良好地運用,如第五場中,楊母在煤油燈下為兒子楊曉冬納鞋子,一邊做一邊唱起《思兒》,而黃華麗盤腿而坐在炕上,將北方大娘最真實的生活場景再現(xiàn)在舞臺上,讓人倍感親切,但她手中納鞋的動作卻屬于虛擬的表演。這種虛實結合最常見于戲曲的表演中,跟隨演唱的節(jié)奏,她手中的動作也隨著節(jié)奏而逐步變化著。虛虛實實的結合寄寓著母親對兒子的滿心期盼和思念之情,同時這種虛實相生的表演也將傳統(tǒng)文化中“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的意境進行了妙不可言的精彩表現(xiàn)。
當代中國民族歌劇的表演受西方文化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在文化碰撞的早期語境中,它是比較強調(diào)寫實性的,要求接近于生活的原貌,因此它的表演程式化程度較隱蔽,不像中國戲曲那樣明顯。由此來看,在歌劇舞臺藝術的現(xiàn)實發(fā)展中,表演藝術的實體性傾向還有待增強,戲曲中的虛擬化表演依然留存在表演主體的審美意識中,也正是這樣虛實結合的手法才能適應日益更迭和變化的文化環(huán)境,滿足人民對民族歌劇藝術前行的追逐,而又不會喪失掉中國民族藝術傳統(tǒng)的表演原則,真正將屬于本民族的民族歌劇藝術魅力充分展現(xiàn)。這就要求民族歌劇表演藝術與中國人民的審美和價值取向始終保持一致,也正是民族歌劇表演者要想取得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所要采用的基本表演方式和原則。
三、結語
改革開放40年文藝輝煌背景下的中國民族歌劇及其表演藝術,正在從舊有的演出條件和演出觀念以及審美觀念方面向新時代轉型提升。這是一個類似跨越式發(fā)展的歷史時期,在遭遇異質文化碰撞產(chǎn)生的不相容性條件下,找到了在西方文化母體和語境中產(chǎn)生的這一藝術形式與中國文化質素之間達成新的可相融契機,具有挑戰(zhàn)精神的藝術家在深入踐行“洋為中用”“古為今用”“辯證取舍”與“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下,不斷創(chuàng)新、改進和重塑,他們身上所散發(fā)出的強烈的時代氣息,用不同的演唱風格和表達方式來詮釋不同的經(jīng)典舞臺人物形象,均可在個性鮮明的音色和發(fā)聲技巧、高素質的“民美通”兼善的演唱藝術的技藝上,實現(xiàn)在復雜多元的中國民間唱法中的靈活運用,形成兼善多元演唱藝術技法的民族歌劇表演。在廣泛接納眾表演藝術寶貴經(jīng)驗的基礎上趨于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系統(tǒng)的表演藝術理論框架。
在全面發(fā)展中國民族歌劇事業(yè)時,不應丟棄自我所獨有的藝術特質(傳統(tǒng)戲曲藝術本位)去迎合外來文化的滲透,這是我們歌劇藝術工作者和研究者堅守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底線,也是發(fā)展中國民族歌劇表演藝術文化傳統(tǒng)的基本原則,在向中國文化自身“回歸”的大語境中,中國民族歌劇也掀起一股回頭看自身的潮流,從過往的經(jīng)典中重拾榮耀,創(chuàng)新求新,創(chuàng)造新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