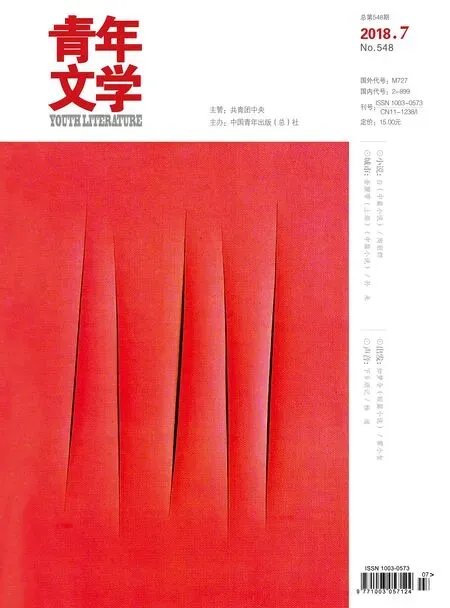弦月夜里的濃湯
⊙ 文/張好好
弦月夜里的濃湯
熟土豆打成泥,在初冬的弦月夜里
濃湯,白色的盤子,香葉,深的勺子
信的末尾:我想念你。濃湯在蠟燭的
影子里,搖曳的微瀾,觸摸到湖心的滾燙
那六月的盛大夏天,清寂湖水是初秋的涼
我在信的末尾:我想念你。艾蒿在你腳下
萬種香葉,它們呼喊著細細的觸手,人生
悱惻里的小暖,番茄的濃湯在小火上
嘟嘟地小滾,土豆泥稠厚,窗花盡失
你風霜的繡像,你無限的輕,潔白,安靜
和真理一樣無辜。謹慎的貓步,艷麗的濃湯
月亮越升越高,此刻的藍湖,我在信的末尾:
我想念你。
不停地徘徊
為了擁有你,我把一生的白云朵
摘下來,裝進白布口袋,又散開
如逐羊群,再聚攏,回到風雪的坡下;
你可在今冬——瞥見雪松睫毛時
心下一動,那白雪的枝丫
它們挺更直,遙望不周山。誰說
亙古難言。別說一別天涯是常情
別說濁酒和濁淚是從此的祭奠
別說,那半個擁抱從此細瘦無蹤。
一個努力的一生,只為擁有你
在圖瓦的弦撥和鼓樂中,青草發愁
大河頹廢,我們是大山的兒女——
理該擁有蕩然的清音……
我眉間的鄙俗,它們洗凈的時刻
你清秀的掌紋,你在青草里徘徊
——不停地徘徊,那默然的永思。
為了擁有你,我已卸去,我亦放飛
花落枝頭,月上梢頭,藍湖的藍,蕩蕩。
風漸漸潛回來
我卻不能大喇喇地向你走去、愛你
抱緊你痛哭——堅若磐石的布爾津
你旋轉的風沙,匍匐戈壁,扶搖土崖
你生生地助力大樹——白楊,白樺
榆樹,柳樹,它們順水招展,溫柔粗獷
那樣的年歲里誕生的孩子,我們在戈壁尋覓
然后記住——大河奔走揚起的柔婉的風
大雨欲來門窗的低吼,黑色的雷擊中藍山
風漸漸潛回來,蹲伏在小巷口,樹,樹
綠莽莽的人家,那些故去的,親人
那死去的,那亡失的童年,齊眉頭發
的少女,她曾經以為,她能夠
大喇喇地愛著,布爾津——這小平原
安全到窒息,穩當到一個淺口的金邊白盤子
她打翻了它。
花朵留下必結的果子
在星星簇擁并奮力揮灑出光芒的某地
你肩胛的保護,保護住一顆純潔的心
它試圖厘清了,無關善惡的命運軌跡
雪,攥緊,成為一塊知冷知熱的醍醐
在水仙盛大的一月,有客自遠方來
請進,請用茶,面對面說出清朗的話
每一個歃血同盟的拜訪,在虛度的人生中
花朵留下必結的果子;河流穿破的草鞋
去到千萬年前說好的某地,那里有碩大的星子
照耀著沒有悔恨的一生,我們喜歡并保持的
雪中漫步。那些死于虛榮和欲望的少女之心
我是僥幸不死的一個——你肩胛的所向
你以清朗的指節叩響我命運的窄門
請進,請用茶,面對面說出清朗的話
河水把拍岸的聲音固執地留在你額頭的微光里
我所等來的顫巍老年,蜜蜂固執地把蜜留在蜂巢里。
爐火知道每一個屋里人的名字
你劈好的木柴,爐膛里的橘色火
搖曳的火光,北風的呼號
一遍遍擦拭偉大的西伯利亞大陸和天空
我們對著火靜默沉思——無事啊空空
牽牛花總會在來年爬起在籬笆上,那么多
天真地張望清涼的太陽在東邊地平線彈跳
——來了。來了。生命的感受——
跌倒,劇痛,傷口在月夜里發出新鮮的汩汩聲
心里坐著的親人,留下空空的席位
木柴燃到盡頭白色的虛炭,簌簌如輕絮
青年時代的暴力和逃奔,收回的斧柄
木紋吸收的血和汗,倉皇和有所思
那些向命運發出乞求聲的,有罪的妥協
雪天的木柴,雨天的木柴,大風天的木柴
泥土夯實的屋子,夏天的陽光,冬天的爐火
我們從一個一個的夢里倦怠走出來,迎風而站
深懂著每一天風的味道,眼前的景多年后歷歷說來
唯有良心堅硬如鐵,你去叩門而門不開
爐火敞開著,用悔恨編織的家族的氈毯
爐火,你天真的清茶的香氣,烤馕的敦厚
爐火知道每一個屋里人的名字,和生長秘密
并理所當然地承擔起安慰的本分——已經有過的
葬禮,青煙……領回家來的大叫的小幼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