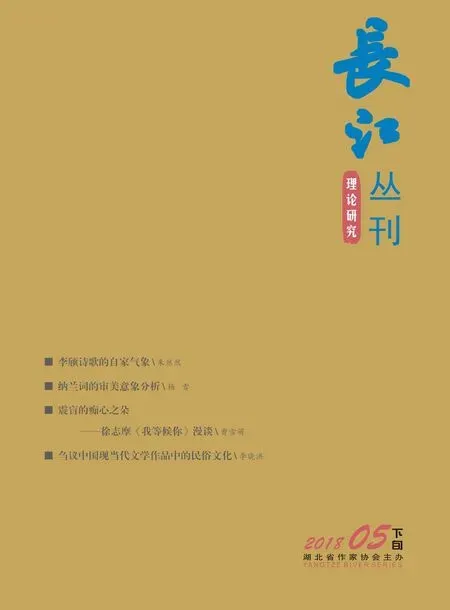女性的成長之路
——讀徐坤的小說《廚房》
■陳 葉/哈爾濱師范大學
90年代的文壇出現了一批新生代作家,而徐坤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徐坤的文學創作分為兩個階段,她前期的文學創作常常是以男性的口吻來進行言說的,前期主要寫了精英知識分子在90年代商業化大潮席卷時所面臨的尷尬處境,從1995年開始她把筆觸轉向了女性文學,一方面是當時女性文學如雨后春筍般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則是作為一名女性作家她從自身的情感體驗出發急于想要用文字來為女性搖旗吶喊,她的文學創作中不僅體現著人文關懷,更多的是對于人生的一種理性思考。
徐坤的短篇小說《廚房》為她贏得了來自學界的很多贊譽,小說主要講述的是女主人公枝子從家庭走向社會,事業成功之后又渴望再次回歸家庭的故事。
一、女性生存空間的轉變
很多文學作品中都會對空間進行詳細地刻畫,這空間大到一個城市,小到一個茶杯,而小說往往會通過對空間的描繪來展現其與人之間的關系。借用挪威建筑理論家諾伯格·舒爾茲的觀點,“人之所以對空間感興趣,其根源在于存在。它是由于人抓住了在環境中生活的關系,要為充滿事件和行為的世界提出意義或秩序的要求而產生的。”小說開頭就寫到“廚房是一個女人的出發點和停泊點。”點明廚房這個空間對于一個女人來說的特殊意義。徐坤開篇便以“廚房”作為自己的敘事據點,試圖反思男權文化的話語規范對于當代女性的心理制約。因為“廚房”是男權社會傳統秩序確立的樞紐。小說中的枝子本是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但是結婚后卻一直在家里扮演著家庭主婦的角色,一日三餐成了她每天的任務,長此以往,廚房變成了一個牢籠,禁錮著枝子的靈魂。終于枝子逃離家庭走向了向往已久的社會,而事實證明精明能干的枝子的確憑借自己的能力在商場上闖出一番天地,成為北京這座繁華都市中亮眼的一顆星。但是在商場多年的打拼,使得此時的枝子極度地渴望能有一個溫暖的地方可以撫慰自己,而這個地方則是廚房,松澤的廚房。她在松澤的廚房中用心地表現著自己,嫻熟的動作、精致的禮服、優雅的身姿這些都在詮釋著枝子的內心,她渴望再次回到這個能給她溫暖的廚房,但是小說卻以枝子拾起廚房的一袋垃圾而終止。小說中枝子經歷了從廚房到社會再到廚房的這么一個過程,而這個空間的轉變也在見證著一個女人的成長,我們不知道這個“出走的娜拉”假如成功回到廚房之后會不會再次選擇離開,她也不一定會如想象中的那般幸福。
二、都市職業女性的情感歷程
枝子在商場上叱咤風云,看似光鮮的背后也有著不為人知的痛楚,開始厭倦商場上的爾虞我詐、勾心斗角,而一個離異多年的女人,愛上了年輕而又充滿藝術氣息的松澤,所以她希望能夠通過廚房這片熟悉的天地來贏取松澤的心。然而年輕的松澤卻是一個生性放蕩不羈的人,逢場作戲的歡愛還可以,對于枝子這種動真格的愛松澤卻顯現出排斥的心理。在廚房里為二人準備燭光晚餐的枝子用著豐富的肢體語言來展示自己,可是他不知道松澤早已看透女老板的心思,他迎合著枝子,因為他不想失去這位畫展投資者,二人在廚房里短暫的僵局讓枝子滿心的希望一點點被打碎。在這場愛情博弈中,枝子失敗了。枝子的失敗,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她是如此的完美,我們是不是只有責備松澤不負責任,哀嘆枝子選錯了對象呢?這樣理解也未嘗不可。難道徐坤只是想給我們講述一個癡心女子負心郎的故事嗎?仔細思考一下,就會發現真正的傷口不在這個地方。枝子雖然走出了廚房,但她始終都沒有走出女性在廚房里形成的自我形象。在現代的都市社會中,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女性都會面臨著情感的困惑,枝子只是萬千都市女性中的一個縮影。
三、廚房里的一袋垃圾
小說結尾處提到了廚房里的一袋垃圾,“夜風猛勁地從樓門口吹了過來。女人的頭發又亂了,幾絲長發貼到臉上來,遮住了她的雙眼。她抬手將發梢掠向腦后,無意間手指觸到了臉上潮乎乎的東西。她轉回身,扭亮了樓道里的廊燈,準備快速上樓。剛一抬腳,一大包東西碰著了她的腿。她低頭一看,原來是廚房里的那一袋垃圾。直到現在她還把它緊緊地提在手里。眼淚,這時才順著她的腮幫,無比洶涌地流了下來。”小說此處可謂是畫龍點睛的之筆,這里的一袋垃圾其實具有更深的隱喻意義,它更像是在與男人松澤的感情對抗中失去的尊嚴。為了一份毫不確定的情感,她放下自己作為一名成功女老板該有的風范,在松澤狹小的廚房中極力地展示著自己,一切的行為舉動都把這個中年女人渴望得到愛的回應一覽無余地展示在松澤面前,但是松澤拒絕了。于是廚房中的表演到此結束,枝子拎著廚房的一袋垃圾消失在透著絲絲涼意的晚風中。她用一袋垃圾引發讀者們的無限遐想,值得人深思,一個女人在返回圍城的過程中受挫,那么她以后該何去何從呢?這是徐坤對于都市職業女性的一種理性的審視和思考,也是千千萬萬個讀者心中的思考。
參考文獻:
[1][挪]諾伯格·舒爾茲 .存在·空間·建筑[M].尹培桐,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社社,1990:220~221.
[2][3]徐坤.廚房[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