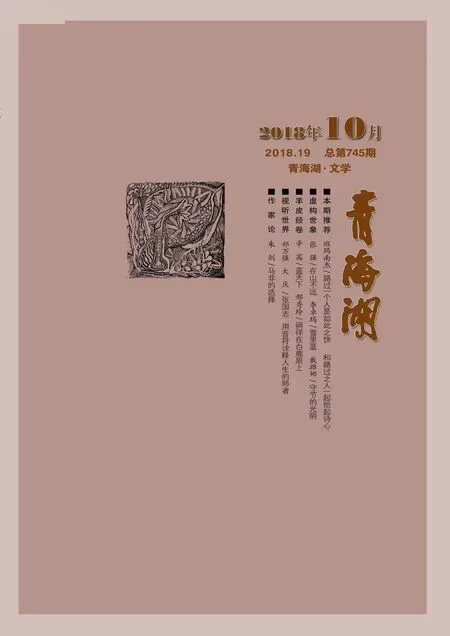現實觸須的敏感與內在鋒芒的敏銳(評論)
■蘆葦岸
在文學生態變異加劇的今天,詩歌受到的震蕩首當其沖,又堅固異常。觀察看,受到沖擊并無法自保不能一以貫之的,幾乎都是詩歌陣營里動機不純的“偽詩人”。反之,對于虔誠的歌者,對于那些壓抑著歌喉以帶血思考介入生活,并迸發向上力量的詩人而言,詩歌領著前行的步履愈益堅毅,他們行走在大地上的身影,拖著長長的驚嘆號,向著遠方,踽踽獨行。是的,走心的詩歌,永遠屬于寂寞者的事業,遠離喧囂,心底堅實心懷廣大,像宗教一樣虔誠地建構專屬通天的高塔。這其中,藏族青年詩人班瑪南杰的寫作無疑具有標本性意義。出道至今,他先后在為數眾多的文學刊物發表作品,并入選多部權威選本。而成為魯迅文學院少數民族創作高研班詩歌班學員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說明他已是一個業有所成的人。其詩自帶芳華,既有現實觸須的敏感,又不失內在鋒芒的敏銳,禁得起評騭。
一
追夢路上的班瑪南杰,充滿激情,又腹有悲憫,以深度美學的方式打開了他作為一個詩人面向世界的洞察。他憂戚的獨白里散射著人生的蒼涼,以及不屈的靈魂掙扎。“那些畫面/和承載那些畫面的空間/都是我生死相依/卻難以托付的秘密//我賜予它們時間和力量/在生命猶如亡靈一般的沉寂中/在稍縱即逝的舞臺上/在人人順從地跳躍的影像中/在黑夜跋涉的世界里/思想赤裸裸地/獨處于難忘的過去與稠密的未來之間”。這首《夢》中的句子,直抒胸臆地,自道著詩人胸中“志氣”。人生如夢,夢由情生,因此“那些畫面/和承載那些畫面的空間/都是我生死相依/卻難以托付的秘密”,詩人直陳夢的依附及其開枝散葉的現實姿態,“不順從”表明他反叛蠅營狗茍的俗世暗流。他明示,置身荒誕的“身”迷惑不了“心”。他寄望詩歌試圖從幽暗的縫隙找尋告慰心靈的力量。
班瑪南杰寫詩已經整整十年。通常的說法:十年一代。那么這個寫作的長度對于他,非常寶貴:不管是一路走得“磕磕絆絆、搖搖晃晃”,無論在寫作路上遭遇多少迷茫與彷徨,但挺住意味著一切,始終初衷不棄。他“非常慶幸找到了適合自己梳理、宣泄和證實生活的方式,這其實如同食物與生命間的聯系一般自然常態”,這是他在處女詩集《閃亮的結》的后記中的自我界定,而恰恰是這種“非詩人”般的存在方式,讓他幸運地入定詩歌的第一現場,埋頭扎進一個多元化的現代社會。現代文明發展與民族古老傳統的反差巨大,每個個體與社會之間充滿各種復雜聯系,生命和命運又是如此難以揣度掌握,每種細微的變化都能夠讓他的身心經歷深深的迷惘與傷痛,無法從一些無形的糾纏中解脫出來,這是他必須面對的現實。這種無奈與糾結,是生存的本相,也是詩歌生態在底部產生巨大沖力的堅實土壤,詩人不回避、不漠視,反而以此掘進更富意味的精神高地和情懷縱深。“因為這樣,我試著用個人化的書寫去進行一次反抗反思,盡力關注社會文化或者人生本性的苦痛與激情所在”。當代詩歌的問題,正是“個人化”與“社會化”之間在書寫上的矛盾無法達成“和解”,自我太過于隱晦和不可調和,現實隔膜又難以被乏力的個人小情緒穿透,以至于形成更大的裂隙,彼此互不買賬。只有當基于個人化的“痛苦和快樂”與普世價值情感中的痛楚發生化學反應的時候,詩歌,才有意義指涉上的當代價值,呈現開放的被接納的經驗在場。顯然,在這個層面,班瑪南杰的覺醒沒有缺位。對于外在生活朝向自身的一切,他認知清醒:“它們的質量就是我本人的質量。”他期待“巨大的沉默和深遠的寂寞”之后的爆發。一種來自詩歌的盤點,或者說并行于生命的詩意出發讓偏安一隅的他極其享受“自制的生活”。
在我看來,正是他身上展現出特有的少數民族詩人的謙虛、豁達、包容與開放的氣度,鑄成了其詩歌的特質,一個敢于向自己的“稚嫩、輕狂、焦慮、淺薄”告別的人,才有走出狹隘的可能,才會向著“厚重和博大的詩歌內涵虔誠進發”的一往無前。他清醒地意識到,一個少數民族詩人要認清自己必須把“夢想”放置于廣闊的詩意空間,甚至世界的文學坐標之中,才不至于固步自封,才會大有作為。
二
“躺過的床上都應該隱藏著一種溫度/每種溫度都應該蘊藏著一個期待展翅的酣夢”。一種有溫度的人生,就是有態度的生命。這夢想的底色,成為推動班瑪南杰詩歌的河床。毫無疑問,《葵花冊》之于詩人的意義,就好比一冊葵花寶典,這首長詩耽于整體性寓意而彰顯的是“故鄉”意義的寫作。在詩人眼里的葵花寶典裝載的不是什么怪力亂神之類的武功存廢的秘笈,而更類似于梵高情懷里的“向日葵”那樣的藝術指南。是詩人對“大武”這個專屬地域特有的關乎生死輪回過程中的細部考量。這種挖掘的專注一定程度上既是對出生地的一次精神檢索,詩人希望通過全方位的“觸碰”,把思考半徑規制在“意想與現實的結合”里,同時也是詩人主動將自己的凡俗之身當成故鄉屬性及其邊界的延續,從實際意義的故鄉上升到精神觀照的故鄉,從實地人文覺察到自身思考的詩性塑造。“……在體內膨脹為另一個胸腔/失衡的情感架空了理性的軀殼/一切迷茫、失意……伺機魚貫而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個人化感受,其實也是大眾化的遭遇。當個人美好的情感圖譜遭遇生活不測,林林總總的無情肆意發威、無法遂意時,一種撕裂的人性開始成為顯赫的“真實”揮之不去。理想豐滿現實骨感就不會只是停留在詩意表達層面,而是以更復雜多變的微妙涌自心頭,“一切迷茫、失意……伺機魚貫而入”。借用評論家耿占春的話說,就是“這些詩歌文本為我提供了把經驗主題化的可能,同時又提供了與晦暗不明的語境保持隱喻關系的方法”。
在《葵花冊》中,詩人以全知的精神維度和強烈的焦慮視角進入一種異數,即標簽化的地域抒情解決不了的深度景觀,班瑪南杰已然明白,詩歌,只有專注于人,才會有出路,才會最有效,人的內心,人的精神和靈魂,在特定情境下表現出來對應于外部世界的明暗、繁復、深邃、冷酷等,更有可能指向人性的“不可馭”。當然,間雜的閃光、溫暖、朗潤、開闊等積極層面的撫慰功能及其催人向上的所指,也隨著詩意的漸入,而逐步形成開放的走向與多維的觸動。“你俯下身/拾回那些熬過冬日依舊炙熱的陽光/走過春風,忽略無數芽苗萌動的心事/掙脫葉脈向歲月延伸的糾纏/跳出年輪在生命刻畫的無奈/毅然趺坐人類苦難的枝頭/只為把光明與溫暖/送進我們即將綻放而又層出不窮的美麗心蕊”。在隱喻、象征、暗示的向度牽引下,詩人想象中的自我塑造是漸至豐滿,通過變形、錯搭、閃回等意念虛實的試探與確認,精神路徑與生活雜感交織扭結,最終形成突圍的銳不可當。這種形象塑造,有著對屈原、李白、但丁、荷爾德林等先知的投影。只不過,班瑪南杰似乎更喜歡把格調處理得晦暗不明,或許這是出于一種現實考慮,而采取的一種“婉曲”,詩人似乎找到了個人心律與人類共振的調值,內在密致的意象組接,隨著情緒的流瀉,導向溫暖與光明,開出不竭的花語。這有點類似波德萊爾《惡之花》對“不滅的靈魂之光”的篤信和“陶醉于痛苦的深淵”的任性。
三
如果說《葵花冊》全景掃描模式開啟了詩人的生死觀,以及由此在展現生命寬度的同時把握精神脈象,并在試圖擺脫單一生猛的青春意緒而汆入復雜落寞的中年情感,在彷徨與自信的悖論中創造“深刻的自己”,那么,在他的一系列新作中,班瑪南杰呈現了作為詩人的又一種狀態:基于現實人性的多維探測,尤其是對階層生態的人本個性挖掘,顯得急切而強烈。
他的《路過一個人是如此之快》無疑是抗爭詩學的一次有效實踐,詩以頗具沖擊力的視覺語言,切入現代社會凌亂的現場。“當下”是作者無法破解卻又必須面對的一道大題。“我猜二道橋附近有許多她那樣的女人/人人都幻想有一塊勞力士金表,最好是男式的/松垮的表帶扣在輕柔的艾特萊斯綢袖口上面/像離異前新婚丈夫緊緊牽著的手”。詩人的意義正是在這樣的“不回避”中獲得對應社會真實的世相,詩中的女人們所在的“二道橋”隱含了極其豐富的俗世外延,這是通向滾滾紅塵的橋頭堡,充滿城鄉接合部的文化符號。女人們的欲望,帶出了強大男權對情感世界的左右和意識舵向。而她們的遭遇和麻木于命運的“自得”,正是人性墮落的悲哀。
這是一首人性速朽的見證之詩。寶貴的時間,不對人生走向智美有效,而是用于提示交易的盡快完成,其揭示力度通過細節刻畫,那種人性之“惡”,竟然墮落到打起盤剝時間的主意來,“發條越來越緊”是為應對“一個接一個干癟的男人”,因有趣、可笑,而更發人深省。詩人選擇從這個斷面剖析滑坡的世道,如一把藏刀揮砍沾滿泡沫的死水。而混跡其中的這個人,他曾經從軍的身份隱藏于手機彩鈴,自負地進行著人格分裂的雙面人生:“一邊操持軍人的利落本色/一邊用心扎進俗世塵埃。”盡管本色有時還殘留著“喚醒”的余味,故鄉也依然堅毅著初心的召喚,但生活的血本,很難從“埋頭苦干”中淘到利益的分幣,鄉音也無法讓孤兒般的兩人在生活著的異地相互溫暖。
在我的詩歌觀察中,“招待所”作為一個具有詩學鏡像被“慢鏡頭”化的獨特性幾乎是第一次見。班瑪南杰在西部高原這個更具混聲元素和時代洪流回音的地域中,找到了如愛爾蘭詩人希尼一樣向下挖掘的出水口,其實,在我們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更多的招待所承擔了濃縮社會圖譜、見證人性的灰暗意識與倔強的生存法則,這個富有“典型”含義的藝術表現,其關鍵在詩人本身是否具有介入能力與保持內省的鋒芒。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認為:“詩就是黑夜,白天以它為鏡子,照出自己的存在。”對于班瑪南杰而言,刨開市井的表層,搜尋喧囂背后那些真實的人性,寫出生活底層的實況,把世人最真的一面淋漓展現,因此他的詩歌斑駁陸離,場景轉換總是朝著在場的向度位移,對人的關注,對人性的洞察與塑造,似乎是他詩歌永久的坐標軸。僅僅是對一碗面的需求,年輕姑娘就可以撕掉“羞澀”,而工地上掙命的男人面對誘惑也能突破“旱田和學費”的禁戒。“僅僅是一大一小兩碗面,/進入身體的熱量,/一個熱氣蒸騰,/另一個汗流浹背”。如此低級的食物需求與肉體交易,觸痛了詩人的心,進而讓他的詩行對應了這樣的藝術法度——文藝作品對“不倫”的表現就是對人類激情的描繪,同時也是對人生種種道德困境的展示,其魅力就在這種困頓卻熱烈的情感中得以放大。顯而易見的是他的“放大”,不走“下半身”的噱頭,而是賦予身體與欲望一種真實的情態,一種“存在”的視覺打量,一種對活著的追問。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提出的“此在”概念是“存在的本質在于把握那個提問者的存在”。也許班瑪南杰冥冥中意識到,對存在的詰問力度,定會轉化成詩人自身存在的意義。于是在他詩歌中的現實,呈現出羅蘭·巴特指認的“我是我所是者”的殘缺圖景。它們散布在破舊的招待所、老人們值守的村里、燈紅酒綠的悅賓樓、商賈熙攘的南方北方,而在宏闊視野下的社會大舞臺出沒的,是轉業軍人、退休領導、年輕詩人、中年商人、街舞小生……眾生相的刻錄,最終淹沒于一條灰塵飛揚的土路,命運的軌跡也終結于戲劇性的一幕:“修路炸山的飛石打瞎了左眼/因此,他無比幸運。先進、模范……/跟著村主任到處披紅戴花,腳下生風/直到撞到領導的座駕/看到那么多人在認真地看著自己的瞎眼/他慌忙摘下紅花指指干癟的眼球:/‘一只眼。看路就看不見您/看您就看不見路。’”對于被“路過的人”,他因為“修路炸山的飛石打瞎了左眼”而成為了一種“幸運”,成為“跟著村主任到處披紅戴花”的“先進、模范”,瞎眼而幸運,巨大的諷喻讓詩歌開篇衍生的悲劇感有了一個及物的共鳴。但詩人似乎意猶未盡,一個更大的“局”緊隨而至:撞到領導的座駕,一種猶如契訶夫似的幽默與譏諷躍然眼前:“看到那么多人在認真地看著自己的瞎眼/他慌忙摘下紅花指指干癟的眼球”。細節背后的人性深刻從圍觀的“那么多人”的麻木與作為主角的“他”借“干癟的眼球”的言外之意試圖轉移話題,最后以“看路不見您”與“看您不見路”的自嘲作哲理式收場,其中有限的回旋余地,加大了詩歌返塑的意義共識。
于是不難理解,在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里,詩人竭力讓自己像一個無比忠誠的布道者那樣踏上了異常艱難的求證路途。他對于動蕩中的底層描述,為當代中國文學的詩歌敘事和社會觀念洞開了一道豁口。
四
行文至此,有必要再繞述一下詩人班瑪南杰的底層意識及其關注的興趣觸點。關于底層意識與作為話語實踐的底層敘述,李遇春曾撰文闡述:一種是“階級”意義上的底層,劃分的依據是經濟標準,即物質財富匱乏的社會群體。再一種是“階層”意義上的底層,劃分的依據是組織、經濟和文化三種社會資源的有機構成,即“綜合人力”較低的社會群體。階級意義上的底層是沿用的革命歷史語境中的“成見”。階層意義上的底層是在新時期以來“后革命語境”中出現的“新見”。
姑且不論新時期文學在底層書寫上的建樹成果矚目,也不遑論后學術時期的“底層”對文本純正意味的嚴重剝離,單就班瑪南杰的詩歌本身所提供的場景和打開方式,就可見一斑。這或許是他新作呈現的一個異數,當然,其所展現的“現實”,有著別樣的“人間煙火”與“社會隱痛”。
“她和別人通話/聲音總壓得很低/像在談論不可告人的秘密/像是從一個秘密工廠/一件接著一件不停輸送/她耐著性子照單全收/再后來她接電話姿勢也低/低到鬼鬼祟祟/低到恨不得接起電話就能隱身/一手扶著電話/另一只手捂嘴監視四周/周圍人看她接起電話/也自覺和她保持距離/她恪守唯一的安全法則——/遠離人群/保持沉默”。詩中袒露的“她”,無疑是一個被性別定義的人,一個和此時代的某個端口緊密相連,而這個端口通向的,正是一個被生活驅趕而聚集的族群,類似“七十二家房客”的那種雜亂、囂鬧,但正是他們,撐起了社會最堅實,也是最有藝術指向意義的人文生態,客觀得沒有參照,也無需調查取證予以回應。一切深度的打開都潛伏在詩人主體責任感對世道的詩意闡釋之中。蘇珊·桑塔格在一次采訪中說:“我不相信有‘人類經驗’這種東西存在。有各種不同的感受力,有各種不同的對藝術的要求,對‘藝術家是什么’也有不同的自我構想。藝術家認為有必要做的事情是,給人以經驗的新形態……藝術家是這樣的人,即他挑戰被接受的觀念,或者給予人們關于經驗的其他信息,或者其他闡釋。”如果說文藝作品應當是對不同的可能性的展示,那么詩歌,就更應該是成功打入日常之象,去表現最富有意味的人事,或者是對最極端的東西在現實面前的特殊觀照,“是創造性的而不是刻板的”。她身上帶有某種屬性的暗示,這是生活困厄對人性逼退的應驗。“她信任聽筒里的聲音/懷疑聽筒外的兩只耳朵/她迷戀按鍵上呼叫每個人的唯一的號碼/厭惡來電顯示上赤裸裸的姓名/反饋給大腦多余的信息/除了充電/她都習慣用不為人知的乳名/稱呼手機”。
文化的先導權最有理由交還廣大底層群眾,詩人也必須有服務百姓的主體性認識。自文學誕生至今,作者只有重視了“人”,注重探究人的本質,尤其是不缺位于各個階層和不同背景下的所有人及其復雜性的深刻揭示,才談得上對文學藝術規律的尊崇。欣喜的是,班瑪南杰的認知起點不僅賦予了詩歌提升社會共識的前提,也給更高要求的文學理解提供了條件。不難看出,班瑪南杰的底層寫作,不是簡單模仿那些局限在流水線上作業的既成定勢的底層人物形象,那種不切實際的幾乎已成宣教口徑的創作惰性,已為他自覺摒棄。相反,他更專注于誠實、勇敢地在生活洪流的基石之中去抒寫、打撈深邃的“感覺”。他詩歌中的底層體驗,是朝向精神之窗發出的縱情而又節制的吟唱。他自覺超越過去既有的主流化底層寫作模式,把藝術視角轉移到對自身生活的肯定,深入體察當前廣泛、復雜、多變的現實生活,發出真實的聲音,他的詩歌,以理性認識為基礎,以感性形象塑造為手段,沿著體察世道的必由之路不留余力地昭示底層寫作的真正價值所在。
作為一個新詩寫作者,如何從生活經驗里探測未知經驗并展現其無限的可能性,從而回避“二手玫瑰”的尷尬與盲動,擯棄習慣性的自我復制是走出概念化詩歌藩籬不可或缺的原創動力,因此,賦予現實以形象才會生成可感的詩意。綜合班瑪南杰的一批新作可見,他的詩愈加注重整體的完整,意象與世相的雙重意味。他忠于現實又不倚重現實,隨時有著出塵的風雅和入世的勇氣。“一個優秀的作家既要精通現實,也要與傳統或歷史建立對話關系。”小說家格非認為,“文學藝術是現實最為敏感的觸須。當今中國的社會發展波瀾壯闊,為作家們提供了豐富的寫作資源和素材。同時,現實極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也給作家們的寫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如果說《路過一個人是如此之快》是集中以調侃的口吻敘寫底層生活的苦難,對主人公經歷的辛酸際遇置于荒誕表達之中,對線索人物的畸變軌跡進行明暗穿插,但在人性塑造上始終表現出的驚人的一致性,隱含的社會批判漸漸生成詩歌內在最打動人心的力量,那么,他的《大武,大路之外》完全可以看做是一個“副本”,詩人力圖把觸及外部世界的眼光轉入內在鋒芒的思考知覺,從復雜的共生關系中擬清自己的面對,把“每次出門”都當成是走在“新的荒原上”,然后“在每一個路口之后自然交錯的空間”傾注想象的熱情,謀求“靈魂的激蕩”,在“一畝常年痙攣的田地”自行“萌芽、抽枝、結穗”,為著“贖罪”或“洗禮”,為著“繁華”之外的“寧靜”被“安排妥當”。對生命意識與文化意味的省思,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詩人自身的心靈寬度與精神的真誠度。
詩歌是回響的脈搏,永遠對求真負責。在意義指向上,班瑪南杰的詩歌始終堅守一種喚醒意識。持“喚醒”主張的法國思想家弗朗茨·法儂認為只有喚醒和鑄造民族意識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才可信、有效、有生命力和創造力。而立足于人的日常感知,才是維系文脈最核心的“魂”,最有力的“根”,最不會走樣的“底色”。任何詩歌,幾乎都是在“隱”與“顯”的二分維度上書寫屬于詩人的個體經驗朝向經驗世界的秘密、智慧與藝術張力。班瑪南杰的詩,正是這迷人的一面,把我迷住。
總之,班瑪南杰的詩呈現了一個少數民族詩人的最大“開放度”,骨子里的進階意識緣于少數民族血液中特有的韌性,他內心的光芒,在駁雜現實敏銳地捕捉詩思之真,精誠致力“寫作方向感”的維系,表現不俗,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