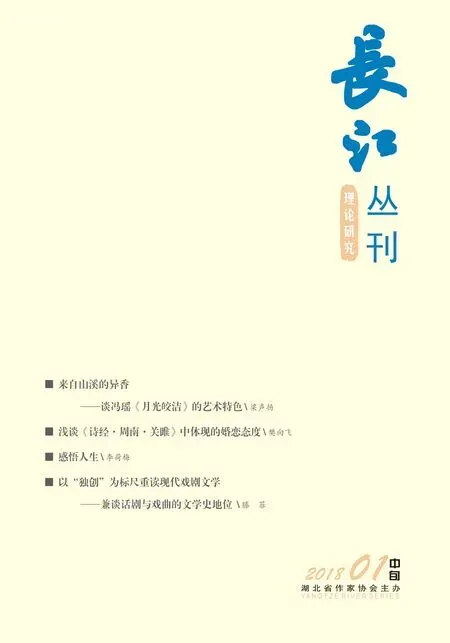基于密爾“自由”思想對90后的思考
李麗萍
一、90后的“自由”新特征
繼80后之后,我們90后也站在了風口浪尖處,面臨各種各樣的正面的負面的評價。但90后有自己獨樹一幟的個性和生活方式,不照搬前人,也不循規蹈矩,開啟了社會最大的創新能量。
(一)“為愛而動”是90后的追求
我們是“90后”,我們有自己的想法,我們有自己的天地,我們渴望被理解。當我們選擇了自己的腳下的路,在面對過來人苛刻地批評時,我們沒有喪失對詩與遠方的追求,反而有著一種只做自己喜歡的自己、敢于堅持就戰勝了自己、我們不會為了別人而改變自己的個性。密爾在講到個性問題時,強調個性就是個人具有獨立意志,根據自己的經驗、知識、性格與利益對外界事物作出判斷,而不是根據他人、社會、傳統、習俗作出判斷。密爾分別用了“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愛好和判斷而行動”、“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欲望和沖動都是他自己的”等說法予以表達。在密爾看來,個性自由就是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安排與自己相關的生活方式和做事方法。“創青春”是屬于我們年輕人的平臺,即使在比賽中沒有得到師長的肯定,我們仍然沒有放棄我們的想法,在路上,在青春的路上,我們沒有屈服于眼前的茍且,我們以自我的方式追求著屬于我們的詩和遠方。 如果“想法”不是“自己本性的表達”,如果不能“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便談不上個性自由,密爾如是說。
(二)“不懼艱險”是90后力量
我們是“90后”,純粹、力量主義和無所顧忌,是我們最大的力量。在密爾看來“惟一實稱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好處的自由。”[1]密爾很反對人類聽憑社會或者其他人代替自己選擇生活方式的人,密爾視之為與動物無異的人類,對個性的發展是很不利的,不利于發揮人類本身所具有的獨特的官能,致使人類淪為平庸。身邊不乏這樣的90后,家人給安排了工作,可我們偏偏對這種“被安排好的人生”不滿足,辭掉工作跑到大城市,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著符合自己專業且待遇不錯的工作,可我們并不喜歡,我們選擇重頭學習自己喜歡的,即使父母覺得我們像個無業游民,其實我們能在滿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同時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但是他們還是不理解。“人性不是一架機器,不能按照一個模型鑄造出來,又開動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規定好的工作;它毋寧像一棵樹,需要生長并從個性方面發展起來,需要按照那使它成為活東西的內在力量的趨勢生長和發展起來。”[2]在密爾那里,個性就是具有獨立的意志,如果一個人不能依照自己的想法來處理自己的事情,而是憑著他人、傳統與社會的習俗來生活的話,那就無異于人形的機器,與動物與沒有什么分別。而90后厲害的地方就恰恰在于,能夠把自己的熱情、勇氣和毅力變成現實,而不僅僅是做一個現實和理想割裂的空想主義者。
(三)“無畏挑戰”是90后的激情
我們是“90后”,我們愛“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那種舞動的勁,帶動著我們青春向上的心靈。我們一樣有著不屈的脊梁,汶川地震的時候,90后的官兵趕赴前線抗震救災,上海世博會,大批的90后志愿者參與其中,奧運火炬傳遞的時候,擁護火炬的那群90后難道不值得大家驕傲嗎?密爾說“欲望和沖動確是一個完善人類的構成部分,與信賴和約束居于同等地位”。[3]個性要求每個人要有激情、有欲望、有沖動。只有有欲望沖動的人才會積極拼搏,積極去闖,這才能使自己的個性得到充分的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
二、90后是具有“自由”思想的一代人
90后不僅是一代人,更是一種價值觀。“自我”成為他們個性自由的代名詞,90后身上崇尚自由、多元、個性化的精神來自自身的文化臍帶,并將影響其一生。90后代表的其實不是一代人,而是一種價值觀念,一種思維習慣,而我們在對90后作出一番品評時,我們實際上是在感悟一個新時代。90后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標簽,更不是幾個被炒熱的人物,而是一種開放性的思考心智。
正如密爾在《論自由》中所傳達的的,在民主大眾的時代,我們要避免傳統習俗、社會大眾對個人自由權利的摧殘,使我們每個人都具有個性,使個人能夠成為自己。“習俗的專制”,導致人類的“集體平庸”,不僅阻礙了個人的獨立、個性自由的發展,而且也會使社會停滯不前。
年輕往往意味著叛逆、張狂、率直、勇猛,這種力量能夠讓我們沖破上一代人已經凝固的經驗和價值觀障礙,創造出一些有趣的東西。中國有句老話叫“船到橋頭自然直”,怕的不是亂撞、碰壁、迂回,怕的是心如死水,偶有微瀾。每一代年輕人,都試圖破壞既有的、凝固的利益格局,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價值。所以他們才會跌跌撞撞、左沖右突、搖搖擺擺。90后甚至00后們生活的這個時代里,更強調“以人為本”,這個時代,人首先要有才華和長處,其次才是彌補短板,人最要命的不是有很多缺點,而是毫無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