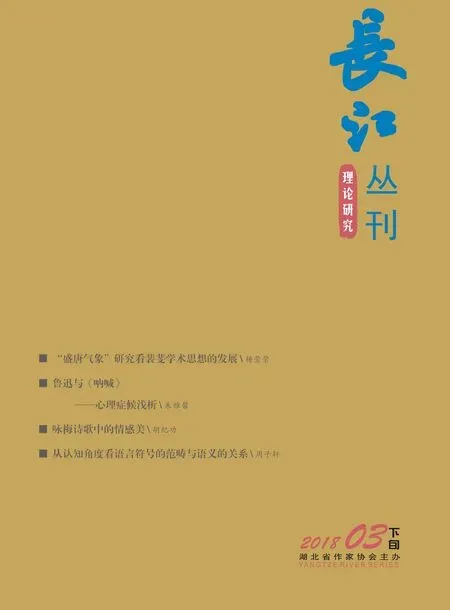全民守法的細節
——以大眾的法律態度為中心
■陳 駿/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教育院
“全民守法”概念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之后,已逐漸成為構建法治國家的主體部分和實踐環節。從法的運行層面而言,“全民守法”應體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也應當注意到當前廣泛存在于城市空間里的隨地吐痰、闖紅燈、廣場舞噪聲擾民等看似瑣碎、細微的違法行為。關于“國啐”、“中國式過馬路”仍然環繞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并且時不時地見諸互聯網媒體或者紙媒報端,繼續淪為輿論空間爭相討論批判的焦點話題。這些行為正在消解法的權威,潛移默化影響著“全民守法”的法治愿景塑造,也是對于法治細節的破壞。追根溯源,當前出現這些現象的背后,是一般大眾的法律態度出現了偏差。因為態度影響行為,行為背后所涉及的是每個人所秉持的態度,若人們對于如何遵守法律的態度出現了偏差,則其難免做出一些微小的違法行為。
一、何謂大眾的法律態度
法律不僅是“行動中的法”,也是“態度中的法”。法律態度從本質上是每一獨立個體對于某一特定目標的評價,這種受到意識支配的評價帶有傾向性,該傾向性最終轉化為外在的行為或行動。對于普通大眾而言,其法律態度的產生正如格蘭諾維特所認為的,“人不是脫離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像原子式地進行決策或行動,而是嵌入于具體的、當下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中做出符合自己主觀目的的行為選擇”。①因此,大眾的法律態度一定是與具體生活場景相關聯,并且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對于他們而言,其法律態度不同于受過嚴格法學技藝訓練的法律職業共同體,由于普通大眾缺乏對法的基本認知,其態度本身并不帶有非常深刻的法律層面見解,相反,他們的態度更多的是深受傳統國民性格、生活經驗、常識邏輯的影響,顯得微小多變。
正因普通大眾的法律態度是微小、多變的,所以他們對于如何守法的認知往往出現了偏差,在守法過程中摻雜了不同的主觀傾向,而這些主觀傾向所積聚而成的態度對于“全民守法”圖景的構建是消極的,需要給予糾正。
二、守法態度偏差與公共空間亂象
眾所周知,一個人終其一生可能并不會與訴訟、法官、檢察官、監獄等司法要素打交道,但對于在城市里生活的絕大多數人,他們的日常行為可能都無法避免與諸多微小的違法行為發生關聯。例如,人們也許其在日常生活中不會做出有違刑法的犯罪行為,但是類似于闖紅燈、隨地吐痰、違章占道、廣場舞噪聲擾民等違法行為仍然很容易做出。因為這些行為在人們主觀意識里并非具有多大的社會危害性或者違法的嚴重性,反而在其態度之中是瑣碎、細微、無關痛癢的。但是這些看似微小的違法行為,卻無時無刻不在困擾他人的衣食住行,影響公共秩序,更影響人們對于法治的直觀感受。從法律態度角度而言,緣何會在城市空間形成獨有的“中國式過馬路”“國啐”“廣場舞擾民”等一系列公共亂象?應當說,正是人們的守法態度出現了偏差。具體而言,其偏差可體現為兩個方面:
首先,人們對是否守法抱有“占便宜”的態度。“占便宜”一詞更像口語化表達,但該詞確實是我們當前國民性格一個具體寫照,也是普遍的心態。將極具口語化習俗化的“占便宜”納入法律態度的討論范疇,有其特定的內涵。因為對于很多人而言,“占便宜”的態度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過“占便宜”可以獲得額外的收益。例如,人們在街頭闖紅燈能夠為其節約數十秒的駐足等待時間,那么省下來的數十秒時間便是人們的額外收益,又如有人在地鐵安檢時候逃票入站行為,則其所逃的地鐵票金額便是其額外收益。無論是時間成本的收益,還是經濟成本的收益,眾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在“占便宜”的心理驅動之下,做出違反交通規則或者地鐵管理法令的違法行為。而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擁有“占便宜”心態的他人,看到生活中的違法行為,極有可能不會嚴于律己或者加以制止,反而會爭先恐后地效仿,否則就是一種“吃虧”。在我們的語境中,“吃虧”是“占便宜”的對立面,發生在身邊的微小違法行為逐漸成為頑疾,一個因素是眾人秉持了“循規守法是吃虧”的理念。人們總能通過各種精心設計的手段規避律法,避免自己“吃虧”。從法理角度而言,法具有預測功能,即人們對于自己行為所發生的法律后果會有所預判。正因為人們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這些小的違法行為所獲得的利益超過了所受的懲罰,即認真守法可能會“吃虧”。由此接踵而至的是效仿跟從,發生更多的微小違法事件,久而久之,法的實效和法的權威便大打折扣,最終可能出現“有法律無法治”的現象,“全民守法”的愿景也可能落空。
其次,人們對違法秉持“法不責眾”的態度。“法不責眾”的態度認為同一行為違反的人多了,法律便不會處罰,執法者便無可奈何,其背后是一種群體僥幸心理的投射,即民眾對法律能否被執行到位的心理預期,是對其違法行為后果的一種大膽預判。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民眾會將違法的規模、執法者能否第一時間抵達、執法力量的多寡等因素充分比較考量,最后得到判斷。帶有“法不責眾”的態度,人們更愿意與執法者進行“博弈”,期待他們的行為能夠逃避處罰。
毫無疑問,當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秉持的“占便宜”“法不責眾”態度,在眾人的主觀意識之中看似微不足道,但實際上這種守法態度所出現的偏差,無形之中是對法律權威的消解,對于構建全民守法的整體格局或者法治社會長遠的塑造,無疑都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破壞。
三、態度改變與全民守法的型塑
我們的歷史傳統或生活經驗所集聚的“見微知著”、“以小見大”、“因小失大”、“防微杜漸”、“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勿以惡小而為之”等成語典故,直觀地體現了細節對于全局的重要性,全民守法也應當體現在看得見、可感知的細節。
毋庸置疑,全民守法的細節之處在于人們要認真對待每一部法令,認真遵守每一條法律,并非有法不守或有令不從。而上述看似微小的違法行為通常游離于法律規制與道德評價的邊緣地帶,違法樣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日常生活之中,眾人往往容易忽視其所作所為的違法性,認為其違法行為微不足道,甚至僥幸認為能夠避免受處罰,或者認為違法成本處于眾人可接受或可負擔的限度之內。因此,要糾正這些行為,必須糾正眾人的法律態度。真正的守法,要求每個人能夠擯棄“占便宜”的傳統國民心態,改變“守法吃虧”的市井心理,糾正“法不責眾”的僥幸心態,型塑正確的守法態度。
具體而言,改變人們的法律態度,應當開始于法治社會的“公民角色”的意識塑造,揚棄“市井小民”或者“升斗小民”的主體角色。因為在“市井小民”或者“升斗小民”的角色之中,人們更多想的是對規則的破壞或者逃避,或者精于算計,例如地鐵逃票或者闖紅燈,或者我行我素旁若無人,例如隨地吐痰、亂倒垃圾或制造廣場舞噪音。而在公民角色之中,諸如社群主義邏輯所強調的,每個人都應當負擔起對社會福祉、公共秩序的責任,每個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或者袖手旁觀。在“全民守法”時代,法治的細節正是體現在每個人對于法律的自覺遵守,這既是公民義務,也是公民美德。
注釋:
①[美]馬克·格蘭諾維特.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M].羅家德,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1~33.
[1]麥可·芮斯曼.生活中的微觀法律[M].高忠義,楊婉苓,譯.臺北:商周出版社,2001.
[2]胡玉鴻.全民守法何以可能?[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