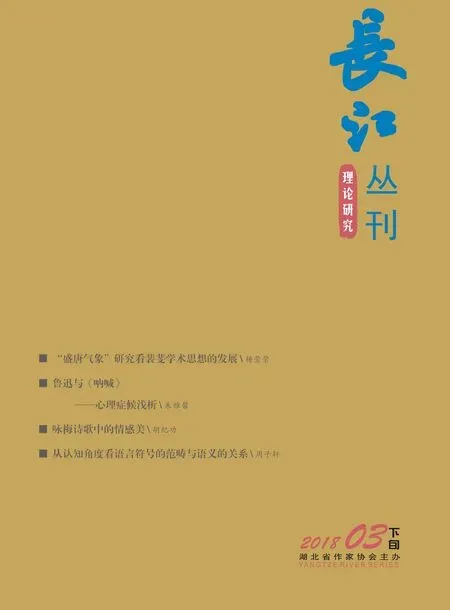PDS教師教育模式存在的問題及反思
■熊曼曼/重慶師范大學
為了有效促進教師專業發展,首先在美國出現了大學與中小學合作建立的教師專業發展學校,簡稱為“PDS”。它是融教師職前培養、在職研修和學校改革為一體的新型師資培育形式。許多人認為,“PDS”是為師范生進行專業準備,也是為有經驗教師提供持續專業發展的新制度模式,同時還是支持教學研究的機構。它是教師教育的一種新模式,也是一種探索和革新,但是在發展推進的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一些不容小覷的問題:
一、教師參與不足,持續發展難以實現
只有部教師參與的合作模式難以實現教師的持續發展。從PDS近些年的發展來看,參與PDS的教師大多是主動尋求專業發展的教師,并且絕大多數是主動參與的志愿者。對PDS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這些參與者身上。即使在整個學校參與的案例中,通常的選擇是允許那些不感興趣的教師轉到其他學校。就大多數學校而言,參與的教師只是組成一個比較小的興趣小組或教師中心,甚至在一些學校,教師自己決定參與的水平或者選擇退出。然而,大量的證據表明,只有當一個學校的全體教師都參與的時候,學校的教育革新和教師的持續發展才能真正實現。因為全體教師的參與能夠分擔他們個人遇到的問題或困難,所以教師更樂于參加合作性的探究。例如,美國密爾沃基公立(Milwaukee Public Schools)與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合作在PDS內建立了教師教育中心,教師們發現,他們從以技能為中心到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及其方法的變革變得更容易,因為積極進取或主動地行為成為創造的動力,良好的氛圍和堅定的信心,能夠促進教師和學生持續不斷地進步,甚至那些過去對教學不太投入的教師也會改變他們的課程計劃,表現出積極性。整個學校的參與也為審視更廣泛的問題(如學校怎樣滿足各種學習者的需要)提供一種環境,這種組織結構能夠更進一步促進一個民主的學習化社區的創建。但是如果參與PDS的是少部分人,或僅僅是一個小的志愿小組,那麼當他們對自己的教學實踐進行孤立的自我反思時,就可能潛伏著一種危險:需要進行的學校范圍的結構性變革將被忽視。只有全體教師的參與,才能形成統一協作、強大有力的態勢,促使對所需要的結構方面的變革,促使校長或其他管理者真正投入到PDS,才能在教師專業發展上有所作為,并為教師成長營建良好環境。
二、層級差異與隔離,角色轉變艱難
大學與中小學兩種不同制度文化之間的層級差異和長期隔離,為PDS有關人員的角色轉變造成困難。長期以來,大學教師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制度上,都常常被視為“專家”、“學者”,相比之下中小學教師往往被看做是低一層次的“教書匠”,他們之間的關系時常是“上”與“下”、“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在許多PDS中,無論是大學人員日常工作議程的提出還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引導,大學教授很容易被看做組織者和指導者,而不是合作學習者。這種層級差異的觀念給PDS帶來一些消極影響,使參與者難以形成良好的合作關系,造成交流和溝通的困難。在一些PDS,教師在大學人員的培訓和指導下參與實習教師的研討和評價,而大學人員要對教師的教學進行觀察和評估,并提出教學行為的反饋意見。研究發現,那些指導實習生并參加每周研討會的教師,其教學技能得到了非常明顯的改進和提高。但是,與其說教師的知識是在與更高的權威、作為教師評價者的大學教授一起工作中建構的,還不如說知識是從大學教授哪里傳遞下來的。相比之下,在成效顯著的PDS中,一些大學人員,甚至當他們作為教師的指導者時,他們也能夠表現出合作學習者的角色。一些學校PDS之所以不太成功,部分原因是校長沒有扮演應承擔的角色,其管理方式存在問題。例如,有些學校,校長不允許教師對他們自己的專業發展做出決定而是對他們的工作嚴加管制。在大學,即使那些參與PDS的“基地教授”能夠較好地扮演應承擔的角色,也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和激勵,卻時常要冒著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更少的研究成果、更加沉重的工作量、更低的社會身份的風險。
三、角色承擔過多,教學質量堪憂
PDS的確為教師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教師對教學進行研究,對實習教師予以指導和教育,同時致力于教育行政的變革、參與決策的制定,他們的聲音傳出教室,響亮四方。這些都成為轉變“教師只能和學生在一起而不能做其他工作”等傳統觀念的強有力的工具。教師是基地管理小組的成員,是實習生的指導者,是家長—學校的聯絡者,是教師教育者,還是大學—學校的聯絡人,然而,教師更重要的角色是課堂教師,教師承擔的最重要的職責是教育學生。過多的職責可能最終導致教師勝任能力的衰弱,并降低他們的工作質量。日趨增多的教師職責可能迫使他們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投身于給定的領域。總之,PDS還處于初創時期,還存在著許多困難。工作需求愿望的加劇,傳統官僚體制的阻礙,學校和大學少部分人員的參與等因素,都是對這種新制度創生的挑戰。盡管PDS顯示出巨大的發展前景,但前進的道路上充滿阻礙和困難。
[1]阮成武.主體性教師學[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
[2]趙昌木.教師專業發展[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