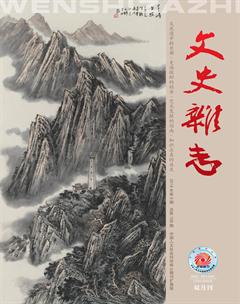如何讀懂諸葛亮的木牛流馬
王仙洲
《三國演義》一百二回說,蜀軍六出祁山北伐,在劍閣以北的懸崖絕壁地帶,孔明造木牛流馬來運糧秣。書中載有制造法文,但誰也讀不懂,如“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自己扭轉舌頭,行走自如,別人扭轉就不走,是什么道理?
注釋《演義》書的說,木牛是四人推拉前面有轅的木頭車子(不確切),流馬是獨輪車(但文不對物,一字未解);尤其注《〈三國演義〉軍事地圖本》的說:“該書有三成左右是虛構的,如諸葛亮造木牛流馬、錦囊妙計等,基本是虛寫的,而且寫的詳,還有尺寸。”這樣,使讀者都認為是隨便虛寫的,沒什么意義,讀不懂就不必去用心讀懂,把書頁翻過去了。可惜,《三國演義》這段文字句句在寫實,把死車寫活了,可謂妙筆生輝——是人們未讀懂,不能識解罷了。
陳壽著《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載:建興六年(公元227年)“冬亮出散關……糧盡而還。”“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十二年(公元234年)春亮悉大眾從斜谷出,以流馬運……八月,亮疾病,卒于軍”。從這段歷史可知,孔明六出(實為二出)祁山北伐,道路險阻,只用當時四輪馬拉車運輸不夠,于是想法改進車子以適應不同出征路徑:在平坦較窄路上改車為二輪,因車不用牛馬拉(是人拉,即遺至今的木板車之類)比較新奇,故當時昵稱木牛。在劍閣以北無路的險阻地帶,簡修棧道而首創獨輪車來運,大部隊行軍時沿路人車不絕,頗似古語“車如流水馬如龍”了,故當時象征性地稱流馬。總之,木牛和流馬是當時兩種運輸糧秣之車。
諸葛亮去世后,陳壽等晉代人,敬其巧思是第一能事,以為超過他的政治軍事才干,故撰書而神其故事;再經裴松之為《三國志》大量作注,到元末明初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引用此文時已千余年,至清初毛宗崗又修訂,待我們讀到書中這段木牛流馬文時已被重重渲染上斑斕色彩,故更顯奇異難懂了。但這些文字畢竟是寫實,慧眼人解字對物,反復推敲,終可以大悟。那上下兩段文(指“造木牛之法”與“造流馬之法”)是渾然一體者。其先敘概貌和功能,再寫結構尺寸,不管描述像牛、像馬、像象,甚至籠統稱木牛流馬,其實句句者在寫獨輪車,惟妙惟肖,十分真實。那么獨輪車在當時有何科學結構和獨特功能,值得這樣特寫?原來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出現先進的蒸汽機車,但晚于諸葛亮時代1500多年,而現代的電動機車就更晚了,且二者不能在山區險阻地帶代替獨輪車運輸。中國在兩漢三國時,全世界都是用四輪馬拉車運輸,車是四平八穩的;惟有蜀漢國的獨輪車著地只一個支點,全靠推車人分開的兩手兩腳和肩的五點合力來掌握它的前后左右平衡,并使車上坡下坎、轉彎拐角、前進后退自如。這其中所運用、所體現的物體運動學、動力學、重力、阻力、共點合力等等,比公元1687年“牛頓三大運動定律”的提出,要早上1450年呢!
按《三國演義》介紹而繪的上述簡圖可知:裝糧的板方囊容二斛三斗約六七百斤(漢朝時1斤約9兩),全重設在后軸處,距前頭車輪和后面人把手處都是2.22尺,這就穩定了前后使之平衡;又把它分成兩個,裝于車架兩側,其底與地面的仰角成30°。這樣重心是兩個,重力就一分為二了。萬一車向一側傾斜,兩個又拉著,人就能夠掌握好車的左右平衡;否則一頃斜車就側翻了。這些都體現在車的結構中。所以《三國演義》所寫尺寸不是虛寫的,而是句句有道理。
現就文(《諸葛亮集》大同小異,裴松之注《三國志》有引用)中最難懂的幾處,不揣淺陋解讀于此,獻芹給讀者:
一、關于“一腳四足”“雙者為牛腳”“轉者為牛足”“前后四腳”。這里,先要識破撰文者對腳和足二字的妙用:查字典可知,“腳字是人或物腿的下端,接觸地面支持身體的部分”,以觸地稱為腳;“足字是器物下部形狀像腿的支撐部分,如鼎足”,以支撐稱為足。這樣來看,腳和足二字的含義就不同了。再看文中用多視覺描寫的:如描寫人,可寫他坐著的樣子,也可寫他跳舞的姿勢。文中描寫車,既寫車停著的樣子,又寫車推起走的形狀。于是,你看車推起走時,前頭車滾輪是一支觸地的腳;車架下有兩雙懸空的支柱作為支撐的四個足,所以它是“一腳四足”。再看車停放著時,那兩雙作為支撐的足,已觸地成腳了,就是“雙者為牛腳”;那轉動的車輪,此時亦支撐著車重量成足了,就是“轉者為牛足”;那前后兩對支柱已注明是前腳和后腳,所以是“前后四腳”。這樣,就準確地認清它是一個車輪、兩對支柱的獨輪車了。
二、關于“形制如象”“方腹曲頭”“頭入領中,舌著于腹”。這段較隱晦地用象的長鼻子可伸觸地來比喻車觸地的滾輪結構——車頭用條木架成曲字形,腹部架成方框載著裝糧的板方囊;而車滾輪如象的頭、臉、鼻子垂于車頸(即領)下,那車輪之框夾如象的嘴含著,其軸心三角杠就如象之舌頭伸到胸腹下了,所以它“舌著于腹”。(這句是“扭轉故事”之伏筆。)
《三國演義》載制造法又說:“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這靬是皮革,攝是調整,鞦是套牲口時屁股上(這里指人肩上)的皮帶。這句是說人在后面推車時,按人的高矮調整好皮帶掛在肩上,然后雙手提起車兩側像轅的兩根車杠,就可推起走了。這車滾輪是堅硬圓木,并包上皮革以耐摩擦壓迫的(像古時運重石柱的木滾筒,不是現代鐵制偏車輪)。它徑面四寸三,加上包的皮革約四寸八的直徑,其圓周長就是dπ=0.48×3.14=1.5尺,這車輪旋轉四轉即1.5×4=6尺。所以“人行六尺”,剛好車獨輪轉四轉,即“牛行四步”。這更說明木牛和流馬的制造法都是在寫獨輪車。
三、關于魏軍既能照樣造來運糧,那怎么卻不會扭轉舌頭?蜀軍一扭轉它就不走,扭復又走,還打了搶糧的大勝仗,是什么道理?上面說明了,這舌頭就是車輪軸心,即2.1尺的三角杠。這杠是選用最堅硬的木料做成,插入車滾筒內,其兩端受車輪旋轉時磨損厲害,是易耗構件,舊車都帶有備用的,所以它兩端裝在車架上不是死榫頭,而是活的,只用銷釘插擋住;若磨損嚴重了,抽出銷釘一扭轉就可更換。所謂扭轉、扭復,就是扭轉抽出杠和扭復插入杠的意思。(故文中未用扳動詞語。)這故事說:蜀軍搶魏軍從隴西運來的糧車,一扭轉就取走木牛流馬的三角杠,棄車而走,當然魏軍就推不走。那一帶缺樹木無法立即補上。六七百斤重的糧,推車人把它奈何不得!當蜀軍又攻克奪回,在煙火迷霧的掩護下,立即扭復插入三角杠,當然蜀軍就長驅而回,因此獲得萬石糧的大勝利。這煙火迷霧,是孔明早就令張嶷引五百兵,五彩涂面,鬼頭獸身,手執旌旗寶劍,放起煙火掩護沖殺的效果。其時司馬懿在亂軍中連金盔都丟了,魏軍以為神助。這些,當然是小說家筆下挽文藝花子之言。而實際上是諸葛亮料定魏軍首次用木牛流馬,不會帶有備用三角杠,出其不意而致勝。這是符合故事情節邏輯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嘛!
綜上可知,小說不是正史。辯證地看,劍閣、陽平至祁山、隴西一帶,筆者修鐵路經歷多年,地形確多險隘。諸葛亮在3世紀初就能創獨輪車運糧,確是巧思而可敬了。但可敬不可神化。當撥開歷代神化木牛流馬的迷霧,就可知這制造文是全寫獨輪車;其結構尺寸是紀實,而行文又用了多視角、多比喻的文藝體裁,欲把死車寫活。這也是符合“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創作規律”的。
作者:瀘州市第十七中學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