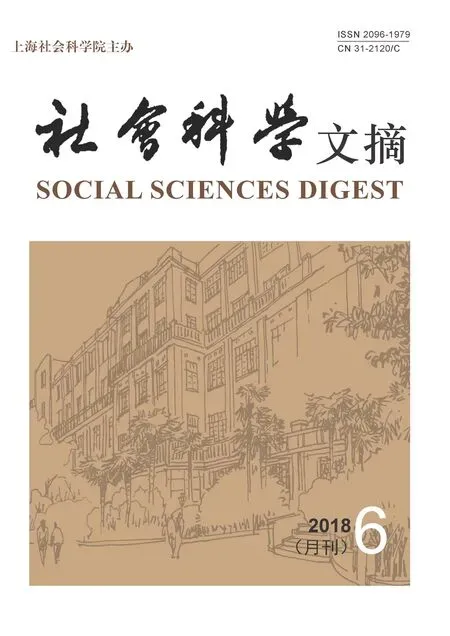憲法學研究須重溫的常識和規范
——從監察體制改革中的一種提法說起
文/童之偉
最近讀到一篇主標題為《另一種觀點:監察法(草案)在憲法上總體是站得住的》的文章及其后續文章(以下簡稱“《另》文”“《另》續文”),感到文中提出的對幾個相關問題要慎重研究的建議較有現實意義,但對該文以“憲法并沒有禁止設立監察委員會或者類似監察委員會性質的機構”為根據,得出不修憲全國人大也有權制定監察法、設立國家監察機關的結論和另外一些相關的說法不敢茍同。筆者愿同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一起,重溫憲法學的相關常識及討論問題的學術規范和職業邏輯。
國家機關“法不禁止皆可為”的提法違背憲法學常識
公權主體“法無授權不可為”,普通公民“法無禁止即可為”——這是實行民主立憲制的國家公認的憲法原則,也是法學低年級本科生上法學基礎理論課和憲法課通常會講到的內容。現在官民雙方和社會各階層都主張把權力(在我國憲法中通常表現為職權,有時是權限)關進籠子,而國家機關“法無授權不可為”其實就是憲法法律圈禁權力的籠子的支架。否定這個原則實際上等于拆籠子。
《另》文最重要的立論根據是否違反常識,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如果《另》文表達的意思確實是本文引言概括的“國家機關憲法不禁止皆可為”,那么人們只能得出其作者缺乏或違背法學常識的結論。《另》文的下列段落表明,其全文立足的基點,確實可以用“國家機關憲法不禁止皆可為”這句話來概括: 設國家監察機關可以不動憲法,因為“憲法并沒有禁止設立監察委員會或者類似監察委員會性質的機構”;“現在的問題是,憲法有沒有對人民代表大會之下的國家機構作出明確的排他性規定?顯然沒有”;“憲法沒有規定監察委員會,不等于全國人大就不能在憲法之外設立監察委員會”;“憲法對人民代表大會之下究竟應當設哪些國家機關以及這些國家機關之間的關系,雖然有明確的規定,但這些規定是開放式的,并非封閉式的,是允許全國人大創新設立憲法規定之外的國家機關的。”因此,“全國人大不修改憲法、不解釋憲法,直接制定一部監察法,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下再設一個監察委員會,是沒有問題的”。
《另》文中上面這些話表明,其作者對公權力主體“法無授權不可為”后面的原理無足夠認識。筆者注意到,《另》文在《中國法律評論》微信公號發表后,讀者的一些跟帖非常及時而恰當地指出了作者的說法違反常識之處。
為反駁微友依據法學常識發言的內容,《另》文作者又發表了《另》續文,但該文沒有證成所欲證明的觀點,反而進一步顯露其作者此前之所以發表違背常識的言論,確實是因為他不了解這個常識后面的基本理據和邏輯。綜合起來看,《另》文及其續文向讀者傳達的信息可能忽視乃至否認了一些原本應該肯定的憲法學基礎知識:1.“在公法領域,法無授權即禁止”,并非像《另》文所說的那樣,只是現在才有人提出且不知出處的“有的觀點”,而是整個中國法學界的共識,也是世界上所有正常立憲國家普遍實行的制度化原則。2.國家機關“法無授權不可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本義。3.國家機關權力受憲法限制,“法無授權不可為”,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本內容和要求。4.“法無授權不可為”所針對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對象是立法機關,在我國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5.提倡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法不禁止皆可為,其論說的客觀效果是去除憲法限制權力的功能。在制憲史上,人類發明的第一種也是最基本最主要的一種用憲法限制權力的方法,是授予權力和限制權力并行列舉法(以下簡稱權力并行列舉法),即憲法通過逐項具體列舉的方式,將一些權力授予相應國家機關,同時也通過此舉宣示授予的權力以此為限。人類發明的第二種也是第二重要的限制權力的方法,是直言禁止法,即直接規定國家機關不得如何、禁止如何等等。就兩者的關系而言,權力并行列舉法是直言禁止法發揮效用的基礎和前提,直言禁止法是權力并行列舉法的重要補充。在限制權力方面,其它所有可能發生效用的方法,包括違憲審查或合憲性審查,都以這兩種主要方法的存在和較正常運作為基礎和前提。
背離常識的認識根源和修正方向
筆者的感覺,《另》文因立足于違背法學常識的基點評說重大憲法學課題,導致全文基本論點、各分論點和相應的論證過程往往顯得不符合法學常理,以致出現同我國憲法的規定和精神背道而馳等諸多問題:1.不了解根據憲法制定法律的特定含義,不熟悉憲法用權力并行列舉法限制權力的原理,以致在討論具體立法的憲法根據時錯誤地理解了《憲法》第62條。作者的根本性錯誤,是因不懂得權力并行列舉法及其限制國家機關權力的原理,從而搞錯了憲法第62條“國家機構”之所指。2.關于全國人大可超越憲法列舉的范圍立法設立新的國家機關的論證不能成立。嚴格地說,作者看起來是要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謀取超越憲法的特權,而實際上可能陷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于不義。3.誤將代議民主當作直接民主談論。由代表與被代表關系等憲法原理所決定,代表機關發揮“靈活性”只能在憲法規定的職權范圍內,超越憲定職權范圍就是突破了憲法設定的底線,必然對法治秩序的核心即憲法秩序造成損害。4.對國家權力和國家機構權力的構成要素及其相互關聯不太了解,所言脫離實際。證據有兩個:一是主張人大超越憲法規定的范圍行使權力時,沒有評估此舉對公民權利可能形成的擠壓,也沒有注意到此舉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否認由公民享有的國家權力所有者權能;二是沒有提及此舉對中央和地方其他國家機關權力必然造成的減損。5.未能區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存在形態,以致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社會意識內容可隨時改變,來證明作為社會存在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構成要素可由全國人大以立法的方式隨時改變,結論不成立。6.解說“立憲原意”,否定了權力并行列舉法限制權力的歷史的和現實的效用。7.銷蝕權力并行列舉法的限權效用,又用“開放”等美好的辭藻來形容其做法,不甚合適。《另》文寫道:“憲法對人民代表大會之下究竟應當設哪些國家機關以及這些國家機關之間的關系,雖然有明確的規定,但這些規定是開放式的,并非封閉式的,是允許全國人大創新設立憲法規定之外的國家機關的。”《另》文所說的開放,實際上就是撤除限制權力的所有柵欄,放縱權力任意出籠,把摧毀憲法限制權力的柵欄當作“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行實踐創新”。8.曲解了憲法規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則,以致不自覺地走向了違背憲法本意的一面。《另》文作者以上關于同一類人在法律面前才有平等,不同類的人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提法,可以說完全與我國《憲法》第33條第2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規定背道而馳。9.支持“大幅度克減”公民基本權利的主張缺乏憲法根據和學理依托。《另》文談論“大幅度克減”一部分公民的基本權利,但這些文字表明,作者對外國憲法中權利克減規則的內容、指向、精神完全不了解。歐美的權利“克減”所追求的是權利保障的實質平等,是要削減強勢者的超強社會影響力,讓弱勢者能夠有效監督,因此,被“克減”的都是在職在任的官員、名人的權利,從來沒有聽說過“克減”已經被剝奪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訴訟權利的情況。國外權利“克減”只克減公眾人物的部分民事權利,如名譽權、隱私權等,絕對不克減任何公民的刑事訴訟權利。
《另文》不少說法違背非專業人員都知道的一些事實或道理。如《另文》寫道:“全國人大是修改憲法的主體,其制定的國家機構的基本法律本身也具有憲法的性質,就是憲法性法律,與憲法之間沒有不可跨越的界限。”中國沒有憲法性法律,只有憲法的相關法,憲法相關法與憲法的關系,一個是根本法,一個是根據根本法制定的法律。除非修憲,全國人大制定的任何法律條款都不可能“跨越”憲法與法律的邊界成為憲法條款。
憲法修不修改一事,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區分剛性需求與柔性需求,僅柔性需求當然不必修憲。若剛性需求與柔性需求并存,也只能剔除按柔性需求修憲的必要性。
討論設立國家監察機關的立法,應避免憲法學基本概念混淆不清、運用失當。《另》文僅在615字的一段話中,就有9處基本概念混淆、運用失當的地方。人是得借助概念才能進行思維的,國家機構、國家機關、部門、機構、機關等概念是相應的客觀實體進入人的思維過程的主觀形式。所以,概念如果與其反映的客觀實體錯位,思維的結果就一定不能準確反映客觀實體本身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
值得討論的學術規范和職業邏輯問題
對于與職業角色直接相關的一些道義問題,可能稱為“職業邏輯”最恰當。堅持適當的學術規范和職業邏輯,對于法學、憲法學發展很重要。本人第一次通讀《另》文時,就覺得相關的學術規范和職業邏輯有提出討論的必要。
第一,不能變相地生造論據。《另》文作者為了證明《憲法》第33條第2款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的“平等”,“是指同一類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強調不同類的人可以不平等。他寫道:“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憲法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但有關教育方面的法律對不同類型公民受教育的權利義務內容都做了具體限定,恐怕就不能說教育方面的法律違憲了。”聯系作者使用“限定”一詞的意向,它只能是限制、減少的意思。老實說,一個稍有憲法意識或政治常識的人,絕對不會相信我國“教育方面的法律”會通過“限定”一部分學生的權利義務,讓不同類的學生受教育的權利不平等。可《另》文為了證成其觀點,似乎違背了本應該有的憲法意識,同時不顧政治常識,提出上述論證。
在通讀《教育法》《義務教育法》和《殘疾人教育條例》后,筆者可自信地說,用我國“有關教育方面的法律”“限定”“不同類型公民受教育的權利義務”,來證明憲法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僅僅“指同一類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實際上是一種生造論據進行論證的做法。因為,這些法律法規的規定,正如憲法意識、政治常識告訴我們的一樣,并沒有“限定”一類公民受教育權利義務以維持不同類公民權利義務不平等的任何規定。這些規定是“限定”某一類公民受教育的權利義務以維持不同類公民權利義務不平等么,看來不是。那些法律中除這些規定外,其他規定更不可能有《另》文說欲證明的那種意思。這個例證之后所引刑法的例子,也存在類似問題,只是沒有這么明顯而已。
第二,法學的學術討論,應避免將法律標準、憲法標準文藝化。《另》文寫道:“憲法沒有明確規定一個國家機構,只要有利于憲法的實施,全國人大也有權立法設置”;“應當依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權力的需要而定,只要堅持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有利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權力”。這些話不僅如前所述,是憲法上沒有根據的空話大話,也是不利于法學研究形成健康學風的。“有利于”什么就做,“依據需要而定”,這類辭藻說得好聽是文藝語言,說得不好聽是官階甚高大權在握人士最愛說最愛聽的人治語言。如果沒有憲法法律,放棄憲法標準、法律標準,“有利于”還是不利于,“需要”還是不需要,最后都是誰官大誰權大誰說了算。所以,《另》文中這些說法的實際效用只能是給以權壓憲法和以權壓法律者鏟屏障、開大門、搬椅子。當然,這可能并非其作者的本意。《另》文上述那類說法,體現了一種“解構”法治、“解構”現有制度,向“政治掛帥”折返的行為傾向。現行憲法擺在那里,它是我們民族公共生活從人治走向法治、從泛政治化走向制度化、規范化的偉大里程碑。在今天的公共生活中,我們無論遇到什么問題,都應該堅持按憲法的規定辦,不應拋開憲法的規定另搞“有利于”“依據需要”之類的標準。這樣做實際上是折返1982年憲法誕生之前的時代。
第三,做某些論述時選擇的立足點算不算職業邏輯問題,有討論的必要。所謂職業邏輯,一般指從事某項職業者基于職業身份而應當遵循的道義的或倫理的準則。從事不同職業的公民因擔任不同的社會角色,他們的工作性質、為社會服務的方式各不相同,社會對他們的要求是在守法或不違法的前提下恪盡職守。任何憲法學者基于其職業責任,面對一個尚有哪怕僅1%或0.1%不合憲的法律草案,他/她都應該花100%的努力去糾正或澄清那1%或0.1%有不合憲嫌疑的文字。但有點讓人費解的是,《另》文作者明知其面對的法律草案很可能多少含有一些合憲性有疑問的內容,但對發現和糾正這種可能的情況似乎全不感興趣,而是將100%的努力花在證明草案的其它部分合憲或不違憲上。
用以上標準衡量,《另》文談論人權、公民基本權利保障和國家權力邊界時的文字,違背憲法學者應該遵循的職業邏輯。憲法是“通過規范國家權力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根本法。”因此,憲法學者的職業責任從根本上說,應該是致力于研究根據憲法有效規范國家權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權利。但反觀《另》文及其續文,可以說其作者在整體上放棄了憲法的立場,違背了憲法學者的職業責任。
按憲法學者職業邏輯的要求,學者的定位不應該是律師,尤其不應該是檢察官,而應該相當于法官。可是,《另》文在所有場合,都是檢察官的自我定位。換句話說,其作者在所有場合的主張都是拆除限制權力的欄桿,放縱權力和壓縮、減損公民基本權利,反對平等保護。這顯然違背了憲法學者應該遵守的職業邏輯,其行為性質與刑庭法官老是同檢察官立場和態度完全一致性質相同。
結語
鑒于以上事理,現可做幾點總結:(1)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立法機關“法無授權不可為”,應屬不可動搖的法學、憲法學基本常識,應該尊重。這可能是憲法學認知和價值的雙重底線,守不住這個底線,憲法學恐怕就沒法做。那時如果硬著頭皮做,就幾乎肯定會與民主法治和基本人權保障的要求反其道而行之。(2)學術規范不能馬虎,否則憲法學者很難對憲法學教學和研究事業做貢獻。職業邏輯尤其重要,堅守職業邏輯是憲法學者取得學術成就的重要保障,也是自己被社會和同行接納的重要前提。更重要的是,法學者、憲法學者遵循職業邏輯,還是國家、社會形成健全法治秩序和憲法秩序的要求。(3)不贊成輕易修憲的觀點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應該對修憲主張中的剛性需求和柔性需求做鑒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