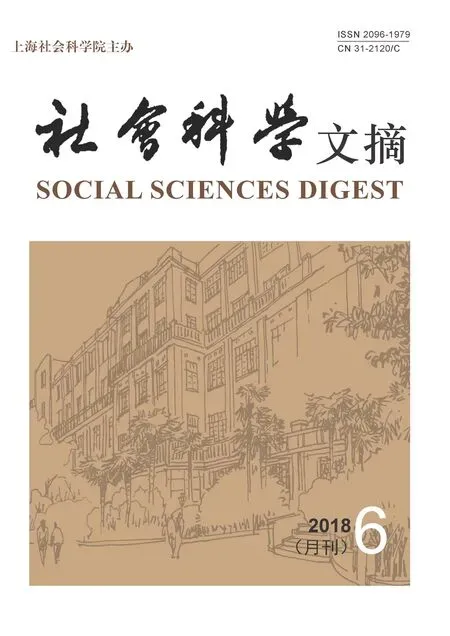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三維語境及其方式創新
文/韓慶祥 張健
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既在自身所處的時代又超越自身所處的時代,對人類社會發展具有普遍指導價值。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則,誕生于170多年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其話語所指涉的某些具體的“現實問題”來說,具有一定的歷史場景,如何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實現研究上的與時俱進,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面臨的新問題;二則,中西文化語境具有異質性,誕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與中華文化相契合,這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三維語境:當今時代、中華文化和研究自身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從邏輯上看,要對哲學“所居的時代”、“所依存的文化”及“思想研究自身的規律”有較為清晰的界定。
(一)后工業時代語境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時代議題
存在決定思維。當今世界依然處于商品經濟歷史區間,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商品現象”研究的基本原理沒有過時。1970年代以后,此時的“商品”已經不是彼時的“商品”了。相應地,此時的“商品”所衍生的一系列社會結構,也已經從根本上迥異于彼時的社會結構了。基于這一商品價值重心的轉變,由商品衍生的經濟結構相應地發生變化:貨幣信用的來源由傳統的“金銀本位”轉變為“需求本位”;貨幣的本質由傳統的“金銀符號”為主轉變為“交換媒介”為主;財富內涵由傳統的“存錢=存財富”轉換為“獲取流動性=得財富”,等等。由此,社會宏觀經濟、政治、文化秩序在經濟結構內變的基礎上出現裂變、解構,當今時代處于深刻變革之中。
(二)中華文化語境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它的契合點
從深層次看,馬克思的哲學植根于西方文化土壤,馬克思哲學的基本范疇本質上屬于西方話語。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即作為具有西方文化基因的原生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如何嵌入中華文化的語境的?一般說,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比較,在兩個方面差異很大。一是歷史淵源之差以千年計。二是中華文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獨特深奧,與西方相比,具有非常突出的異質性。中華文化把世界三分,即顯態的“陽”、隱態的“陰”和抽象的“形而上”,由此,世界分成顯態世界、隱態世界和形而上世界(本源世界)。在此方面,西方沒有關于隱態世界和形而上領域的深入區分。就認識路徑來說,西方文化自亞里士多德起,強調的是通過“實驗”和“推理”為核心特征的“外求法”,本質上是通過“五種感官+意識”來認識世界。而中華文化,從伏羲、黃帝到老子,從道學到佛學,都強調通過以“內觀”和“悟”為核心特征的“內求法”,本質上是通過“思識+藏識”來認識世界。在這里,道學和佛學認為,人的認知結構可分為四層:五種感覺、意識、思識和藏識,通過“意識+五種感官”向外認識世界,叫作智觀;通過“思識+藏識”向內認識世界,叫慧觀。文化的源遠流長、“三分世界”的世界觀和“內觀而非外求”的認知路徑,這三者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哲學內核。可見,與西方文化相比,中華文化的基因與西方具有很大的異質性。那么,在兩種文化具有異質性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如何在中國文化土壤里獲得生長的條件的呢?
(三)思想研究自身的分向演進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方式的創新
從觀念上層建筑自身發展的規律來看,當今時代思想研究本身也在發生重大變化。今天的“研究體系”本身出現兩種變化趨向:一是純粹學理性研究;二是應用性研究。前者可以稱之為“學術性研究”,后者則可稱之為“智庫性研究”。無論是學術性研究還是智庫性研究,歸根究底都是來自時代和社會的內在需求。這意味著,作為一種本質上也是“研究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同樣要受到這種趨勢的規制。在這個意義上,當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要想獲得巨大影響力,就需要認真關注和考慮這種研究自身的發展規律和趨勢。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華文化的深層契合:“大公無私”之理念
任何事物都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體。不同文化體系雖然各不相同,但也存在著共性,即,都在深層內涵上包含著這樣三個要素:世界觀,如何看世界;方法論,通過什么路徑認識世界;關于人和社會的基本認知,如何看人和社會歷史。如前所述,中華文化和原生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前兩個方面體現著異質性。這意味著,二者的共性存在于第三個方面,即關于人和社會歷史的基本認知。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人和社會發展的核心理念
在原生態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工業社會時代的分析中,“商品”是切入點,“資本”和“勞動”是分析的邏輯路向。以此為框架,清晰生成三條邏輯線索。一是從“人與自然的交換—人與人的交換—人與社會的直接交換”,看社會歷史的演變;二是從“私有—階級私有·國家所有—社會公有”,看社會形態的變革;三是從“私—公·私—大公”,看社會文明的進步。
首先,生產力發展的歷程表明,人類歷史的發展具有內在規律,人類社會最終會走向共產主義。從交換的角度,馬克思把人類社會分為“自然經濟時期”、“商品經濟時期”和“產品經濟時期”三個階段。自然經濟時期,人通過“種地”生存,生產力處于“填飽肚子”的水平,即“農業時代”;商品經濟時期,隨著種植的東西越來越多,除了夠吃的還有剩余,此時社會開始出現“種A想B,種B想A”這樣一種發展趨勢,由此,社會進入“A”和“B”相互交換階段,這就是“商品時代”;隨著種植的東西繼續增多,到達了像空氣和陽光一樣多之時,這時,人們不再關心“這是誰的東西”,社會按需要分配,這就是產品經濟時代。可見,人類社會的發展,從較早的“填飽肚子”,到后來的“A換B”,到未來的“按需分配”,這是一種客觀趨勢。這意味著,只要人類歷史不中斷,社會最終會進入共產主義階段。
其次,“私有—階級私有·國家所有—社會公有”,這是人類社會制度選擇演進的基本線索。“私有”,指的是在前商品經濟時期,生產力水平很低,只能解決人們的生存問題,主要生產資料只能抽象地“共有”或者歸小部分所有。在這里,因為原始社會階段的“公有”源于物質匱乏,其本質含義是:在一個特定群體內,如果有限的生存資料給了一部分人,其他人就要餓死,所以,為了大家都活著,這些資料只能共享。這是原始社會“公有”的事實。但是從邏輯上看,這種共享的前提是,必須在特定的群體內,而不是整個原始社會。而且深入一步說,這種共享也只能在特定群體內,因為該階段人們獲取生存資料的能力極其低下,即使有心也無力更無法讓這種共享涵蓋全社會。就此而言,原始社會的“公有”,既非商品階段上基于契約認定的“共同持有”內涵,也非未來產品時代的“人人都有”的意蘊。由此,整個前商品社會時期,人類社會的所有制,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私有制。
“階級私有·國家所有”,指在商品經濟時期,商品后面的主體——資本和勞動,分別選擇的兩種制度路徑。“資本”選擇的是私有制,“勞動”選擇的是國家所有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商品社會中,歸根究底只有兩種社會主體——有身外之物者(資本)和無身外之物者(勞動)。前者,在交換中使用身外之物(資本),后者只能使用身內之物(體力、腦力),因此,兩種主體的優勢具有根本區別。一般說,兩種主體之間的博弈具有如下必然性:圍繞著商品的分配,二者都想通過控制國家政權來控制商品的分配規則;如何控制,都通過自身的優勢。具體看,資本的優勢是“有錢”,它要通過“金權政治”的邏輯來設計制度;勞動的優勢是“有組織化”,它要通過建立一個嚴密的政黨體系來控制國家,進而通過國家控制生產資料,即國家所有。這表明,社會進入商品經濟歷史區間,制度的演進開始出現從“私”向“公”的突破。
“社會公有”,指的是在產品經濟時期,社會生產資料變成了社會所有制。其內涵是:因為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人人都不再對擁有生產資料感興趣,社會按需分配。而深入看,因為你需要,這就是你的;你不需要,這就是社會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所以,從內涵上看,產品經濟時代的公有制,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所有制。與“國家所有”這種商品經濟時代的公有制相比,這種公有制既實現了在邏輯上人人所有,同時在事實上也人人所有的內在要求,是一種充分和真正意義上的公有制。
綜合上述三個階段,可以看出,社會制度選擇從最初的“私有”唯一,經過了“階級私有·國家所有”雙存,一直會發展到未來的“社會公有”新的唯一,其內在邏輯體現為:“私—私·公—大公”。
(二)中華文化中的“人”和“社會”:基本邏輯
首先,“天人合一”與背后的“去我”理念。中華文化強調“天人合一”,“天人”即天和人的關系;“合一”即如何處理人與天的關系。關于這一問題,中華文化主要從兩個層面探索,即佛學的形而上研究和道學的超驗性研究(形而下)。佛學的邏輯是:心(非肉體也非精神,音譯為“阿賴耶識”,“心”是意譯)是實體性、根源性存在,內含三種機制,即“萬物本源機制”(能藏)、“記憶機制”(所藏)和“‘我’之意向性機制”(我愛執藏)。其中,“萬物本源機制”與宇宙萬物相通聯,是人能回到本源的基本通道。該機制處于心的核心部位。次外一層,是“記憶機制”,這一層不斷覆蓋核心層,由此造成人與本源連接的阻隔。心的最外層是“‘我’之意向性機制”,該層產生心的第一個衍生體—“意”(音譯為“末那識”,“意”是意譯)。在“意”中,內生兩種意向性,即“我執”和“法執”,相應分別產生兩個領域:“我執”產生“根身”即肉體,“法執”產生“器界”即自然界和社會。至此,佛學建構了一個獨特的對世界的觀察框架,即:心(本源)→意(末那識)→人(根身)→社會和自然(器界)。這一框架可從兩個角度理解:一是直接看,心是本源,人和自然界都是本源的次生結構,“本源”主宰“次生結構”。二是反過來看,人與自然、社會在本源上一體,人要想主宰自己和外部世界,必須回到本源。由此,佛學追問一個終極的、形而上的問題,即:人從哪里來的?人應該向哪里去?佛學的思路大致如下:人要想獲得主宰地位,就必須回到本源。如何回到本源?去除“我”,逐漸走向無我,這是一種“本源(阿賴耶識)←無我←去我←本源有我(末那識)”之路。
其次,“貴德,行善”與“忘我”理念。中華文化強調“貴德,行善”。所謂“貴德”,源于“道”和“德”兩范疇及其內在關系。“道”意指本源,“德”則是其在人身上的映現,具體展示為“仁義禮智信”五大要素。在道學范疇體系里,人體“五藏”(中華文化對“心肝脾肺腎”及其超驗功能的指稱)類似于計算機硬件,“五德”類似于這一硬件的軟件。要言之,道學中的“德”是一種實體因素。而在儒學中,“仁義禮智信”則是一種倫理規范,它的有無及多少決定著一個人的人格的健全與否及品質優劣。而在邏輯上,行善的本質是“利他”而“忘我”。
最后,“無私,大公”與“無我”理念。《道德經》說“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如此,源于道學對生命本質或者生命隱態規律的深刻認識。道學的邏輯是,元神聯通本源,回到元神首先必須抵制“消極”五神,修養“積極”五神。儒學強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佛學倡導“普渡眾生”,勸人“積德行善”。可見,無論儒道釋從哪個角度著眼,都最終指向人要無私,要追求大公。因為,無私的含義是“沒有我”,大公的本質是“沒有了我”,因此,合起來看,其理念是“無我”。
綜合中華文化的理念和原生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邏輯,不難發現,在關于人和社會發展的問題上,中華文化的深層理念是“去我—忘我—無我”,馬克思主義的深層邏輯是“私—私·公—大公”。在這里,兩種不同質的文化,其價值取向出現了交匯點,那就是:都追求“公共性”和“大公”,都認定“從小私走向大公”是一種客觀規律,其區別不過是,中華文化從生命的本質入手,認識到了這一規律;原生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則通過對“社會發展進程和邏輯”的系統性分析,發現了這一規律;而無論路徑如何差異,最終都是“殊途同歸”。這一特點,決定了原生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華文化土壤中具有很深的根基。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方式的創新:“研究什么”與“怎樣研究”
(一)研究什么
首先,從學術研究方面說,研究人的精神性需求,需要全面準確把握“精神研究的譜系”,并在不同譜系中進行自覺整合構建,形成具有特色和優勢的新研究模式。
其次,從智庫性研究來說,當前中國社會的發展性需求是一種非物化的需求,集中體現為制度和精神兩個層面的新需求;相應地,要展開智庫性研究,就要在兩個層面有所突破,即:如何認識當前中國的制度變革和當前中國的精神需求。
(二)怎樣研究
第一,在學術性研究層面,當今世界進入一個后工業社會時代,如何研究這個時代,應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前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決定著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走向。在這個意義上,把握當今時代特征,核心是界定全球經濟格局的新內涵。
第二,在智庫性研究層面,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完成了“生存性需求”向“發展性需求”的轉換;如何針對這一轉換展開對策性研究,應該成為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重要議題。“生存性需求”,內核是物質性需求。相應地,解決此類問題的本質做法就是進行生產性努力。但是,隨著“發展性需求”上升為主導需求,生產性努力就不能勝任了,因為“發展性需求”比“生存性需求”更高級、更復雜。這就意味著,如何解決新時期條件下的“發展性需求”,是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智庫性研究的基礎性、核心性問題。
總之,綜合上述“研究什么”和“怎樣研究”兩方面,關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方式之創新,我們認為,總的原則是著眼兩個向度、著手兩個問題:兩個向度,即學術和智庫兩類研究方式;兩個問題,即面對人的精神性需求的日益凸顯,要在學術層面構建馬克思主義精神研究譜系;面對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轉型,要在智庫層面展開兩個重大研究,即研究第五個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研究重大社會問題的深層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