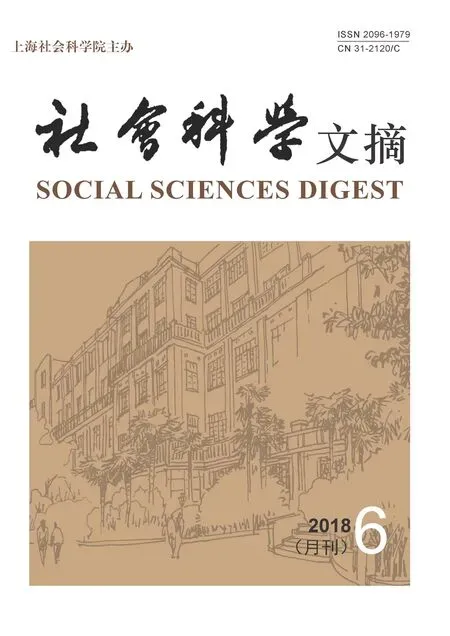國家理論:電影理論中的中國學派和中國話語
文/陳犀禾 翟莉瀅
引子:“中國沒有電影理論”
電影理論是一個長期被西方學派和話語把握的領域。記得20世紀80代中國開始編撰《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卷》的時候,時任編委會委員的程季華1986年曾經找我談過一次話。他告訴我,編委會在討論擬設條目時,對是否應該設立“中國電影理論”的條目發生爭議,時任編委會副主任、著名電影導演和理論家張駿祥認為:中國沒有電影理論。張駿祥當時作為電影局的領導、且學貫中西(張早年留學耶魯)、創作和理論成果累累,可以說是一言九鼎(當時《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卷》的主任雖然是夏衍,但因年事已高,張駿祥是主要負責人)。程季華作為中國電影史的專家,對此難以認同,他會后找到我并征詢我的看法。我當時剛剛從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系畢業,參加了鐘惦棐領導的“電影美學小組”,1986年初發表了《中國電影美學的再認識》,提出并闡釋了早期中國電影理論中的“影戲說”,主張它是可以和歐洲同時期先鋒派理論和蒙太奇理論相提并論的中國電影理論。所以,我對程季華明確說中國有電影理論,并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程季華立即確定讓我負責撰寫《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卷》中的“中國電影理論”條目。我后來找到我的同學鐘大豐合作(他曾對中國早期電影中“影戲電影”的形式和風格進行過深入研究),他負責撰寫49年以前部分,我負責撰寫49年以后部分。整個詞條約六千余字,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卷》第一版中正式發表。
從這一事例可以清楚看到,從文化大革命陰影中走出來的20世紀80年代,在文化思潮和理論上的一個重要傾向是向西方學習,西方的理論規范和話語深刻影響了那一代許多電影學者和藝術家。20世紀80年代這一開放過程在中國電影發展的道路上打下了它的烙印,推動了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發展,但是它也常常遮蔽了我們自身的理論傳統和學術話語。
中國經驗和中國話語
事實上,中國電影人從上個世紀初拍攝電影開始,就有了關于電影的理論思考,如20世紀20年代的“影戲說”,20世紀30年代的“軟性電影”理論。前者有濃厚的本土色彩,后者則可以明顯看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但是一些西方學者仍把它看作是一種中國的本土論述)。然而對當代中國電影產生了長期而持久影響、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在當代中國電影中最重要的理論話語則是“國家理論”。所謂“國家理論”,廣義上可以指一切對電影和國家關系的理論思考。具體地說,是指主張把電影作為一種體現國家意志和維護國家利益的電影本體論思考。它可以體現在電影批評、歷史研究和理論研究等各種形態中,但是其核心原則是把電影功能和國家利益緊密相連,發展和建構起一套從社會功能出發的電影本體論思考。
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毛主席在親自為《人民日報》社論撰文《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中,就為建立這樣一種電影觀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影片由從20世紀30年代就在上海從事進步電影運動的孫瑜導演,趙丹主演。影片一出來(1950年底),就受到當時報紙和媒體的一片好評。但是,毛主席顯然對《武訓傳》和影片歌頌的以傳播文化為己任的武訓其人持有不同的觀點,他質問道:(影片表現的)“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應當歌頌的嗎?”顯然,毛主席把對一部電影的批評放在千頭萬緒的國家大事的重要位置,絕不是偶然的。當時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當時的文化界、電影界對于新中國的文化和電影將要走向何方顯然并不清楚,許多人(包括《武訓傳》的創作人員)以為上海電影中的傳統將會原封不動得到延續,事實證明他們錯了。在毛主席看來,如果1949年以前的電影應該為打破一個舊中國服務的話,那么1949年以后的電影就應該為建設一個新中國服務。不認清這一點,就可能導致《武訓轉》所暴露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事實上,他當時對建設新中國的文化和電影已經有了一幅清晰的藍圖,并準備把它付諸實施。對《武訓傳》的批判可以看作這種改造和建設的第一步,也是1949年以后中國當代文化重大轉向的一個明確標志。
在批判《武訓傳》的文章中,毛主席明確表達了一種新的關于電影的思想,即要求電影服務于新的國家和新的社會,并提出了電影中應該如何展示新的國家形象:即歌頌“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反對“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和“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由此確立了以新的國家為核心價值的新中國電影的發展方向,也確立了以新的國家為核心價值的新中國電影批評和研究的典范。在隨后的年代中,中國的電影批評和研究通過批判許多當時認為不健康的電影,鼓勵在銀幕上塑造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新人,同時對理論和批評戰線以《電影的鑼鼓》和《創新獨白》為代表的一系列錯誤傾向進行了嚴厲的清算,為給新中國電影建立了一種以國家為核心價值的經典理論理清了思路。
中國電影思想中的國家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一度走向邊緣。那是一個“和戲劇離婚”的年代,一個影像本體論的年代,一個崇尚心理分析和符號學年代。80年代中后期“主旋律”概念的提出,為中國電影中的國家理論續上了香火。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社會和政治氛圍的變化,西方的后殖民理論恰當其時地被引進中國。王一川、張頤武等中國學者運用后殖民理論對當時紅極一時的第五代電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一時頗為引人注目,可以看作是國家理論在電影研究界的重新抬頭。隨著全球化不斷深化,民族國家意識的強化,國家理論終于在世紀之交全面激活,并在21世紀初的中國電影研究中重新走向中心,并形成以下幾大主題,如:
1.當下中國電影理論和批評中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
2.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電影民族性研究;
3.國家電影產業研究;
4.好萊塢電影在中國市場和對文化影響的研究;
5.中國電影“走出去”研究;
6.電影中的國家文化安全研究,等等。
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理論的傳統闡述相比較,新的國家理論也與時俱進,在關于電影的題材、電影的創作方法、電影的形式和電影的功能方面都有新的調整,如電影的功能,新的提法是“塑造國家形象”“傳播主流價值觀”和“增強軟實力”。在以上種種發展和調整中,國家理論的核心原則:把電影功能和國家利益緊密相連,沒有變。
國家理論和中國學派
相對于西方電影理論在早期注重于影像本體的研究(如關注于認知心理的影像美學、蒙太奇和長鏡頭理論等),1949年以后的中國當代電影研究在毛澤東電影思想的指導下發展起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電影理論:國家理論。國家理論是一個以國家為核心價值的電影理論和批評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在西方電影理論史中被置于核心地位的電影藝術形式和特性的研究則被置于工具和應用(形而下)的層面,而對于電影如何表達國家身份和服務于國家利益(當時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成為核心議題。這一理論建構在十七年時期達到了相當成熟的地步,而在新世紀以來的發展中所達到的的完整性和系統性是史無前例的,并涌現了大量成果,對當代中國電影創作實踐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巨大的影響。事實上,它比世界上在20世紀60年代世界電影思潮中提出的“第三電影”理論、民族電影理論和20世紀七八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后殖民理論等思考電影和國族關系的理論要早得多。
第三電影理論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形成了美蘇兩國為主導的全球權力體系。一些殖民地也擺脫了殖民控制,獨立成為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了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在此背景下,1950年法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人口學家與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這一概念是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第三等級”(即平民)提法為根據而衍生的。據此,“第三電影”就是指“第三世界國家即工業上欠發達的國家部分的電影生產”。這一概念首先出現在1969年3月的古巴電影期刊《Cine Cubano》的一篇對阿根廷電影團體“解放電影”的采訪報道中,該團體認為“第三電影在陳述上和意識上都是革命的,它會發明一種新的電影語言,以便創造一個新的意識和新的社會現實”。隨后弗爾南多·索倫納斯和奧克泰維爾·杰提諾的重要文獻《邁向第三種電影:發展第三世界解放電影的筆記和實驗》(1969)將電影分為三類:“第一電影”為好萊塢電影;“第二電影”是歐洲藝術電影,是“第一電影”的另一條出路;而“第三電影”則是“在革命性開創中邁向一種立于體制之外,與體制對抗的電影”,是一種“解放電影與游擊電影”,一種“去殖民化文化”,是一種革命電影。總而言之,第三電影理論從早先更多關注影像本體及創作者的心理分析,轉向對民族國家話語建構的關注上來。
后殖民主義的學術思潮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關注被殖民國家在后殖民時期在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的“國族身份”。后殖民主義理論在學術界影響力巨大,愛德華·薩義德所著的《東方學》(1978)是這一領域的經典著作。薩義德將研究目標指向了被西方學術界邊緣化的東方或第三世界,并且他“使用了福柯的話語概念和權力-知識連結的概念來考察西方帝國主義的權力和話語如何建構了一個程式化的‘東方’的方式”。他認為“西方和東方之間存在一種權力關系、支配關系、霸權關系”,并且東方“可以被制作成、被馴化成‘東方的’”,還時常扮演著相對于西方的“他者”的角色。可見,“東方”除了指涉其地理位置,還蘊藏了強烈的政治與文化內涵。總之,在薩義德的理論中,在意識形態上制造代表“理性”的歐洲和代表“非理性”的東方是同時進行的,東西方的表征被鎖定在相互連接但并非對等的權力關系之中。后殖民理論也常常被借用成為電影批評范式之一。薩義德就曾集中以西方電影中的阿拉伯人形象進行批判,形成了獨特的、具有電影理論視角的話語。
在學術主題上,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第三電影”理論和20世紀七八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后殖民理論都著重思考了電影和國族的關系。但是在學術品格上,后殖民理論更為精致和更注重闡釋性,對后殖民文化的混雜性、“模仿”和“協商的第三空間”津津樂道;而第三電影理論既注重闡釋性,也富于實踐性,試圖給發展中國家的民族電影指出方向,具有一種建設性的品格,它和中國的國家理論比較接近。這可能和理論話語建立的時代相關,因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一個世界革命風起云涌的年代,而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世界局勢則相對平穩。但是,第三電影理論由于對好萊塢敘事美學取絕對的排斥態度,反而在實踐中難以為繼,走入了尷尬境地。而中國的國家理論在藝術風格上則強調大眾化和人民性,并沒有陷入精英主義美學的死胡同。
從時間上看,毛澤東的電影思想遠早于第三電影理論,是一種具有原創性和生命力的電影思想,其理論資源至少還可以追溯到20世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系統闡述了文藝“為什么人”和“寫什么”的問題。毛澤東在革命最艱苦的抗戰年代來談文藝當然絕不是“為藝術而藝術”,而是為了革命和政權。更早還可以追溯到列寧關于電影的論述。列寧早在建立俄國蘇維埃政權時就說過:“你們必須牢記,在一切藝術中,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電影”。所謂“最重要”,當然是指電影對無產階級革命和政權(國家)的重要性。除了列寧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他們的革命思想也對藝術的國家理論有重要貢獻。
國家理論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資源則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哲學。首先,中國傳統文化哲學的學術品格歷來強調經世致用,有一種“功能主義”的基因(這里只是就方法論的意義而言,并非指西方哲學中的“功能主義”),接近實用主義。例如中國的儒學,強調“入世”和“功業”。中國學術對物質世界的思考也常常貫徹了一種功能主義的路線,如中華醫學中所謂的“腎為先天之本”,其中“腎”的概念主要是一種功能性系統,而不是西醫解剖學意義上的“腎臟”。而當代最著名的例子則莫如鄧小平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這里,對“好貓”的定義并不是從解剖學(生理結構)的角度出發,而是從現實功能的角度出發。其次,中國文化歷來有“文以載道”的傳統。中國早期的電影理論,如“影戲論”和“軟性電影論”也貫穿了這種文化基因。這一以功能為導向的電影本體論思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得到了延續,并整合了新的理論資源,發展成為一種新的“國家理論”。
結語:國家理論和中國夢
今天,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我們面臨著在中國文化和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中,創建中國學派和中國話語的任務。我們以為,中國學派不可能憑空建立,具體到電影理論和批評,中國電影理論和創作批評中的關于國家理論的歷史經驗和當代成就是建立中國學派的寶貴資源。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文藝要服務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創作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習近平的講話繼承和發揚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精神,并對今天新時代文藝的性質進行了系統闡述。“中國夢”思想作為國家建設的宏偉目標將對當下中國電影研究中的國家理論建構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剛剛過去的十九大上,習近平主席又再次強調社會主義文藝需“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并且以“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為目標。其中,“國家”的主題躍然而出,并增加了一種全球化的視野。
基于以上歷史和現實,我們認為國家理論應該成為電影理論和批評中的中國學派和中國話語的重要建設課題之一。當然,作為一種理論話語,國家理論強調體制中心和黨的引領,未來可以在其內含的人民性的內涵方面作進一步闡述,強調中華民族文化的立場和主體性,這樣更有利于中國學派介入和形塑世界文化的新格局,使中國學派(象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一樣)成為當代世界文化版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向心力的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