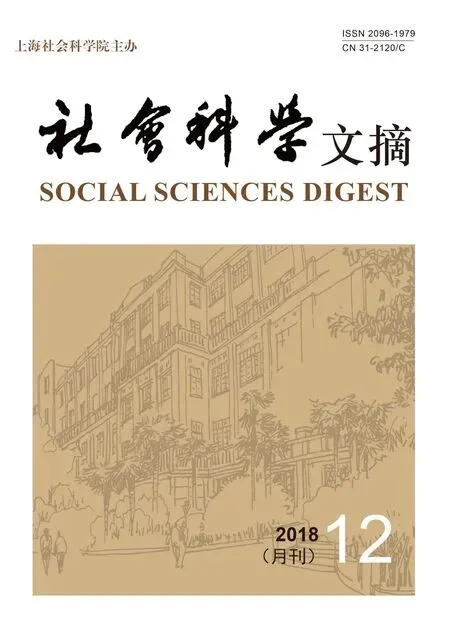中美外交互動模式的演變:經驗、教訓和前景
外交互動模式是特定時期國家間關系的產物,是對一定時期內國家間形成的共同認可和相對固定的交往方式的概括和總結。中美建交40年來,隨著國際形勢和雙邊關系的發展,中美外交互動的模式不斷更新和演變。
溫故而知新。回顧中美外交互動模式的演變,探討其對兩國關系的積極作用,對于兩國共同努力克服中美關系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推動雙邊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在簡要梳理中美外交互動模式演變歷程的基礎上,重點分析21世紀以來中美外交互動的新特征,并探討其在中美雙邊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文章最后部分結合中美關系面臨的新形勢,就外交互動模式的發展提出若干思考和建議。
中美外交互動模式的演變歷程
外交互動往往與雙邊關系同步演進。以1979年1月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為界,中美政府間交往經歷了從相互試探、秘密溝通向經常性、多層次、全方位互動的演變。建交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中美互動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機制化磋商已成為當前中美外交互動最主要的特征。
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之前,中美互動主要經歷了三種形式:一是從1955年到1970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二是在亨利·基辛格博士和理查德·尼克松總統訪華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三條秘密的信息傳遞渠道,即“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渠道”“巴黎渠道”“聯合國渠道”;三是由尼克松總統訪華所開啟的兩國領導人面對面的交流,以及中美兩國在對方首都互設聯絡處開展直接的官方交往。
吉米·卡特總統上任后,積極推進中美建交談判。1978年12月16日,兩國共同發表《中美建交公報》,決定于翌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受卡特總統邀請,鄧小平副總理訪問美國。中美外交互動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鄧小平訪美期間,中美兩國簽署科技合作協定、文化協定及建立領事關系和互設總領事館的協議。根據兩國領導人的共識,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也于1980年正式成立并舉行首次會議,成為協調兩國經濟關系的重要機制性框架。
20世紀80年代,羅納德·里根政府時期,兩國克服了因美國國會通過《與臺灣關系法》所引發的關系緊張。1982年8月17日,兩國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即《八一七公報》)。美國重申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八一七公報》與《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共同構成了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這一時期,中美外交互動進一步發展。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總統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里根成為中美建交后首位在任時訪華的美國總統。1985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訪問美國。兩國實現了第一次元首互訪。
受1989年風波的影響,中美高層交往一度中斷。1993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西雅圖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與比爾·克林頓總統舉行了首次會晤。江澤民強調中國政府對美關系堅持“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方針。克林頓重申美國信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原則。這次首腦會晤推動中美關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其后,1997年和1998年,中美兩國領導人成功實現了互訪。
進入21世紀后,中美關系日益緊密,兩國交往向各層次、各領域拓展。這一時期,隨著中美兩國高度相互依賴,中美關系越來越具有全球性的影響力,兩國間的外交互動也不斷發展。這突出地表現在首腦會晤頻繁,對雙邊關系的引領作用更加突出,高層對話機制建設不斷深入,以及多邊領域合作成為雙邊關系的重要推動因素。中美外交互動模式的新發展,既反映出兩國關系邁向新的高度,也表明中美兩國在致力于維護雙邊關系穩定和促進國際和平與發展的過程中,為探索有效的交往方式所做出的努力。
中美外交互動模式的新發展
(一)首腦外交作用更加突出。
在中美關系中,首腦外交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國家元首對雙邊關系的戰略引領。衡量首腦外交在中美外交互動中的地位,可以考察三個方面的指標:一是首腦互動的機制化水平;二是首腦外交對雙邊關系發展方向的規劃能力;三是首腦外交討論的議題范圍。
首先,中美首腦外交更加常態化和機制化。中美首腦會晤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越來越呈現出常態化和機制化的特征。冷戰結束后,中美首腦會晤頻繁,尤其是兩國積極利用參加多邊會議的機會舉行雙邊會晤。1993至2000年,克林頓政府時期,中美兩國元首共舉行11次峰會。2001年至2008年,喬治·W·布什政府時期,中美兩國元首會晤更加頻繁,總數達到17次。從2009年至2016年,貝拉克·奧巴馬政府時期,中美元首保持經常性會晤,共舉行18次峰會。2017年,唐納德·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的第一年,中美兩國元首順利實現互訪,并在G20漢堡峰會期間舉行了雙邊會談。在美國總統就任首年便實現中美元首互訪,是中美外交史上的第一次。
其次,國家元首對中美兩國關系發揮著戰略引領作用。元首引領作用突出地體現在其對兩國關系發展方向的戰略規劃上。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期間,與奧巴馬總統就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達成共識。2012年2月,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在同奧巴馬會晤時,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翌年6月,習近平以主席身份再次訪問美國與奧巴馬總統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舉行會晤時,明確闡述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核心內涵。元首會晤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為未來中美關系的發展確立了目標和方向。2017年美國政府更迭一度引發中美關系的震蕩。2017年4月,中美兩國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實現了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的首次會晤。同年11月,特朗普總統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
第三,中美首腦外交的議題不斷豐富,更具全球性特征。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關系具有鮮明的全球性特征。早期的中美首腦外交主要集中在雙邊關系,如臺灣問題、經貿關系、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進入21世紀后,中美首腦會晤的議題不斷豐富。在雙邊議題之外,反恐合作、朝核問題、伊核問題、氣候變化、能源問題、國際治理體系改革等全球和地區性議題越來越多地成為兩國首腦互動的關注點。2011年中美首腦華盛頓會晤后發表的《聯合聲明》,還首次以正式文件的方式提及歐洲,表達了兩國對歐洲經濟和主權債務問題的關注。首腦外交討論議題的拓展體現了中國在全球事務中影響力的上升,也反映出中美關系對世界的重大影響。
(二)中美對話機制建設不斷深入
隨著中美兩國間需要處理的問題越來越多,合作的領域越來越廣,在首腦外交層面之外,兩國也加強了在戰略和工作層面的互動,并努力將這種互動機制化。目前,中美之間已經建立很多政府間對話和溝通的機制。這些機制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科學和技術、教育、文化、反恐、核不擴散及地區和國際事務等廣泛領域。
首先,中美高級別對話機制具有較強的延續性。美國方面雖歷經多次執政黨輪替和政府更迭,中美高級別對話機制始終得到繼承和發展,成為中美兩國政府重要的交流平臺。2005年8月在北京舉行的中美戰略對話是兩國之間第一個高級別定期對話機制。2017年4月,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決定進一步改進原有的雙邊對話機制,新建立了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等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其中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系首次創建。與之前的中美高級別對話機制相比,新的對話機制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一是提升了安全對話的分量。2011年,兩國在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創設了戰略安全對話,由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參加。此次調整后,軍方代表提升至國防部長/參謀長級。二是突出了經濟對話的地位。此次改革后,經濟對話成為一個獨立的機制,并延續了之前的中方由副總理參加的做法。三是積極應對新興議題。網絡安全近年來成為中美雙邊關系中的一個熱點議題,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的建立,有利于兩國加強分歧管控,防止個案干擾中美關系大局。四是重視人文交流的積極作用。此次改革將之前的人文交流高級別磋商機制提升為與其他三大對話機制并行的社會和人文對話。這顯示出兩國對人文交流的重視。對話內容涉及教育、科技、環保、文化、衛生、社會發展、地方人文合作等合作領域。
其次,中美對話機制具有豐富的層次性。中美高級別對話機制具有明顯的機制“帶動效應”和整合統領的功能。中美商貿聯合委員會、中美關于全球和地區議題的次級對話機制,以及中美關于國防和防衛政策的磋商平臺等一系列原有和新建的雙邊磋商機制,履行著落實高級別對話具體成果的職能。例如,近年來,兩國建立了關于亞太、非洲、拉美、中東、中亞及南亞等地區事務的對話磋商機制,還建立了中美投資論壇、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中美環境合作聯合委員會、中美海事安全對話等一系列專業領域的對話機制。此外,中美還加強了地方合作機制,建立了省/州、地方乃至社區層面的機制性聯系。例如,2011年啟動的中美省州長論壇旨在深化中美省/州級官員之間的聯系。
再次,中美對話機制的積極作用明顯。實踐表明,中美對話機制有助于兩國通過信息分享,降低不確定性和管理相互預期,從而為兩國增進互信、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提供平臺和渠道。定期開展對話還有助于兩國將具體問題上的分歧限制在特定的磋商框架之下,防止爭議擴散和干擾兩國的總體關系。此外,經常性的面對面交流,還有助于決策者和各級業務部門發展良好的私人關系,并最終轉變為互利的工作關系。
(三)多邊領域合作是中美關系發展的推動因素
一方面,全球性議題成為中美合作新的增長點。中美在多邊機制就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進行磋商,不斷豐富兩國間的外交互動,推動雙邊關系向縱深方向發展。奧巴馬政府時期,中美合作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合力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合作對中美雙邊關系的意義還在于,它為兩國探索在全球治理領域的合作提供了模板,也為中美通過合作共同解決雙邊關系中存在的問題提供了動力。
另一方面,多邊合作機制成為中美外交互動的重要載體。多邊組織為中美互動提供了國際規則和磋商機制,從而使兩國關系處于一定的框架之內。未來,兩國應在這一共同決定的指引下,積極開展多邊領域合作,努力促進全球治理體制機制完善。
新使命和新要求
新時期,中國積極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美兩國應積極深化合作,妥善處理兩國間的敏感問題,建設性地管控分歧。中美外交互動模式應當積極適應這一新的使命,為促進兩國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第一,繼續發揮元首外交的戰略引領作用。實踐證明,元首外交對中美關系健康穩定向前發展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在中美關系未來發展中,兩國元首的政治決斷和歷史擔當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突出地反映在兩國元首對中美關系發展方向的戰略規劃。未來,中美兩國應繼續推進元首互動的常態化,加深對彼此戰略關切和核心利益的理解,切實保證兩國元首對中美關系全局的統籌和駕馭。
第二,不斷充實和豐富中美外交互動的內涵。在雙邊關系層面,中美兩國應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關切的基礎上,積極探討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中美還應就網絡安全等新興議題展開經常性對話,防止這些議題演變為戰略懷疑的新話題。在亞太地區層面,兩國應加強在亞太地區框架建構方面的互動,共同建設開放、包容的地區合作機制,避免形成排斥對方或針對對方的封閉性安排。在全球和地區事務層面,中美兩國應加強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機制內的溝通和協調,商討應對全球性挑戰之策,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轉變。
第三,充分發揮高級別對話機制的作用。中美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是根據兩國元首的共識建立起來的,對兩國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具有積極作用。未來,中美兩國應努力維護高級別對話機制的運行,發揮好高級別對話機制的作用,并切實提高對話機制對解決兩國現實問題的效能。未來,兩國應將“議題導向”和“結果導向”作為推進高級別對話機制建設的努力方向。
第四,努力加強中美第二軌道外交的建設。在中美交往日益復雜、多元的今天,各種民間交流機制有益地補充、配合和推動著官方交往。第二軌道外交因其獨特性,能夠成為中美外交互動中的新亮點。
結語:互動模式的再思考
回顧中美建交40年來外交互動模式的演變,我們清晰地認識到,國際形勢和雙邊關系的發展推動中美兩國不斷創新互動模式,進而使兩國關系保持總體穩定和不斷發展。同時,我們也觀察到,任何外交互動模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都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并客觀上依賴于中美兩國共同的努力。當兩國重視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并努力以建設性的思路化解兩國間的矛盾和分歧時,外交互動往往更加順暢,效用更加容易得到發揮。相反,兩國間正常的外交互動機制就可能會遭到破壞,其效用也難以充分發揮。
隨著形勢的變化,中美關系發展面臨新的不確定性。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推行單邊主義,在中美關系上擱置已有的交往機制或在商定的問題上出爾反爾,在貿易問題上實施霸凌主義,導致中美經貿摩擦升級;在臺灣問題上出臺所謂“臺灣交往法”,直接挑戰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在南海問題上,無視中國核心利益且炫耀武力。所有這些都對兩國關系形成新的挑戰。在中美關系的發展中,外交互動往往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兩國進行溝通和對話越多,就越可能能避免出現消極和負面的誤判。
為此,面對更加復雜、多元的雙邊關系和更具挑戰性的國際環境,中美兩國應共同努力加強外交互動機制建設,將之作為促進雙邊合作和建設性管控分歧機制保障。在這一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美國必須放棄冷戰思維和改變把中國作為主要競爭者的“對手”意識,只有根本立場的轉變,才能使現有機制發揮預定作用,還能使兩國在新形勢下形成新的有效互動模式。這是個長期的歷史進程,勢必經歷多次考驗和反復后才能走上正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發揮元首外交對兩國關系的戰略引領作用,確保中美關系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解鈴還需系鈴人”,特朗普政府到底能否認清世界大勢和中美關系的內在邏輯,將是下一階段中美關系交往的模式和實質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