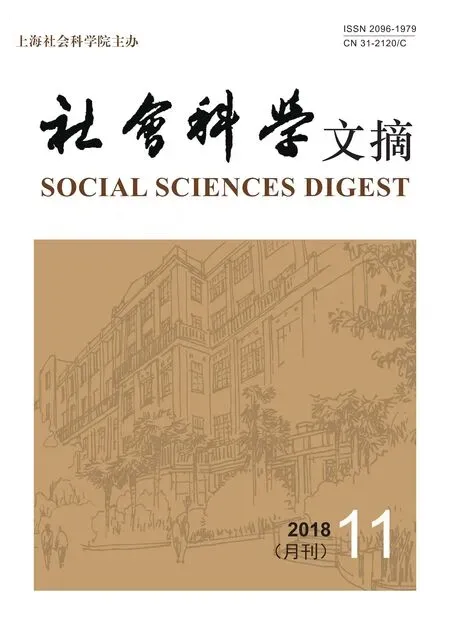改革開放40年中國憲法學的回應與貢獻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憲法學在基本原理、憲法制度、基本權利以及國家權力運行等領域取得了積極進展,其理論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從1978年憲法頒布到整個20世紀80年代,憲法學者為改革開放的正當性與新憲法秩序的構建而作出的貢獻尤其值得認真梳理與探討。
探尋改革的理論邏輯
在80年代,中國社會的核心詞是“憲法”,1982年憲法的頒布以及82年以來的憲法宣傳與理論探討豐富了充滿活力但急需理論依據的改革現實。
當時的憲法學界的主要工作是:設計符合中國實際的憲法體制;把握新憲法的精神與構造;為新憲法的實施做好理論貯備等。1985年以前學界的主要任務是普及、宣傳憲法知識,傳播憲法觀念,提高全社會的憲法意識。從1985年以后,學界從知識轉向憲法原理的理性思考,把研究視角轉向憲法學基本理論、基本原理與基本制度的研究,即從知識的普及轉向理論的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于國家始終處于建構與轉型期,憲法學界沒有充裕的時間做體系化的基礎理論研究,過去的憲法生活又缺乏穩定性,基于憲法文本的理論研究受到限制。到了80年代中期,基于1982年憲法的全面修改與憲法秩序的建立,社會發展需要憲法理論的解釋與建構。可以說,80年代是中國憲法學尋求自我、探尋理論邏輯的時期,出現了迄今為止仍然保持學術影響力的學術精品。
同時,由于改革開放政策的啟動,對學術的寬容與開放的立場,成為雙向互動的機制。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大量的實踐問題要求憲法學理論的回應與創新,而新的憲法理論又為改革實踐的發展提供新的學術活力,深化改革開放。這一時期,中國法學界關注變革中的世界,為學習世界有益的法制經驗提供平臺與途徑。在開放的背景下,學術研究更加自由,學術精品不斷出現,不斷為國家發展提供活力與動力。
重建憲法秩序
在80年代,特別是從1978年憲法向1982年憲法的轉型過程中,憲法學者們關注憲法秩序的建構與憲法實施。從1980年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到1982年12月4日憲法的通過,在長達兩年多的修改憲法時間里,憲法學界的著名學者直接參與修憲過程,多數學者參與各種形式的討論。這是整個80年代具有標志性的憲法實踐與憲法學研究。王叔文、許崇德、肖蔚云、何華輝、吳家麟、廉希圣等老一輩憲法學家親自參與了憲法修改過程,為民族的未來和人民幸福生活設計憲法體系與制度。從憲法結構到內容,從制度設計到條文的安排,憲法學界的參與是廣泛而深入的,尤其在部分重大制度的設計中,憲法學者提供了十分豐富的理論支持,確實凝聚了一批憲法學者的心血。
從1982憲法頒布到1983年8月期間,出版了13本介紹憲法的小冊子,發表了400多篇文章。從1982年到1999年,共發表憲法學論文總計約2900篇,出版專著226本。這一時期憲法學研究的基本特點是,圍繞著1982年憲法進行學理的闡釋和分析,宣傳與解釋憲法精神與規定,力求以憲法為紐帶凝聚共識,增強人們對“新憲法秩序”的信任與期待。
根本法地位
隨著人們對憲法生活的期待,如何建構具有共識性的憲法概念是當時急需回答的實踐問題。為了回應實踐的需求,這一時期憲法學界探討了憲法概念、憲法地位以及憲法效力等基本原理。
在1982年憲法的實施中,學界強調憲法應有的“法律性”,力求合理平衡政治性與法律性價值,提出以法律性為基礎的開放性、綜合性的憲法概念。如1982年出版的《政治與法律叢刊》將憲法定義為“規定國家根本制度,效力高于普通法律的法律”。許崇德認為“一個國家有很多法律……憲法只是其中一種,但是憲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居于根本法地位”。可以說,塑造憲法的法律性,以法律性重新解釋憲法概念是當時基本的學術傾向。
何華輝、許崇德在《我國新憲法同前三部憲法的比較研究》《憲法與民主制度》等論著中闡述了如何理解憲法的問題。如在《憲法與民主制度》一書中,他們將民主納入憲法概念之中,認為“憲法是以民主事實為依據,并隨著民主的發展而發展……社會主義憲法是最高類型的憲法”。針對憲法形式與實質問題,許崇德認為,憲法是實質與形式的統一,要從根本法意義上解釋80年代的憲法。
從總體上看,80年代憲法學研究強調憲法的法律屬性,強化其實效性,這一思考在進入90年代得到了進一步深化,對于解釋和研究新憲法秩序產生了積極影響。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爭鳴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學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開展了“人治”與“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民主與法制”等問題的討論。這些學術問題涉及憲法的基本原則與理論,對于尋求改革共識具有重要意義。憲法學者積極參與討論法學界重大理論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討論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這場討論的意義在于,突破50年代后期開始形成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問題的研究禁區,在“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問題上形成共識,并對“立法上是否平等”問題爭鳴,推動整個法學研究。討論的焦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包括立法平等?”當時形成了兩種觀點:一是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包括司法方面,也包括立法方面;二是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專指司法上的平等,立法上是不能講階級平等的。
蔣碧昆等在《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文中認為,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則的含義應該是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與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能從概念上等同起來;張光博在《也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文中認為,1954年憲法規定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與資本主義的提法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我國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因此詞句雖然相同,實質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這個原則包括三個方面內容,即公民在立法上的平等、執法上的平等與國家適用法律上的平等;程輯雍在《社會主義法制的平等原則不能割裂》一文中針對“立法上階級不平等”和“司法上階級平等”觀點,明確提出“任何不同社會的法,其制定與實施是統一的,立法與司法是統一的”。這場學術討論在80年代初產生了重要學術影響,體現一種寬松、自由而民主的學術氛圍。從1979年到1980年圍繞這一問題發表的論文和文章就40多篇,是一場改革開放前期的學術啟蒙。
改革的憲法界限
整個80年代的中國社會面臨著新的挑戰,特別是如何處理改革與憲法的關系成為焦點問題。當時,在憲法與改革問題上,出現了三個問題,即改革入憲問題、憲法規范與社會發展沖突的解決方式以及改革的憲法界限。80年代出現的“關于憲法無形修改”的討論集中反映了改革時期如何平衡憲法價值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
1984年中共中央公布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學界開始考慮如何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憲法依據。但憲法規定與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并不一致,特別是在“計劃經濟”的理解上出現不同的看法。有學者提出“無形修改”觀點,認為“即在不變動憲法典條文,而更換其中某一條或條文中某些詞語句的內容,使憲法的某些規定具有新的含義”,由此判斷“憲法第15條的計劃經濟規定已因該決定得以修改,這種修改并非違憲,而是為了使憲法保持科學性,更加符合現實的一種方式”。“無形修改”的看法引發學界的討論,有學者認為政治上的權威、法律上的權威與理論上的權威是不同的,無形修改的看法不利于憲法權威的樹立,現實上有危害性。在改革初期出現憲法與改革問題的討論是正常的,體現了學界在改革中如何保持憲法權威與界限的一種學術“焦慮”。1988年對1982年憲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形成了兩條修正案,從憲法實踐上結束了爭論,但對憲法變遷的探討仍未停止。
當時,憲法與改革涉及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選擇憲法修改方式。面對80年代改革的現實,憲法學界積極尋求規范與現實相對平衡的方式。1988年2月27日,為了適應改革的需要,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研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向七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修改憲法案時,彭真副委員長提出:這次對憲法的修改采取修正案的方式,這是美國的修憲方式,比法國、蘇聯和我國過去的修改憲法辦法好。彭沖副委員長和王漢斌秘書長對實行這種修憲方式作了說明。采取這種修改方式,得到了委員長會議和常委會會議全體組成人員的贊同。從此,這一修改憲法方式被肯定下來,1993年、1999年、2004年與2018年的憲法修改均沿用了修正案模式。采用憲法修正案是憲法修改方式的重大創新,體現了憲法學研究的開放性。
憲法監督
80年代是改革開放政策全面實施的10年,1982年憲法規定“今后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越是加快改革開放步伐,越要注意維護憲法的權威與尊嚴。因此,如何使憲法保持生命力,有效預防和解決違憲現象是全社會,尤其是憲法學界特別關注的問題。
1982年憲法修改時,憲法學界的多數學者希望吸取文革的教訓,設立專門的憲法監督機關,以加強憲法監督。許崇德在《憲法修改十議》中提出憲法的監督和實施問題,認為這次修憲“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誰有權解釋憲法?二是由誰監督憲法的實施,是否需要設專門機構,給以特定權限,按法律程序開展監督?”此后憲法學界發表了大量的憲法監督、憲法訴訟、憲法實施相關的論文和學術著作。代表論文有:胡錦光《論憲法監督制度》、于浩成《一個極其重要的建議:關于憲法實施的保障問題》、陳云生《現代憲法保障問題及其發展趨勢》、許崇德《經濟體制改革與憲法實施》、王叔文《我國憲法實施中的幾個認識問題》、蔡定劍《我國憲法監督制度探討》等。
1985年第一屆憲法學年會上,學者們就討論了在中國如何實施憲法問題,表現出對中國實踐問題的極大關切。今天,中國憲法學仍然面臨著如何建構憲法監督體制機制的問題。整個80年代,學界為憲法監督的制度建構與理論的體系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積累了豐富的學術成果。
憲法釋義
憲法解釋學的形成體現了我國憲法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和深化。1978年憲法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1982年憲法再次確認這一憲法解釋體制。由于當時環境的影響,80年代學界對憲法解釋體系化的研究是不夠的,但對憲法條文的釋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界的學術自覺。
從1982年到1985年學界進行憲法的釋義、宣傳與介紹的工作,對憲法知識的啟蒙發揮了積極作用。經歷了長達10年“文革”的國人期待著人的尊嚴與自由,希望穩定而安全的法律秩序。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賦予中國憲法學深沉的責任與使命感,成為民眾的生活方式。或許歷史造就了中國憲法學的生活觀與哲學,它除了理論詮釋功能外,還擔負著信仰與信念的塑造功能。因此,這一時期的新憲法的宣傳,應理解為憲法生活化的過程,其作用不僅僅是知識的普及。張慶福編的《憲法學研究述略》一書是最早以學術綜述的形式對憲法學進行專題性研究的專著,對80年代憲法理論研究產生重要的學術影響。
為宣傳憲法精神,學界以釋義、解釋為中心開展學術工作,客觀上起到了以條文為中心的憲法解釋功能,可以說它是憲法解釋學或者釋義學的初步思考。1983年出版的司法部統編教材《憲法學》在談到憲法概念時,將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結合起來進行說明,提出憲法解釋的必要性在于:一是對具體條文的涵義進行權威性的解釋;二是確認某項法律是否違反憲法,以維護憲法的尊嚴,保證憲法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效力。該教材同時認為,解釋權是“憲法條文和法律條文的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補充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或者用單行法加以規定”。
可以說,沒有80年代對憲法文本或者條文的解釋性宣傳,就不可能出現今天具有共識的解釋學方法論。當時學界在憲法文本問題上也處于價值與事實之間的沖突,既注釋文本又懷疑文本,承受了學術與現實政治的雙重壓力。如今解釋學成為中國憲法學的基本方法論,雖然需要進一步體系化,但其理論探討源于80年代的學術探索。
教材體系
這一時期憲法學的重要使命是適應改革開放的需求,為國家制度與法律秩序提供合法性。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性,80年代的憲法學還沒有完全擺脫“意識形態化”,主要圍繞“以秩序為本位的制度”建設,學術的積累主要體現在憲法學總論與教材建設上。全國各地法學院的恢復與法學人才培養的客觀需求使憲法學更加注重知識的梳理與傳授,憲法學整體的知識創新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
吳家麟于1983年主編的高等學校法學教材《憲法學》,成為20世紀80年代憲法學的代表性成果,奠定了新中國憲法學教材的基本框架與體系。
在比較憲法學與外國憲法學研究方面,為了適應開放的政策,80年代憲法學界率先介紹、翻譯與研究外國憲法與比較憲法,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特別是以1982年憲法的修改為契機,憲法學界注意以比較的方法研究各種憲法現象,自覺地把中國憲法體制置于世界宏觀的憲法體系之中,尋求憲法的公共性價值。代表性著作有:羅豪才、吳拮英著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和政治制度》,何華輝著的《比較憲法學》等。
198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和政治制度》作為一本外國憲法的教材,八章內容基本囊括了當時外國憲法的基本內容,即歷史、體系與運行。但這本書并沒有以國別憲法介紹為體例,而是在每章內容中分別介紹相關國家的制度,并做比較,使學生在了解一國國家具體憲法制度的同時具有比較法視野,獲得憲法知識的整體感。因此,這本書既作為外國憲法教材,也可以作為比較憲法的教材,是80年代具有學術影響力的比較憲法教材之一,在外國憲法理論的介紹與研究方面具有學術特色。
1987年陳云生翻譯出版了《成文憲法的比較研究》,這本書提供了憲法學研究的新信息,即定量的分析與實證研究。該書的銷量達到13000多本,創下80年代專業書籍的記錄。作為新中國第一本系統的比較憲法學譯著,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該書之所以得到學界的關注與廣泛引用,也許是作者提出的學術觀點引起中國憲法學者的興趣,即“我們主要目的是更充分地了解憲法說了什么,同時通過收集信息和將之系統化,對成文憲法這一現象本身更為深刻的洞察。我們只想讓憲法說話”。從這本書產生的學術影響看,80年代學界已開始關注憲法學方法的多元化與實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