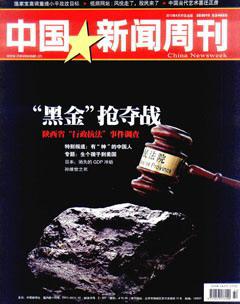“涉黑”資產的罪與罰
王全寶

8月中旬,公安部發出全國打黑除惡專項斗爭第八批涉黑案件掛牌督辦通知,對涉及全國22個省、區、市的52起重大涉黑案件掛牌督辦。同時,公安部明確要求,要依法查處全部涉黑資產,徹底摧毀其經濟基礎。
在8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首次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特征被明確寫入,同時,該修正案還增加了財產刑,除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處以自由刑外,還可以并處罰金、沒收財產。
一直以來,無論在學界還是實務界,對于“涉黑”資產的界定存有爭議。有專家提醒,面對黑惡勢力公司化運作的新形勢,打黑必須掃除支持其發展壯大的物質基礎,不過在《物權法》實施已3年,私人合法財產受保護的今天,對待“涉黑”資產要分清“非法”和“合法”的界限,避免打擊擴大化。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黃太云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修正案將明確這些模糊問題,但一般要三審才能通過。
公司化運作
今年2月28日,據重慶官方公開的統計數據顯示,自2009年開展打黑除惡專項行動以來,共抓獲涉黑涉惡人員3348人,立案查辦涉黑團伙案件63個、涉惡團伙案件235個,凍結、扣押、查封涉案資產24億元。
但隨著判決生效,如何處置涉案資產就成了問題。如何厘清這些身涉黑、白兩道,既從事商業經營又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嫌疑人所積累的巨額財產的非法與合法,就成為重慶打黑運動后期的工作重心。
關于這個問題,幾年前就被中央所關注。從2001年4月開始,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嚴打”整治斗爭。兩年后,有關部門在進行“打黑”總結時發現,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聚斂了相當的血腥資金后,開始開公司、辦企業,把罪惡之手伸向經濟領域。
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對劉涌案經再審后作出判決: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劉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與其所犯其他各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一波三折的劉涌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終于落下塵埃。但人們對劉涌案的關注遠未結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置劉涌名下的7億巨額資產。
當時某媒體一篇《劉涌人生最后84小時》的報道稱:劉涌在接到最高法院再審通知后曾說,他給家里掙下的家業,夠老婆和孩子花上幾輩子了,他也算是心安了。
公安部第四研究所預防犯罪研究室原副主任、現任北京市公安局研究室副主任龍顯雷曾在《中國新聞周刊》撰文指出,由于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成立公司的目的在于以公司為平臺向社會經濟生活滲透,搜刮財富,它們的公司主要也就是兩類:一類是從事非法經營的公司,另一類是從事壟斷經營的公司。這兩類公司都公開違反國家法律、商業規則和社會公德。
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盡管披上了“公司”的合法外衣,但掩蓋不了以非法的有組織暴力為后盾,追求對一定區域社會資源的控制本質。
龍顯雷進一步分析認為,實現了公司化發展的黑社會犯罪集團成了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系統結構,有著獨特的運作規則和程序,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和擴張力。只要組織結構不解體,少數成員的損失和受到經濟制裁只能傷其皮毛而難于動其根本。
因此,在進行嚴打斗爭時,有關部門尤其強調,要查處、沒收全部涉黑資產,徹底摧毀其經濟基礎。以防其有再生的可能。
“黑”“灰”之辯
今年兩會上,在參加“兩高”報告討論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監會原副主席邵秉仁說,打黑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要區別“黑社會”和“灰社會”的不同。
邵秉仁指出,現在的民間經濟中有大量的糾紛,也有欺行霸市的現象。對于犯罪的、涉及命案的嚴厲打擊是必須的,但對于單純是搶市場、占地盤的經濟糾紛則要有所區別,不可籠統地納入“黑社會”范圍。中國的某些行業如歌舞廳、洗浴中心等“灰色地帶”,常常在法律邊緣游走,因此會尋求一些權力部門和權力人物的保護,但究竟是不是黑社會則需要嚴格界定。
在“黑社會”和“灰社會”引起爭議的同時,“打黑“案件如何區分所涉財產“黑”與“白”也早已引起社會關注。
2006年3月3日,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以張執新、張執文為首的“大小地主”涉黑團伙案在黑龍江高院二審終審,張執新、張執文分別被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這個案件曾被有關部門認為是黑龍江在全國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取得的重大成果。根據當時黑龍江省公安廳提供的消息,2003年4月28日偵破此案后,他們已經將張氏兄弟的財產全部查封。包括兩人所聚斂的價值5000多萬的資產,以及銀行貸款5000多萬元。
當時辯護律師對這種做法提出了質疑。“要查封公司的資產,就必須指控其涉嫌犯罪。”該律師認為,“在本案中,被指控的是張氏兄弟而不是他們的公司。根據《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偵查機關不加區分地一概扣留、查封是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侵犯,應當予以糾正和返還”。
更有律師認為,通過違法犯罪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并非“黑社會性質組織”獨有,不能僅僅根據賭博等違法犯罪活動認定這個組織涉黑。
當時有媒體質疑:是不是只要定性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就把名下所有資產統統罰沒?公安部門某負責人回應說,這個沒有明確規定,并稱正在跟有關部門溝通。
“但從我們這個角度看,一定要打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經濟基礎,用黑錢辦的公司,那肯定都是要沒收的。如果不沒收,它有經濟基礎,還有一定的能量。”該負責人說。
目前相關法律在涉黑資產認定上存在的模糊界限,業已成為社會和司法界關注焦點,并引發了對涉黑團伙組織者動輒被處億元高額罰金的質疑。
尚待明朗
2002年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含義作出法律解釋:組織結構緊密,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國家工作人員提供非法保護,以暴力為后盾。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原局長張新楓在參加一個研討會時表示,有些城市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已經從公開的搶劫、綁架、敲詐勒索等“掠奪式”犯罪,向制販毒品、組織偷渡、走私、詐騙、開辦賭場和色情場所等隱蔽的犯罪發展。其中有些還以非法所得注冊公司、投資辦廠,有計劃地向合法經濟領域滲透,企圖壟斷經營,奪取更大的經濟利益。
這被看作是2000年12月4日,中國在全國范圍內部署首次“打黑除惡”專項斗爭之后,對黑社會發展趨勢的一個官方描述。
對于如何界定涉黑財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很多涉黑性質組織辦的企業盈利后,并不是拿過來直接支持涉黑的違法活動,它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洗錢。比如這些企業在合法的注冊過程中,采用非法的方式比如行賄受賄、偷稅漏稅的違法方式。這些財產列為涉黑資產應該沒問題。
“但是在辦理具體案件的時候,不能一棒子把凡是涉黑企業或涉黑人員做過的事情通通地打死。我們所說的掃除黑社會的資產,斷絕他的經濟來源并不是說就像土改那樣搞政治運動,還是要依法嚴打。”王太元說。
從沈陽“劉涌案”到重慶打黑,曾代理諸多涉黑案件的北京律師許蘭亭感覺,在處理涉黑資產上,實踐中各地司法機關標準不一,尺度不同。例如,有的判決書寫道,非法所得予以追繳。但何謂非法所得,卻沒有嚴格明確的標準可供遵循。
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周雷也表示,司法機關和辯護律師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財產是犯罪所得還是合法勞動經營所得應審慎研究和甄別,避免損害當事人的合法財產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