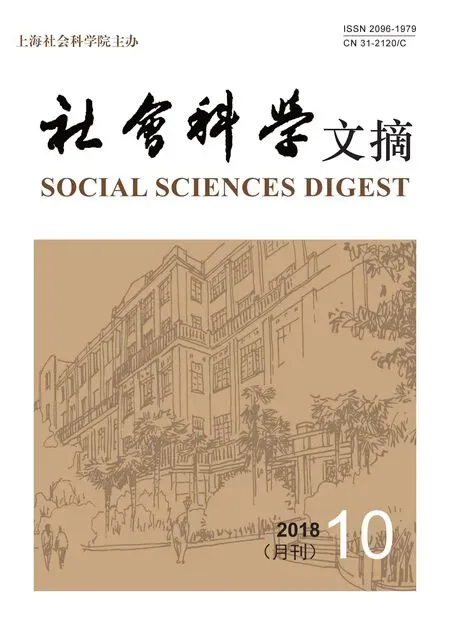話語研究的跨學科新動向與對策
話語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實踐活動。話語結構是被制度化、意識形態化、自然化的認識和描述世界的方式,反映并塑造社會、政治和文化結構。話語研究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一直伴隨著向其他學科的滲透、融合和延伸。這一趨勢也向研究者提出諸多學術挑戰,采用有效策略應對這些挑戰能推動該研究領域的發展。
話語研究的跨學科交叉方式
批評話語理論的跨學科性首先表現在它涉及領域的多樣性。芭芭拉·約翰斯通認為,批評話語研究不是單一的學科,甚至也不能被看作是語言學的子學科,而是一套系統的方法,研究的問題跨越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甚至深入到其他領域。她提到,在美國大部分話語研究者不是語言學系的人,他們從事的是英語、人類學、文化、傳媒、教育學、外語、修辭學、文藝批評、社會學、心理學、醫學、法律等領域的研究。其次是其理論上的多源性。批評話語研究的誕生與多個學科相聯系,包括修辭學、語篇語言學、人類學、哲學、社會心理學、認知科學、文學研究、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和語用學。三是其研究對象的多樣性,包括話語和非話語的社會符號——或者二者的結合物,而研究非語言的社會符號需要借助傳播學、信息學、網絡研究、藝術研究等領域的知識和方法。
由于它跨越的學科眾多,范戴克等建議使用“批評話語研究”來代替“批評話語分析”,或簡稱“話語研究”。無論怎樣指稱這個領域,從其發源和學科交叉狀態來看,它主要涉及兩個維度:一是語言研究的維度,二是其他學科知識的維度。其中,語言分析是手段,研究者對話語生產者使用的語言形式或表達的概念內容進行描述,這些描述可以是微觀的用詞層面,更多的是語篇和語類層面,也可以是各種語言修辭手段和其他符號的運用。第二個維度是目的,即通過批評性分析,揭示藏匿在話語背后的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視角,揭露話語生產者的社會政治意圖,甚至進而提出突破現行話語結構或話語體系的有效途徑。
對于兩個維度的交叉方式,范戴克區分了兩個研究傳統:一個是語言學為導向的話語研究,另一個是社會科學的各種話語研究。它們有各自的不足,“第一種研究經常忽視社會學和政治科學有關權力濫用、不平等的概念和理論,而第二種研究很少從事具體的話語分析”。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實際上可以把話語研究分為三類。
第一類研究也被稱作批評話語分析,研究者既關注語言形式的具體使用,也關注與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等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話語結構。他們多數有語言學背景,在修辭學、語篇語言學、文體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或語用學領域受過學術訓練。這些學科都研究語言在社會文化情景下的使用,但與批評話語研究在側重點上存在三個重要區別。第一,批評話語研究是多學科交叉,而傳統學科多為兩個學科之間的交叉。第二,批評話語研究更具有動態性,它研究不同語境和社會結構賦予話語的不同意義,而傳統的語言研究更靜態化,比如社會語言學研究不同社會群體使用語言的一般特征。第三,對批評話語研究者來說,語言研究只是手段,它重點研究的是話語與符號如何反映和塑造各種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身份建構、權力關系、意識形態視角等社會現象。
第二類主要關注話語的系統使用方式及其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這是法國人主導的研究傳統,代表人物包括福柯、阿爾都塞、佩舍等。在他們看來,話語是意識形態在語言中的物化。福柯認為,話語本身既是被爭奪的對象,也是開展斗爭的場所,話語研究在于揭示藏匿在語言背后的權力關系,其目的在于改變話語結構,打破它對思想的控制。這同時也是圍繞合法性開展的斗爭,這種合法性體現在誰有權力決定語言的使用,并進而決定在學術界和學校使用哪種話語體系。雖然福柯等不從事具體的語言形式分析,但也會研究某些用辭所代表的社會政治傾向,考察它的起源、在歷史過程中使用頻率的變化、用詞和指稱上的演變、使用模式,因為這些都反映社會群體關系的變化和斗爭過程。
第三類研究重點分析話語的概念內容,而不是語言形式。研究者也談論話語與權力,卻更多地把話語看作是權力和意識形態斗爭的工具,而不是像福柯那樣認為話語本身就是斗爭的目標和場所。他們關注更多的是“話語權”,而不是話語霸權(hegemony)。在他們看來,話語權既包括“權力”也包括“權利”,而批評話語分析所說的霸權是一種權威或影響力。比如有中國學者指出,運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描述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實踐,既不利于我們形成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還傷害民族自信,引發對中國道路的懷疑。顯然,他們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遵循薩義德的后殖民主義話語理論,后者研究殖民主義對現代社會結構和話語結構的影響。
三類研究存在兩個關鍵區別:一是話語研究與相關學科的結合程度和方式不同,二是他們對話語、權力和意識形態及其關系的定義不同。
話語研究的跨學科新動向及面臨的挑戰
從事外語研究的中國學者做的基本屬于第一類研究,它多集中在話語體現的各種社會不平等,新的研究并沒有脫離這個基本視角,但其跨學科領域和方法有所拓展。以下圍繞露絲·沃達克提到的六個新動向進行拓展討論和評述。
第一,研究知識型經濟對社會各領域的影響。在經濟上,新自由主義的一個典型特征是社會福利國家向市場驅動型國家的轉變,同時,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以來,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輸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全球體系內取得霸權地位。諾曼·費爾克勞一直關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如何重構經濟、政治和社會關系,致使經濟領域對政治和社會領域進行著“殖民化”。經濟話語侵入學校、醫院等非經濟的社會領域。比如,大學教師在自我描述中會使用team objectives(團隊目標),business effectiveness(業務高效),maintenance of customer-focus(堅持以顧客為中心,這里“顧客”指學生),achievement of organizational goals(機構目標的實現),而這些都是典型的管理學話語。要鑒別出這類話語,研究者不僅需要語言分析能力,還要熟知管理學的概念,甚至熟悉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體系。
第二,把認知科學的方法應用于話語研究。這是對范戴克等的社會認知研究的延伸,他們主要關心的是明顯帶有意識形態的認識是如何通過話語轉變成社會共識的,即研究話語結構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揭露社會歧視行為,更重要的是揭示話語控制心智、塑造社會信念和態度的方式,因為一旦形成這樣的信念體系和認知模式,就會產生系統性的、持續的歧視行為。沿著這個方向,中國學者可以探索如何跳出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做研究,真正實現認識論上的轉變和學術上的創新。
第三,研究新媒體對政治生活的影響。新媒體改變著人們交流、處理人際關系以及做事的方式,政治家可以通過網絡“聊天”這種非正式的話語形式完成意識形態的灌輸。政治和專業知識的權威在表面上被消解,使政治話語更容易被自然化。這些變化向話語研究者提出諸多挑戰,其中包括:(1)網絡社交的多模態化使基于口頭和筆頭語篇分析而形成的傳統話語研究方法受到挑戰;(2)網上存在大量無法追溯來源或來源混雜的語篇,這對研究話語參與者和語篇間性造成嚴重困難;(3)這種混雜性特點造成話語權力的分散,使研究話語中隱藏的權力關系更加困難;(4)結果,話語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過程及效果變得更復雜、更微妙、更難測量;(5)語境變得更復雜,話語參與者游離于線上和線下語境,且跨越時空談論同一個話題。上述變化甚至需要我們對“話語”“權力”“意識形態”“語境”等這些與政治領域相關的核心概念及其表現形式做出重新認識。
第四,研究多媒體和新語類帶來的影響。網絡語篇經常是由語言、圖像、視頻、音頻、表情等各類符號元素構成的多媒體、多模態混合體,語言甚至有時在其中不占主導地位。而且,范萊文指出,由于某些多模態語篇在設計時具有層次性,其中某些元素被突出,被前景化,讀者甚至都不需要按照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線性方式閱讀,從而形成了新的語類結構。再者,很多網絡語篇表面上看起來結構松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連貫性差。分析這樣的語篇,需要沃達克所說的“新的多模態理論和方法”。而且,這些新的理論和方法應該是跨學科的,范萊文指出,多模態研究不僅需要借用話語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還要從其他相關學科汲取靈感,比如藝術和設計理論”。
第五,研究話語結構的形成及其歷史演變過程,預測話語的未來走向。這實際上是沃達克等的話語歷史分析法的延伸,他們起初用這種方法研究二戰后奧地利反猶主義話語。最近幾年,隨著右翼勢力在法國、奧地利、荷蘭、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崛起,各式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新納粹主義等歧視性話語也成為西方學者研究的重點。分析這類歧視性話語都需要研究其歷史根源和歷史語境,這樣,“語篇間性”“話語間性”“語境重構”等就成為核心概念。
第六,綜合運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克服研究的隨機性,使研究過程變得可追溯,分析結果可驗證。沃達克這里所說的“隨機性”,主要指生硬地套用某種理論和方法來解釋一些話語實例。批評話語分析經常被指缺乏明晰性、客觀性和可驗證性,克服方法論上的這些缺陷也要借助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以上提到的第一、三、四方面主要涉及研究對象和領域的擴展,第二、五、六方面主要涉及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創新。因此,要想在話語研究的前沿領域有所建樹,研究者不僅需要重新認識一些核心概念,而且需要掌握跨學科知識和新的研究方法。
應對挑戰的跨學科策略
既然話語研究是跨學科的研究,應對學術挑戰的策略當然也應該是跨學科的。
第一,適應話語使用方式的變化,加強話語研究的跨學科力度。林恩·揚等總結出話語變化的四個趨勢:專業技術化指技術和專業語言進入社會政策,專業化詞匯和名物化結構的使用令公共話語聽起來多了一些專業性和合法性,少了一些主觀價值,但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能力;會話化走向反面,使話語帶上非正式的個人色彩,在無意識中完成意識形態灌輸,比如政治家的網絡“聊天”;市場化指借用商品交換的話語來談論教育和政治等非經濟領域的話題,比如上文提到的大學教師的話語;全球化的話語更強調一些所謂的“普世價值”——如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熱衷全球化的人用一種歷史決定論的語氣,極力把它描述為“不可逆轉的”“沒有其他選擇的”“能給所有人帶來利益的”,淡化全球化趨勢對地方經濟和文化特色造成的破壞。
這些趨勢不僅需要研究者重新認識權力和意識形態的表達和傳導方式,而且需要他們拓展自己的跨學科知識。否則,在“批評的”層面——在揭示話語背后隱藏的權力和意識形態時,就難以從理論上得出學術嚴謹的結論。
第二,綜合運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克服研究方法的隨機性。從方法論上來看,沃達克的話語歷史研究法、費爾克勞的三維分析模式和范戴克的社會認知研究法,都僅僅是研究“途徑”(approach),而不是“方法”(method)。可喜的是,研究者已經在使用各種語言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詞匯語法分析、邏輯語義分析、語篇結構分析、語料庫、語言統計、語言認知實驗等方法,試圖對話語進行形式化和量化的分析。但是,它們多數涉及容易量化的詞匯層面,而不是宏觀的語篇層面,對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分析更是局限于主觀判斷和主觀歸納。
面對跨學科的研究,沃達克主張應該根據不同的話題和研究對象借鑒不同的理論和方法。比如研究對語篇和其他符號的認知時,可以采用心理學和認知科學常用的實驗方法,包括使用各種認知和心理測量儀器,來克服訪談和調查表研究的缺陷。研究多模態語篇也可以借助研究藝術和傳媒的方法實現創新。總之,話語研究應該系統地利用跨學科的研究成果、證據和方法,提高其客觀性和科學性。
第三,要把握前沿課題,但也要在進入不熟悉的跨學科領域時保持學術謹慎。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涉及解釋的權威性問題。就跨學科的話語研究而言,公認的“解釋的權威性”(interpretive authority)只可能產生于兩種情況,一是研究者博學廣聞,能自由徜徉于多個學科,比如福柯;二是雖然研究者的學術背景是語言研究,但通過多年的研究實踐已經對語言之外的相關學科領域相當熟悉。像沃達克長期研究歐洲的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關心歐盟內部的政治格局變化;范萊文是媒體與傳媒學教授,對批評話語分析、多模態和視覺符號有深入研究。
這并不是說只有這些專家才能搞跨學科研究,只是說在進入一個不熟悉的領域時,研究者應該對研究的切入點保持學術上的警覺。比如研究醫學話語時,你可以通過分析病人與醫護人員和親屬等的會話,研究病人對“病人”“醫生”“生病”等的概念如何被塑造,這是有語言學背景的人借助初步醫學知識都能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將這樣的研究擴展到美國的醫療體制和醫療隊伍在管理病人上使用的話語,你就要對美國的醫療體制——比如醫療補助計劃、可支付醫療選擇法案等相當熟悉。
第四,尋求相關領域專家的合作,使研究過程真正體現跨學科性質。這無疑是跨學科研究最理想的模式。韋斯和沃達克提到,他們在研究失業和就業政策時,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語言學家參與其中。合作本身也是一個專業知識交流過程,語言學家要學習跨文化交際和社會學理論,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要了解語言學和話語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同時經濟學顧問和國際問題專家也被邀請參加討論或舉辦講座。
研究宏大的前沿問題更需要這樣做。作為其歷史話語研究的延伸,沃達克等近期在研究歐盟組織內的身份政治與決策模式。在這項研究中,作為語言專家的他們與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合作,提出了一些模型,用來解釋具有復雜歷史背景的歐盟內部的緊張關系和矛盾關系。他們收集的語料包括采訪、政策文獻、政治演講、媒體報道、歐盟官員的內部觀點等等。可以設想,這樣的研究必將取得令人信服的結果。
應該承認,國內的話語研究者很少進行這樣的合作研究,這顯然與話語研究的跨學科性質不相稱,也難以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高層次研究成果,提高我國的話語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多次提到話語權和話語體系建設,他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要“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一重要講話啟示我們,對話語的研究在中國大有可為,而這需要研究者增強民族自信,開拓跨學科的視野,掌握跨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方法,開展跨學科的合作研究,去創造高質量的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