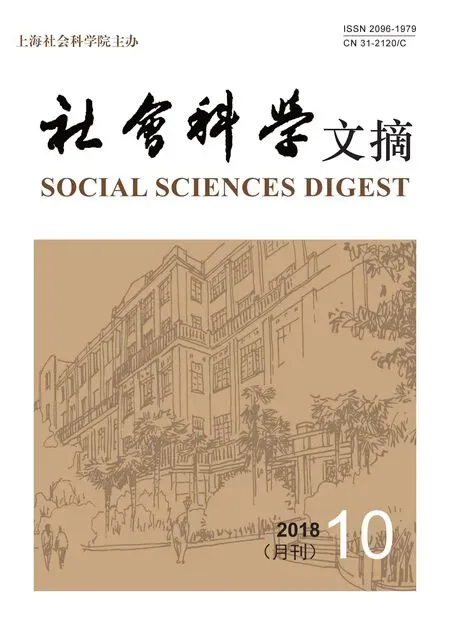美印視角下的“印太戰略”:政策限度及中國的應對
自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主動調整對中國的戰略布局,推出以空海一體戰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為主的涉及安全、政治、經濟等內容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特朗普主政后,美國退出TPP,“重返亞洲”無疾而終,為了應對戰略形勢變化,奧巴馬執政后期近乎銷聲匿跡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被重新拾起。從亞太到印太,最大的變化在于將印度納入戰略視野,企圖在西南方向及印度洋地區構筑對中國的“合圍”。
同時,源于廣泛的相似性與地理毗鄰,印度對中國長期以來始終存在“攀比心理”。在中國先于印度崛起情境下,印度對中國的防范心理強烈。中國海軍索馬里海域的護航行動、中巴安全合作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在南亞國家的發展與落實等正常的安全、經濟交流合作,均被視為針對印度的圍堵、遏制甚至挑釁。作為對中國在南亞-印度洋開展務實行動與廣泛合作的回應,印度開始尋求在東亞-太平洋區域平衡中國影響的合作方。以2017年6月莫迪訪美為標志,印度開始接納“印太戰略”,尋求在從美國西岸到印度洋西岸的廣闊空間內回應中國的行動并實現印度大國抱負的理想,客觀上讓美國成為未來中印關系發展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美印戰略訴求的契合
受現實主義支配的國際關系理論,在人性本惡的假定前提下,要求主要大國對實力對比的變化做出反應。美印兩國投身“印太戰略”,核心訴求是應對中國崛起,不論是美國的對華遏制策略,還是印度的對華防范心理,都是戰略層面對中國崛起的“條件反射”。
(一)基于現實主義原則的美印安全合作
特朗普曾在多個場合提到“原則性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并試圖把這一概念理論化。2017年5月,特朗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演講中首次提到原則性現實主義:“我們正在采取原則性現實主義(We are adopting a Principled Realism),(它)根植于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利益……我們將根據現實世界的結果做出決定——而不是僵化的意識形態。我們將以經驗教訓為指導,而不是僵化思維的限制。”此后在阿富汗以及聯大一般性辯論發表演講時,特朗普又多次提出原則性現實主義概念。2017年底出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開篇明義:“本國家安全戰略優先考慮美國利益”(Thi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uts America first),接著提出“美國優先國家安全戰略(An America Firs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基于……一種原則性的現實主義戰略,是以結果而不是意識形態為導向的”。
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印軍事安全合作就已經逐漸加強。2015年奧巴馬以主賓身分出席印度共和國日閱兵,不但成為第一位受邀參加印度國慶活動的美國總統,也是唯一任內兩度訪印的美國總統。2016年印度防長兩度訪美,先后與美方達成兩項重要協議:美國給予印度(非北約盟友的)“主要防務伙伴”(Major Defense Partner)地位;簽署《后勤交流備忘錄》(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特朗普上臺后,兩國很快就密切防務關系達成共識。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印度的“主要防務伙伴”地位再次進行了確認。2018年8月,美國宣布印度成為全球第37個,也是亞洲繼日本和韓國之后第3個獲得戰略貿易許可(STA-1)地位的國家。“主要防務伙伴”與STA-1的落實,使印度獲得原本僅向美國盟友開放的廣泛軍民兩用科技,終結了自1998年印巴核試驗以后美國對印度施加的技術封鎖。
(二)對沖防范“一帶一路”倡議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逐漸豐滿、合作逐步落實,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金融、基礎設施合作版圖不斷延伸,印度洋已經成為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展方向。在此背景下,美印兩國在“印太戰略”構想中找到了相互需要的動機和互為憑借的利益契合點。對美國來說,太平洋-印度洋航線長久以來都處于其控制之下,鏈接世界經濟最活躍地區——亞太,與世界主要石油資源生產地——中東的關鍵航線不可能拱手讓人。雖然長期內,印度崛起與實力增長也會對美國控制大洋的戰略安排造成威脅,但至少目前這一潛在威脅還不足以與中國崛起的現實緊迫性相比較。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給沿線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發展機遇,如果美國直接進行干預,一是目前美國國內的政經實情恐怕無法支撐,二是不少沿線國家,甚至包括一些美國盟友,都無法認同。因此,盡可能使用離岸平衡策略,拉攏印度參與對中國的遏制圍堵就是合理選擇。美國拉印度“入伙”印太,既可以利用中印這兩個發展中大國之間的矛盾,防止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又可以利用中印這兩個亞洲大國之間的矛盾,防止亞洲的整體崛起。
相較于美國,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態度要更為復雜。一方面,印度經濟發展面臨的最迫切的需求就在于基礎設施的改善與外國投資的增長,這方面“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都是理想合作對象;另一方面,南亞與印度洋地區歷來被印度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任何域外國家的介入都會引起印度的高度警惕,因此對于“一帶一路”印度始終反應冷淡。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雖不樂見南亞及印度洋沿岸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但受限于自身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無力提供替代性的區域合作選擇,曾經被寄予厚望的“季風計劃”至今仍沒有具備可操作性的政策出臺。綜合而言,印度雖然渴望獲得參與“一帶一路”與中國密切合作所能帶來的經濟好處,但實現“印度的印度洋”的戰略企圖,以及對所謂“珍珠鏈”、中國“包圍印度”等等戰略設想的地緣政治憂慮,卻促使印度選擇接納美國拋來的“印太戰略”“繡球”,希望借助美國力量平衡中國的影響。
美印戰略訴求的分歧與“印太戰略”局限性
近20年亞太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部分歸功于全球化進程中區內各經濟體廣泛而深入的經貿合作,以中美貿易和東亞生產網絡為核心的亞太經貿體系在做大蛋糕的同時,讓所有參與國家均從中獲益。相較而言,“印太”并不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地緣政經框架,其時代背景、國際環境、經濟內涵與亞太概念迥異,戰略構思中還包含若干矛盾之處。
(一)美印與中國博弈的“兩盤棋”
中美博弈,是典型的守成大國-崛起大國博弈,涵蓋面廣、內容復雜、情節波折。改革開放之初,美國曾經試圖把中國的發展納入西方軌道,在經濟、政治體制乃至價值觀等方面演變中國。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增長超過預期,并在實踐中發展并逐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演變的企圖早已破產。同時,受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與近些年民粹主義、極端政治沖擊,美國曾經對中國擁有的不對稱實力優勢正在縮小。在安全方面,雖然公認中美軍事實力仍存在巨大差距,但以軍事資產衡量的絕對差卻逐年縮小,部分領域中中國的后發優勢開始顯現。更重要的是,當前美國政府奉行單邊主義政策,在零和思維指導下不加遮掩地實施貿易保護措施,一方面阻礙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正常運行,另一方面主動挑起與幾乎所有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糾紛。相較而言,“一帶一路”建設聚焦合作與發展,秉持平等、開放、包容原則,本著量力而行態度與沿線各國共享發展成果,其中蘊含的走和平發展道路治國理念,與美國的單邊主義、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思維形成鮮明對比。
中印博弈至少在目前階段仍然是區域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印現階段的首要任務必然是發展經濟,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必不可少。對印度來說,一方面中美博弈必然增加印度在兩國中的回旋空間,保持中美斗而不破格局,同時與中美談判博弈獲取好處,可以說是最優選擇;另一方面,印度自尼赫魯時期就擁有強烈的大國抱負,歷史上還是不結盟運動的領導國家,在已經成為公認的新興大國與國際體系中重要國家的今天,印度保持獨立自主大國地位是必然選擇。與美國拉攏印度搞“離岸平衡”不同,印度的戰略目標在于實現“印度的印度洋”,這一具有排他性的地區戰略與美國的“印太戰略”并不相符。即使印度在中國崛起背景下接受“印太戰略”概念,對建立美日印澳四國或美日印三國安全合作機制興趣上升,但完全跟隨美國,把自己降格為美日關系中日本那樣的從屬地位,這樣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二)“印太戰略”與美國優先存在矛盾
從歷史經驗看,當守成大國試圖構建針對崛起大國的遏制包圍圈時,對同盟體系中相對落后國家的讓利與扶持必不可少。二戰后,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對西歐各國進行廣泛的經濟援助,最終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冷戰格局及其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遠東方向的戰略圍堵需求,促使美國采取扶持日本、韓國與中國臺灣的經濟政策,最終成就了日本經濟復蘇與亞洲四小龍崛起。而在今天的美國,大規模對外援助幾無可能,甚至一般的自由貿易原則都面臨著國內政治的巨大壓力。
事實證明,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并不是特朗普團隊“拍腦袋”生造的競選口號,而是有著廣泛社會經濟基礎的現實訴求。美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主要源于經濟不平等。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公布的數據,1989—2013年間美國不同階層家庭財富增長差異巨大。2013年,美國最富裕10%的家庭占有總財富的76%,排名后50%的家庭僅僅占有總財富的1%。
在美國優先原則下,雖然美國試圖在“印太戰略”中拉攏印度,以離岸平衡策略制衡中國,但指望美國像二戰后那樣通過大規模援助與貿易讓利手段來構建新的政治安全同盟體系的可能性顯然較小。《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指出以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維護美國“四項關鍵利益”(Four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即“美國人民和國土安全、促進美國繁榮、以力量求和平以及增加美國影響力”。在特朗普政府的任務清單中,美國優先或者說美國國內事務優先的重要性遠超“印太戰略”,當兩者利益出現抵觸時,保證美國優先是更符合其政治經濟需要的選擇。
中國的應對
美國拉攏印度加入“印太戰略”,走的是冷戰思維指導下遏制與對抗的老路。而印度出于平衡中國在南亞-印度洋地區影響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正面回應,希望從美方的拉攏中獲得實際利益。同時,印度對于介入中美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戰略博弈始終保持謹慎態度,不輕易選邊站。考慮到美印兩國的戰略目標差異,特別受制于美國優先原則的政策限度,預料“印太戰略”的實施效果將比較有限,美國借助印度實現“離岸平衡”遏制中國的目標較難實現。
(一)以務實合作增進互信關系
隨著2018年4-6月間莫迪兩次訪華并與習近平主席舉行會晤,兩國最高領導人引領中印合作開創新局面的預期有所增強。作為兩大發展中國家,中印都需要維護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捍衛全球化下的發展權益,在反對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方面有共同需求。
事實上,中印作為世界上經濟體量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天然地擔負著落實發展權利的任務。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中印都支持多極化發展趨勢,支持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反對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與逆全球化思潮,兩國聯手合作逐漸增加。2018年6月,莫迪首次以上合組織正式成員國政府首腦的身份參加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兩國在上合組織框架下的合作正式展開。在此之前,中印已經在金磚國家、G20、聯合國氣候談判等重要國際治理框架下都展開了務實合作。長期來看,政府與民間的務實合作有助于不斷提升中印兩國的相互信任關系,筑起兩國關系長久發展的基石。因此,在兩國領導人的帶領下,中印雙方需要基于共同需求,在多邊和雙邊層面上繼續加強務實合作,中印增強互信的前景將更加值得期待。
(二)加強中印基礎設施與融資合作
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國家,普遍存在基礎設施發展落后問題,基礎設施發展落后導致的廣義貿易成本成為制約南亞國家發展貿易的主要障礙,這一障礙遠比關稅的負面影響更大。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2005—2015年間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年均資金缺口在0.5-0.75萬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表明,亞太30個發展中經濟體在2010—2020年間的基礎設施投資總需求約為8萬億美元,其中南亞為2.3萬億美元,而印度則占南亞的92%,達2.17萬億美元。
中國是“印太”地區經貿合作潛力最大、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范圍最廣的國家。從資金實力、技術水平、工程經驗、適用性等各個方面來看,對于印度這種擁有巨大人口規模和幅員遼闊國家的大規模基建,中國的經驗顯然非別國所能媲美。同時,中印基礎設施合作的機制也已經具備,“一帶一路”與亞投行都是現成的選項,只要中印兩國加強互信,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與相關融資領域的合作可謂順理成章,進而構成兩國關系穩定的基石。2015年6月《亞洲基礎設施銀行協定》簽訂之時,印度以83.67億美元的認繳股本和7.5%投票權成為亞投行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股東,反映了印度提高基礎設施水平的迫切需求,也充分表明了印度在這一領域加強合作的意愿。
(三)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長期以來,南亞經濟發展波動性大,抗風險能力較弱。印度作為南亞發展表現最佳的經濟體,同樣面臨著貿易壁壘高、自由化水平低的問題。中國目前已經與巴基斯坦和馬爾代夫簽署雙邊FTA,其中中巴第二階段FTA談判已經啟動。另外,中國與尼泊爾、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的FTA也已經啟動前期協商,唯獨與印度尚無任何雙邊貿易安排。中印貿易近些年保持了增長勢頭,但印度對華貿易逆差較為顯著,2017年印度對華貿易逆差達到517億美元。有鑒于此,印度對于談判中印FTA的熱情不高。
然而,印度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賴于制造業水平提升,這必然要求貿易條件的更大改善,在中印雙邊FTA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兩國共同參加的區域/多邊貿易安排就成為了最佳替代方案之一。在美國退出TPP之后,太平洋-印度洋區域內最具前景的自由貿易安排就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與日本、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印兩國都主張迅速達成RCEP談判,實現第一階段成果,在美國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當下發出亞洲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堅持全球化發展方向的聲音。一旦RCEP得到落實,中印經貿關系將會進一步鞏固,兩國共同對抗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逆全球化思潮的立場也將更加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