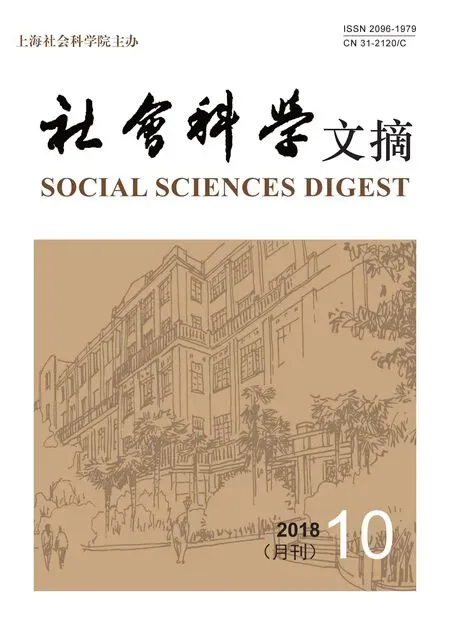重思馬克思的“邏輯與歷史相統一”
“邏輯與歷史相統一”是馬克思在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展開深入批判、廓清社會科學研究具體路徑基礎上確立起來的科學的方法論原則,在當今社會科學研究中被廣泛運用。然而一直以來,學界仍然存在著對“邏輯”與“歷史”究竟如何統一、“歷史”的真實內涵等問題的認識蔽而不明的狀況。從本質上來看,這與對馬克思思想的知性科學的闡釋方式有密切關聯。
一種知性科學的闡釋:范疇的邏輯次序與歷史進程相統一
談到“邏輯與歷史相統一”這一方法論原則,可能通常人們會引用恩格斯的“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段話來加以闡釋,認為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含義就是范疇的邏輯次序與歷史進程相統一而已。在這種闡釋當中,歷史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客觀進程的次序性,邏輯是對歷史認識的范疇運動的規律,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就表現為范疇從簡單到復雜、從抽象到具體的這一順序都保持了與歷史發展進程次序性的一致。這從本質上來說,是從知性科學的角度做出的闡釋。倘若陷入以上的思路,就無法領會到“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真正要義,因為它根本不是馬克思從任何諸如經濟學、政治學之類的知性科學研究的路徑中獲得的成果,他恰恰是在對這類研究路徑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這一方法論原則。
即便是順著這種知性闡釋的思路考察下去,我們也會發現它的明顯的漏洞。恩格斯的那段話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書評中,而不是在介紹《資本論》的文章中講了如上一段話的。我們也知道,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僅僅考察了商品和貨幣,而沒考察資本。商品和貨幣所體現的是簡單的流通領域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遠比歷史上的一種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生產關系要簡單得多”,不僅如此,恩格斯說范疇的邏輯次序與歷史進程保持了一致性只是為了表達更為通俗易懂罷了,他認為這還不能恰當地闡明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真正含義。
那么,就范疇的邏輯次序與歷史進程是否保持一致性這一問題而言,馬克思的觀點究竟是什么?在他看來,只有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會保持這種一致性。簡單的范疇是否一定會在具體的范疇之前存在還需要依情況而定,以貨幣為例,他闡明了這一觀點:“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雇傭勞動等等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從這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范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于支配地位的關系或者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系,這些關系在整體向著以一個比較具體的范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復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歷史過程。”而且,他還指出,范疇的邏輯次序未必要與歷史進程保持一致性,往往還會出現不一致的狀況。在查閱了歷史學家的相關文獻后,馬克思發現在那些經濟形式已經很發達、但在歷史上還不成熟的社會形式那里,存在著最高級的經濟形式例如發達的分工,但是貨幣卻并不存在,秘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另外,盡管在歷史發展的較早階段貨幣就已經展現了它的全面的功能,但是它也還僅僅是在商業民族中作為一種處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發揮作用。甚至在古希臘和羅馬時代,當它們處于解體的時期,貨幣才得到了充分地發展,然而,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當中,貨幣卻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前提。因此,馬克思認為,貨幣這個十分簡單的范疇,并未經歷了歷史上所有的經濟關系,只有在最發達的社會狀態之下它才釋放出最充分的力量。
經過這番深入地考察之后,馬克思得出了如下結論:“比較簡單的范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范疇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充分發展恰恰只能屬于一個復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范疇在一個比較不發展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分的發展。”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最后的判斷是:“把經濟范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來安排是不行的,錯誤的。”
另外,我們通過更為全面的考察還發現,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是從人類社會歷史的共時性結構的角度研究事物之間的橫向關系。因此,如果將表達這些關系的邏輯順序就直接等同于歷史進程的次序性顯然是以偏概全的做法。
至此,我們可以做出判斷,不能從人類社會發展客觀進程的次序性意義上來理解“歷史”,因而也就不能從范疇的邏輯次序與歷史進程相統一的角度來談論“邏輯與歷史相統一”,也就是說,這種知性科學的闡釋方式是站不住腳的。
歷史存在論闡釋:邏輯與實踐建構的生活世界相統一
那么,馬克思又是從什么角度談論邏輯與歷史相統一呢?他是從歷史唯物主義學說開啟的有別于一切知性科學的歷史存在論視域當中提出并闡發這一觀點的。
我們選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前提——“勞動”范疇為例,對馬克思的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歷史存在論的真實內涵加以說明。在馬克思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研究的“勞動”范疇事實上是已經經過了他們思想上的抽象,“勞動”已不再是與自然打交道的自然狀態的勞動,而是異化了的勞動。其感性特質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思維抽象當中被剔除了出去,從而獲得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中勞動的同質化的特點。感性的活生生的人與自然打交道的勞動不復存在,最后剩下的這個抽象的“勞動一般”成為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建構其理論的邏輯起點。
馬克思認為,“勞動一般”在其本源上并不是現代頭腦的產物,而是有其更為深刻的歷史起源。即使經濟學家再進一步運用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思維過程的這一“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從勞動、需要、交換價值這些簡單的范疇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這些具體的再現,但是,這也只是用思維來掌握具體。這個深刻的歷史起源才是研究中最為關鍵的內容。
因此,有必要再對“勞動一般”的起源具體展開分析。在人類歷史進程中,隨著社會分工的逐步發展,人們必須通過交換來獲得生存資料和生活資料,社會共同體的再生產也必須借助于它,這樣交換就漸漸成為人類社會經濟結構的普遍形式和廣泛基礎。而交換本身要求一個具有社會性意義上的共同的標尺,因此,只有剔除了勞動本來具有的感性特征,才能轉化為作為交換的共同尺度的“勞動一般”。在生產商品的這個過程之中,商品的價值表征的是一種特定的生產關系,這一關系意味著人要服從于外在的尺度,個體的勞動要轉變為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的“勞動一般”。在這種狀況下,個體的感性勞動就被強行納入到了整體性的社會勞動機制當中,隨之而來的一種后果是,人的特質與自身相剝離而轉變成商品的東西與自身相對立,“勞動一般”取得了無條件的主體的地位,從此化身為在個人之外并支配著個人的異己的社會力量,也就是積累起來的死勞動對活勞動的支配關系,質言之,資本原則對社會中個體的全面的支配關系。一般來說,“勞動一般”已經成為抽象之物,不再具有現實性,可是在現代資本社會當中,它卻又真實地發揮著作用,這看起來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然而正是這種匪夷所思道出了社會現實的本質:資本原則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普遍的支配原則,人類深深地陷入到普遍異化的社會狀況當中而無法解脫。
以上事例的分析,說明了邏輯與歷史的相統一是與它的深刻的歷史起源的相統一,所以,馬克思說:“把經濟范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來安排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于各種經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們在‘觀念’上的順序,而在于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換言之,邏輯與歷史的相統一不能用與歷史進程的次序性的統一來表達,統一是與“相互關系”或“內部的結構”的一致性,而這種“相互關系”或“內部的結構”馬克思指稱的是生產關系。他形容生產關系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是“一種普照的光”、“一種特殊的以太”。在馬克思這里,生產關系不是作為知性科學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生產關系,而是全部社會關系意義上的生產關系。它是由生產實踐所建構起來的生活世界,即便馬克思沒有使用“生活世界”這個術語,在他的歷史存在論視域中,生產關系都是人的理性前的社會存在,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性交往,是個人原始地身處于其中的‘社會生活條件’。正是這個生活世界決定了理論的邏輯理路和架構。就“勞動一般”而言,它即是對“勞動”本身的所發生的現實的異化的能動再現,倘若沒有社會現實的這一異化過程,根本不會出現“勞動一般”這個抽象范疇。
那么,如何進一步將馬克思的邏輯與歷史相統一這一方法論原則的歷史存在論內涵完整準確地揭示出來呢?從馬克思建立的這一嶄新視域來審視:其一,他首先強調的是作為感性活動的勞動即“實踐”是建構人類世界的根基;其二,只有從實踐出發而不是從意識本身的辯證運動出發去闡明觀念和知識的形成過程,才能揭開思辨范疇對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學的遮蔽,使建立在理性法則基礎之上所構建起來的科學研究的真正基礎即本真生活真正呈現出來,從而闡明事物的本質,形成真正的知識。
“邏輯與歷史相統一”正是這一思想視域的產物,它高度凝練并彰顯了其核心精神。馬克思在這里首先強調的是“歷史”的首要地位,只能從歷史當中獲得邏輯,而不是彼此顛倒過來,否則就是重新回到了黑格爾的“邏輯就是歷史”的思想當中,那種認為馬克思就是將范疇的邏輯在現實生活中的次第展開視作是歷史的觀點,是對馬克思作了黑格爾式的歪曲。其次,領會“歷史”概念的真正含義尤為重要。在馬克思的闡釋中,“歷史條件”、“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相互關系”這些相近的用詞,都在指向歷史不能指稱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次序性,它應是人類在生產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生活世界,這才是邏輯的真實來歷。再次,“相統一”的根本含義,一方面是邏輯植根于生活世界,沒有人們在生活世界中的生產實踐活動及其展開過程,就沒有頭腦中邏輯的再現;另一方面,邏輯是對歷史能動地再現,而不是直接地、消極地反映,否則范疇的邏輯次序就應該是始終保持著與歷史進程的一致性。
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路徑:政治經濟學批判與現象學經驗的觀察
馬克思說過:“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在他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屬于這種“獨立的哲學”,因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研究以既定的未經批判性考察的理論前提作為出發點,以抽象的形式推演現實的社會生活的運動的軌跡,而那些使前提得以成立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根本沒有被納入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研究論域,因而在其理論建構中必然生成了難以解決的痼疾,無法深入到現實的社會生活的本質當中。
“勞動一般”這個古典政治經學理論前提的歷史起源并未得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深入分析,進一步說,對勞動如何轉變為勞動一般或者說勞動如何發生異化的這個問題的探討在他們那里是缺失的。馬克思洞悉了這一研究路徑的本質性的缺陷并對其進行了深入地剖析,他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不去考察“勞動一般”如何而來以及其之所以主體化的過程,因而現代私有財產是由勞動的異化所建構而來的這一客觀事實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視域當中是始終處在被遮蔽的狀態,這就充分暴露了他們的研究路徑在其根基上的問題。運用抽象范疇表述社會現象和事件僅僅意味著邁出了科學抽象這一步,而這些現象和事件背后的生活世界更需要加以探討,因為抽象范疇及其推演所表達的內容起源于此,只有完成這一步,才能達到對現實的社會生活的真正的把握,從而對社會問題作出正確的診斷,并由此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在這一點上,馬克思超拔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之處在于,他能“在科學的歷史抽象中找到原有的關系(簡單關系),再一步步再現今天真實的復雜關系和顛倒了的社會結構”。
對抽象范疇及其所表達的社會存在,都要從人們的社會生產實踐中去發現它的起源,并據此說明知識的形成,這是馬克思在歷史存在論視域下為我們提供的不同于其他一切知性科學研究的嶄新路徑,即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它是達到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根本路徑。馬克思所做的即是對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研究對象的理性“范疇”展開批判性研究,“批判”的真實含義是探究既成的社會事實的起源,因而它真正深入到了歷史的本質維度當中。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一批判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在西方并未得到其追隨者和闡釋者的足夠重視和認真對待。
直至20世紀60年代末,在霍克海默、阿多諾等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影響之下,德國年輕一代學者踏上了回歸馬克思思想的歷程,以巴克豪斯、賴希爾特為代表的新馬克思閱讀運動獨樹一幟地將其視域集中在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上,深度詮釋其理論內涵。巴克豪斯提出的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十分貼切和中肯的評價,說明了他的確準確地表達了馬克思的觀點:在現代社會當中,未經范疇批判而表現為思想異化的科學理論和在現實生活中作為現實生活異化的資本統治事實上保持了一致性,批判異化了的思想就是批判現實生活狀況的異化。那么,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的這一思想的批判實質上是實現了對資本統治這一社會現實的批判。正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一正確的研究路徑中,馬克思才能做到思想與現實的一致,邏輯與歷史的相統一。
批判堅持要從理性范疇規定之前的實踐出發,那么,怎樣才能逐步接近這個現實的生活世界呢?馬克思認為,需要借助于“經驗”的觀察,首先要做的是祛除理性范疇和意識形態對生活世界的遮蔽,那么,回到事實本身、運用現象學的原則就是必經的步驟,然后從生產實踐出發,觀察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如何被生產出來。
事實證明,馬克思的這一研究路徑發掘了現實之所在,洞察了社會問題的真相,由此達到了邏輯與歷史的相統一,正是在這一研究中,馬克思為其建立理想中的新知識形態——歷史科學做出了最初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