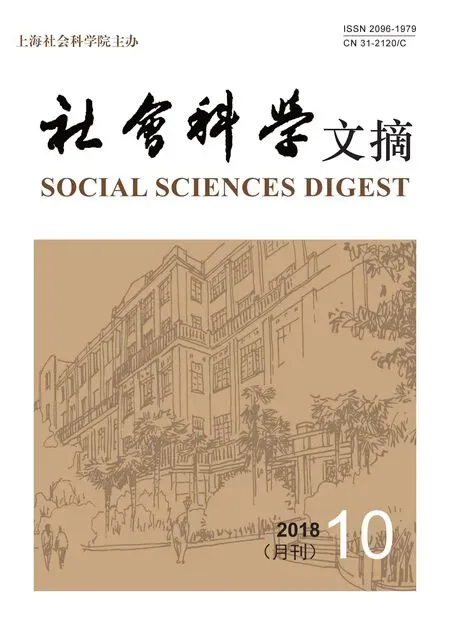論美學與文藝學的關系
關于美學和文藝學的關系,一直存有爭議
在中外美學界,關于美學與文藝學之間的關系,一直存有爭議,迄今為止,大致已形成了以下三種看法:
一是美學與文學藝術無關,美學與文藝學是毫無關聯的兩個學科。如被稱為“美學之父”的鮑姆加登,在所界定的“感性認識的科學”這樣的美學定義中,藝術就未被提及。蘇聯美學家尤·鮑列夫認為“文藝美學”“音樂美學”之類的提法原本就不夠科學,是“把美學泛化了、庸俗化了”。德國美學家康拉德·費德勒更是曾以激烈的口吻斷言:“美學不是藝術理論”,“美學和藝術的結合”毋寧說是“美學領域的第一謬誤”。從邏輯上來說,這類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研究對象、研究視點、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異,“美學”當然不應是一般的“藝術理論”。但由于文學藝術呈現為感性形象,能夠給人以情感感染,因而無論從源于鮑姆加登的“美學”之本義的“感性學”,還是從后來康德及其他許多美學家所主張的美是一種心神愉悅的情感判斷來看,美學與文藝學之間又有著天然的不解之緣。
二是美學基本上就是文藝學。如黑格爾在他的《美學》中,雖亦論及自然美與現實美,但在“全書序論”中已點明,他的美學,是一部關于“美的藝術的哲學”,其研究對象的范圍是“美的藝術”;俄國文藝理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強調“整個藝術、特別是詩的共同原則的體系”才是美學研究的中心對象;蘇聯學者布羅夫認為美學就是“藝術哲學,是一般藝術理論”;我國美學家馬奇在《關于美學的對象問題》一文中亦曾明確強調:“美學就是藝術觀,是關于藝術的一般理論。”這類將美學等同于文藝學,否定了美學與文藝學之間學科界限的看法,顯然是不合理的,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按此看法,美學與文藝學,只能二者留存其一。如認定“美學就是藝術觀,是關于藝術的一般理論”,“文藝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或將美學的研究對象完全集中于文學藝術,現已成為世界性學科的“美學”,也就同樣失去存在的必要性,難以成其為獨立學科了。
三是美學與文藝學密切相關,認為美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現實美、自然美,也包括文學藝術美,美學可介入文學藝術的研究,形成諸如“文藝美學”“藝術美學”之類的交叉學科。如《美國學術百科全書》對“美學”的定義是:“美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其目標在于建立藝術和美的一般原則”;德國《哲學史辭典》認為美學“研究的是美與藝術”;在我國,胡經之先生的看法是,文藝與審美,既不完全等同,亦非毫不相干,二者之間是一種交叉關系,并據此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開始了關于“文藝美學”這一交叉學科的研究與探索。與第一種、第二種看法相比,這類看法無疑更為合理,不僅有助于美學體系自身的完善,以及美學研究的切近實際,亦有助于文藝學研究的擴展與深化。多年來,在我國美學界,這類見解與主張基本上也已成為共識,且已形成了“文藝美學”“藝術美學”以及更為具體的“小說美學”“詩歌美學”“繪畫美學”“書法美學”“音樂美學”等研究門類,并已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在教育部頒布的現行學科專業目錄中,文藝美學與藝術美學 ,也已分別被列為中國語言文學的二級學科“文藝學”與藝術學的二級學科“藝術學理論”中的主要研究方向。但由于美學與文藝美學、文藝美學與文藝學之間的界限尚存混亂,以及究竟何謂文學藝術的美之類問題的模糊,在我們現有的研究中,也還存在一些需要深究的問題。
美學與文藝學常被混淆
我們已有的“小說美學”“詩歌美學”“繪畫美學”“書法美學”“音樂美學”“文藝美學”之類著作或教材,常常給人不顧學理與實際效果,讓美學過度侵入了文藝學領地的感覺。
或未經理論內涵的有效置換,將原有的文藝學范疇貼上了美學標簽。如在我們的美學教材中常見以下論述:“在魏晉玄學的影響下,魏晉南北朝美學家提出了一大批美學范疇和美學命題,如‘氣’‘妙’‘神’‘意象’‘風骨’‘隱秀’‘神思’‘得意忘象’‘聲無哀樂’‘傳神寫照’‘澄懷味象’‘氣韻生動’等。所有這些范疇和命題,對后代都有深遠的影響。”且不說將一些古代文論家稱為美學家是否合適,進一步推究會意識到,將許多本已有特定內涵的文藝理論術語改稱為美學范疇,這除了貼上一個美學標簽之外,似乎并不具理論內涵的增值意義。誰又能說清楚“氣”“妙”“意象”“風骨”“神思”之類的文藝學范疇與美學范疇的“氣”“妙”“意象”“風骨”“神思”等有何實質性區別?
或將原有的文藝理論,納到了美學的名目之下。如在一些題為“藝術創作美學”的著作中,我們僅由“藝術本體”“藝術創作動機”“藝術構思”之類章節標題就會感到,這“藝術創作美學”不就是“藝術創作學”嗎?在不少美學史、文論史著作中,亦常見美學思想與文藝思想的重合,如由“小說萌生的語境”“小說意識的自覺”“小說繁榮期的建樹”之類論題及相關內容就會讓人感到,一部《中國小說美學史》,大致上也可叫作《中國小說理論史》;李澤厚那本影響頗大的《美的歷程》,也基本上是一本“美學”特色并不突出的關于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簡史,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對中國古典文藝的匆匆巡禮”。在朱光潛先生的那部《西方美學史》中,亦多見“但丁的文藝思想”“文藝的社會功用”“意大利的文藝理論與美學思想”“狄德羅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藝術的本質和目的”之類文藝理論內容。面對這樣一些論著,人們必會愈加困惑于何謂美學,何謂文藝學。
即以一些比較優秀的藝術美學論著來看,作者雖對一般藝術研究與美學研究盡力予以區分,但二者亦存纏繞不清的缺憾。
瀏覽美學、文藝學、藝術學論著,我們還會發現,同一個人的同一些思想,可被甲說成是“美學思想”,亦可被乙說成是“文學思想”或“藝術思想”,而實際上,這“美學思想”與“文學思想”“藝術思想”的所指之間,并沒多少根本區別。同一位作家、藝術家的作品,有人以審美特色論之,有人以藝術特色論之,所論內容也往往沒多大差別。
這樣一種混淆美學與文藝學的現象,當然不止見于我國美學界,讀一下日本美學家今道友信的《東方的美學》就會感到,他所講的孔子、孟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劉勰等人的美學思想,不就是我們的中國古代文論中所講的他們的文藝思想嗎?在今道友信的論述中,王羲之的《書論》也被稱為“美學著作”,羊欣也被稱為書法美學者,這與一般書法史上所說的《書論》是書法理論著作,羊欣是書法理論家,又有何本質區別呢?在論及《文心雕龍》時,今道友信道:“這些詩人輩出之后,《文心雕龍》對文學的美學原理,創作方法和欣賞的原則等極有深意的問題,作了探討。若與西方同時代的情況相比較,恐怕這確實是可驚嘆的高水平的文藝論。”這里,作者已徑直將“美學原理”與“文藝論”等同劃一了。既然“美學原理”就是“文藝論”,那又有何必要在已有“文藝論”的情況下,再另外加一個“美學原理”的名目呢?
傳統美學準則無法全面解釋文學藝術的特征與價值
美學之于文藝學研究的重要意義或許在于:能夠從美學角度,更為科學、更為深入地解釋文藝作品的特征與價值,但我們已有的相關見解與論述,則時見捉襟見肘,或生硬牽強。
在中外美學史上,極具普遍性的一種觀點是:“美”的事物的根本特征是能給人心神愉悅的快感,審美價值就是愉悅價值,這看法無疑是符合實際的。但用以“心神愉悅”為基本特征的審美價值觀解釋自然美與現實美,容易說得通,而用之于解釋藝術美,情況就比較復雜了。因為在自然與現實事物中,令人愉悅之“美”或不愉悅之“丑”,是比較容易區分的,如凡一位心智正常的人,面對一叢鮮花時都易生欣悅,面對一堆糞便時常會厭惡作嘔,前者即可謂“美”,后者即可謂“丑”。而用此道理解釋文藝作品的美時,就不如此簡單了,有的說得通,有的則榫卯難合了。
對于表現了自然與現實中原本就是美的事物的作品來說,這是說得通的。如在閱讀“兩個黃鸝鳴翠柳”“東風夜放花千樹”這樣的詩詞時,在欣賞齊白石的花鳥畫時,我們自是會產生“心神愉悅”之美感。但當面對表現了丑、惡、兇殘之類事物的作品時,我們就不是如此的“心神愉悅”了,因而也就有點說不通了。英國美學家李斯托威爾在1933年出版的《近代美學史述評》中就曾指出,在藝術欣賞過程中,不可能全是“純粹的享樂”,“當觀看莎士比亞、易卜生、梅特林克或者霍普特曼的一些偉大的悲劇的演出時,或者當閱讀哈代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憂郁而又具有強烈的悲劇性的小說時,誰不曾忍受過最殘酷的痛苦呢?誰又不曾一下就為杜米埃那種卓越的漫畫,為左拉或莫泊桑所寫的那種卑微而又帶有獸性的人物,為吐魯斯-勞特累克所畫的賣笑的娼婦,或者為田尼哀所畫的酒氣醺醺的農民,所吸引而又感到厭惡呢?”英國著名詩人艾略特也曾這樣指出,文學作品的價值決非僅是體現在讓人得享閱讀的“愉快”,認為“當文學被‘純粹為了愉快’來閱讀的時候,它是最危險和最扭曲的”。事實上,諸如《哈姆雷特》《戰爭與和平》《紅樓夢》這類偉大的文學作品,給予讀者的,就決不可能僅是“心神愉悅”之類的審美滿足。如果僅是“純粹為了愉快”而閱讀,恐也就難以體悟到這些作品的偉大之處了。
近些年來,有不少西方學者,對傳統的以“心神愉悅”為基本特征的美學準則,論及藝術之是非的見解表達了更為強烈的質疑。美國學者丹托在《美的濫用》一書中,就曾更為明確地指出,“好的藝術”不一定是“美的藝術”,并舉例說“馬蒂斯的《藍色裸女》是幅好作品,甚至是一幅杰作——但若有人說它美則是一派胡言”。這類質疑與反駁,是值得深思、值得重視的,當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探究:藝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學的對象?美學應從哪些方面介入文學藝術的研究?
文藝美學應著眼于文學藝術中的美學問題
由于美學與文藝學,畢竟是兩個不同學科,二者之間,既有密切聯系,又有根本區別,交叉而形成的文藝美學之類,自然也應既不同于美學,亦不同于文藝學。也就是說,只有切實抓住文藝美學的特征,真正從文學藝術中的美學問題著眼,我們的文藝美學之類的研究,才有可能走向深入,才能更有成效。具體來說,應進一步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應進一步明確文藝美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視點及研究方法等。雖然,與文藝學相同,文藝美學之類的研究對象亦是文學藝術,但二者應有的區別是:文藝學重在研究的是不同藝術門類的特點、創作規律、藝術技巧、價值系統等,在價值系統中當然亦可包括審美價值,而文藝美學則應與一般文藝學不同,應更專注于研究文藝作品的審美價值,并深化關于文藝作品的“美”及相關的美學問題。
第二,既然文藝美學要研究的是文藝作品的美,就要進一步深究:到底何謂文學藝術的美?又何謂文學藝術的丑?如以能否給人心神愉悅的標準判斷,文藝作品中的美當是源于這樣三個方面:一是作品中表現的原本就是自然與現實中那些美的事物;二是作者肯定性、贊美性的情感傾向;三是作者的藝術化能力,即如同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所說的,美的藝術的優越性在于“它美麗地描寫著自然的事物”。根據這三個方面,文藝作品中的美與丑,會有如下復雜情況:同是自然與現實中的美,在文藝作品中,會因作家、藝術家“美麗地描寫”而益生美;亦會因作家、藝術家藝術才華之不逮而敗壞其美;同是自然與現實中的丑,會因作者肯定性、贊美性的情感傾向及“美麗地描寫”而生出審美價值;又另有一些事物,如蛆蟲、尸體、血腥暴力、屠戮殘殺之類,因難以投入作者的肯定性、贊美性情感,故而無論作家、藝術家如何“美麗地描寫”,恐也難以叫人“心神愉悅”,但正如美國學者丹托所說的,這類“不一定是美的”藝術,同樣可能是“好的藝術”。
第三,要加強對不同門類文藝作品審美特征的研究。如以語言為媒介的詩歌、小說之類,緣其語言符號的靈活性、抽象性及自由表現性,會創造出諸如李白“白發三千丈”、李商隱“望帝春心托杜鵑”之類無法訴諸感官,無法像造型藝術、表演藝術那樣直觀,卻有著決定了文學藝術獨特生命力,造型藝術、表演藝術無法替代,能夠給人以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及更多自由想象之欣悅的審美效果。同是語言藝術,重在抒情的詩歌與重在敘事的小說,其審美特征又有差異,詩歌重在以意境感人,小說則主要以形象感人。與語言藝術不同,在綜合性的舞臺表演藝術中,現實中的丑陋、邪惡人物或凄慘的場景等,會因演員的高超演技而博得觀眾的喝彩。
法國美學家杜夫海納在《美學與哲學》中曾這樣談過文藝作品審美價值的生成特點:“我們必須做到集中注意力于作品本身,并且以無利害的方式去欣賞它,玩味它。也就是說,除審美興趣外,不為其他興趣所動。”杜夫海納所說這樣一種純然靜觀的審美狀態,可能更適于形式美感更為突出的造型藝術,而對于語言媒介的小說、詩歌之類時間藝術,就不易做到。可見,只有著眼于不同藝術門類的審美特征,相關的藝術門類的美學研究才能更為深入,否則,就易導致膚淺化與普泛化。就筆者所見,吳功正先生的《小說美學》,堪稱是一部真正的“小說美學”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扣住小說家的審美感知的整體性、審美情感的典型性及典型人物這一基本審美范疇,比較充分地闡明了小說美學的相關問題。但其中的有些論斷,如“小說美學作為藝術美學之一種的審美本質,它是再現又是表現,既有造型性又有表情性”,“小說是在主體和生活結成的審美關系中進行審美創造”,“小說美學的特殊本質是,主體對生活的認識在審美中進行”等,也因其道理的普泛化,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其特定的“小說美學”內涵,影響了其學術深度。
經由上述分析,我們或許可以更為清楚地意識到:只有進一步明確文藝美學的研究視點、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等,深究何謂文藝作品的“美”,以及不同藝術門類的審美特征,切實抓住文學藝術中的美學問題進行研究,才能更好地避免美學與文藝學之類研究的重復與纏繞,才能使美學對文學藝術的介入更富有學術增值之效,才有助于回答原有文藝理論難以回答的某些問題,也才能有助于美學與文藝學自身的豐富與發展,有助于人們的審美能力與作家、藝術家創作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