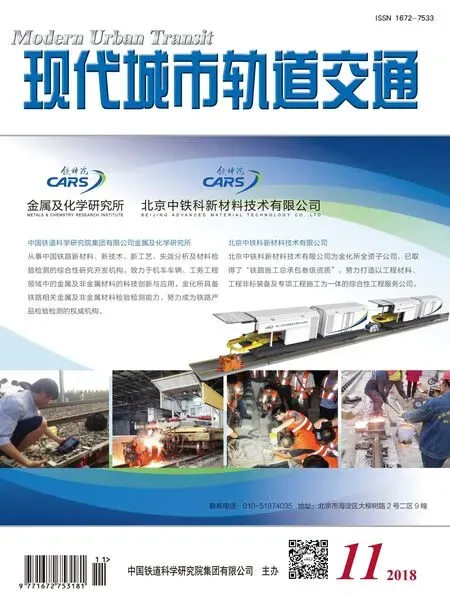地下水位對青島地鐵盾構隧道變形影響研究
徐祥云,胡云飛,高福軍,李地元,王文健
(1. 中鐵八局集團昆明鐵路建設有限公司,云南昆明 650200;2.中南大學資源與安全工程學院,湖南長沙 410083)
0 引言
我國地鐵工程的埋深一般小于 20 m。地層在該深度以內一般存在上層滯水或者潛水。另外,在我國的濱海濱江地區,可能還有承壓水,且埋深較淺。在 20 m 埋深內,地層大多為第四紀沖擊層、沉積層,也存在很多是強風化或者全風化巖層,這些地層多為松散無膠結的巖土體,可以看作可變形的多孔介質材料。巖土體在荷載和地下水的雙重作用之下,變形會造成其裂隙孔隙通道的改變,從而影響孔隙水流動。孔隙水流速的變化不僅會影響巖土變形,而且也會造成周圍土體物理力學性質的變化。這種復雜的力學行為會對隧道工程產生影響,甚至引發安全事故[1-5]。因此在地下水的影響下,地下工程的設計與施工面臨很大的挑戰。
Plaxis 2D 有限元分析軟件可以對上述力學行為進行模擬。本文以青島地鐵 1 號線盾構隧道工程實際地質條件和相關測量數據為基礎,通過 Plaxis 2D 有限元分析軟件,構建盾構隧道模型,進行地下水對盾構隧道掘進周圍土體變形的影響和分析,并將分析結果與現場實測結果進行了對比驗證。
1 Plaxis 2D 盾構隧道模型建立與土體變形計算
1.1 盾構隧道模型的建立
此隧道開挖范圍內穿越 5 層土體,從上到下分別是:①素填土;②粉質黏土;③中、粗砂;④粉質黏土;⑤含黏性土礫砂。所以地層模型分為 5 層。實際隧道拱頂埋深 7.6~12.0 m,洞徑 6.2 m,建模取隧道中心線距地表 10.7 m。隧道襯砌結構采用均質圓環,厚度為 0.3 m,橫向剛度取 0.75。模型選用 15 節點三角形單元。在劃分網格過程中,全局疏密度選擇中等,而且為了保證隧道周圍網格劃分的質量,在隧道周圍進行了加密類組操作,如圖 1 所示。

圖1 安子站 — 安子東站區間隧道模型

表1 土體參數
1.2 模型參數的確定
土體本構模型為Mohr-Coulomb 模型。根據現場實測數據進行土體參數選取,結果如表 1 所示。
1.3 Plaxis 2D 有限元計算結果
根據勘察結果,區間地下水類型主要為第四系孔隙潛水、微承壓水和基巖裂隙水。其中第四系孔隙潛水含水層主要為填土,接受側向逕流、大氣降水及海水潮汐補給,以側向逕流排泄為主,場地內水位受潮汐影響小。為考慮地下水對盾構隧道施工圍巖變形的影響,首先模擬地層無地下水的情況,再模擬地下水位發生變化時候的情況,包括 4 種不同地下水位,標高分別為:-10 m、-7.6 m、-5 m、-3 m。考慮施工效應對數值模擬的影響,模擬施工順序為:初始自然狀態—開挖導致地層損失—襯砌—注漿。開挖完成時進行一次計算,為開挖即時響應,這時變形量較小。襯砌并注漿后,變形量趨于穩定,這時再進行一次計算,可以與之前的結果進行對比。計算結果以隧道周圍土體位移云圖表示,見表 2。各工況下土體最大位移記錄于圖 2。
通過對比地下水不同標高情況下隧道周圍土體變形量可以發現,在初始開挖階段(無襯砌、注漿),周圍土體最大位移量隨著地下水升高而增加,由 2.113 mm增加到了 11.73 mm,后者大約是前者的 5.5 倍。這和山區公路隧道采用鉆爆法開挖施工時,周圍土體變形受地下水影響的變形規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6-7]。在襯砌、注漿之后,土體最終階段的變形量在 15~18 mm 的范圍內變化,變化量并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地下水位為 -5 m 時,最終位移量達到最小值,地下水位升高或降低土體最終位移量都增大。-5 m 大約是第一層土層素填土和第二層土層粉質黏土的交界處。粉質黏土的滲透性極差,可以看作不透水層。所以當地下水位在②粉質黏土以下時,隧道周圍土體的有效應力隨地下水位升高而減小,而當地下水位在②粉質黏土以上時,隧道周圍土體的有效應力隨地下水位升高而增大。這可能與隧道周圍土體最大位移量隨地下水位升高而先減少后增加有關。

表2 隧道周圍土體位移云圖

圖2 不同地下水位下隧道周圍土體最大位移量

圖3 DC24 監測面橫向地表沉降曲線
2 實測結果對比分析
安安區間盾構隧道布置有 38 個地表沉降監測面,監測面垂直于盾構隧道軸線方向。主要監測面的監測點一般為 9 個,次要監測面的監測點為 2 個。現選取一典型主要監測面 DC24,其地下水位為-3.4 m。對盾構開挖完成時和注漿完成時 2 個時間節點上的地表沉降數據進行分析。位于開挖隧道軸線上方的監測點沉降量最大,兩邊沉降量逐漸減小,如圖 3 所示。開挖完成時,最大地表沉降量為-11.27 mm;注漿完成時,最大地表沉降量為-18.15 mm。這與 Plaxis 2D 數值模擬結果中地下水位為-3 m 的情況具有較好的一致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 Plaxis 2D 數值模擬結果的正確性,對實際工程具有較高的指導性。另外,注漿完成時,地表最大沉降量為-18.15 mm,并沒有超過 GB 50911-2013《城市軌道交通工程監測技術規范》中-30 mm 的控制值,地表沉降量在安全的范圍內。
3 結論與展望
(1)通過有限元軟件 Plaxis 2D 的模擬,發現在初始開挖階段(無襯砌、注漿),周圍土體最大位移量隨著地下水升高而增加,并且增加量較大。地下水位為-3 m 時,土體最大位移量是無地下水時的 5.5 倍左右。數值模擬結果與實際監測結果具有一致性。
(2)在襯砌、注漿之后,土體最終的變形量在不同地下水位情況下變化不是很大。在本文所述的地層條件下,土體最大位移量隨地下水位升高而先減少后增加。這可能與土體的有效應力變化路徑有關。
目前地下水對隧道工程的影響機理分析雖然有一些成果,但還不是很深入清晰,造成了許多隧道施工、運營階段的地下水問題無法預期,只能在出現之后采取治理,造成大量損失。因此,建立科學合理的地下水預報機制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減少隧道地下水事故發生。除此之外,關于地下水問題的相關規范也需要進行進一步完善,如公路隧道防水標準、地鐵防水標準等。只有進行科學的研究,才能夠建立完善的科學機制,從根本上解決隧道施工地下水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