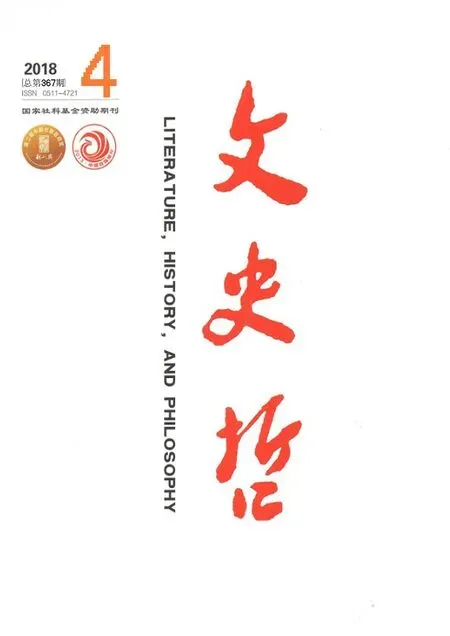論牛女傳說在古代詩歌中的反映
趙逵夫
“牛郎織女”傳說是我國形成最早、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民間傳說,織女的原型是秦人的始祖、因“織”而名垂青史的女修,牽牛(牛郎)的原型是周人始祖、發明了牛耕的叔均。“牽牛(牛郎)織女”傳說的形成是周秦早期文化交流的結果*參見趙逵夫:《再論“牛郎織女”傳說的孕育、形成與早期分化》,《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4期。。由于它所表現的思想與漢代以來不斷加強的門閥制度相抵觸,故元代以前文獻中沒有關于這個傳說的較完整的敘述。但是它一直在民間流傳。西周以來的詩篇中,有一些零星的反映,有的表現了某些情節,有的寫到某些情節要素。存留下來的這類作品中,有個別民歌,而更多的是文人的作品。雖然這些作品的著眼點不完全一致,但總體上可以使我們看到它的基本情節,同時又可以看到它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傳播與分化的狀況。其中有些作品此前未引起學者們的注意,今加以論證,以為研究“牛郎織女”傳說提供一個方面的材料。
一、反映牛女傳說根源的詩歌
(一)先秦時代詠牛女的詩歌
“牽牛織女”的傳說自西周末年即已在民間廣泛流傳。大體作成于公元前9世紀中葉的《詩經·小雅·大東》中說:

《詩經·秦風·蒹葭》為秦襄公時作品,當成于公元前8世紀六七十年代。這首詩表現一個人一直想靠近水對岸的“伊人”而總無法靠近的情節。其第一章云: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第二章、第三章文字稍異,而同第一章一樣,都是表現一個男子迫切希望靠近自己追求的人,卻總無法靠近的思念。關于這首詩的詩旨,學者們看法分歧,但當代大部分學者認為是表現了愛情的主題。詩中寫“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正是初秋季節,同自古相傳牛女相會于夏歷七月初七的時間一致。“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同《古詩十九首》中《迢迢牽牛星》一詩所表現的情節也一致。朱熹《詩集傳》云:“伊人,猶言彼也。一方,彼一方也。”“在水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朱熹集注:《詩集傳》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76頁。這同《古詩十九首》的《迢迢牽牛星》一詩中說的“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意思是一樣的。《迢迢牽牛星》是從織女角度言之,《蒹葭》則是從牽牛角度言之。西周以前,秦人居于西犬丘,即今甘肅天水西南、禮縣東北部、西和縣北部的一大片地方,正當漢水的上游地帶(西漢水、東漢水在西漢以前是一條水,西漢之時由于地震,上游東流至略陽而淤塞,故南折而流入長江,與沔水分為二)。那一帶有幾條水交匯,又有丘陵,正與《蒹葭》所寫景況一致。晉代甘肅詩人傅玄的《擬四愁詩》中說:
牽牛織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無由。
也同《蒹葭》所寫一致。1975年12月在湖北云夢秦簡中出現了兩段有關牽牛織女的文字,其第三簡中言“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年,棄若亡”(“亡”同“無”,言織女棄之而去,若無其人),同后代傳說中牛郎織女婚后又分離的情節一致。這說明牛女傳說在先秦之時已經形成*參見趙逵夫:《由秦簡〈日出〉看牛女傳說在先秦時代的面貌》,《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又成書于東漢末、曹魏初的《三輔黃圖》一書中載,秦始皇之時,引渭水入咸陽,其上架橋,取法牽牛織女橫渡天漢相會的情節*書中記載:“始皇窮極奢侈,筑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帝宮,象紫居;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見何清谷:《三輔黃圖校釋》卷一《咸陽故城》,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2頁。,可見牽牛織女傳說在秦人群體記憶中的深刻印象。
在周族群中,情形也是一樣。《詩經·周南·漢廣》也是以“牽牛(牛郎)織女”傳說為背景的。因為在1950年代有的學者尚主張“牛郎織女”傳說的悲劇情節形成于魏晉以后,所以人們對《漢廣》一詩的理解同對《蒹葭》的理解一樣,一直突不破舊的思想觀念的束縛。《漢廣》第一、二章如下: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第三章與第二章相近,只是個別字詞有變化。喬木,即高大的樹木,“不可休思”,言不可在它下面休息停歇,即不可靠近。這是比喻天漢邊上的游女,因其地位太高,自己不能靠近。詩中每章都說漢(實指天漢)太寬,不是可以游過去的;太長,也不是可以繞過去的。然而追求者的態度,如歐陽修《詩本義》所理解:“薪刈其楚者,言眾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眾女雜游,我欲得其尤美者。”*歐陽修:《詩本義》卷一,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第8頁。抒情主人公是男子。詩言雖女方地方高,但他永遠不放棄。我以為這正是表現了三千年前牽牛織女的傳說。詩的第二章、第三章還說如女方要過來,他會備馬去接,表現出極端的熱情與迫切心情。全詩總的是表現了牽牛不懈追求與無比思念的情形。《古詩十九首》中的“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河漢女”其實也由“漢之游女”而來。梁朝女詩人劉令嫻有《答唐娘七夕所穿針詩》,是貴族婦女對一個并不認識的女娘所贈詩的答詩,其開頭說:“倡人效漢女,靚妝臨月華,連針學并蒂,縈縷作開花。”似南方乞巧中有讓樂人扮作織女者。“漢女”即《詩經·周南·漢廣》中的“漢之游女”,指織女。這是南北朝之時人以“漢之游女”即織女之證。
《漢廣》與《蒹葭》是分別產生于周秦兩地的最早的詠“牽牛織女”傳說的民間歌謠。
將《詩經》中的《大東》《蒹葭》《漢廣》三篇聯系起來看,牽牛織女有關傳說在西周末年已初步形成。《蒹葭》、《漢廣》分別產生于秦國與漢水流域的周南之地,不是偶然的。以往受《詩序》的局限只在“文王之化”的說教中打轉轉,而一直未能揭示出其傳說上的根據。我們揭示出其藏在作品背后的本事,不僅有利于認識詩歌本身所包含的豐富內容,也有利于對于我國“四大民間傳說”中影響最大的“牛女傳說”形成、傳播過程的研究。
(二)漢代詠牛女的詩歌
漢魏間人所著《三輔黃圖》中載始皇“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是秦人對于牽牛織女記憶的具體的表現。至西漢之時,在長安西南昆明湖兩側立了牽牛、織女二石像,體現牽牛織女被阻隔天漢兩側的古老神話*書中記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于池之東西,以象天河。”見何清谷:《三輔黃圖校釋》卷四,第254頁。。這又同以周人為中心的關中一帶人們的群體記憶有關。可見“牽牛織女”傳說在周人、秦人群體記憶中印象之深,與這個傳說對周秦文化的影響之大。大漢帝國的空前統一與強大,漢王朝同周邊少數民族和西域各國的頻繁交往,不用說也進一步擴大了牽牛織女故事的傳播。昆明池邊這一對石像,在東漢班固的《西都賦》、張衡的《西京賦》中也都寫到*班固《西都賦》:“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云漢之無涯。”張衡《西京賦》:“昆明靈沼,黑水玄阯。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見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一《西都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頁;《文選》卷二《西京賦》,第65頁。。
產生于漢代的《古詩十九首》之《迢迢牽牛星》,全詩描寫牽牛織女隔著河漢流淚悲傷的情節,為人們所熟知。傳為枚乘之作的《蘭若生春陽》也是以“牽牛織女”傳說為題材的,卻一直為人們所忽略。詩云: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愿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在云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嘆戀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
此詩應為西漢末年民間之作,是以牽牛的口吻抒發了對織女的想念之情,與《迢迢牽牛星》正好各寫一方*參見趙逵夫:《〈迢迢牽牛星〉〈蘭若生春陽〉二詩關系淺談》,《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2期;趙逵夫:《〈玉臺新詠〉所收〈枚乘雜詩〉作時新探》,《西北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美人在云端”一句同《詩經·周南·漢廣》中“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的意思相近。
如果還在以往的思維定勢中認為西漢之時不可能有以“牽牛織女”為題材之詩,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學者們公認產生于西漢末年之書中所載歌謠為證。漢代《易林》的《夾河為婚》一首(“屯之小畜”繇辭)為:
夾河為婚,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
這是一首民歌,在《易林》中又見于“臨”之“小過”。又《天女推床》一首(“大畜之益”繇辭)中說:“天女推床,不成文章。”用《詩·小雅·大東》的句意,明顯是寫織女的孤獨憂思甚明(“床”即機床,指織機)。則“牽牛織女”的傳說從西漢至東漢一直流傳于民間。如說“牽牛織女”的傳說在漢代沒有流傳,只能說在南方和東南一帶尚未流傳開來。在東南、南方的流傳應在漢末三國社會動蕩中,一些北方人開始南遷之后,尤其在西晉之末很多士族豪門大批南遷之后。
可見,從西周末年直至漢代,牽牛織女的傳說在西北以至整個北方已廣為流傳,并多次出現于歌謠之中。這同《秦簡·日書》中已寫到牽牛織女婚后不足三年織女即離去的情形是一致的。
東漢末年蔡邕的《青衣賦》中說:“非彼牛女,隔于河維。思爾念爾,惄焉且饑。”*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校注:《全漢賦校注》下冊,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23頁。又其《協初婚賦》(即《協初賦》)中說:“其在近也,若神龍彩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云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校注:《全漢賦校注》下冊,第941頁。這篇賦是寫男女婚姻之合協的,所謂“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備乎夫婦”。所寫牽牛披云沿漢水而求織女的文字,與《蒹葭》一詩意境頗為相近。
以前學者們都以漢代以前詠牽牛織女之詩只有《古詩十九首》中的《迢迢牽牛星》一首,這是由于受到經學思想等的觀念束縛,使我們不能將《蘭若生春陽》等作品同“牽牛織女”傳說聯系起來。秦簡《日書》中說“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睡虎地秦墓竹簡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48頁。,為我們提供了捅破堵隔我們思維的那一層薄膜的利刃。但多年中對這段文字及《日書》中另外兩段相關文字的解釋也受以前某些學者關于“牛郎織女”傳說產生時代看法的影響,未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現在可知,從西周至東漢,牽牛織女的傳說一直在民間流傳,吟詠“牽牛織女”傳說之詩不下六首。
(三)魏晉南北朝以來詠牛女的詩歌
魏晉南北朝詠牛女之詩詞中有不少也表現出牛女傳說的基本情節及同周秦文化的關系。
魏曹丕《燕歌行》一詩中說: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幾句詩反映出牽牛織女本為夫婦,因罪而被隔在銀河兩岸。詩中的“爾”為復指,即“你們”。“辜”即罪。這顯然反映了牽牛、織女被天帝分在天漢兩側的情節,但究竟因何罪被分離,傳說中不是很清楚,不過隔離在“星漢”兩岸是清楚的。“河漢”“星漢”實都是由漢水上游(即西漢水)而來。
齊梁之間詩人王僧儒有《為人傷近而不見詩》,開頭兩句:“嬴女鳳皇樓,漢姬柏梁殿。詎勝仙將死,音容猶可見。”以下言及自身的憂慮:“我有一心人,同鄉不異縣。異縣不成隔,同鄉更脈脈。”然后說:“脈脈如牛女,何由寄一語。”詩由牛女之事想及自身,又言如牛女之相隔不能相親。則“嬴女鳳皇樓”正是寫出織女同秦人的關系,秦人為嬴姓,少昊之后。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故以鳳鳥為圖騰,其后裔有鳳鳥氏、玄鳥氏、伯趙氏等。元代傅若金的《七夕》寫道:
耿耿玉京夜,迢迢銀漢流。影斜烏鵲樹,光隱鳳皇樓。云錦虛張月,星房冷閉秋。遙憐天帝子,辛苦會牽牛。
寫“天帝子”而說到“鳳凰樓”。比傅若金稍早的元代作家劉秉忠的七律《銀河》一詩中也說:“一道銀河萬里橫,遙看似接鳳凰城。”下面寫七夕之夜牛女相會。其中又說到“鳳凰城”,反映出傳說中潛在保留的有關傳說本事之根源。明代小說《牛郎織女傳》中寫到織女、牛郎婚后也是居于鳳城之鳳凰樓。可見這部小說是吸收了一些較早傳說的。如其卷二《鳳城恣樂》一節,說牛女成親一月后,天帝令“送歸鳳城居止”,“離了宮禁,送歸鳳城”。下一節《天孫拒諫》中也說:“自歸鳳城,半毫不念及職事”,“一在鳳凰樓并肩凝眺,則在珠翠幙對飲笙歌”。書末詩中也說:“鳳城聚首夢重圓。”
杜甫流寓秦州期間所作《天河》云:
常時任顯晦,秋至輒分明。縱被微云掩,終能永夜清。含星動雙闕,伴月照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詩的前四句都是寫天河。第三聯的下句“伴月照邊城”由天河而聯系及秦州(今之天水市秦州區)。當時之天水在今秦州區之西南七十里,當今秦州與禮縣一帶。天水之得名,即由天河而來。早期秦人居于漾水河與漢水(今之鹽官河,晉南北朝以后看作西漢水的正源。早期秦人靠近漾水,以之為漢水源頭)交匯處,用所居之地的水名“漢”命名天上的星帶,然后將秦人始祖因“織”而名留青史的女修來命名天漢邊上最亮的一顆心,稱為“織女星”。杜甫所居近其地,故借以抒發感情。其第二聯兩句含有對“安史之亂”前唐朝政治的感慨在其中。末句似表示了對于秦州一帶少受戰亂騷擾的慶幸。杜甫在秦州所作五律《蒹葭》中有“秋風吹若何”和“叢長夜露多”之句,也作于秋季,傷賢者之失意。杜甫還有五古《牽牛織女》,也應作于秦州之時,詩中所表現思想感情同上兩首一致。前人誤編至居夔州之時,乃是只以詩的體式為斷,以為五古之作皆不在秦州,實誤。這些作品雖屬政治感懷,但字里行間透出詩人對于牛女傳說同秦地關系的了解。
(四)關于織女、牽牛在天際方位的反映及誤解
晉初著名詩人陸機的《擬迢迢牽牛星》一詩中說:“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這是言牽牛在向西北方向回轉,織女向東南方望牽牛。謝靈運《七夕詠牛女詩》中寫織女“徙移西北庭,竦踴東南顧”,是說織女在西北的庭院中徘徊焦急等待,又有時提起腳跟向東南面張望。因為織女雖有心,但她因其所處的地位,不能隨便活動,只有牽牛在無休止地設法走近織女,卻總是不能。這同前面所說《詩經》中《漢廣》《蒹葭》二詩所表現是一致的。這兩詩是最早表明織女星、牽牛星在天際的方位的作品。《史記·天官書》:“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張守節《正義》:“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也。”*司馬遷撰,裴骃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311頁。此言織女星在天河以北。其實織女星在天河以東,與早期秦人在漢水上游、漾水河以西,周人在今隴東馬蓮河流域的方位大體一致,只是織女星稍偏北,牽牛星稍偏南。所以,這早期的幾首詩反映出了織女星、牽牛星的正確方位,也反映出牛女傳說同周秦文化的關系。
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的《漁家傲》(別恨長長歡計短)云:“河鼓無言西北盼,香娥有恨東南遠。”詩人李復的古體詩《七夕和韻》中說:“東方牽牛西織女。”北宋末葛勝仲的《鵲橋仙·七夕(涼飆破暑)》中說:“天孫東處,牽牛西望。”(上句是言織女本在西而東處以會牽牛)南宋吳詠的《七夕聞鵲》中說:“黃姑(按指牽牛)西不娶,織女東未嬪。”元代趙雍的七絕《七夕》二首其二說:“牽牛河東織女西。”同時的詩人李序有七古《七夕篇》,其中說:“河西織女天帝子,今夕東行見河鼓。”(“河鼓”指牽牛)以織女在天河之西或言西北,以牽牛在天河之東或言東南。表述都是正確的。因為天河從北向南并非由正北向正南,而是上部偏東,下部偏南。故南宋時周紫芝《牛女行》言“靈河南北遙相望”,也無大錯。
晉以后,有的人在這上面就犯糊涂了。晉初蘇彥的《七月七日詠織女詩》中說:“織女思北沚,牽牛嘆南陽。”這就完全錯了(水之北為陽。以“南陽”與“北沚”相對,牽就對仗,也欠嚴謹)。而南朝梁殷蕓《小說》竟據此說:“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武文主編:《中國民間文學古典文獻輯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73頁。于是此后很多論牽牛星、織女星者都將方位搞錯。
真正引起學者們關注的是杜甫的《牽牛織女》開頭兩句,今本各種杜集中均作:“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其實牛女相會是織女由河西走向河東,是“出其西”,牽牛原在河東,是“處其東”。故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說:
“牽牛”“織女”四字宜倒轉。牽牛三星如荷擔,在河東;織女三星如鼎足在河西。公涉筆偶誤耳。*浦起龍:《讀杜心解》第一冊卷一之四,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133頁。
我以為杜甫原詩本是作“織女出河西,牽牛處其東”,是后來的編集、整理者輕易改動而成現在的樣子。推測被改動的原因有二:一,詩題作“牽牛織女”,“牽牛”在前,“織女”在后;二,舊注以為該詩表現了“三綱”中“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思想*王嗣奭《杜臆》卷四《牽牛織女》一詩云:“蓋以牛女無私會之事,以興男女無茍合之道。又以男女之合,比君臣無茍合之意也。”然而看杜甫此詩末二句云:“方圓茍齟齬,丈夫多英雄。”似杜公對于夫妻間一有矛盾總是丈夫一方有理,且對妻子蠻橫摧殘以至休去,并不認同。,故疑原詩以織女在前與詩意有違,是傳抄中形成的竄亂,故加以對調。這就引起清人戚學標的辯駁。戚學標《七夕》一詩云:
織女不在東,牽牛不在西,何故杜陵老,詩乃顛倒之?東西既易位,心志安得齊?*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4401頁。
如上所說,在杜甫之后李復、趙雍等已有意無意地作了糾正。但此后還是有人因杜詩中的這兩句而犯錯誤。如北宋張商英的《七夕歌》開頭說:“河東美人天帝子”,“河西嫁得牽牛夫”。南宋王之道《次韻魯如晦七夕》寫織女:“明朝河漢隔,西向望牽牛。”所以戚學標所針對的不僅是杜甫一人。我想杜甫可能是冤枉的。
總之,從晉至清代,在大部分人的詩作中以織女在天河之西或西北,牽牛在天河之東或東南,是清楚的。宋代以后所存杜詩《牽牛織女》文字上有問題,致使此后個別詩人行文錯誤,本不足怪。但時至今日還有個別學者犯糊涂,就很不應該了。因為這既不合于實際,在意識上也完全抹殺了牛女傳說同周秦文化的關系,從學術上來說,是極其膚淺、輕率的表現。
“牛郎織女”傳說是有悠久歷史的,歷幾十年地下的考古挖掘和早期秦史與先周歷史的探索,為我們打開了一扇又一扇可以看到很多以前未知現象的窗戶,我們應該對有些問題進行認真思考,細心研究,作出正確的結論,而不能因循守舊,以訛傳訛。
二、反映牛女傳說情節要素的詩作
據《淮南子》佚文,烏鵲架橋的情節在西漢初年已經形成。但是,還有些傳說要素是從歷史文獻中看不出來的,如什么時間形成牛郎作為一個農民的身份特征的?古代民間傳說中,最早的說法是玉帝(天帝)發怒將他們分別處于天河兩岸,后來變為王母將他們分隔在天河兩岸,這個轉變是什么時間形成的?北方傳說中是王母在牛郎快要趕上織女時,在二人之間劃出一道河來,形成天河;而近代南方傳說中則是織女自己離開,是織女自己劃出了一道天河將牛郎與自己隔開,這個分化是什么原因?還有,牛郎所養的牛具有靈性,也是在幾個情節的形成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母題,這是什么時間出現的?等等。下面我們借古代詩詞對傳說中的一些要素加以窺探。
(一)“鵲橋”描寫及其在某些詩中的誤解
白居易《經史事類六帖·史事類》卷九引《淮南子》文:“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唐代韓鄂《歲華紀麗》卷三引《風俗通》:“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風俗通》即《風俗通義》,東漢應劭所著。故如前所說,牽牛織女鵲橋相會的情節西漢時已產生。按理,至東漢之時傳播應更為廣泛。古代大部分的詩作中都寫到烏鵲(喜鵲)架橋的情節。元初趙秉文的《七夕與諸生游鵲山》中更說:“靈仙役鵲渡河去。”古代的傳說中認為是有仙人令烏鵲為橋的。這同北宋張耒《七夕歌》中“神官召集役靈鵲”,有靈官專門司其職的表現是一致的。
“牽牛織女”傳說傳至南方以后,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之一是出現了“星橋”的說法。這是由于詞義的誤解而形成的。南朝著名詩人庾信《七夕詩》:
牽牛遙映水,織女正登車。星橋通漢使,機石逐仙槎。隔河想望近,經秋離別賒。悉將今夕恨,復著明年花。
庾信這里說的“星橋”是指“星河”上之橋。“星河”即銀河。如西晉王鑒《七夕觀織女詩》:“隱隱驅千乘,闐闐越星河。”南朝齊張融《海賦》:“浪動而星河如覆。”庾信之父庾肩吾的《七夕》詩中說:“倩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雕陵鵲是寓言中的巨鵲,見《莊子·山木》。“填河”,這里指群飛于河面上成為橋。因為河谷處總低于兩岸,故言“填河”。詩中言“填河未可飛”,是說不可驟然飛去,以免織女踩空。庾信所接受“牛女相會”中的情節要素,不可能同他父親的完全不同。只是因為庾信的作品影響大,有的文人又未能理解原文之義,產生了誤解。陳后主的《同管記陸瑜七夕四韻詩》中說:“星連可作橋。”這也就可以看出這個以宮體詩見長,成日只知道玩弄詞句的亡國之君的學養。唐天寶詩人梁锽的《七夕泛舟》寫牛女相會,后四句先說:“片歡秋始展,殘夢曉翻催。”接著說:“卻怨填河鵲,留橋又不回。”意思是烏鵲填河架橋使她(織女)渡過之后,并不撤去,而是等她天亮前再渡河回去。可見“填河”只是架橋之鵲很多而已。劉禹錫《七夕二首》其二:“神馭上星橋。”這未必如陳叔寶之理解而應同庾信之“星橋通漢使”一樣。李清照《行香子》(草際鳴蟲)云:“星橋鵲架”,便說得最為清楚。
南宋趙長卿《滿庭芳·七夕》中說:
星橋外,香靄菲菲。霞軺舉,鸞驂鵲馭,穩穩過飛梯。
寫到“星橋”,也寫到“鵲”,只是鵲的任務變成了“馭”,而不是駕橋。這就產生了另一個混亂。我認為“鵲”與“鸞”非同類,在人們的意識中不在同一檔次,“鸞驂鵲馭”的“鵲”似乎是“鳳”字之誤。《樂府詩集》卷四十五載晉《七日夜女歌》,寫牛女相會,其第八章云:“鳳輅不駕纓,翼人立中庭。”南朝梁詩人何遜《七夕詩》中說:“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潢。”王筠的《代牽牛答織女》末二句:“奔精翊鳳軫,纖阿警龍轡。”蕭綱《七夕》中說:“紫煙凌鳳羽,紅光隨玉駢。”陳叔寶《同管記陸琛七夕五韻詩》中說:“鳳駕今時度,霓騎此宵迎。”由陳入隋的詩人王昚《七夕詩二首》其一說:“天河橫欲曉,鳳駕儼應飛。”初唐沈叔安《七夕賦詠成篇》:“彩鳳齊駕初成輦,雕鵲填河已作梁。”唐高宗李治《七夕宴縣圃二首》其一:“羽蓋飛天漢,鳳駕越層巒。”其二中又說:“霓裳轉云路,鳳駕儼天潢。”北宋晏幾道《蝶戀花二首》其一:“喜鵲橋成催鳳駕。”南宋陳著《江城子·七夕風雨》開頭:“紛紛都說會雙星,鵲橋成,鳳驂迎。”元、明、清時代詩詞中提到“鳳輅”“鳳軫”“鳳輦”“鳳駕”“鳳驂”的詩詞也不少,且多“鳳鸞”并列之例。據此,則“鸞驂鵲馭”本作“鸞驂鳳馭”。作“鵲”恐是后人因其寫七夕應有鵲而輕改。這樣看來,趙長卿這首詞所寫“星橋”,應如劉禹錫、李清照之作,是指星河上之鵲橋。
又宋初楊億的《七夕》詩中“鵲橋星渚有佳期”,“星渚”即星河之渚,也從另一方面對“星橋”作了正確的說解。晏幾道《鷓鴣天·七夕》:“橋成漢渚星波外,人在鸞歌鳳舞前。”意思也一樣。
但因為不少詩中出現“星橋”,很可能作者也并未弄清是怎樣的含義,只是照前人之句嵌入。于是,明代小說《牛郎織女傳》中便將“星橋”作為了天上的一個景點。其第二卷即有《星橋玩景》一節。由此即可以看出古代詩詞對后來小說戲劇創作的影響。
古代詩作中還有一個“烏鵲銜石填河”的說法。中唐詩人王建七古《七夕曲》寫織女在相會前后的心情,中云:“遙愁今夜河水隔,尤駕車轅鵲填石。”將此前詩人說的“烏鵲填河”誤解為“精衛填海”那樣的銜石填河。北宋李復的《七夕和韻》是寫牛女故事和七夕風俗的詩中較長的一首。其前半寫牛女故事的部分中說:
銀潢七月秋浪高,黃昏欲渡未成橋。卻向人間借烏鵲,銜石欲半河已落。
詩中寫到烏鵲也是“銜石”造橋,承王建之意,同自西漢以來關于“鵲橋”的理解完全不同。又宋初楊億七律《七夕》(清淺銀河)“匆匆一夕填橋苦”,也是意思不清楚。按《淮南子》中說“烏鵲填河成橋”,不是說如“精衛填海”那樣銜石填海,而是很多烏鵲飛到天河上形成橋。李復同王建一樣將“填河”理解為“鵲填石”,才有了“銜石欲半”之說。齊梁間詩人范云《望織女詩》中“不辭精衛苦,河流未可填”,是以牽牛的口吻,言如天河可填平,他都愿意像精衛那樣去填,但這做不到。所以,其義同架橋沒有關系。唐沈叔安《七夕賦詠成篇》“雕鵲填河已作梁”,李嶠《奉和七夕兩儀殿會宴應制》“橋渡鵲填河”,都是指飛鵲在天河上搭橋,而不能成為“烏鵲銜石填河”,這是唐宋時代牛女傳說中普遍存在的情節的證據,注解相關詩者也不能不注意這一點。
由于“鵲橋相會”的故事產生得很早,流傳太廣泛,文人詩作中的這種誤解歧說,同“以星作橋”的說法一樣,終被廣泛而深入的民間傳說淹沒了。晚唐李商隱《七夕》詩中說:“鸞扇斜分鳳幄開,星橋橫過鵲飛回。”就是將“星橋”解作星河上的橋,即鵲橋,是明確回到了原點。李清照的《行香子》(草際鳴蟲)下闋云:“星橋鵲架”,便明白不過。南宋以后“烏鵲銜石”的說法很少有人提起*明湯顯祖七律《七夕·文昌橋上口占》首句“共言烏鵲解填橋”,是為牽就平仄格式將“架橋”說作“填橋”。明夏言《踏莎行·七夕》中也說“底須烏鵲為填橋”。“填橋”不詞,有語病。,一些含混的說法,也基本上消除了。
北宋梅堯臣五古《七夕詠懷》中說:
喜鵲頭無毛,截云駕辀車。
韓琦的七律《七夕》中說:
若道營橋真浪說,如何飛鵲盡禿頭。
南宋吳泳的五古《七夕聞鵲》二首其二:
獨有雕陵鵲,造梁河之滣。頻年事填河,頭禿弗愛身。
這些詩根據民間傳說為民間主流說法找到“證據”。喜鵲由于七夕為織女架橋、頭上的毛也被踩踏脫去的說法至今存在。唐末徐夤有七律《鵲》,其前四句云:
神化難源瑞即開,雕陵毛羽出塵埃。香閨報喜行人至,碧漢填河織女回。
此詩中雖然說到“填河”,但同時說“雕陵毛羽出塵埃”,則顯然與庾肩吾詩中“雕陵鵲”“填河”的意思一致。
(二)關于“云橋”的說法
南宋許及之的七律《次韻酬張巖卿七夕》第五句云:“因依‘鴻烈’成橋語”,即將烏鵲架橋之說追溯至《淮南鴻烈》(即《淮南子》)中“烏橋填河成橋而渡織女”之記載。
南朝梁蕭紀《詠鵲詩》:“今朝聽聲喜,家信必應歸。”烏鵲后來被叫做“喜鵲”,韓愈、李正封聯句《晚秋郾城夜會聯句》:“室婦嘆鳴鸛,家人祝喜鵲。”則中唐時已有“喜鵲”之稱。這同傳說中它為織女架橋,使牽牛織女得以相會的情節有關。上引梅堯臣《七夕詠懷》中也作“喜鵲”。南宋蔡伸的《減字木蘭花·庚申七夕》:“金風玉露,喜鵲橋成牛女渡。”都說明了這一點。
(三)因烏鵲誤傳而形成一年中只在七夕會面一次情節的形成
北宋詩人強至的七古《七夕》寫出不少流傳在民間的情節,對我們了解“牛郎織女”傳說宋代在南方流傳的狀況有很大參考價值。其中說:
世傳牽牛會織女,雨洗云路迎霞車。初因烏鵲致語錯,經歲一會成闊疏。牛女怒鵲置諸罪,拔毛髠腦如鉗奴。
天帝命牽牛、織女每七天相會一次,而喜鵲錯傳為七月初七會面一次,因而罰喜鵲任架橋之勞。晏幾道的《鷓鴣天·七夕》開頭兩句說:“當日佳期鵲誤傳,至今猶作斷腸仙。”南宋趙以夫的《夜飛鵲·七夕和方時父韻》中說:“佳期鵲相誤,到年時此夕,歡淺愁深。”元代張翥詞《眉嫵·七夕感事》開頭三句:“又蛛分天巧,鵲誤秋期,銀漢會牛女。”至今民間傳說中說七夕之后見烏鵲頭禿是受到懲罰(或言是織女過天河時踩去了其頭上的毛,或言車子輾去了頭上的毛,見前引宋梅堯臣《七夕詠懷》、韓琦《七夕》、吳詠《七夕聞鵲》)。
關于一年中牛女相會的次數,盛唐時詩人王灣提出一個看法。他的五絕《閏月七日織女》后兩句說:“今年七月閏,應得兩回歸。”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南宋姜特立的七絕《閏七夕》《閏七夕呈譙內知舍人》也是由此發論。
(四)關于牛女傳說主題及同七夕節關系的描寫
詠牛女故事的詩當中寫得好,而且反映了正確的理解和較好的思想情趣的作品很多,但也有些承襲著魏晉時形成的有意歪曲的說解,影響及后世。有的詩人則對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引《道書》云:“牽牛取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之中。”*宗懔著,姜彥稚輯校:《荊楚歲時記》,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42頁。這實際是土地高度集中的東晉與南朝統治者為愚弄廣大勞動人民所編造的情節。宋初劉筠的《戊申年七夕五絕》其一云:“天帝聘錢還得否,晉人求富是虛辭。”可謂一語中的。南宋許及之七律《仲歸以結局丁字韻二詩七夕乃連和四篇至如數奉酬》其四云:“聘錢猶欠入驅營,野語訛傳亂史青。”也是對此說的否定。雖然是文學作品,但也反映出作者的學識,很是難得。
張耒有七古《七夕歌》,所寫故事的基本情節,仍然是文人層面所傳播的殷蕓《小說》中所講“年年織杼機勞役,……容貌不暇整。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居遂廢纴織。天帝怒,責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那一套,但寫到七夕夜神官召集喜鵲架橋,及牽牛、織女離別之時千言萬語說不盡,而來接織女的龍駕已備好,天河邊上靈官怕誤了限定的時辰,一再督催上車開車的情節,“空將淚作雨滂沱,淚痕有盡愁無歇”,表現了一種深刻的思想,同《紅樓夢》中所寫元春省親后回宮前一段情節很相近。“天地無窮會相見”,立意也很好。從這個方面說,仍是歷代寫牛郎織女故事的詩中的優秀作品之一。
元代中期詩人方叔高的《七夕詞》:
織女女有夫,牛郎郎有妻。可惜不相守,夜夜河東望河西。一歲才一會,會合一何稀!吾聞河西有田郎可犁,云中織錦女有機,胡不一耕一織長相隨。長相隨,無別離。
從“夜夜河東望河西”一句看,過來相會,然后離去的是織女,故牽牛夜夜向河西望。詩人謂:天河之西也有地,何不讓牽牛即居于河西,牽牛耕地織女織布,一起生活?這是針對南方傳說中由織女主動離去這一情節而說的。方叔高為江州湖口(今江西湖口)人。這實際上對當地的傳說提出了懷疑,對這個變異的傳說中所體現的豪門士族的意識予以否定。
清戚學標《七夕》詩的后半云:
年年七夕會,一渡河之麋(趙按:借作“湄”)。既會輒又返,何如不渡為?豈惟人事迕,天上有乖離。不見奔月人,忘為后羿妻。帝孫本驕貴,益視田夫卑。天錢縱可貸,勸君勤耕犁。
戚學標是天臺齊召南之高足,于《說文》《毛詩》研究有成,著述豐厚。前面已說過,作為學者,他看出了杜甫《牽牛織女》一詩前兩句中的問題。他是浙江太平(今溫嶺)人,詩中言牛女分離是織女自己離牽牛而去的,原因是“益視田夫卑”。這與南方傳說中織女從牛郎口中套出藏其仙衣的地方,即穿上仙衣離去,牛郎追趕,快要趕上時織女拔出簪子在身后劃了一道天河將牽牛堵在天河另一面的情節是一致的。我之所以說這些情節及這種對織女的看法是牛女傳說由北向南傳播中形成的分化,反映了從西晉末年及以后幾次大批南遷的中原豪門大戶的意識,因為它同漢代的“迢迢牽牛星”所表現“終日不成章,泣啼零如雨”的情形完全相反。這說明近代南方民間文學中的這種表現不是憑空產生的,也不是近代才形成,它有著很深的歷史根源。
明末金陵人楊宛有《思佳客·七夕后一日詠織女》云:
迢遞佳期又早休,鵲橋無計為遲留。臨風吹散鴛鴦侶,遠近空傳鸞鳳儔。從別后,兩悠悠,封題錦字倩誰投。金梭嫞整愁添緒,淚逐銀河不斷流。
描寫牛女相會時間短暫引起的愁緒,十分細膩。其中“封題錦字倩誰投”之句,應是說織女。因為她出身高貴,下嫁農人,這由尾聯的二句即可看出。這反映了南方傳說不同的原始情節,與漢代古詩《迢迢牽牛星》的情節是一致的。顯然,他們婚姻的悲劇是家族、家長造成的。傳說的本質是反映人們對自由婚姻的向往與對門閥制度的批判。
三、反映人物稱說與變化的詩作
(一)由“牽牛”到“牛郎”稱說的變化與“河鼓”“黃姑”的誤會
織女的名字自古未變,但在牽牛(牛郎)的稱說上有變化,且也存在混亂。這主要表現在一些詩人騷客的作品中。
首先,稱牧牛者、牽牛農耕者為“牛郎”,至遲在西晉時已經出現。葛洪《神仙傳·蘇仙公》中說:“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為牛郎。”至唐代自然已成普遍之稱。
其次,牛女傳說中的牽牛在南北朝梁代殷蕓《小說》中已被稱作“牽牛郎”。在唐代民間稱作“牛郎”應已比較流行。中唐詩人孟郊《古意》:“河邊織女星,河畔牽牛郎。未得渡清淺,相對邀相望。”這里稱作“牽牛郎”,很可能是因為五言詩句子為“二三”結構,后面必須是三個字。為了補足字數而在“牛郎”之前加了“牽”。晚唐詩人胡曾《詠史詩·黃河》云:
沿流欲共牛郎語,只待靈槎送上天。
則直作“牛郎”。此后,詩文中稱“牛郎織女”者漸多。如兩宋之間陳淵《七夕閨意戲范濟美三首》其三:
祝君樽酒醉羅裳,此夜應須石作腸。幸自書生惡滋味,那堪千里羨牛郎。
這是民間的稱說進入文人筆下的表現。
(二)有的詩中稱牽牛為“河鼓”,在南方又音變為“黃姑”
在天文學著作或論星象之著作中稱牽牛星作“河鼓”,并無不妥。上古之時為測定日月及五星(金、木、水、火、土)運行位置所定坐標中有為人們所熟知的牽牛星和織女星,后來隨著天文學的發展,二十八宿另選兩個距黃道較近的星座代替了牽牛星、織女星,而名之為“牛宿”、“女宿”。又因為稱說中“牽牛星”與“牛宿(或稱牛星)”易混,在天文學著作中改稱牽牛星為“河鼓”。《太平御覽》卷六引《大象列星圖》:“河鼓三星在牽牛北。”*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六《天部六·星中》,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0頁。又《爾雅·釋天》:“河鼓謂之牽牛。”但“河鼓”是古代天文學的名詞,同牛女傳說沒有關系。有的詩人在這一點上思維不清,說“牛女傳說”中講到牽牛也稱作“河鼓”,這就不妥了。如中唐詩人徐凝《七夕》詩:“一道鵲橋橫渺渺,千聲玉佩過玲玲。別離還有經年客,悵望不如河鼓星。”南宋許及之七律《仲歸以結局丁字韻二詩七夕乃連和四篇至如數奉酬》其四中說:“河鼓牛郎隔河漢,成橋烏鵲為津亭。”同時李處權《賀新郎·再和》:“河鼓天孫非世俗。”元代李序《七夕謠》:“河西織女天帝子,今夕東行見河鼓。”這就造成了混亂。
古代南方“河鼓”又因音而誤作“黃姑”。梁武帝蕭衍《東飛伯勞歌》(《玉臺新詠》卷九作《歌辭》):“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白《擬古十二首》其一應即擬此,其中說:“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樂府詩集》卷四十一《相和歌辭》收元稹的《決絕詞三首》,第一首開頭為“乍可為天上牽牛織女星,不愿為庭前紅槿枝”,第二首卻作“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則出于模仿的原因甚明。他們要擬古,故稱說上依之,作為“古”的印記。他的五絕《白微時募縣小吏入吏臥內嘗驅牛經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白亟以詩謝云》末二句云:“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在他的意識中是并不誤的。然而,在“河鼓”誤作“黃姑”之后,又形成更荒唐的錯誤,竟以為“黃姑”是織女的代稱。南唐后主李煜的《落花》詩中說:“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竟然將織女變成了“黃姑女”,這可以說是典型的不學無術、只會玩弄字句的詩人。所以他只有亡國后的幾首詞有點真情。宋初西昆體詩人楊億七律《七夕》(東西燕子伯勞飛)中說“河鼓天孫信靈匹”,又說“定與黃姑享偕老”,“河鼓”“黃姑”出現在同一首詩中,不知他究竟是怎么理解的。
但楊億在另外一首詩中將“河鼓”處理為牽牛星在天漢邊上所處的位置,則消除掉了名稱上的沖突,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其《戊申年七夕五絕》其一說:“天孫已渡黃姑渚。”就解決了這個矛盾。同時這一組詩的第四首中說:“莫恨牛渚隔鳳州。”“黃姑渚”也稱“牛渚”,于理也順。南宋向子湮的《更漏子》一詞開頭即說:“鵲橋邊,牛渚上。”楊億的《七夕》(東西燕子伯勞飛)很可能是其早期的作品。
宋代學養深厚的著名作家宋祁的七律取楊億“黃姑渚”之說而張揚之。他的《七夕》兩首之一說:“烏鵲橋頭已涼夜,黃姑渚畔暫歸人。”其后韋驤《七夕》中又云:“漫道銀潢能限隔,未畏河鼓畏風波。”“河鼓”與上聯“銀潢”相對,與本聯“風波”平列,亦指河渚,即“黃姑渚”或曰“牛渚”。這樣,沖突便消解掉了。明代小說《牛郎織女傳》中即吸收了這一點。其卷一《牛女相逢》一節開頭即說:“天漢之西有黃姑渚,天孫于此浣紗,牛郎從此飲牛。”這是有學問、有頭腦的詩人針對南方民間的廣泛誤解、一些淺學文人在談牛女傳說、以七夕為題材作詩也常提到“黃姑”的情況下用的一種對策,同陳叔寶、李煜之流比起來,可謂天壤之別。
(三)關于牛郎、織女身份與性格特征的反映
南宋同時的三位詩人各有一詩點出了牛女傳說中“男耕女織”的身份特征,值得注意。一首是項安世的五律《紹興次韻趙卿閏七夕》,其后四句云:
耕織關民事,婚姻自俗訛。乾坤大務本,觀象莫蹉跎。
一首為許及之的七律《次韻酬張巖卿七夕》,其首二句云:
星文人事古難磨,女織男耕力最多。
在詠牛郎織女的詩中,第一次點出人物身份上“男耕女織”的特征。范成大《鵲橋仙·七夕》中從故事情節的角度提到這兩點:“雙星良夜,耕慵織懶,應被群仙相妒。”也表現出男耕女織的農民的身份。
元代郝經有《牽牛》一詩,40句,前16句寫牽牛所居之環境,意為迎織女處:“野花照天星,星中花亦盛。長夏蔓草深,疏籬掩斜徑。”“堂陰青錦帳,墻背紫苔瑩。”完全是一片農家居處的景象,其描寫的具體細致,很有小說家想象鋪排的特色。下面說:
時方鵲橋成,佳節當秋孟。織女能翦裁,天河洗尤稱。女以秋為期,郎將花作證。風雨開云屏,鸞皇鏘月鏡。
織女雖本為天仙,但其特長還是剪裁女紅,及在天河中洗衣之類婦女干的活計。
元代方叔高《七夕詞》云:
織女女有夫,牛郎郎有妻。可惜不相守,夜夜河東望河西。一歲才一會,會合一何稀。吾聞河西有田郎可犁,云中織錦女有機。胡不一耕一織長相隨。長相隨,無別離。
方叔高為江州湖口(今江西湖口縣)人。南方七夕節側重于乞巧活動,不太講牛郎織女的故事,有的地方情節上也有分化,如以織女是哄騙牛郎找到仙衣后自己去等。方叔高的詩反映出當地傳說中牛郎、織女本是農民(織女在同牛郎在一起之時是農民),是清楚的。
明清之間吳景旭《滿江紅·七夕》之首二句:“女織男耕,不過一阿家翁耳。”也是把牛郎織女純看作農民。
從有關神農氏及神農時代的傳說和史前階段的地下考古發掘看,我國從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時期開始,即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形態(從采集農業到種植農業)。在奴隸社會時期已是一個農業國家,進入封建社會后,自耕農人數不斷增加。至20世紀中期,仍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為農業人口。男耕主要解決吃的問題,附帶提供有關穿、住、取暖、燃料的材料;女織,主要解決穿的問題,同時又協助耕種收割。“牛郎織女”的故事是中國幾千年農業經濟社會的高度概括的反映。
古代詩詞中寫到織女之巧的地方很多,如“誰能重操杼,纖手濯清瀾”(李治《七夕宴懸圃二首》其一),“織女能翦裁”(郝經《牽牛》),“金梭飛飛擲煙霧,織作青鸞寄幽素。青鸞織成不飛去,仙郎脈脈愁無語。”(明初張以寧《七夕吟同張士行賦》)
蕭齊時詩人范云所寫《望織女詩》以牽牛的口吻表現之。“盈盈一水間,夜夜空自憐。”寫出一個地位低而鐘情農民的心態,寫得很生動。我們后面還會談到。有的詩中甚至寫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南宋初年王庭珪的七絕《牽牛》:
一泓天水染銖衣,生怕紅埃透日蜚。急整離離蒼玉珮,曉云光里渡河歸。*此詩見《全宋詩》卷二十五,第16876頁。然而卷六十二(第39026頁)又題作《牽牛花》,原文只有“朱”作“銖”,“飛”作“蜚”,“河”作“云”,其他全同,而歸于施清臣名下。
寫牽牛在與織女相會過之后,自己一個紅塵凡俗生怕遇到其他天仙,急急離開。歷來寫七夕牛女相會的詩作中,因為多同乞巧風俗相聯系,絕大多數是從織女角度寫,從牽牛(牛郎)角度寫的很少。再則此前寫織女渡河去會牽牛,都是龍車鳳駕,儀仗排場,此詩所寫似乎只有織女一人,匆匆來去。所以,更接近于民間傳說。而且首句“一泓天水染銖衣”以“天水”代指天漢,正揭示出今甘肅“天水”地名之來源。漢武帝改上邽郡為天水郡。《漢書·地理志下》:“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11頁。《水經注》:“上邽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龍出,風雨隨之,故漢武帝改為天水郡。”《秦州記》亦言:“郡前有湖,冬夏無增減,故有天水之名。”《水經注》“水有白龍出”云云,帶有傳說的性質。“白龍”實隱喻秦。《史記·高祖本紀》言高祖醉斬白蛇,即“白帝子”。以白于五行配西。天水湖在禮縣東北部之故“天水縣茅城谷”,即今草壩鄉草壩村。村里今存宋代《南山妙勝廨院碑》言:“唐貞觀十三年賜額‘昭玄院’、‘天水湖’,至本朝太祖皇帝登位,于建隆元年將昭玄院賜敕皇改‘妙勝院’,天水湖改‘天水池’。”天水的得名就因為地處西漢水上游秦人發祥地之故。天水后又名“秦州”,也歸因于此。
(四)傳說中的玉帝和王母
北宋張商英的《七夕歌》后四句寫牛郎織女何以被分隔在天河兩岸云:
貪歡不歸天帝怒,謫歸卻踏來時路。但令一歲一相逢,七月七日橋邊渡。
張商英是蜀州新伊(今屬四川)人,所寫情節與殷蕓《小說》中所寫一樣,應是上層社會所傳,顯示了同廣大人民群眾不一致的另一個層面的傳說。詩中所寫阻礙了牽牛、織女正常家庭生活的是天帝。
周紫芝有七古《牛女行》和《七夕》,從對牛女傳說的描寫方面說,則更為細致生動。其《牛女行》云:
天孫曉織云錦章,跂彼終日成七襄。含情倚杼長脈脈,靈河南北遙相望。天風吹衣香冉冉,烏鵲梁成月華淺。青童侍女驂翔鸞,玉闕瓊樓降華幰。明朝修渚曠清谷,歸期苦短歡期遠。昔離今聚自有期,天帝令嚴何敢違。
此詩于情節、場面的描寫上細致生動,很可傳誦。詩中說“天帝令嚴何敢違”,反映了當時安徽一帶傳說中左右牛女境遇的也是天帝。
楊億《七夕》詩中“天孫已渡黃姑渚,阿母還來漢帝家”,是聯系《漢武故事》言之,“阿母”指西王母。楊億為建州浦城(今屬福建)人。晏殊七律《七夕》中說:“天孫寶駕何年駐,阿母飆輪此夜來。”以上兩詩都是“天孫”與“阿母”并提,則北宋時民間流傳中,同織女的命運相關的人物還有王母。明末朱一是《一寸金·辛丑閏七夕與柳耆卿調異》:“此夜方平,還同王母,羽輦投何處。”*朱一是:《梅里詞》,《續修四庫全書》第17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頁。則同近代傳說一樣,作“王母”。今北方民間傳說中都說織女為玉帝和王母的外孫女,是同古代的傳說一致的。
(五)牛郎織女故事中的“牛”與牽牛花
關于牛女傳說故事中的牛,古代詩詞中也有所涉及,至少是注意到這個傳說的因素。如唐代末年詩人王建《宮詞》中說:“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宮中乞巧要擺有木刻的牛,可見唐代“牛郎織女”故事中牛已是一個獨立的角色。又北宋劉筠的《戊申年七夕五絕》之第四說:“淅淅風微素月新,鵲橋橫絕飲牛津。”楊億《七夕》(清淺銀河暝靄收):“誰泛星槎見飲牛。”宋祁《七夕兩首》其二:“西南新月玉成鉤,奕奕神光渡飲牛。”據張華《博物志·八月槎》所寫,飲牛者即牽牛。然而這里指出“飲牛”,則不是如“牽牛”的為專有名詞。這也為后代小說中特別地寫到一條老黃牛作了一個鋪墊。前引張澍《牽牛贈織女》中說“我亦飲吾牛”,王樹楠詩《織女贈牽牛》中的“牛兮莫使扣爾角”,《牽牛復織女》中的“只管牽牛不服箱”等,都提到牛。《織女戒牽牛》一詩中“莫忘牛衣臥泣時”一句,雖然“牛衣”本指供牛御寒的披蓋物,但也同民間故事中牛郎披著牛皮追織女至天上的情節有一定聯系。
南宋釋元肇《牽牛花》一詩云:
星河明滅映籬根,風露開成碧玉溫。曉色未開忙斂恨,柔條無力絆天孫。
這是說牽牛花應代替牽牛(牛郎)纏住織女,不要讓她離去,但它未能做到。這是從另一個方面同牛女傳說故事聯系起來。
宋末林逋山的《牽牛花》:
圓似流錢碧剪紗,墻頭藤蔓自交加。天孫滴下相思淚,長向秋深結此花。
言說牽牛花是因織女思牽牛而流淚,至人間變成花。這是關于牽牛花同牛女傳說關系的另一種說法。
由這可以看出,在民間從古以來廣大人民都將牛女傳說故事同現實中的很多現象聯系起來。我們前面提到的喜鵲頭上脫毛(因入秋換毛)等都是突出的事例。這反映牛女傳說自古以來的深入人心。
南北朝以后興起的格律詩多是抒情之作,即使敘事性很強的作品,也只是寫到鵲橋相會這個主干情節或某些情節要素。但我們由這些零星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到“牛女傳說”在民間流傳的情況及一些要素。
由于這個長期流傳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傳說故事同幾千年封建禮教,尤其同漢代獨尊儒術以后“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封建禮教的對立,而遭到統治階級及其文人的排斥與掩蓋。在“牽牛織女”的傳說中,最突出地體現了它的主題思想的是織女這個人物,是她愿意同一個牽牛人生活在一起,才有了這個故事。以至于上層統治階級及其文人造出受天帝之命救助董永的“七仙女”來混淆視聽,替換織女在廣大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消除她在廣大人民心中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是,在牛女傳說上鬧出最大笑話的三個人,一是梁武帝蕭衍,寫出“黃姑織女時相見”的句子;二是陳后主陳叔寶,誤讀庾信之詩,寫出“星連可作橋”的句子;三是南唐后主李煜,寫出了“迢迢牽牛星……粲粲黃姑女”的句子。這應該不是偶然的。在這似乎偶然的表現上有很多必然的原因包含其中,讀者可以自己去思考。
四、以牽牛織女口吻所作之詩
南北朝詩人有關牛女傳說與七夕的詩作中,有一些是用了牽牛和織女的口吻,它既反映了當時關于牽牛織女傳說的情況,對后來“牛郎織女”故事的戲劇、小說創作也有一定啟發,可以說是民間戲劇的濫觴。
(一)南北朝詩人以牽牛、織女口吻所作之詩
詠牛女之事而分別以牽牛、織女口吻所寫之詩最早有南朝詩人顏延之的《為織女贈牽牛詩》、沈約的《織女贈牽牛詩》、范云的《望織女詩》和王筠的《代牽牛答織女詩》。顏延之《為織女贈牽牛詩》曰:
婺女儷經星,姮娥棲飛月。慚無二媛靈,托身侍天闕。閶闔殊未輝,咸池豈沐發。漢陰不夕張,長河為誰越。雖有促宴期,方須涼風發。虛計雙曜周,空遲三星沒。非怨杼軸空,但念芳菲歇。
婺女,即女宿,二十八宿之一。本來牽牛星、織女星因是天空中最亮的星,命名早,遠古之時人們用為觀察日、月、五星運動的坐標。后來隨著天文學的發展,因牽牛星、織女星距離黃道較遠,故二十八宿中另選二星座以代替之,一曰牛宿,一曰女宿(亦名婺女)。本詩作者以織女的口吻言,自己不如婺女、姮娥之能侍于天闕。這里是以牽牛為天上之星神,故云。經星,即木星,也稱歲星。“閶闔殊未輝,咸池豈沐發”雜用《離騷》與《詩經》之典,表現了織女對牽牛的真摯感情。詩的末六句表現了織女對牽牛只能等到七夕才能相會的安慰之情。
沈約《織女贈牽牛詩》曰:
紅妝與明鏡,二物本相親。用持施點畫,不照離居人。往秋雖一照,一照復還塵。塵生不復拂,蓬首對河津。冬夜寒如此,寧遽道陽春。初商忽云至,暫得奉衣巾。施衿已成故,每聚忽如新。
織女說自己的粉黛等紅妝之具和明鏡上面滿是灰塵,只有每年秋天到來才拭一次。這體現了古人所謂“女為悅己者容”的意思。詩通過寫鏡子而將織女忠于愛情的內心世界揭示出來。古人將五音同四季相配,商音配秋,因而用“商”代指秋季。“往秋”與“初商”相對而言,指每年的七月之初。“每聚忽如新”一句表現了對織女忠貞愛情的贊頌。
范云的《望織女詩》是以牽牛隔著天河遙望織女時的口吻寫的:
盈盈一水邊,夜夜空自憐。不辭精衛苦,河流未可填。寸情百重結,一心萬處懸。愿作雙青鳥,共舒明鏡前。
表現了牽牛由于自己地位的低下,不能與織女在一起的自我可憐,及積極爭取長期在一起的決心。然而環境無法改變,只是懷著深深的感情,抱著一個良好的愿望而已。
王筠《代牽牛答織女詩》曰:
新知與生別,由來儻相值。如何寸心中,一宵懷兩事。歡娛未繾綣,倏忽成離異。終日遙相望,只益生愁思。猶想今春悲,尚有故年淚。忽遇長河轉,獨喜涼飚至。奔精翊鳳軫,纖阿警龍轡。
“涼飚至”也是指時至初秋。“翊”即飛。“鳳軫”即鳳車,指織女所乘。“纖阿”,神話中御月運行的女神,也用以指善馭者。“龍轡”猶言龍駕,指以龍為御的車。詩中將牽牛相遇時的歡喜與即將分離的悲憂情緒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四首詩,可能先是沈約、范云擬顏延之之作,或二人大體同時動筆;王筠則因三人之作有意和之。四首詩各有意趣。
齊梁之際的詩人謝脁的《七夕賦》中有以織女口吻所作歌一首,也屬此類。歌曰:
清弦愴兮桂觴酬,云幄靜兮香風浮。龍鑣蹀兮玉鑾整,睠星河兮不可留。分雙袂兮一斷,何四氣之可周?
表現織女同牽牛臨別時心情,撫琴而內心悲愴,互敬桂花酒以謝。接織女者的一切準備工作就緒,所以織女看著星河再不能牽延不行。“分袂”用《九歌·湘夫人》中“捐余袂兮江中”的典故。詩中寫牛女相會是由織女渡河到牽牛一邊來,這同近代很多年畫中織女從橋上過來,牛郎和孩子迎上去的情節是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后代相關傳說中的一些情節甚至細節,也都是在民間長久流傳中形成。
(二)唐以后詩人以牽牛織女口吻所作的詩
唐代的戴叔倫有《織女詞》一首,完全是用織女的口吻寫的。詩如下:
鳳梭停織鵲無音,夢憶仙郎夜夜心。難得相逢容易別,銀河爭似妾愁深。
“仙郎”指牛郎,因為牛郎(牽牛)也是天上的星神。末句表現織女的情感深沉真切而不落舊的窠臼,寫出了多少男女分隔兩處的婦女的悲愁!
晚唐曹唐的《織女懷牽牛》也可歸于此類。詩云:
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封題錦字凝新恨,拋擲金梭織舊愁。桂樹三春煙漠漠,銀河一水夜悠悠。欲將心向仙郎說,借問榆花早晚秋。
“封題錦字凝新恨”之句及上面所講以牽牛、織女口吻寫的代言體的詩作,對后代的戲劇小說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第一部反映這個民間傳說故事的通俗小說明代的《牛郎織女傳》中,牛郎、織女表情達意就往往各吟一詩。至于從元代開始產生的有關牛女故事的戲曲作品,不用說主要是由詞曲聯結起來,以代言體的形式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動,展示情景和表現情節的發展的。
宋末蒲壽窚的一首七絕雖題作《七夕》,但完全是以織女的口吻來寫的:
盈盈一水望牽牛,欲渡銀河不自由。月照纖纖織素手,為君裁出翠云裘。
末句中的“君”聯系第一句看是指牽牛。全詩是織女在孤獨與思念中織素時的自白。織女在分離之時為牽牛織出衣裘,也是他人所未道。
元代初年詩人方夔的《七夕織女歌》完全是以織女的口吻寫的一首歌:
牛郎咫尺隔天河,鵲橋散后離恨多。今夕不知復何夕,遙看星月橫金波。拋梭擲纴愁零亂,彩鳳飄飄度霄漢。重來指點昔游處,香奩寶篋蟲絲滿。一年一度承君顏,相別相逢比夢間。舊愁未了新愁起,已見紅日銜青山。當初漫道仙家別,日遠月長不見接。不似人間夫與妻,百歲光陰長會合。
描寫織女在七夕相見之后的心理細致感人,其所推想也皆合于情理。末四句實際上借著以天上與人間的比較,對上層社會中婦女的生活處境表示了同情。尤其說“重來指點昔游處”一句,蘊含了對過去經歷的回顧,使敘述含有了時間上的立體感。比起只是寫織女的排場與鵲橋相會中的壯觀環境來,情節性更強一些。末四句是對于將他們分離兩處的極大的怨恨。“不似人間夫與妻,百歲光陰長會合”,包含著對上層社會一些婦女由于門戶之見所造成婚姻悲劇的同情。
清代甘肅著名學者、詩人張澍《養素堂詩集》中有《牽牛贈織女》、《織女答牽牛》各一首。其《牽牛贈織女》:
絳河漲鴻波,帝子渺何處?恨望待靈查,金鳳吹殘暑。生別倏一年,寸心填離緒。何期聚今宵,玉露濕白纻。鳳軫莫稽遲,龍鑣莫延佇。涼夜靜無聲,婉孌定華余。白榆影自橫,丹桂香如許。橋架雕陵毛,藥成抃握杵。我亦飲吾牛,尋歡來前渚。相見翻緘愁,暫停七襄杼。未盡繾綣懷,虬漏催蓮炬。思逐浮云飛,脈脈不得語。
曲盡情愫,多感人之句。末二句言相見后未盡情懷,織女返回的時刻已到。“虬漏”指上有虬龍裝飾的漏壺(古代計時器具)。“蓮炬”指接其返回天宮的侍衛所持火炬。其《織女答牽牛》云:
一別頓經年,膏沐若為態。相思水一涯,坐使針黹廢。妝鏡凝暗塵,璇閨織愁字。夏日浩苦長,幕外靜尨吠。火逝商飆來,蹀足整龍轡。修渚水盈盈,清暉想昵愛。消息芻尼通,投杼玉釵墜。暫得侍衣巾,款情寫未易。明睞飛霞莊,桂觴莫辭醉。憶昔結發時,聘錢為君累。謫居悵河梁,恨無晨風翼。會促夜已闌,贈君盈衿淚。*張澍:《養素堂詩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5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1頁。
“幕外靜尨吠”用《詩經·國風·野有死麕》的典故,言尨之吠不吠皆無關,本無生人至也。兩詩分別從牽牛、織女二人的角度抒發思念之情,將一些情節在表白中帶出。
這種以織女或牽牛口吻為詩的表現方式到戲曲產生之后便很少有人采用。近代王樹楠卻用它寫出了四首佳作。其《織女贈牛郎》云:
年來理我機上絲,為郎織就云錦衣。牛兮莫使扣爾角,背上穩穩馱郎歸。
《牛郎答織女》云:
茫茫大界起風波,為避風波莫渡河。我心堅比支機石,肯向君平眼底過。
又《織女戒牛郎》云:
從古仙凡無定種,前身郎是牧牛兒。而今得意來天上,莫忘牛衣臥泣時。
《牛郎復織女》云:
府庫空虛道路荒,天殘夭猾更披猖。從今河上逍遙去,只管牽牛不服箱。*王樹楠:《陶廬詩續集》卷十一,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編:《西北文學文獻》第十五卷,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第385、386頁。
直如戲曲的佚曲。由之可以看出這種表現方式對同題材戲劇作品的推動作用。其中《織女戒牽牛》中說的“前身郎是牧牛兒”一句,也很符合牽牛由人(叔均)變為星名(牽牛星),又由之而變為民間傳說故事中人物的過程。最末一首末句中的“牽牛”不是星名或人名,而是一個動賓詞組,是要注意的。
王樹楠為清末民初學養深厚又具有現代科學意識的學者,曾入張之洞幕府、充清史館總纂,是否對“牽牛織女”傳說的本事也有所思考,今不可知。當然,本詩中其實也反映了作者對當時政治形勢的一些憂慮,只是以平靜心情出之。在這一組詩的前面有《七夕》七絕四首,在《牛郎答織女》和《織女戒牛郎》之間又有《七夕》七絕四首。
總之,以上這些作品在有關牛郎織女傳說的戲曲與小說出現以前從不同方面反映古代民間傳說的大體狀況,除作品在內容、表現形式、構思語言等方面的藝術創造之外,在“牛郎織女”傳說的豐富、發展方面的意義,也不容忽視,它們實際上是牛女傳說由詩歌向戲劇、小說的過渡。
從漢代至宋元,沒有完整、細致表現“牛女傳說”的小說、戲劇作品產生。我們只能從歷代文人的詩詞作品和不多的民間歌謠中窺見關于它的斑斑點點。而我們將這些斑斑點點組合起來觀察,也還大體可以看到它在民間流傳的情況。這樣,就不僅完全可以否定個別人認為“牛郎織女”完整故事形成很遲的種種看法,也可以使我們發現一些古代文學創作中值得重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