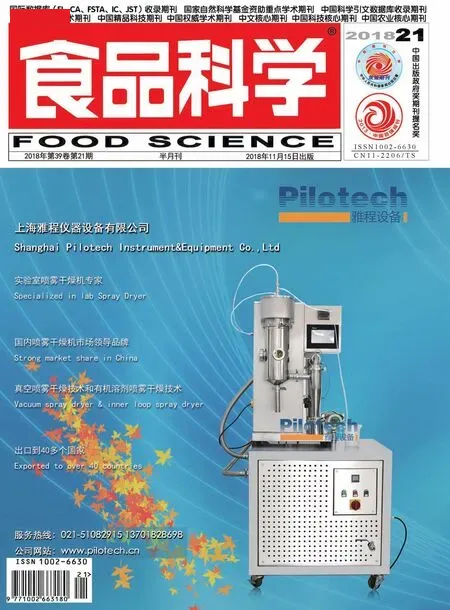家禽定點屠宰場不同屠宰區域空氣的微生物結構
戴寶玲,肖英平,孫鳳來,王佩佩,桂國弘,戴賢君,楊 華,*
(1.中國計量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農業科學院農產品質量標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1;3.杭州余杭區仁和街道農業公共服務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0)
雞肉在世界消費市場上是增長速度最快的優質肉類,其肉質細嫩、滋味鮮美,因其具有高蛋白質、低脂肪、低熱量、低膽固醇等營養特點,且供應充足、物美價廉,現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主要肉類食品[1]。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消費觀念也發生變化,開始越來越注重飲食的衛生。為了保障公共衛生安全,我國已經相繼在各個城市的主城區全面限制活禽交易,主張家禽“集中屠宰,冷鮮上市”[2]。但有些屠宰場條件差,空氣不流通,屠宰環境中可能存在不同種類微生物;而雞肉食品營養豐富,是微生物生長的良好載體,其在屠宰和加工過程中的污染很難避免,如果控制不好將導致產品變質,影響產品貨架期,甚至引起食源性疾病的發生[3-4]。目前對雞肉加工和運輸銷售過程中微生物污染的研究較多,如屠宰加工過程中產生的交叉污染[5]。朱國良等[6]2014年調查了寧波市場生雞肉微生物污染情況,發現有沙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和單增李斯特菌等污染。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屠宰各環節和銷售中雞肉微生物和特定食源性致病菌,對于屠宰場各屠宰區域中空氣微生物研究較少;然而空氣中的沉降微生物對雞肉表面污染和屠宰場工作人員的健康有重要影響,因此對家禽定點屠宰場的空氣微生物結構特征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為雞肉食用安全提供有利依據。傳統的基于分子生物學研究微生物的方法主要有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熒光原位雜交、變性梯度凝膠電泳、克隆文庫分析等[7-8],這些方法只能檢測到部分微生物或者特定病原微生物,在種類和數量上有很大的局限性[9]。而近年來,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的迅速發展,其在分析微生物群落結構時,有著獨特的優勢,已成為微生物群落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10]。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與試劑
平板計數瓊脂(plate count agar,PCA)培養基杭州微生物試劑有限公司。
1.2 儀器與設備
恒溫培養箱 上海一恒科學儀器有限公司;離心機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PCR擴增儀 德國Biometra公司;HiSeq測序儀 美國Illumina公司。
1.3 方法
1.3.1 樣品采集
在浙江某家禽定點屠宰場不同的屠宰區域,包括掛禽間、宰殺瀝血間、浸燙間、脫毛間、凈膛間(包括凈膛和清洗),分別收集屠宰前和連續屠宰5 h后空氣微生物,具體方法為:把PCA平板均勻放在各區域四角和中間位置共5 個點,置于距地面1 m的高度,在同一時刻將5 個點的平板打開暴露5 min,隨即加蓋,置于37 ℃恒溫箱中培養48 h,取出計數取平均值。屠宰前平板編號為掛禽間(BH)、宰殺瀝血間(BSI)、浸燙間(BSC)、脫毛間(BD)、凈膛間(BE);屠宰后平板編號為掛禽間(AH)、宰殺瀝血間(ASI)、浸燙間(ASC)、脫毛間(AD)、凈膛間(AE)。
1.3.2 DNA提取及擴增
采用ZR Fungal/Bacterial DNA MiniPrep?試劑盒進行空氣平板微生物DNA提取。具體為:在無菌條件下,將500 μL無菌生理鹽水加入各PCA平板中,刮取平板中所有菌苔置于滅菌離心管中,各區域的5 塊平板樣品混合后離心,去除上清液,將沉淀重懸在200 μL無菌生理鹽水中,加入ZR BashingBead Lysis Tube,后續按照試劑盒說明書提取DNA,瓊脂糖凝膠電泳進一步檢測。
以提取的D N A為模板,引物為3 3 8 F(5’-ACTCCTACGGGAGGCAGCA-3’)和806R(5’-GGACTACHVGGGTWTCTAAT-3’),對屠宰場環境的細菌16S rRNA基因V3~V4區進行PCR擴增。
1.3.3 測序和質量控制
應用Illumina HiSeq測序儀高通量技術對屠宰場空氣的細菌16S rRNA基因的V3~V4區進行測序。
1.3.4 生物信息學分析
采用高通量技術對家禽屠宰場空氣中的細菌16S rRNA基因的V3~V4區進行測序,QIIME 1.7.0軟件(http://qiime.org/scripts/split_libraries_fastq.html)對獲得的序列進行篩選,得到高質量的DNA序列[11-12]。根據測序及計算的結果和聚類分析,得到一系列樣品序列概況值(序列數量、物種數量、Shannon指數、Simpson指數、豐度指數和覆蓋度指數),并繪制稀釋性曲線、菌群結構柱狀圖、菌群豐度熱點圖、菌群結構的主坐標分析圖等,從而反映屠宰場在屠宰前和屠宰后各個屠宰區域空氣微生物的多樣性及其豐富度。
1.4 數據統計分析
將屠宰場各個屠宰區域在屠宰前后空氣沉降的菌落總數的平均值轉化為CFU/皿,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ANOVA)來比較不同屠宰區域屠宰前后細菌數量或相對豐度的差異,對有顯著性差異的處理進行t檢驗。
2 結果與分析
2.1 屠宰場空氣沉降微生物數量

圖1 家禽屠宰場空氣菌落總數Fig.1 Total airborne bacterial counts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poultry slaughterhouse
如圖1所示,屠宰前和屠宰后不同屠宰區域的空氣沉降微生物數量有一定的差異,特別是在掛禽間屠宰后空氣沉降菌落總數比屠宰前高出71%,可能是因為屠宰中,掛禽間活雞多、密度大,通風換氣差;還有糞便干燥后隨著雞跳動會飄到空氣中,破壞了環境,也利于一些病原菌的生長;另外病原菌易于附著在雞咳嗽、鳴叫噴出來的小液滴上而進一步擴散傳染[13]。各個區域屠宰后菌落數都增加,只有浸燙間屠宰后菌落總數反而比屠宰前減少了60%,可能是因為浸燙間溫度高,燙毛水造成的水霧使空氣不流通,空氣中的微生物不易沉降。劉秀萍等[14]調查生豬屠宰前后的環境微生物,也檢測出一定數量的菌落。趙慧等[15]分析了屠宰場車間空氣微生物,認為這是肉制品污染的原因之一。
2.2 屠宰場空氣沉降微生物物種豐度及多樣性
通過對家禽定點屠宰場在屠宰前和屠宰后空氣微生物提取的DNA質控、篩選等處理,最終獲得159 658 條有效序列,屠宰前5 個屠宰區域采集樣品平均獲得19 075 條,屠宰后平均是12 856 條,兩組有顯著性差異(P=0.035)。根據聚類分析,所得測序結果如表1所示,各樣品最終獲得152~190 個操作分類單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在屠宰前后樣品分別平均獲得178 個和174 個OTU,兩組無顯著差異(P=0.968),各樣品的覆蓋度指數均為1,稀釋曲線均趨于平緩(圖2),說明測序的結果合理,幾乎覆蓋了屠宰場空氣中的所有物種,能夠反映樣品真實多樣性組成。進一步根據得到的OTU信息,用ChaoI指數、ACE指數、Shannon指數及Simpson指數來評估樣品微生物物種的豐富度和多樣性(表1)。

圖2 各樣品稀釋曲線Fig.2 Rarefaction curves showing bacterial community diversity

表1 樣品測序概況Table1 Summary of sequencing results for all samples
2.3 空氣沉降微生物結構
從微生物分類門的水平可知(圖3A),從家禽定點屠宰場5 個區域在屠宰前和屠宰后各收集的沉降空氣微生物中,主要包含厚壁菌門(Firmicutes)、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綠彎菌門(Chloroflexi)等。其中厚壁菌門、變形菌門和放線菌門是屠宰場空氣微生物的優勢菌門,分別共占每個屠宰區域每次采樣空氣微生物的84%以上,其平均相對豐度分別為45.41%(22.01%~63.28%)、34.82%(11.39%~48.84%)、12.19%(3.91%~29.60%),Kim等[16]研究屠宰過程中雞肉胴體微生物時,也檢出這3 種為優勢菌門。Kristiansen等[17]在研究豬舍空氣微生物時發現厚壁菌門、變形菌門和擬桿菌門為主要的微生物。屠宰前和屠宰后沉降菌種類大致相似,但屠宰區域之間或每個區域屠宰前后空氣微生物的相對豐度有差異,其中掛禽間和宰殺瀝血間的厚壁菌門在屠宰前的相對豐度都較高,而屠宰后分別減少了21.55%和33.80%。

圖3 家禽屠宰場不同區域空氣菌群結構Fig.3 Structure of airborne bacterial communities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the poultry slaughterhouse

圖4 家禽屠宰場不同區域菌群豐度熱點圖(屬水平)Fig.4 Abundance of bacteria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poultry slaughterhouse at the genus level
從屬的水平上分析(圖3B),屠宰場空氣微生物種類較豐富,微生物的相對豐度幾乎都在70%以上。優勢菌屬主要為葡萄球菌屬(Staphylococcus)和不動桿菌屬(Acinetobacter),其相對豐度分別為36.90%(19.46%~53.46%)和13%(4.68%~23.41%),有研究表明,肉雞在進入屠宰鏈時,它的羽毛、皮膚和糞便等都攜帶有大量的天然微生物,這些微生物會擴散到空氣中,在后續的屠宰過程中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導致肉雞的污染[18]。

表2 家禽屠宰場不同區域條件致病菌相對豐度Table2 Relative abundance of conditional pathogens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poultry slaughterhouse%
從微生物分類屬的水平上進一步分析,菌群豐度熱點圖(圖4)展示出,不管是在屠宰前還是屠宰后,各個屠宰區域空氣中的葡萄球菌屬(Staphylococcus)污染較嚴重,相對豐度均超過16%(表2),葡萄球菌屬是常見的革蘭氏陽性菌,廣泛存在于自然界,也是人體皮膚、黏膜的寄殖菌,可引起人和動物局部的化膿性感染,也可引發膿毒血癥、心內膜炎、腦膜炎等嚴重感染[19]。還檢測出屠宰場空氣中有不動桿菌屬(Acinetobacter)、寡養單胞菌屬(Stenotrophomonas)和埃希菌屬(Escherichia),均具有一定的致病性,屬于條件致病菌。其中不動桿菌屬細菌平均相對豐度為13%(4.68%~23.41%)(表2),其主要分布于外部潮濕的環境中,營養要求低,易生長,黏附力極強,在臨床上發生率大于70%[20],并且院內感染發病率依舊不斷升高。寡養單胞菌屬相對豐度變化范圍為0.62%~12.38%,它是革蘭氏陰性菌,是院內感染的重要菌種[21],該菌主要引起肺部呼吸道感染[22],是癌癥患者體內重要的病原體,特別是那些有阻塞性肺癌的[23],據研究統計被此菌感染后患有菌血癥的病人死亡率為14%~69%[24-25]。大多數埃希菌屬是人和動物腸道中的正常菌群,但逐漸也發現自然界中存在一些致病性的埃希菌屬,主要由正常菌群條件致病,以泌尿系統感染常見[26],也易引起呼吸道感染[27]。尤其是在屠宰場的脫毛間空氣微生物存在以上4 種條件致病菌較多,可能是因為脫毛間空氣潮濕,利于病原菌增殖,或者是由于脫毛機揚起的羽毛、灰塵等使得空中微生物增多。
2.4 空氣沉積微生物樣品的主坐標分析

圖5 各樣品細菌菌落結構的主坐標分析Fig.5 Principal coordinate analysis (PCoA) of the dissimilarity between airborne bacterial samples
根據各個樣品OTU計算樣品間的加權UniFrac距離,再對10 個樣品進行主坐標分析。如圖5所示,可以看出PCo1和PCo2分別解釋63.67%和20.77%差異性。各處理樣可以分為3 個集合,其中BH、BSI、BSC、ASC和AD聚集在一起,BD、ASI和AH相聚較近,BE和AE屬同一屠宰區域(凈膛間),空氣微生物種類及豐富度相近。
3 結 論
空氣中的微生物逐漸成為禽類肉制品的污染源[28],但對家禽屠宰場空氣微生物結構研究還鮮有報道,實驗發現家禽屠宰場的不同屠宰區域沉降菌數量存在一定的差異,并且屠宰生產后比屠宰前微生物數量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屠宰后掛禽間菌落總數比屠宰前高出71%。采用高通量測序技術分析家禽定點屠宰場不同屠宰區域空氣的微生物結構發現,厚壁菌門、變形菌門和放線菌門為空氣沉降微生物的優勢菌門,葡萄球菌屬和不動細菌屬為優勢菌屬,同時也發現存在一定量的葡萄球菌屬、寡養單胞菌屬和埃希菌屬,這些屬的細菌均為條件性致病菌。在后續雞肉的屠宰與加工過程中,雞肉存在安全隱患,由此說明有關食品安全部門應制定有效的干預措施,對家禽在加工過程中確保微生物安全是很重要的[29-30],本實驗對家禽屠宰場空氣微生物的檢查,為雞肉微生物污染的溯源和營造一個規范的屠宰環境提供了科學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