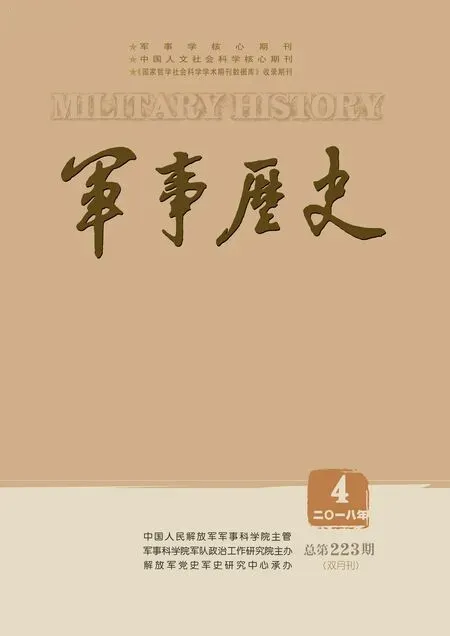海派文化視閾下的上海抗戰
——兼論上海抗戰文化的歷史地位
★
上海抗戰,實際上包括以兩次淞滬抗戰為主體的武裝抗戰和以民眾為主流的上海抗日救亡運動,這是上海抗戰中兩個既各具特色又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海抗戰的這兩翼,既系統而全方位地凸顯了上海抗戰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重要的歷史作用和地位,也深刻彰顯了海派文化的內涵和特性。
海派文化是以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上海區域性文化為基礎,揚棄并吸收近代西方工業文明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文化流派。這一文化流派通過長期的歷史積累與沉淀,形成了具有厚重歷史文化底蘊的別具一格的海派精神、海派風范和海派品格。在抗日戰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上海抗戰文化,則是上海抗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在民族戰爭烽火熏陶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隸屬海派文化體系的支脈,在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曾作出重大貢獻。
一、海派文化倡導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上海抗日軍民始終貫徹的一條主線
19世紀40年代上海開埠以來,這座江南水鄉小鎮在加入世界近代城市行列的同時,也飽含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國家恥辱、民族罹難和民生凋敞的歷史記憶。飽受苦難的上海人民,對于西方列強殘酷的民族統治和血腥壓迫有著切膚之痛,他們以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奮起反抗。上海近代化城市的發展過程,也是上海人民開展反帝愛國斗爭的過程。
以愛國主義為主線的民族精神,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中華民族屢遭外族入侵而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因,也是上海在歐風美雨包圍之中仍然中氣十足的根本原因。這種鮮明的城市文化特征,自鴉片戰爭以來,經過太平天國運動、上海小刀會起義、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中共誕生后的五卅運動、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等一連串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實踐洗禮,歷久彌新,鑄就了海派文化中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凸顯了堅定的民族性和頑強的斗爭性,也折射了上海抗戰的本質和主流。
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淞滬抗戰,從七七事變到八一三淞滬會戰,從孤島抗戰到太平洋戰爭后租界淪陷,直至迎接抗戰的最后勝利,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盡管一波三折,有高潮也有低谷,有公開沖突也有地下斗爭,有烽火疆場的浴血奮戰也有秘密戰線的腥風血雨,但不論形勢如何險惡,也不論付出多大代價與犧牲,卻始終沒有停止過。特別是全面抗戰爆發后,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攜手合作,共同抗日御侮。上海各個黨派團體,各界人士,廣大民眾,各行各業,男女老少,除了極少數漢奸之外,無不同仇敵愾,共赴國難。上海灘上,從資本家到工人,從洋行高級職員到棚戶貧民,從大學教授到青年學子,從文化名人到小商小販,從影星到舞女,都在愛國主義精神召喚之下,匯聚到同一個戰場,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致抗日,出現了上海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民性的抗日愛國斗爭的歷史場景。上海抗日救亡運動弘揚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折射出愛國主義的不朽光彩。特別是在兩次淞滬抗戰中,中國軍隊不畏強暴、英勇抗敵的偉大壯舉載入史冊。一·二八淞滬抗戰主要參戰部隊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他們順應民族的意愿和人民的期望,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高舉愛國主義旗幟,以民族自衛戰爭針鋒相對地反對日本的侵略戰爭,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捍衛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抗日將士眾志成城,涌現出許多悲壯的英烈人物和戰斗事跡。如三十六師進攻匯山碼頭之戰,“以血肉之軀”,“突貫攻擊”*《大公報》,1937-09-04。;九十八師姚子青營寶山城保衛戰,“孤軍殉城”,“為國效忠,可歌可泣”*龔傳文:《八一三淞滬抗戰回憶》,載《20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第1卷,341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十一師、十四師、六十七師將士打出了四次反攻羅店的“血肉磨坊”之戰*凌維城:《懷念抗日英雄謝晉元》,載《上海文史》第4輯,6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空軍的八一四空戰,閻海文跳傘身陷重圍而臨危不懼、殺身成仁;沈崇誨駕機撞擊敵艦與敵同歸于盡,忠骨未留;謝晉元率“八百壯士”決心“壯烈犧牲,以報國家”*《掃蕩報》,1937-10-31。,進行了氣壯山河的四行倉庫保衛戰。展現了中國軍人為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視死如歸、頑強戰斗的精神風貌。
與此相呼應,上海抗戰文化界的奮力抗爭,則更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和持久抗戰的堅定性。必須指出,上海抗戰文化在其發展的每一個關節點上,都及時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明確指導。盡管階段不同,斗爭目標和工作方針有所區別,但抗敵御侮斗爭主旨始終堅定不移。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抗戰文化斗爭的中心任務,是宣傳和鼓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號召全國人民一致奮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對日本占領東三省、反對日本侵略上海等。七七事變和八一三淞滬會戰期間,中國共產黨以上海抗戰文化為主要陣地,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以各種形式,全方位地展開文化藝術界的抗日救亡運動,其中心任務包括伸張中國人民團結御侮的正義立場、樹立日必敗我必勝的堅定信念、謳歌中國軍隊英勇抗敵的斗爭精神、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的險惡用心和法西斯暴行、動員民眾參戰、呼吁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支持等。“孤島”時期,留居上海的進步文化界愛國人士普遍受到迫害,進步的社會文化機構和文化團體被查封取締,上海抗戰文化運動在日偽殘暴殖民統治下轉入地下。中國共產黨根據上海所處的新環境,及時轉變策略方針,迅速改變大規模抗日運動的斗爭模式,由集中轉向分散,由公開轉向半公開或隱蔽。提出要采取各種斗爭藝術,“注入抗日反漢奸的內容”,利用租界尚未被日軍占領的特殊環境,壯大發展抗日力量,重建進步文化陣地,開創了“盛極一時的孤島文化”。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全面淪陷。根據上海出現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再次調整斗爭策略,強調“嚴格執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工作方針”,對上海抗戰文化給予明確指導,使其在內容和形式上,貫徹“灰色化”“大眾化”和經營管理“事業化”的方針*劉曉:《上海總結》(1940年4月30日),中央檔案館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爭得立足和生存地位的同時,隱晦曲折地、不屈不撓地開展著抗日救國的斗爭,既積蓄了力量,又發展了自己,并以新的戰斗的姿態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二、海派文化展示的“海納百川”的城市風范,為上海文化界的聯合抗敵奠定了基礎
上海是一個“海納百川”的國際化大都市,它不僅吸納了全世界的先進文化元素,也繼承了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形成中西合璧的現代文化。這種城市風范為上海文化界聯合戰線的建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客觀條件。
首先,上海是全國抗戰文化的發祥地,是抗日戰爭前期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更是全國文化界聯合抗戰的引領者。從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海在全國率先組成了聯系和團結文化領域一切主要力量的文化界抗日統一戰線。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上海的文化戰線形成了聯合作戰的陣勢,原先的左翼文化戰線與其他各個抗日黨派團體的文化力量,在“抗日御侮,共赴國難”的使命下并肩戰斗。上海文化各界不僅以鮮明的民族抗戰精神呼吁文化界的團結合作,而且以實際行動建立了文化統一戰線的各種組織,發動和進行了大規模的持續的抗戰文化和宣傳活動,為全國樹立了文化抗戰的榜樣。上海文化界堅持面向人民大眾,與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相結合的方向,并且在斗爭實踐中創造了許多成功的方法和形式。廣大文化人在抗日洪流中毅然走出書齋,沖破“亭子間”和文藝的“象牙塔”,以民眾喜聞樂見的文化作品提供于社會,使文化從少數文化人的手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人民大眾的抗戰利器,從而使文化與抗戰有機地融為一體。上海抗戰文化在這方面也為全國抗戰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經驗。
其次,上海抗戰文化運動是與國際上反法西斯力量和一切進步的文化運動息息相關、互為支援的。上海是中國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匯的中心,是聯接全中國、全世界的橋梁和紐帶,也是中國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與主要渠道。抗戰期間,以申城中外報刊為陣地的主要輿論戰線,對兩次淞滬抗戰和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作了及時報道和廣泛宣傳,讓全中國和全世界了解上海的抗戰,并通過了解上海的抗戰,進一步了解中國的抗戰,從而引起全中國和全世界的極大關注。申城報刊以大量篇幅,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世界各國政府的立場和態度,及時報道全國民眾、海外僑胞和世界各國人民的聲援和支持。強調中國抗戰必須聯合蘇聯,聯合英美,“我們的國際外交是以中蘇的密切結合為軸心,以英、美、法為維護的二重外交。”*張仲寶:《蘇聯的對外政策》,載《蘇聯革命與中國抗戰》,113頁,上海,三聯書店,1937。進一步堅定了國人抗戰的決心,增強了打敗侵略者的勝利信心。
再次,上海抗戰文化力量具有強勁的輻射力和延伸性,成為推動許多地方抗戰文化事業的生力軍。從八一三抗戰到上海淪為“孤島”前后,大批的上海文化人和文化團體,由盛極一時的上海抗日文化戰場陸續轉移到抗戰大后方和抗日民主根據地,把抗戰文化從大上海撒播到祖國的東西南北。他們當中,郭沫若、茅盾、陽翰笙、田漢、馮乃超、胡風等人,先后轉移到了武漢、重慶等地。丁玲、周揚、艾思奇、冼星海、沙汀、賀綠汀、呂驥、袁牧之、吳印咸、光未然、陳波兒等人,進入了延安和華北抗日根據地。丘東平、任光、夏征農、錢杏邨等人,進入了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這是上海抗戰文化的一次大規模轉移,也是抗戰文化新陣地的開拓。上海文化人以戰斗的姿態與當地的抗戰文化相結合,譜寫了各地抗戰文化聯合抗戰的光輝篇章。例如,在武漢成立的“全國劇協”“全國影協”“全國文協”等文化抗日救亡團體,基本上都是從上海轉移而來的文化界領軍人物,不少還是在他們的倡導和組織下成立和發展的。
三、海派文化不懈奮斗的創新品格,凸顯和提升了上海抗戰的歷史地位
上海抗戰文化的形成,經歷了抗日戰爭血與火的熏陶,一方面繼承了上海城市文明的海派風格,另一方面又為上海城市文明海派風格的建構增添了新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勃興于斯、斗爭于斯的上海抗戰文化,以其不懈奮斗的創新品格,成為凸顯和提升上海抗戰歷史地位的有力見證。
發生在上海的兩次淞滬抗戰,都是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戰役。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法西斯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發動對淞滬地區的武裝侵略,駐守上海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和前來增援的第五軍與上海民眾奮起抵抗,給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一擊,成為中國局部抗戰歷史進程中承前啟后的關鍵性一役。九一八和一·二八時期,上海爆發的武裝抗日斗爭和民眾抗日救亡運動,在世界上率先舉起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旗幟,揭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37年七七事變后僅一個月余,日本法西斯就把侵略魔爪伸向上海,遭到中國愛國軍民的頑強抵抗,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一場氣壯山河、震驚中外的八一三淞滬抗戰。七七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淞滬會戰,揭開了中國全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也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的東方戰場正式形成。而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上海是其發祥地和前期的中心。有鑒于此,上海一些文化工作者提出“表現上海”的口號,倡議“要抓住上海的個性,發掘上海的靈魂,歌唱上海的斗爭”,以便通過“正視上海的現實,理解上海的現實”,進而“理解抗戰中的祖國”*蔣天樞:《表現上海》,載《戲劇與文學》第1卷第3期,1940年5月。。上海抗戰文化人士以此為遵循,積極反映兩次淞滬抗戰和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斗爭史跡,宣傳上海抗戰的革命精神,總結上海抗戰的經驗教訓,涌現了一大批很有分量的上海抗戰作品。例如《上海抗日血戰史》《上海之戰》《上海浩劫記》《上海二十四小時》《上海大戰》《保衛大上海》《閘北孤軍記》《八百英雄》《姚子青》《上海的屋檐下》《夜上海》《放下你的鞭子》等,還相繼舉辦淞滬戰區遺跡繪畫展覽會、淞滬戰跡油畫展覽會,開設講座,組織報告會、演唱會等,直接反映兩次淞滬抗戰,反映上海抗戰時期的社會風貌,為上海抗戰留下了一大批彌足珍貴的文獻檔案資料,也見證了上海抗戰史跡的激昂悲壯。
上海抗戰文化是沿著開拓創新的路徑前行的,因而有力地印證了上海抗戰的歷史地位和時代意義。九一八事變后,上海先后成立了各種抗日救亡團體,其數量之多、范圍之廣、影響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至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全市已經組建了180多個抗日救亡團體,其中文化界抗日救亡團體就有70多個。這些抗日救亡團體大部分是由中國共產黨人參與或組織領導的,許多屬全國首創的,得到全國各地的效仿。1935年7月28日,上海的文化社團聯合組建了文化界的抗日統一戰線——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并創建了機關刊物《救亡日報》。同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告成立,更擴大了上海文化界的抗日陣地。一方面,發起成立這些文化社團的愛國文人,紛紛表示在國難當頭之際,全體文化界人士都應該拋棄門戶之見和新舊之別,聯合起來,團結一致,不做“專門唱歌娛樂人的‘百靈鳥’”,而是要做抗戰軍民的“感覺器官,思想神經,或是智慧的瞳孔”*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載《解放日報》,1942-03-11。,為抗日救國而努力戰斗。另一方面,他們又創造性地采取各式各樣的斗爭形式,包括出版抗日救亡的書刊,組織各種文藝宣傳隊,通過時評、話劇、電影、詩歌、小說、曲藝、篆刻等各種文藝形式,宣傳抗日救亡。特別是《風云兒女》《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在上海的誕生,更是轟動全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運動新局面。
應該指出,大批革命精英和愛國文化名人對上海抗戰文化的創新活動居功至偉。他們既具備優良的文化素養,又胸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人文品格。面對民族危亡、國難當頭的緊急關頭,他們身經兩次淞滬抗戰的炮火洗禮,滿腔熱情地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潮流之中,以戰爭為題材,從文化領域的各層面,與侵略者展開英勇斗爭,形成一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文化新軍,把上海抗戰文化推向高峰。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塊圣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推動下,上海抗日救亡運動與淞滬抗戰功績交相輝映,書寫了上海在民族解放斗爭史上的光輝篇章。歷史證明:上海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特殊貢獻和重要地位,將永垂青史。作為上海抗日救亡運動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上海抗戰文化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