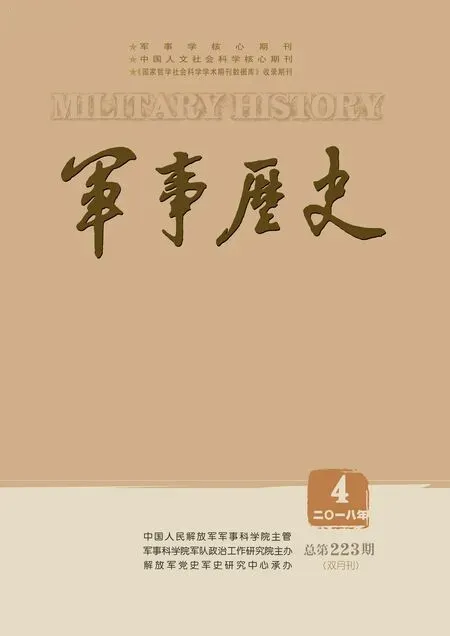從陸權走向海權的戰略思考
——基于雅典與斯巴達爭霸的歷史視角
★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戰爭。在27年的交戰中,雙方互有攻守,最終以陸權為主導的斯巴達人建立了強大的艦隊,在羊河口之役徹底摧毀了雅典的海上優勢,成為古希臘世界的霸主。海權之爭是世界軍事領域一個歷久彌新的主題,在許多關鍵的歷史轉折點,海上力量的強弱甚至影響著大國的興衰。
一、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形成
(一)自然環境是影響國家戰略的先決條件。不同的地理、水文和氣候衍生出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孕育出千姿百態的人類族群。雅典與斯巴達雖然都位于地中海東部的巴爾干半島,相距不到200公里,但是獨特的自然環境導致兩邦之間產生相去甚遠的地域文化。雅典城邦位于阿提卡半島,三面環海,綿延的海岸線使之具備了發展海上貿易的獨特優勢。城邦周圍多山地丘陵,不宜種植糧食作物,卻可以培育葡萄、橄欖等經濟作物。山區礦產資源豐富,能夠開采石料、銀礦和陶土,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雅典逐漸成為一個商業為主的海洋城邦。斯巴達城邦坐落于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拉哥尼亞平原,三面環山,只有南面靠海,海岸線平直,沿岸多礁石,出航的條件受到極大限制。“斯巴達”一詞的本意是“可以耕種的平原”,河流滋潤著城邦周邊的土壤,農業也因此得以發展,斯巴達自然而然地發展成一個農耕為主的陸地城邦。
(二)社會環境是推動國家戰略的重要因素。公元前16世紀,愛奧尼亞人進入阿提卡半島與當地的皮拉斯基人雜居,形成雅典最初的氏族部落。公元前8世紀,王權衰落,政權由氏族貴族執掌,廣大平民遭受不平等剝削,氏族內部的階級矛盾構成了雅典社會的主要矛盾,“跨出了摧毀氏族制度的第一步”*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4,9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隨著海上貿易的興起,工商業奴隸主的實力不斷增強,推動了一系列政治改革,雅典逐步走向民主化的道路。海外擴張、注重商貿和強調海權的思想成為雅典人的共識。相比之下,斯巴達的建立更為激進。公元前12世紀,斯巴達人南下定居拉哥尼亞平原,不斷擴大勢力范圍,迫使當地居民繳納賦稅。一批原住民試圖通過起義反抗,被斯巴達人鎮壓之后淪為奴隸。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矛盾構成了斯巴達社會的主要矛盾。奴隸主重點關注的問題是如何擴大農業生產,如何爭奪更多領土和如何鎮壓奴隸的暴動。因此,內陸擴張、固本安邦和強調陸權的思想根植于斯巴達人的血脈之中。
(三)戰略選擇決定國家的未來走向。國家戰略的選擇是綜合考慮戰略環境中的各方因素,為實現戰略目標而做出的合理選擇。戰略選擇受到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制約,深刻影響著國家的建設與發展。雅典的地緣環境適宜外向發展。綿延的海岸線和優良的港口資源使其具備發展海上力量的先天優勢。貧瘠的土壤迫使其必須通過對外貿易補給自身需求,海上交通線對于城邦生死攸關。另一方面,民主體制改革已經有效緩解了內部矛盾,雅典的外患遠高于內憂,因而更需要外向擴展,建立海上霸權。斯巴達的地理位置相對閉塞,不易向海外擴展。同時,城邦位置易守難攻,自然條件優厚,基本可以實現自給自足。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斯巴達幾乎不必擔憂外在威脅,卻時時需要關注國內的動蕩因素,城邦內部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起義和暴亂頻繁,因而需要內向發展,建立穩健型的陸上霸權。在正確的戰略選擇下,雅典擁有了一支強大的海上艦隊,而斯巴達鍛造出一支令人聞風喪膽的陸上力量。雅典與斯巴達日益強盛,逐漸成長為古希臘世界的雙雄。
二、海權與陸權的較量
(一)平衡的破壞。“各國之間的交往大多都是涉及重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地理考慮。”*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芙:《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77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在一段時期內,地理條件的限制使內向型和外向型的兩大城邦在各自的勢力范圍相安無事,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波斯帝國的介入攪動了平靜的局面。公元前490年,橫跨歐、亞、非三洲的波斯帝國向希臘本土發起進攻。無論是在經濟還是軍事領域上,波斯帝國的實力都遠遠超過希臘各城邦。強敵壓境,各城邦不得不改變以往相對孤立的關系,結成提洛同盟,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也加入其中,共同為民族存亡而戰。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較量中,雅典和斯巴達海陸兩大戰場發揮了自身的優勢,最終將波斯的勢力從歐洲驅逐出去。希波戰爭結束后,斯巴達退出提洛同盟,與原先的盟友重新結成伯羅奔尼撒同盟,古希臘世界形成兩大同盟對立的局面。
(二)“非對稱”的僵局。“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實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利益沖突和相互猜忌使兩大同盟之間的摩擦不斷升級,一場霸權爭奪戰拉開帷幕。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兩大同盟都決定避強擊弱,運用“非對稱”作戰,在各自最擅長的領域擊敗對方。雅典最初采取的是“伯利克里戰略”,即以海制陸,在陸上堅守城池不與斯巴達軍正面沖突,在海上派出艦隊不斷襲擾伯羅奔尼撒半島附近海域,阻礙海上交通運輸,試圖通過消耗逼迫斯巴達求和。斯巴達反其道而行之,從陸路進攻阿提卡半島,離間提洛同盟內部成員,試圖圍困和孤立雅典。雙方的“非對稱”作戰看似可行,卻只能營造均勢,無法贏得決定性的勝利。雅典雖然封鎖了科林斯海灣,使伯羅奔尼撒海上力量難以施展,但是斯巴達依靠本土資源,依然實現了自給自足。斯巴達雖然從陸上包圍了阿提卡半島,卻對雅典的海上運輸無能為力,戰爭陷入僵持狀態。
(三)“對稱”的終局。唯有在對手擅長的領域將其擊敗,才能實現最終的勝利。隨著戰局的發展,雅典和斯巴達都意識到僅僅憑借單方面的優勢是無法迫使對方屈服的,開始探索如何奪取海陸雙權。雅典選擇了向西西里發起遠征。西西里位于地中海中部,自然資源豐富,可以為雅典供給糧食和木材。此外,島上人口充裕,可以為發展陸上力量提供所需的兵源。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島內各城邦發生爭執,互相殘殺,雅典認為時機已到。維護海軍的高額成本和常年征戰的消耗已經使雅典略顯疲態,一舉拿下西西里可以贏得新的轉機。不幸的是,西西里遠征超越了雅典的戰略能力,不僅沒能實現目標,而且被隨后趕來的斯巴達軍夾擊,遠征軍幾乎全軍覆沒。斯巴達則向他們曾經的老對手——波斯帝國尋求援助。波斯雖然曾被提洛同盟趕出歐洲,卻一直渴望能夠恢復昔日的榮光,伯羅奔尼撒戰爭為之提供了一個契機。在戰爭后期,斯巴達承認了波斯在小亞細亞西海岸希臘各邦的統治,以此換取了軍事和經濟援助。波斯的支持打破了戰爭的平衡,斯巴達迅速建立起足以與雅典抗衡的海上力量。公元前405年羊河口之役,斯巴達軍全殲雅典艦隊,徹底摧毀其海上力量,曠日持久的戰爭終于落下帷幕。
三、從陸權走向海權的啟示
歷史上發展海權的國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先天型和后天型。先天型的代表例如雅典、西班牙、荷蘭和英國等海洋性比較明顯的國家,主要特點是多為海島或大部分國土與海洋相接,自然條件相對惡劣不宜發展農業,周邊存在大陸性強國,難以向內陸發展。在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驅動下,會自然而然地選擇走向海洋,憑借海上力量發展對外貿易,拓展海外殖民地,緩解國內的生存壓力。后天型的代表例如斯巴達、法國、德國和美國等陸地性比較明顯的國家,主要特點是國土面積較大,同時與大陸和海洋接壤,自然條件優厚可以實現自給自足,陸上軍事力量雄厚,周邊環境相對穩定。并在綜合國力增長到一定程度,或是陸上資源開發相對飽和時,會以陸權作為支撐,向海外尋求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一)發展海權是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海洋覆蓋了地球表面積的71%,是溝通世界各大洲之間的重要網絡。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發展海權是眾多國家崛起的關鍵一步。公元15世紀地理大發現后,人類的文明進入全球化時代,海洋成為各國爭奪的焦點。1511年馬六甲海戰,葡萄牙確立海上霸權。1529年薩拉戈薩條約,西班牙與葡萄牙劃分海上勢力范圍。1639年唐斯海戰,荷蘭擊敗西班牙成為世界海軍第一強國。1676年奧古斯塔海戰,法國取代荷蘭,坐上了第一的寶座。1692年拉和岬海戰,英國從法國手中接過寶座,最終成就了“日不落帝國”。在大國興衰的歷史長河之中,海權的交接往往伴隨著地區主導權的更迭。“國家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經歷對決定其當代戰略有著無可置疑的重要作用。”*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運籌帷幄》,中文序言,4頁,江蘇,譯林出版社,1989。隨著科學技術和作戰理論的革新,現在戰爭已經逐漸從傳統的海陸平面發展到陸、海、空、天、網、電等多維空間,但海洋仍是目前唯一可以同時實現長期維持軍事存在和遠程大規模兵力投送的領域,具有無可替代的戰略價值。當今的世界格局之下,海上主導權是一國強盛的重要標志,也是走向強盛的重要一環。
(二)穩固陸權是發展海權的必要前提。近代,美國在海權領域的認識和成就著實令人嘆服,僅僅兩百年的時間,就建立了一支世界一流的海上力量,從一個英屬殖民地走向了世界的巔峰。許多國家羨慕美國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幅員遼闊,安全壓力小。可是,如此安逸的周邊環境并非上天賜予,美國為之奮斗近一百年,經歷了一番艱難的探索之后才實現從內陸向遠洋的擴展。立國之初,美國就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必須從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手中爭取獨立。其后,美國發起西進運動與印第安人爭奪生存空間,與墨西哥交戰確立起在美洲的絕對霸權,又通過南北戰爭捍衛了國家的統一。可以說,正是美國陸軍用血與火為國家鋪就了走向繁榮的通路。面臨海外威脅時,廣闊的國土面積和龐大的人口基數,能夠發揮較強的緩沖能力,但是內部矛盾往往會導致政權的動蕩和瓦解。因此,影響國家發展的威脅來自海上,影響民族存亡的威脅則源于陸上,必須處理好陸地戰略與海洋戰略統籌協調。
(三)理念創新是戰略轉型的精神動力。公元17世紀,針對西方的入侵和周邊海域的動蕩局勢,中國和日本曾不約而同地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盲目排外和固步自封構成了兩國海洋政策的主基調。巧合的是,兩百年后,英國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撬開了中國的國門,美國又通過1853年的黑船事件結束了日本的“鎖國”。中日兩國的經歷如此的相似,其后的選擇卻又是如此的不同。西方的艦船利炮并沒有撼動中國的封建桎梏,社會上所出現 的“開眼看世界”思潮,也沒有被統治階級所接受。然而,中國知識分子為救亡圖存所做出的努力卻成就了日本海權意識的覺醒。自1851年《海國圖志》傳入日本,短短5年間就出現了23種版本,為了能使之廣泛流傳,部分版本在漢字文本上標注日文假名。1868年,日本天皇頒布“王政復古”詔書,開啟了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改革運動,扭轉了日本衰敗的命運。在某種意義上,1894年甲午戰爭是對清廷“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驗收。最終,“日本取代中國成為遠東頭號強國,它南有臺灣,北有朝鮮,取得了日后向東南亞推進的穩固基地,也構成了進軍滿洲的跳板”*徐中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275頁,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2008。。一直以來,日本都是一個極具學習能力的民族。公元7世紀大化改新時期,孝德天皇曾多次大規模派遣“遣唐使團”到中國學習漢文化以及政治、經濟體制,在經過消化和吸收后,與日本的傳統文化相互融合。公元19世紀,日本開啟明治維新,派出使節遠赴英、美、德、法等12個國家進行考察,系統學習了西方的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制度,在戰略上也走向了海權。因此,創新意識是引發變革不竭的精神動力,唯有將求知的渴望和探索的勇氣植入民族性格之中,才能真正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推動陸權向海權的戰略轉型。
(四)追逐利益是海權發展的物質驅動。發展海上力量是一筆巨額的投入,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后盾。英國自17世紀初開始建立近代海軍,至18世紀末總噸位躍升為世界第一。“僅在1689年~1714年間,英國用于海軍的撥款占其國防總支出的35%,而同期法國的數字還不足10%。”*王銀星:《安全戰略、地緣特征與英國海軍的創建》,載《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當時,資本主義尚處于工場手工業階段,經濟水平有限,而英國政府卻能向海軍投入大量的資金,其決心和魄力可見一斑。在英國的決心背后,一個重要動因就是經濟利益,經濟利益是社會行為的根本動因,也是驅動海洋戰略的天然催化劑。隨著新航路的開辟,世界進入了全球化的時代,各國的資本、商品和市場都經由大海聯系在一起。英國政府清醒地認識到“在一個商業的時代,贏得海洋要比贏得陸地更為有利”*J.F.C.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第2卷,31頁,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海上力量的強弱將決定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海權不僅影響著國家利益,還與國民利益息息相關。工業革命之后,英國的生產力迅猛發展,成為“世界工場”,“它龐大的遠洋船隊把數不盡的工業品運往世界各地,再把原材料運回國,加工成工業品,然后再運出去。”*安德魯·蘭伯特:《風帆時代的海上戰爭》,8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遠洋運輸的需求與日俱增,維護海上交通安全和開辟海外殖民地也成為國家戰略的重點。國家和公民的利益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共同構筑絕對的海上霸權。
(五)厚積薄發是實現戰略目標的最佳路徑。國家的戰略目標必須與戰略能力相稱,在實力尚未充盈之前,韜光養晦、厚積薄發是最為明智的選擇。1823年12月,美國總統門羅發表國情咨文,其中外交方面提到,“今后歐洲任何大國不得把美洲大陸業已獨立自由的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李慶余:《美國外交:從孤立主義到全球主義》,48頁,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00。,開啟了“門羅主義”時代。“美洲人的美洲”既是對孤立主義的沿襲,又是美國對自己在美洲地區主導權的宣告,為日后發展成為全球性大國做好了鋪墊。無論是在戰略時機和戰略目標的選擇上,“門羅主義”確實可以稱得上是一招妙棋。首先,在19世紀初期西班牙、法國等神圣同盟國家在英國的阻撓下難以對拉美地區形成有效的武力干涉,使美國處于一個相對有利的戰略環境。其次,美國也清醒地認識到英國是美國崛起道路上最危險的敵人,竭力避開英國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主要勢力范圍,選擇在美洲地區慢慢積攢實力。美國的韜光養晦顯然頗有成效,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英國的實力日漸衰微,不得不放棄“光榮孤立”,被卷入歐洲大陸的戰事之中,而美國卻一步一步將勢力范圍擴展到太平洋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國已經飽受常年的戰亂,變得千瘡百孔,而美國卻順理成章地接過英國手中的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