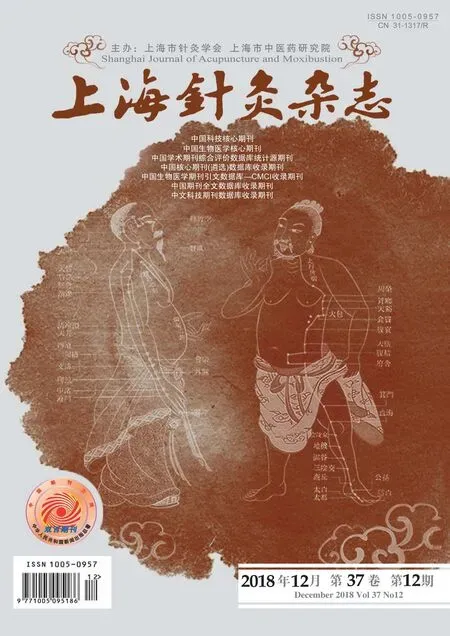針刺聯合康復治療對腦卒中后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并吞咽障礙臨床觀察
朱金妹,何俊,焦素芹,韓樂園
(常州市德安醫院,常州213000)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和吞咽障礙是腦卒中后常見并發癥,嚴重影響了患者的功能康復及生活質量。呼吸與吞咽擁有共同的解剖基礎及共同的神經支配,有研究表明卒中后吞咽障礙與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密切相關[1-2]。有報道腦卒中后伴有吞咽障礙患者的低通氣指數(AHI值)明顯升高[3-4]。有研究表明睡眠呼吸紊亂出現的打鼾與咽部吞咽的亞臨床機能紊亂相關,并且吞咽的機制可能受機械性或化學性刺激的影響,其中包括呼吸暫停的影響[5-6]。有研究表明腦梗死合并吞咽困難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患者的發病率較非吞咽困難患者明顯增加[7]。本試驗擬觀察針刺聯合口咽部綜合康復治療腦卒中后吞咽障礙從而達到治療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的臨床療效。以完善腦卒中并發癥的臨床診斷及相應的康復治療手段,提高腦卒中患者的生活質量。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在常州市德安醫院康復中心住院經確診為腦卒中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并吞咽困難患者80例。采用隨機數字表法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40例。遵照赫爾辛基宣言及“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8],均簽訂知情同意書。兩組患者年齡、性別、病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詳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1.2 納入標準
①符合全國第四次腦血管病會議制定的腦卒中診斷標準,伴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合并吞咽障礙患者;②病程<3個月;③年齡18~85歲;④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排除標準
①重度卒中者(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16分);②重度認知障礙(簡易精神狀態量表MMSE≤9分);③完全性失語者;④中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⑤既往曾有持續正壓通氣(CPAP)治療;⑥有嚴重心肺功能疾患或急性疾病者。
2 治療方法
2.1 對照組
采用常規神經內科治療及口咽部綜合康復治療。
2.1.1 基礎訓練
①呼吸和咳嗽訓練:用鼻部吸氣口部呼氣、慢慢吹水泡及咳嗽訓練。每組10次,共做3組。②感覺刺激法:用冰棉棒輕輕壓在軟腭弓、咽后壁和舌后部。緩慢移動,左右交替,進行10次。③唇、舌、下頜的運動訓練。④特殊手法治療:門德爾松手法局部按摩,每日1次,每次10 min。⑤直接吞咽訓練:肌電反饋下吞咽訓練、攝食訓練。療程30d。
2.1.2 口咽部肌肉功能性電刺激方法
將兩塊電極片固定在下頜下方二腹肌、甲狀舌骨肌部位。選雙向方波,波寬700 ms,輸出強度以耐受為度,一般0~15 mA,時間20 min。每周5次,療程30 d。
2.2 治療組
在對照組基礎上聯合針刺治療。
取啞門、頂顳前斜線、頂顳后斜線、風池、天突、廉泉、合谷。先囑患者取坐位,盡量低頭,選用0.30 mm×40 mm毫針,精確定位啞門穴后,沿下頜方向緩慢刺入1寸,施以緩慢的提插捻轉手法,至手下有針感為度,患者往往表現為一瞬間的電麻感,此時應立即出針,壓迫針孔。然后囑患者平臥,復針病灶側頂顳前斜線、頂顳后斜線、風池、天突、廉泉、合谷穴,行平補平瀉法,其中頂顳前斜線、頂顳后斜線得氣后使用電針,電針參數為疏密波、頻率為2/50 Hz,強度以患者能承受為度,留針30 min。每周5次,療程30d。
3 治療效果
3.1 觀察指標
3.1.1 洼田飲水試驗
患者喝下30mL溫開水,觀察所需時間及嗆咳情況。結果可分為5種情況:①一次喝完,無嗆咳,按計時又分為5s之內喝完,5s以上喝完;②2次以上喝完,無嗆咳;③一次喝完,有嗆咳;④2次以上喝完,有嗆咳;⑤常常嗆咳,不能將水喝完。
吞咽功能判斷:①正常為在5s內喝完,分級在Ⅰ級;②可疑為飲水時間超過5 s以上,分級在Ⅰ~Ⅱ級;③異常為分級在Ⅲ、Ⅳ、Ⅴ級[9]。
3.1.2 數字化吞咽造影檢查(VFSS)
患者咽下5 mL泛影葡胺與食物調制成稀流質、濃流質、糊狀、固體4種食物,通過X線攝影機進行檢查,評估患者吞咽情況;由放射科醫師對口腔期(包括準備期及口腔期)的食團運送情況、咽期咽喉部食物殘留情況及誤咽情況進行評分,分別為口腔期總分0~3分,咽期總分 0~3分,誤咽總分 0~4分,最后總分為10分,吞咽功能越好,分數越高[10]。
3.1.3 夜間最低血氧飽和度(LSaO2)和低通氣指數(AHI值)
兩組治療前后采用多導睡眠監測患者夜間LSaO2和AHI值指標。
3.2 療效標準[11]
痊愈:吞咽障礙消失,飲水試驗評定1分;VFSS評分10分。
顯效:吞咽障礙明顯改善,飲水試驗評定2分;VFSS評分7~9分。
有效:吞咽障礙稍有改善,飲水試驗評定3分;VFSS評分4~6分。
無效:吞咽障礙改善不明顯,飲水試驗評定3分以上;VFSS評分3分以下。
3.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t檢驗;等級資料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以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3.4 治療結果
3.4.1 兩組治療前后洼田飲水試驗結果比較
兩組治療前飲水試驗分級比較經秩和檢驗,Z=﹣0.276,P=0.685>0.0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治療后洼田飲水分級比較Z=﹣3.23,P=0.004<0.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詳見表2。
治療組洼田飲水試驗總有效率為90.0%,對照組為70.0%,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000,P<0.05)。詳見表3。

表2 兩組治療前后洼田飲水試驗分級比較(例)

表3 兩組洼田飲水試驗臨床療效比較(例)
3.4.2 兩組治療前后VFSS評定結果比較
兩組治療前VFSS得分比較經秩和檢驗,Z=﹣0.07,P=0.846>0.0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治療后VFSS得分比較Z=﹣2.746,P=0.006<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詳見表4。
治療組VFSS總有效率為92.5%,對照組為75.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501,P<0.05)。詳見表5。

表4 兩組治療前后VFSS評分比較(例)

表5 兩組VFSS臨床療效比較(例)
3.4.3 兩組治療前后睡眠監測指標比較
治療組治療后LSaO2較治療前提高,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組AHI值較治療前下降(P<0.05),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6。
表6 兩組治療前后睡眠監測指標比較(±s)

表6 兩組治療前后睡眠監測指標比較(±s)
注:與同組治療前比較1)P<0.05;與對照組比較2)P<0.05
指標 組別 例數 治療前 治療后LSaO2 治療組4078.50±5.7485.13±5.571)2)對照組4078.93±5.0982.18±4.411)AHI值 治療組4025.12±9.8714.10±5.031)2)對照組4026.64±7.9722.47±6.631)
4 討論
現代醫學研究發現,針灸治療可以有效提高大腦皮質的興奮性,改善血流動力學與腦微循環障礙,從而增強神經反射的修復與重建,通過配合吞咽康復訓練可促進正常模式形成,提高神經系統的興奮性,吞咽功能得以最大程度地恢復[12-14]。頭針是結合針灸學理論、現代神經解剖學、生物全息理論發展而來的針法,目前臨床應用最廣泛的是頭穴標準化國際方案[13]。本研究選用國際頭針標準方案中頂顳前斜線和頂顳后斜線,在該部位針刺可有效興奮吞咽中樞,喚醒麻痹的大腦皮層,針刺雙側頭穴改善腦血流量,調暢氣血,改善腦部功能,誘發正確的吞咽反射,從而改善吞咽困難[15]。啞門、廉泉和天突為咽部要穴,針刺產生的刺激可傳至以上運動神經元,調節大腦吞咽中樞對于吞咽反射的控制作用,協調吞咽肌肉的感覺和運動功能,促進損傷的神經修復,有利于吞咽功能的恢復[16-17]。風池穴歸屬足少陽膽經,貼近吞咽反射中樞,可使腦干恢復對吞咽反射的調控,吞咽功能得以恢復[18]。合谷穴是頭面部的常用遠端配穴,且療效顯著。綜上本研究所選用的腧穴經絡皆與舌、咽喉有關,符合針灸“經脈所過,主治所及”的治療特點。現代醫學認為通過對腦卒中吞咽困難患者進行康復訓練,可刺激患者的中樞神經,促進運動投射區的重新建立,促進發放神經沖動慢慢恢復,從而使患者獲得運動能力[19-20]。
目前國內外對于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與腦卒中關系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于兩者相互影響及發病情況,而腦卒中后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發生的機制目前尚不是很明確。有研究認為上氣道咽腔部分的肌肉的活動是維持上氣道開放、對抗咽腔負壓的重要力量[21]。上氣道的咽腔部分是呼吸和吞咽的共同通道,咽壁的肌層由咽縮肌和咽提肌兩組橫紋肌組成;咽縮肌既決定了咽喉的吞咽功能,也影響了呼吸氣流的動力學;呼吸和吞咽擁有共同的神經解剖學基礎,影響吞咽功能的相關肌肉,也會影響呼吸道的維持和開放,呼吸與吞咽密切相關[22]。張維等[7]研究發現,腦梗死合并吞咽困難者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的發病率較非吞咽困難者明顯增加;Martinez-Garcia MA等[23]的研究結果表明,卒中后伴吞咽困難者在穩定期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發生率較急性期減少,且與吞咽肌的功能恢復一致。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對卒中后的功能康復有嚴重的負性作用,并被認為是腦卒中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24-26]。
目前臨床上改善腦卒中后吞咽障礙的治療技術已經比較成熟易掌握,比如吞咽功能訓練、冰刺激、低頻電刺激、肌電生物反饋、經顱磁刺激、球囊擴張術及針灸等,臨床可操作性強,患者耐受性較好,效果肯定。現在國內外對于卒中后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的治療方法僅僅局限于持續正壓通氣(CPAP)。但腦卒中患者對于CPAP治療的依從性較差,難以長時間配合。本研究采用目前國際公認的吞咽評定項目洼田飲水試驗評定、數字化吞咽造影檢查(VFSS)評定;多導睡眠監測是診斷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的金標準,低通氣指數(AHI值)是其主要判斷標準,夜間最低血氧飽和度(LSaO2)作為參考,本研究采用多導睡眠監測中的AHI值和LSaO2對患者進行臨床評估,評估指標具有一定的權威性。
本研究運用針刺結合現代康復治療技術將針對吞咽障礙的治療應用于腦卒中后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患者,取得了良好的臨床療效。研究結果表明針刺聯合口咽部康復治療腦卒中后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并吞咽障礙療效更優,患者的吞咽功能、LSaO2及AHI值較前明顯好轉。希望借此為尋找和建立簡單有效的腦卒中后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患者的康復治療模式提供一種新的解決途徑,并為進一步完善腦卒中患者并發癥的臨床診療提供一種新思路。
[1]劉振華,王世軍.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合并腦卒中的危險因素分析[J].中華神經醫學雜志,2016,15(6):625-628.
[2]張麗霞,張虔,伍琦,等.腦卒中后睡眠呼吸暫停與吞咽障礙的相關性分析[J].實用老年醫學,2015,29(12):1034-1037.
[3]王東,張波,石進,等.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夜間睡眠呼吸紊亂的初篩調查[J].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2005,28(9):608-610.
[4]Bassetti C, Aldrich MS, Quint D. Sleep-disordered breathing in patientswith acute supra-and infratentorial strokes[J].Stroke, 1997,28(9):1765-1772.
[5]Okada S, Ouchi Y, Teramoto S. 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and weight loss improve swallowing reflexin patients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J].Respiration, 2000,67(4):464-466.
[6]Teramoto S,Sudo E,Matsuse T,et al.Impaired swallowing reflex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apnea syndrome[J].Chest, 1999,116(1):17-21.
[7]張維,張杰,柳開忠.腦梗死患者吞咽困難與睡眠呼吸紊亂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醫師雜志,2010,12(5):633-634.
[8]金平.衛生部頒布《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7,20(2):39.
[9]邱曉,吳毅,趙霞.肌萎縮側索硬化吞咽障礙評定研究進展[J].康復學報,2017,27(1):55-61.
[10]Ramsey DJ, Smithard DG, Kalra L. Early assessments of dysphagia and aspiration risk in acute stroke patients[J].Stroke, 2003,34(5):1252-1257.
[11]竇祖林.吞咽障礙評估與治療[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243-251.
[12]孫慧麗,熊桂華.針刺配合康復訓練對假性球麻痹患者吞咽功能恢復的影響[J].中國現代藥物應用,2013,7(17):219-220.
[13]譚小燕,譚遠皎,梁美琛.低頻電刺激聯合冰刺激及吞咽康復訓練治療腦卒中患者吞咽功能障礙的療效觀察[J].中國醫藥導刊,2015,17(4):349-350.
[14]王德深.關于針灸穴名國際標準化方案[J].針刺研究,1984,9(3):203-235.
[15]沈特立,東貴榮.病側、雙側頭穴透刺對腦梗塞TCD的影響[J].上海針灸雜志,2002,21(1):8-10.
[16]閆志剛,路林生,張東旺.天突配膻中穴與廉泉配膻中穴治療中風后吞咽困難的療效對比[J].河北中醫藥學報,2013,28(4):31-32.
[17]張菡,姜有君,魏清琳,等.體針加點刺金津、玉液治療中風后吞咽困難療效觀察[J].中國針灸,2013,(S1):11-13.
[18]劉春燕,張大偉,周鴻飛.風池穴與吞咽障礙治療的相關性探討[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7,19(12):161-163.
[19]陳偉慶,白春梅,馬丹.腦卒中吞咽障礙采用康復訓練綜合治療對其吞咽功能影響觀察[J].中國醫師雜志,2016,18(4):614-616.
[20]Chen L,Fang J,Ma R,et al.Additionaleffectsof acupuncture on early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acute ischemic stroke: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BMC Complement Altern Med, 2016,16:226.
[21]Dotan Y,Golibroda T,Oliven R,et al.Parameters affecting pharyngeal response to genioglossus stimulation in sleep apnoea[J].Eur Respir J,2011,38(2):338-347.
[22]張麗霞,伍琦,王彤.腦卒中后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與吞咽障礙[J].中國康復醫學雜志,2016,31(2):241-243.
[23] Martinez-Garcia MA, Galiano-Blancart R, Soler-Catalutla JJ,et al. Improvment in noctumal di-sordered breathing after first-ever ischemicstroke[J].Chest,2006,129(2):238-245.
[24]Menon D,Sukumaran S,Varma R,et al.Impact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n neurological recoveryafter ischemicstroke:a prospective study[J].Acta Neur ol Scand, 2017,136(5):419-426.
[25]Boulos MI, Wan A, Im J,et al. Identifying obstructive sleepapnea after stroke/TIA:evaluating four simple screening tools[J].Sleep Med, 2016,21:133-139.
[26]King S,Cuellar N.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san independent stroke risk factor: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stroke prevention guidelines,and implicationsfor neuroscience nursing practice[J].J Neurosci Nurs, 2016,48(3):133-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