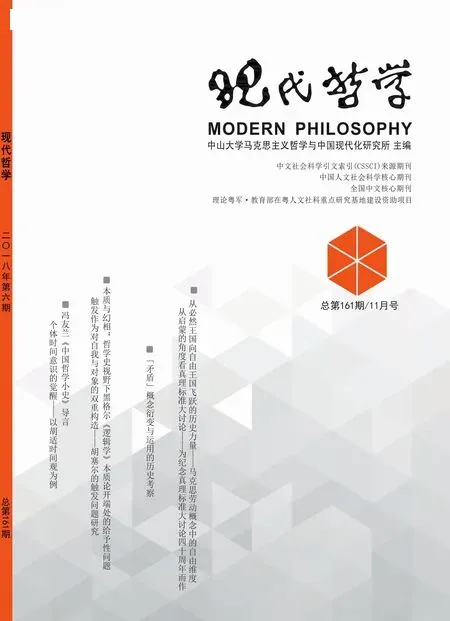工分制以及工分的稀釋化
——以廣西華楊大隊第十生產隊為例
馮裕強
對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生產效率研究,學界有諸多論述。最著名的莫過于林毅夫的“退出權”論,認為退出權的缺失是集體化生產組織形式低效率的原因[注]林毅夫:《技術、制度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第36—37頁。;以及周其仁的“產權不完備論”,從產權確立角度揭示了集體化剝奪農民產權的邏輯,從產權變遷角度來解釋了集體化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低效率。[注]周其仁:《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上)——一個經濟制度變遷史的回顧》,《管理世界》 1995年第3期。而張江華通過一個個案研究,得出相反的觀點:集體化時期的工分制是一種相當有效的勞動激勵制度。[注]張江華:《工分制下的勞動激勵與集體行動的效率》,《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5期。前人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多樣的理論視角和研究范式,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之處。“低效論者”主要是從制度經濟學視角對集體經濟制度進行分析,即從投入和產出來看待當時的生產效率。雖然其結論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卻忽視了工分制度在中國農村落地的復雜過程和勞動人民的主觀能動性。另外,張江華雖然提供了較有說服力的論證,但其討論的基點依然是經濟理性人的假設,即足夠的物質激勵會激發個體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為此,筆者選取廣西華楊大隊第十生產隊為個案,結合相關檔案、賬冊和口述史資料,以期對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生產效率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之所以選取本案例,主要基于三點考量:一是個案的代表性,華楊大隊及第十生產隊既非先進亦非落后的農業生產單位,其社會經濟在當地總體而言處于中等水平[注]以1975年人均分配收入為例:十隊82元;華楊大隊74.7元;全縣69.54元;全區63.06元。社員分配水平排隊情況,無論是全縣還是全區,均以“61—80元”的隊數分布區間占比最大,高縣共3076個生產隊,有1223個生產隊,占比39.76%;全區共38256個生產隊,有14548個生產隊,占比38.03%。(數據來源:華楊大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檔案館藏,檔案號(下同):71/1/75/53;高縣農村部:《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農業局藏;黃桂地區革委農辦室、黃桂地區中心支行:《黃桂地區農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農業局藏。)按照學術慣例,本文出現地名、人名均作了匿名化處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資料的系統性、完整性,華楊大隊地處山區,遠離縣城,在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熟人社區,受到外界的干擾較小,其保存的賬冊資料系統性、完整性較高;三是地方社會的可進入性,由于筆者在當地擁有一定人脈關系,在開展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可以獲得較為真實的信息。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這一案例的研究結論在某些方面與其他地區存在共性,但是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生態環境、風俗習慣、耕作制度等存在諸多差異,因此,筆者無意于把本文的研究結論普適化,只是希望通過對這一個案的考察,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剖析工分制度實踐的復雜邏輯,從而展現集體經濟制度生產效率的一個歷史面向。
一、工分制的實踐
華楊大隊位于廣西東南部的高縣,一個被稱為“八山一水一田”的邊遠城鎮,而該大隊的第十生產隊就是典型的山區生產隊。據1975年統計,華楊大隊總人口1837人,耕地面積為1813.9畝,其中水田為1683.7畝,旱地為130.2畝,山地則有22000多畝,人均耕地0.99畝;十隊總人口是142人,總耕地面積為171畝,其中水田有165畝,旱地僅為6畝,人均耕地1.20畝。[注]華楊大隊:《一九七五年農業統計年報表》,高縣檔案館藏,71/1/75/52。與其他生產隊相比,并沒有臨近河流,只有一條小水溝供其灌溉!并且四面環山,交通非常不便。
(一)評工議分
工分在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生產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社員靠它分配糧食和現金,隊干用它組織生產、調節社員的生產積極性等。所以辛逸認為:“工分制既是一種分配制度,同時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集體勞動的管理制度。”[注]辛逸:《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第127頁。70-80年代十隊的記分方式與全國的其他村落一樣,都采取計時和計件兩種記分方式。在非農忙季節,一天10分,每天分3節,一節3.3分,每年生產隊評1-2次等級。
“評工確定每個村民的‘底分’,即確定每個村民在整個生產隊的工分系列中的位置”。[注]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43頁。評工分一般是根據勞動者的性別、年齡、身體狀況和勞動技能等,在生產隊干部的組織下,由全體勞動者評定半年或一年的單位工日的得分。評工分在十隊并不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純粹是“過場”[注]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42頁。,而是非常認真、嚴肅的事情。十隊一般在夏收預分和年終分配之前花2-3天進行工分的評定,如果只是走過場,半天便可完成,沒必要花如此多的時間;同時由于人們的身體狀況、勞動態度、家庭負擔、年齡大小每年都會不一樣,合理地評定工分也就顯得尤為必要。而在評工分等級時,總會出現一些爭吵。其中最易引起爭吵的情況主要有兩種,一是當兩個社員的勞動能力差不多,其中一個卻比另一個的等級低時,就會引起社員的不滿;二是一些成年勞力即將步入“老年人(60歲)”的社員,因為其各方面機能的衰退,包括體力、耐力和干活速度的明顯下降,大家就會把他的工分等級評低一到兩級,這些“準老人”就會非常氣憤。在一個熟人社會中,經過長期勞動,彼此的勞動效率大家都非常清楚。“幾個熟人之間,常在一起工作,誰干活勤快誰磨洋工,大家心里都跟明鏡似的。”[注]孫敏:《集體經濟時期的“工分制”及其效率產生機制——基于J小隊“工分制”的歷史考察》,《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這樣就有效抵制那些渾水摸魚的人,避免了“高分低能”的現象出現,保證了評工等級的公平性。
而這又引起一個學界經常討論的“磨洋工”問題。那到底有沒有人偷懶、怠工呢?筆者就此問題進行了訪問:答1:在生產隊做工,不會有多賣力,除了包工。我們這邊一般都有脫粒機打谷,因為我們這里人少田多,基本上都是包工。做集體工,有時肯定會拖拉點的,不會很賣力,只是普普通通去做。包工了大家就賣力了。(LXH170509[注]引文后為訪談記錄編號。大寫的英文字母為訪談對象姓名的首字母,“170509”表示此訪談于2017年5月9日做的。引言括號內容為筆者所加。下同。)答2:沒有什么偷懶的。工也做,就是慢一點。(LQJ170709)答3:有些人啊,(現在)請別人做工,也有個別比較懶點。(XJD170707)
“大部分人還是有底線的,那個年代的人的思想還是比較單純的,不會干太不負責的事。只有一小部分比較機靈的人不講質量”。[注]李懷印、張向東、劉家峰:《制度、環境與勞動積極性:重新認識集體制時期的中國農民》,《開放時代》2016年第6期。可見,“偷懶”在集體化時代確實是存在,但一般只“小偷”,不會“大偷”。同時我們注意到,即便是當下進行集體勞動,也會有個別偷懶的現象,即偷懶是屬于一種常態性的社會現象,而不是人民公社時期所特有。另外,如果你怠工嚴重影響了生產進度,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懲罰。“這活你干得多干得少,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比如插秧,5個人為一小組共同完成1畝,在隊長評定完工分后,社員之間就可以通過內部協商的方式給干得好又快的多一個工分,落后的就減少一個。一次干活一兩個工分值不了多少錢,所以他們也不會太計較的。但是,如果你老是干活懶散,盡想著偷懶,下次小組長就不會叫你出工了。”[注]孫敏:《集體經濟時期的“工分制”及其效率產生機制——基于J小隊“工分制”的歷史考察》,《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在集體化時代,確實存在偷懶現象,但只存在少數人身上,并且主要存在于按時計工中。即便有人偷懶,大部分人還是有底線,“普普通通”地去做,不會干太出格的事。首先,大家生活在熟人社會中,平時一起工作、生活,有很多交集,如果偷懶,必然會遭到大家的嫌棄、嘲笑甚至排斥,這在評底分時也會影響其工分等級的評定;其次,大家有著共同的利益,每人的口糧都來自集體的生產,沒有人愿意生產隊減產,這對誰都不利;第三,農業并不像工業那樣講究精確度。在工廠中,少了哪一道工序或者步驟,產品就變成廢品,但農業并非如此。以水稻種植為例,從浸種、播種、插田、管理到最后收割,期間經過30多道工序,而有些工作是相同的,如犁田要犁一、犁二,秐田也要秐兩到三次,這次做得粗糙一些,下次別人再補上,這樣對稻禾的生長也就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也就是說,在農業的龐大生態系統中,部分偷懶并不會造成明顯的減產。而關鍵的工種:浸種、插秧和割禾基本上都是包工,幾乎不存在怠工現象。所以對于磨洋工,并沒有像有些學者所強調的那樣嚴重。
(二)按勞記分
在工分制度中,記工分是學者們詬病最多之處,即缺乏監督,隊干舞弊,干多干少一個樣,工分沒有與收入掛鉤,無法區分勞動者間的差異等等。
十隊是在60年代末由兩個生產隊合并而成,所以,在日常勞作中,社員總會習慣性地分成兩組。為了公正記錄工分,兩邊各推選一名記分員記錄對方的工分,同時還另選一名總記工員,兩位記分員每天都要把各個社員的工分匯總到總記工員處。由于社員在一天內經常做不同的工種,如果自己記了本組社員的工分,另一個記分員則要把他們的工分、工種抄回去,所以我們在工分簿上看到很多“√”。當時出工就畫一個圈,不出工則打個叉,并作相關說明,以免社員日后翻舊賬。
可見當時的勞動管理是非常精細的,隊干要進行私自加減工分幾乎不可能。因為在收工時或次日,記分員便會向大家聲報各人的工分數,同時兩名記分員均保存一份工分表,總記工員每月還會按時張榜公布。所以,隊干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不大,即便有,社員也會很快察覺。
由于整個高縣都是田多地少,社員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種植水稻。據記分員許某講述,以前插田是發牌的,插田的主要工種包括:鏟秧、擔秧和插秧。鏟、擔秧的計分方式一樣,均按你的底分來折算。插秧則是插多少桶就得多少牌,收工后,再把這些牌上交給記分員,由他進行統計。(XJD170323)插秧的計分公式是:插田面積×28÷總工牌×個人工牌+擔腳=當天個人工分[注]本文的三條公式均為筆者根據記分員的講解和《工分簿》的記錄整理而成。
當時生產隊規定每插一畝田的工分是28分,根據大家當天插的田畝數算出總工分后除以總牌數,這樣就得到每個牌的工分數,接著用這個工分數乘以你所插的工牌數,最后再加上你當天擔肥所得工分(生產隊根據距離遠近來規定每擔肥的擔腳分),這樣才得出你的總工分。為了盡可能地公平公正,鏟秧人每桶秧都要鏟12片。有的人手腳快就得11、12分,慢的只有7、8分。當然,為了防止有些人偷工減料,生產隊先前規定好每蔸大概插多少條秧苗,行間距多少,如果你插的條數過多或過少,插得過深或過淺、過寬或過窄,擔秧員就會指出你的不當行為。所以擔秧員不僅負責擔秧還要負責對插秧人進行監督管理,以確保所插的秧符合規格。與插秧的計分方式一樣,鏟、擔秧的計分公式是:
插田面積×12÷總底分×個人底分+擔腳=當天個人工分
從插秧和鏟、擔秧的公式中,每插一畝秧可得28分,每鏟、擔一畝秧得12分,也就是說,這一系列工作做完有40分,一天插一畝田正常需要4個一級工,每人插0.25畝,而十隊當天出工的社員大部分都是二、三級工,平均每人插了0.29畝。此外,十隊所插的田是分布在四個不同地方,這其中距離的遠近也會對工作效率產生影響。即便如此,當天的勞動效率還是高于正常勞動水平。
割禾與鏟、擔秧的計分方式相似:(割禾面積×40+生谷重量×7)÷總底分×個人底分+擔腳=當天個人工分
從公式中可以看到,生產隊更側重于割禾面積,谷重工分只占了小部分。兩者兼顧是較全面和合理的計分方式。因為如果禾稻長得不好,或者沒什么收成,僅算田面工分對生產隊不利。對于為什么每割一畝田得40分,每收100斤稻谷有7分,經多次詢問,終無果,得到更多的回答是“當時就是那樣計”。但我們知道40分就是4個一級工一天的勞動工分,即一天割一畝水稻正常情況下需要4個一級勞動力。每收生谷100斤獲得7分,這意味著每脫粒100斤的稻谷并擔回生產隊的工作量值7分。那么當天的工作效率如何呢?我們看到,當天收入246.4分,按10分計,需24.6個一級工,而當天出工的只有21人,且大部分都是二、三級工,還有部分社員只出工1-2節。[注]華楊大隊賬本資料:《工分簿》,1973年。勞動效率遠遠高于生產隊的規定。在后兩個工式中,我們看到,“底分”在評工記分的重要性,一般而言,底分只是用于按時記工,按件記工一般不用底分,但華楊大隊的十隊卻把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使社員的勞動能力與收入緊密相連,既激發了社員的積極性又確保了分配的合理性。
二、工分的稀釋化
所謂工分的稀釋化,即把非農業生產的工分拿回農業之內進行分配,從而導致工分被稀釋、分值下降的現象。這里的“農業”是指狹義上的農業。而造成工分稀釋化的原因主要有:國家大量征收的公購糧、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文化教育事業、隊干的補貼工等。下面將一一進行論述。
(一)公購糧

表1 十隊糧食分配表(計算單位:畝;斤)[注]由于人口的變動等其他原因,統計表的總人口數與參加分配的人口數并不相等,1973年實際參加分配的人口數為135人,1975年的為141人,1979年的為156人。
數據來源:華楊大隊:《一九七三年收益分配統計表》,《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統計表》,《一九七九年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檔案館藏。
據統計,十隊在1975年的畝產相對較高,當年華楊大隊的畝產為1025[注]華楊大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農業統計年報表》,高縣檔案館藏,71/1/75/52。斤,所屬的石頭公社為1110[注]石頭公社:《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農業統計年報表》,高縣檔案館藏,71/1/75/52。斤,十隊雖然豐收,但并沒有達到公社甚至大隊的平均水平。其中的原因非常復雜,涉及到諸多方面。如其地處山區,受山地地形影響較大,特別是氣候、光照、水分和土壤肥力的影響。另外,此地距縣城20多公里,交通不便,購買肥料、農藥等需大量時間,這勢必造成殺蟲、追肥的滯后。當然還有生產管理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隊干的管理水平。許某說:“我們隊插田是最(落)后的,經濟收入就不是,收入是(排)中間的。”當究其原因時,他解釋道,“我們可以割(松)脂,有點收入,所以經濟收入不是最后(差)的,插田、割禾呢,我們這些人拖拖拉拉,安排工作不夠妥當,時間沒抓得夠緊,插田、割禾就落后一點了。”(XJA170325)在1975年的收入分配表中,我們得到了印證。當年華楊大隊的林業收入為22730元,而十隊的林業收入就高達5164元,幾乎占了四分之一。當年人均分配82元,在13個生產隊中,排名第5。[注]華楊大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檔案館藏,71/1/75/53。這不得不說得益于松脂款,同時也說明生產隊干部的管理不盡如人意。另一方面,還因為十隊地處山區,所有的田地都在不同的山坳間,分布廣泛,彼此間相距又遠,這就大大增加了生產管理的成本和難度。在無法改變自然條件的情況下,隊干的管理水平則至關重要,所以有不少學者認為集體經濟是管理出來的。[注]參見吳重慶:《集體經濟是管理出來的》,《中國老區建設》2013年第2期;王景新等:《集體經濟村莊》,《開放時代》2015年第1期。農作物的生產具有非常強的季節性,雖然沒有工業要求那么精細,但在什么時候該做什么、怎么做則是非常講究的。
在70-80年代,十隊的公購糧一直保持不變。其中公糧為7415斤,這是生產隊必須無償上交的。購糧為14431斤[注]華楊大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檔案館藏,71/1/75/53。,價格為9.5元100斤。公購糧共需21846斤。1975年糧食總產為129727斤,由于豐收,多交了2000斤雙超糧。據老農們介紹,上交的公購糧數額是按照土改時各隊分得田畝的等級來計算。在上表中,公購糧每年占總糧的比分別是:24.0%,18.3%,22.0%,平均占兩成左右。這對于一個山區生產隊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數額。
由于國家每年都要從生產隊抽去約20%的糧食,會大大減少社員的分配量。在生產隊,工分是通向糧食的橋梁。糧食被拿走也就等于工分總值被抽走,工分值必然隨之下降,稀釋化再所難免。這在全國并不少見。如江蘇秦村的第11生產隊,“平均每年向國家貢獻11800元,相當于人均每年上繳四十多元。這相當于農戶人均集體收入的一半以上,遠高于年終人均現金分配。”[注]李懷印、張向東、劉家峰:《制度、環境與勞動積極性:重新認識集體制時期的中國農民》,《開放時代》2016年第6期。那么在人民公社時期,國家從農村中抽取了多少資源,為工業化做了多大貢獻?學界不少學者都有研究。鄭有貴認為,1959-1978年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從農業部門拿走凈積累高達4075億元;[注]鄭有貴:《比較視角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5期。程漱蘭則指出,1952-1978年,農業凈流出資金為3120億元,等于同期國有企業非固定資產總值的73.2%;[注]盧暉臨:《通向集體之路:一項關于文化觀念和制度形成的個案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32頁。馮海發等認為,1952-1990年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總量達11594億元。大體上,在工業化過程中國民收入的積累部分約1/3來自于農業。[注]馮海發、李溦:《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數量研究》,《經濟研究》1993年第8期。由于學者們采取的方法、數據、截取的時間段各不相同,得出的數據也不一樣。但都指出一個事實,即國家對農業進行了過度抽取,人民的負擔過重,以致于生產隊在農業現代化方面僅能做最低程度的投資和維持“簡單再生產”[注]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22頁。。
(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在人民公社化時期,國家修建了大量水利設施,而這些設施,大部分都是從各個生產隊抽調人員進行建設的。由于這些勞力從事的工作與生產隊的農業生產并沒有直接關聯,所以有學者稱之為“無效勞動”[注]張江華:《工分制下的勞動激勵與集體行動的效率》,《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5期。。正是這些“無效勞動”極大稀釋了生產隊工分的含金量。
華楊大隊在60-80年代修建了五個小型水庫、一個水電站和一座橋。九隊和十隊由于無河流經過,所以沒有水庫。但在1967年左右,十隊與九隊合資,在流經兩隊的水溝下游,修建了一個水碾房。以方便附近的村民碾米和增加兩隊副業收入。這樣就需要一個人來專職看管水碾房,所以會計在在賬本中記錄著:“1969年8月21日,收許某睇(看)水碾谷工資:15.5元”。[注]華楊大隊賬本資料:《十隊會計總賬(1967-1972)》。
此外,大隊還組建了一個專業隊。“專業隊就是開田、開荒、種山,說是改田造地,每個生產隊抽出幾個人,在大隊成立一個組織。”(TXL170316)專業隊在生產隊抽調的人是要經過大家評議的,一般都是勞動好手。在十隊,“許某在大隊做專業隊,主要搞大隊副業,生產隊出工分,一般都要10個人,鄉(公社的)他也去過。”(XJA170325)由于管理不善,大隊的專業隊并沒有做出什么成績,倒是給各個生產隊產生了不少工分。
當時廣西比較大的工程是“6927工程”,即在1969年2月7日為“迅速扭轉北煤南運”而興建的金城江至環江紅山鐵道工程,稱為“金紅鐵路”。《關于抽調民工一萬八千名參加金紅鐵路工程修建的通知》規定:高縣需抽調3000,“每人每月工資30元,其中40%交回生產隊,參加生產隊分配,60%由民工個人支配。民工的口糧供應,除從生產隊帶足本人的口糧外,按工種定量標準,不足部分由國家供應。”[注]中共黃桂市黨史辦公室、黃桂市檔案局編:《廣西黃桂地區黨政重要文件選(1949.12—1997.8)》,黃桂:大眾印刷廠,1996年,第457頁。十隊選派了31歲的徐某支援這一工程所以我們看到:“70年3月24日,收(轉信用)6927工程民兵許某12-2月回隊款:28元”。[注]華楊大隊賬本資料:《十隊會計總賬(1967-1972年)》。
廣西在1971年以后開始大規模地開展農田基本建設,農村社隊按10%的比例抽調勞動力,組織農田基本建設常年施工隊,在冬春季節進行突擊。1974年秋,全區基建上工人數高達810萬人,動工3.6萬處,包括修水庫,戰石海,平整耕地,搞人造平原,打涵洞,架渡槽等,是廣西歷史上農田基本建設規模最大、投入資金和勞動力最多的一年。[注]高言弘編:《廣西水利史》,北京:新時代出版社,1988年,第323頁。
在1959年全國勞動力分配規劃中農村勞動力約有20997萬個,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有10794萬個,占比51.4%。而在農業中,進行糧食生產的約為8000萬個,占總勞力的38.1%,種植其他作物的約有2793萬個,占比13.3%。[注]國家農業委員會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第133頁。也就是說,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力占總勞力的一半,而真正種植糧食的勞動力不到4成。足見在人民公社時期,大量勞動力被抽去從事非農業生產工作,特別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所以不少學者呼吁重新思考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效率問題。徐俊忠認為,由于“去工業化”,社員只能去種田,所有產出主要就在那幾畝田里,這必然導致人民公社效率的低下。而由于統購統銷政策,就決定了不可能有太多東西拿出來分配。即使去工業化后,在人民公社體制下,還是做了很多無法在當時的分配中顯示出來的好事,包括直到今天農民還在享用的農田水利設施。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地講那時候的人出工不出力、勞動沒有效率。[注]徐俊忠等:《集體經濟村莊》,《開放時代》2015年第1期。盧暉臨則主張我們應該打開視野看效率,特別是延后的效率,農業基礎設施的興修對于農業生產的影響往往不能在當下立即體現,而需要在一個更長的時段才能觀察得到。[注]盧暉臨等:《集體經濟村莊》,《開放時代》2015年第1期。另外,李懷印強調,我們不應僅依據1980年后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得出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生產必然低效的結論,更不應將當時的低水平勞動生產率簡單歸因于集體組織本身。事實上,社會、生物和管理等多種因素可以說明,社員在集體生產中為什么必須增加勞動投入,并維持最低程度的勞動生產率。[注]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99頁。
(三)文化教育事業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如果說要“打開視野看效率”,那么文化教育事業更需如此,教育所產生的效果往往不能在短時間內呈現,而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沉淀。
在70-80年代,十隊共有2名民辦教師和1名公辦教師。公辦教師的薪酬全部由國家支付,而民辦教師則需要生產隊來承擔。十隊在1973年上交了981斤統籌糧及161元統籌金,其中統籌金是為4名大隊干部和4名民辦教師以及1名獸醫統籌的。[注]華楊大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三年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檔案館藏,71/1/73/44。但是,華楊大隊在73年共有13名民辦教師,平均每個生產隊出一個。據當時的大隊干部介紹,并不是所有民辦教師都可以統籌,只有教得比較好的才有資格統籌。至于沒有得到統籌的教師則回各自生產隊記工分,大隊再發少量的補貼。(CPY170105)此言非虛,在縣檔案館的檔案中記錄了1971年華楊大隊教師隊伍的基本情況。當時公辦教師6人,教齡最長的有24年,最短的有12年,即其從1959年9月開始從事教師行業;工資月薪最高的有51.5元,最低的有29.5元。[注]《高縣中小學教職工登記表》,高縣檔案館藏,71/37/1/38。按照當時的物價水平,這是相當高的收入了。而民辦教師有10人,有工資的5人,最高28元每月,最低24元。回生產隊記工分的5人,大部分的教齡是2-3年。[注]《高縣中小學教職工登記表》,高縣檔案館藏,71/37/1/37。民辦教師占總教師隊伍的62.5%。當時高縣民辦教師的待遇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國家補助加大隊統籌;二是國家補助加生產隊記工分,不足部分由學校學費或勤工儉學收入補足。[注]《關于民辦教師生活待遇的一些情況匯報》,高縣檔案館藏,78/37/1/67。另外還有自籌教師,采取這種形式的教師數量較少,華楊大隊主要采取前兩種方式給民辦教師記酬。
當時華楊大隊一共有四所小學,十隊與九隊由于地理位置比較偏遠,所以大隊在兩個生產隊中間設立了一所分校,由這兩個生產隊推選1-2名教師任教,九隊的龐某就是其中一個。1968年9月其在大隊的中心校任教,教了一年之后,被分配到這里,最初他的補貼是4元,并在生產隊記工分。當時其他學校都收1.5元的學費,但是他只收1元,并在1972年開始實施他的“惠農政策”——免收學費,所有適齡兒童免費入學。這一創舉紛紛迎來家長們的熱烈歡迎。為了填補學生的學費,他在學校周邊的荒地上種起了木薯、紅薯、茯苓等作物,其中收入最大的是8毛錢一斤的茯苓,基本上解決了學生的學費問題。(PDZ170324)實施1年之后,由于學生數量急劇上升,十隊推選了年僅20歲的許某前去任教。許某說:“試過兩年沒收學費的,具體哪年就不記得了。那時一個學生的學費要交1塊5。所以就要勞動,有收入了就減輕學生的負擔。”(XJA170325)但這一“政策”只實施了3年便夭折了。一方面是因為收入減少;另一方面是大隊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龐某的愛人回憶說:“那時他主張搞點副業,這樣就不用學生交學費,同時也減輕家長的負擔。但是他被別人批評,說他帶壞樣,還說你做得那么好,但是你教不好,不讓他搞那些。”(LHQ170416)這樣的創舉在當時應該是少有的,遺憾的是重重阻力導致了它的消亡。
學校的作息時間與農業生產相匹配,也分為一天三節,每周上6天課。因為沒有統籌,許某上一天課就算一天工,周日不出工就沒有工分。生產隊開始只給他評了三級工——9分,因為“我們還是后生,做不了多少,體力沒有多少,一級一般要擔得100多斤,我們一般是三級,四、五級一般是老人或者是婦女。如果一個月有四個星期日你沒參加生產勞動,就少了36分。”(XJA170325)可見教師與社員一樣,對工分都是非常重視的。
到1978年,華楊大隊共有7個公辦教師[注]《高縣中小學教職工登記表》,高縣檔案館藏,78/37/1/69。,16個民辦教師[注]《高縣中小學教職工登記表》,高縣檔案館藏,78/37/1/68。,民辦教師約占總教師的69.6%。當時“全縣教師6161人,公辦2530人,占41%,民辦3626人,占59%。”[注]《教育情況匯報》,高縣檔案館藏,78/37/1/67。1977 年,我國中小學教師共841.3萬,而民辦教師高達491 .2萬人,占56%。[注]王獻玲:《中國民辦教師始末》,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第117頁。足見民辦教師在中國教育事業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貧苦落后的農村地區,可以說是基礎教育的主力軍。以高縣為例,從1965年到1978年間,全縣普及了五年教育,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了99.3%。“小學由469間增加到996間,初中由5間增加到181間……小學生由49822人增加到84835人,初中生從3241人增長到32774人”。[注]《教育情況匯報》,高縣檔案館藏,78/37/1/67。教育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廣大貧下中農子女入學的需求。當然,我們也不應過分地夸大民辦教師的作用,一方面,民辦教師教學水平有限,大部分是初中畢業就轉為教師,知識儲備、教學技能等方面都落后于大專院校畢業的公辦教師;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政治環境,各種運動擾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學生學習的時間極大減少。在這些情況下,教學成果定然是不太理想的。即便存在不少問題,廣大民辦老師還是為中國鄉村教育的發展特別是識字教育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礎。
(四)隊干的補貼工
在工分的稀釋化中,隊干的補貼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有學者[注]李嶼洪:《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的“特殊”工分——以河北省侯家營村為個案》,《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認為,正是各級干部的補貼工過高,致使工分值被拉低,嚴重影響了社員的積極性,從而導致集體勞動效率的低下。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干部的補貼工分,合計起來,可以略高于生產隊工分總數的百分之一,但不能超過百分之二。”[注]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646頁。《關于執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的補充規定(草案)》則補充了:“生產隊干部一律不實行定工生產、定額補助。但是可以根據生產隊的大小,每人每月補貼2至3個勞動日。因公誤工的,同樣照補工分。”[注]王祝光編:《廣西農村合作經濟史料(上)》,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8頁。這說明生產隊干部的補貼工分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根據生產隊的大小,隊干額外付出腦力勞力多少,在年終分配時補貼工分;二是因公誤工補貼,即到縣、公社、大隊或者在小隊等其他地方公干,生產隊要根據其底分進行記工分。這二者都歸為隊干的補貼工。那么政策在十隊落實得如何呢?

表2 1975年用工分析表(單位:十隊、華楊大隊用工:日;高縣用工:萬日)
注:1975年高縣統計生產隊數為233個。數據來源:華楊大隊:《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檔案館藏;黃桂地區革委農辦室:《黃桂地區一九七五年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農業局藏。
我們看到,十隊的生產隊干部補貼工為3105工,即31050分,約占總用工的9.90%,嚴重超過了規定。那十隊是否亂補貼呢?事實上并沒有,而是嚴格按照上級的要求記工分。據多位隊干、社員的回憶,生產隊干部的年終補貼最高是隊長和會計的300分,其他隊干如記分員、保管員等在200-100分之間,每個干部補多少都經過社員大會民主評定。300分相當于一個月的工分,一年平均下來每月2.5天,并末超過規定。而問題在于因公誤工補貼。 隊干們認為,那時主要是會議太多,三天兩頭要去開會。(LXH170707,XJB170708)在賬本中記錄了許多會議事項,如參觀廣東信宜、在公社辦學習班伙食、往黃桂學習920經驗伙食和在大隊辦隊干會吃菜金等。[注]華楊大隊賬本資料:《十隊會計總賬(1967-1972)》。這說明:一方面,會議的名目繁多,諸如參觀學習、農副業、隊干、黨建等,但真正關于農業生產的會議并不多,開了大量的“無效會議”;另一方面,由于會計的賬本記錄都是與現金收支相關的賬目,所以這些會議都需要生產隊支付金額不等的伙食費,另外還有大量只開半天、不需要帶錢糧的公社、大隊級的會議沒有記錄。
如此多的會議導致的后果是:不僅帶回來大量工分,使生產隊的工分值進一步稀釋化,降低工分值;還由于各級干部都在小隊與大隊、公社之間穿梭,隊內的生產勞動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導致生產效率的下降。“隊長在的時候,都下老實干啊,跟著隊長干。隊長不在時,有的時候也肯定會放松下。”[注]李懷印、張向東、劉家峰:《制度、環境與勞動積極性:重新認識集體制時期的中國農民》,《開放時代》2016年第6期。有些社員則認為:“干部們今天開會,明天又開會,一開就是半天一天的,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談,無非是想出點花頭來拿‘安耽工’。”[注]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31頁。頻繁的會議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干群關系的緊張。
在上表中,十隊、華楊大隊和高縣在1975年的生產用工占總勞動日的比分別是85.40%、83.70%和82.70%。可見,區域越大生產用工越少,而生產用工越少意味著非生產用工越多,即花在基礎設施、國家大型工程和其它方面的工作更多。總體而言,大部分生產隊要用約15%左右的勞動日去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這并不是特例,在山西東北里生產隊,1977 年非生產用工比例達到7.7%,還不包括高達18.98%的農田基建工。[注]黃英偉、張晉華:《集體化時期人口、收入分配與農業勞動生產率——以山西省東北里生產隊為例》,《農業考古》2014年第4期。那么在外面掙的大量工分拿回生產隊進行分配,必然會稀釋農業生產的工分值。在1975年,十隊用于社員分配的總金額是11492元,勞動日值0.37元,人均分配82元。[注]華楊大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檔案館藏,71/1/75/53。如果我們把占14.6%的非農業生產用工去掉或者改為由國家支付,只對占85.40%的生產用工進行分配,那么,勞動日值將提升到0.43元,提高了0.06元。假設一個社員一年掙得3000分,即300個勞動日,那么他將多得18元,這18元可以很好地提升其生活水平!
所以,有學者認為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生產效率低,這并不全面,對生活于其中的農民亦是不公平的!首先,“低效論者”所謂的“低效”主要是指在農業中投入大量的集體勞動,但是“產出”卻很低,以經濟學中的投入產出標準來衡量人民公社制度。事實上,真正進行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并不多。在十隊,一位婦女說:“強的勞動力又抽出去了呀,就剩下二、三級的婆娘在家,有的上山搞副業,沒有多少勞動力的。”(XJA170325)而在江蘇秦村,一位老隊長估計,生產隊的70%以上的農活是由婦女來完成的,“要不是有婦女支撐,生產隊早就完蛋了”。[注]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81頁。可見,女性在集體化時代發揮了關鍵作用。那么在只有二、三級勞動力且處于山區的情況下,十隊不僅養活了142人,還支援了國家21846斤糧食。就其本身而言,效率已經是很高了。其次,“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本應由國家支付的工資卻被攤派到各個生產隊,以及每年抽掉大約占總糧食20%的公購糧,并上調大量物資。這樣農村中用來分配和食用的產品大約只占60%。十隊在1975年的全年收入金額為21524元,最終用來分配的金額是11492元,占比53.39%;全年收入糧食129727斤,分配口糧為84600斤,占比65.21%。[注]華楊大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統計表》,高縣檔案館藏,71/1/75/53。這樣的分配比例并非底層政府的胡亂規定,而是按照國家規定行事的,“中央原來規定的總扣留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分配給社員的部分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從當前人民公社的生產水平來看,這個扣留和分配的比例,還是適當的,應該堅持。”[注]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333頁。最后,我們試著打開視野看效率,大量民工所進行的非農業生產建設也是卓有成效的。即便在華楊大隊這樣落后的地區,當年修建的水庫還有兩座為人們所用,修建的橋梁、魚塘、溝渠等也在沿用,現今大部分農田基本設施都是在集體化時代修建的。
三、余 論
時至今日,仍有學者認為集體化時代的農業生產效率是極其低下的,以致于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他們所謂的“事實”是抽取集體化時代的某些特定時期并加以無限放大,最后全盤否定集體經濟制度。如“大躍進”和1966-1969年文革高潮等時期。在這些特殊時期,不可否認國家在政策上出現了不少過失,導致了嚴重后果,但這只是歷史長河的短短幾年,并不是集體經濟的穩定期。所以,以特定的“點”來否定整條“線”并不可取。
在“低效論者”看來,導致農業生產低效的原因是集體生產中農活工種多、勞動分散,所以不能有效監督導致“搭便車”現象。通過筆者的實際訪談和結合相關資料發現,在農業勞動中的確存在怠工現象,但并沒有“低效論者”所標榜的那樣嚴重。首先,偷懶現象放到今天仍然存在,而不是只存在于集體化時期,那么用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來批駁一種制度顯然是不成立的。其次,農業并不像工業那樣要求標準化、專業化、規格化,其中某一環節缺漏就會導致產品的不合格。農民在生產過程中不會因為插秧插得間距寬一些禾苗就不生長,不會因為某塊泥土過大就會導致作物的減產,大部分糧食作物都要經過幾十道工序才能收獲,即便某些社員工作不到位,其他社員也會進行補救。而對于關鍵的工種,生產隊一般都會安排技術較強、經驗較豐富的隊員承擔,所以在農業中是可以存在一定量的怠工現象的。第三,經濟學家們往往把農民看成是經濟理性的個體,而忽略了農民是處于熟人社會的關系網中,彼此間并非像老板與員工那樣冷冰冰的關系,而是講究人情、面子和禮俗規約,熟人社會自帶約束懲罰機制。更重要的是,在長期的生產勞動過程中,不僅各人的勞動能力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且還會形成一套習慣性做法和衡量標準,很多勞動并不需要嚴密監督。[注]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84頁。同時每人的口糧都依賴于集體生產,具有共同的利益認知。所以,怠工現象并沒有像某些學者所臆想的那么泛濫。
另外,不少學者認為導致社員生產積極性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不能準確計量其所投入的勞動量,導致投入與收入脫勾。如前所述,農業非企業,農業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和復雜性,很多工種并不需要也不能準確計量。如擔一擔糞肥,不必每擔都要過秤,只需要大概那么重就可以,如果事事都“斤斤計較”,不僅非常繁瑣還會浪費大量時間,效率不僅不會提高反而會下降。我們通過分析十隊的工分制發現,在糧食種植中,每個人的工分收入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天的收獲量和其底分的高低,底分的高低就是其勞動能力大小的體現,所以投入與收入是緊密相連的。雖然十隊不能代表所有的生產隊,但是,集體化時期各地的生產組織方式和分配制度都大體相同,所以其在一定程度上蘊含著普遍性。
還有,“低效論者”所謂的“低效”是假定所有社員都集中在生產隊進行農業生產,由于產出不高,從而得出低效的結論。但我們發現,社員、隊干、大隊干部以及各種物資都在不同程度上處于“流動”狀態,或開會、或上調。也正是因為這些“流動”產生了大量的非生產性用工并導致工分的稀釋化,以至于工分值不斷降低,最后趨于平均主義。研究發現,稀釋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國家大量征收的公購糧、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文化教育事業、隊干的補貼工,事實上還有合作醫療、照顧困難戶、補貼倒欠戶等,囿于篇幅,本文只能對主要原因進行論述。也就是說,在有限的土地上,生產隊不僅要負責社員的口糧、伙食、醫療、托兒、讀書、理發、養老、死葬、生育補助等,還要負擔大量的上調物資,最后用于分配的勞動成果僅占六成左右甚至更少。所以,我們認為,集體化時期的勞動效率雖不能說很高,但起碼并非“低效論者”所說的那樣低下。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并不認為工分制是一種完美的制度。在用計時制時效率普遍較低,而在比較精準計量社員勞動的時候,又會給隊干帶來了不少工作;由于口糧分配占了大部分,少量的工分糧并不能很好地激勵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倒欠戶的連年累積給生產隊帶來沉重負擔等。我們要做的不是以此來否定歷史,而是實事求是地看待這些功過,從中吸取有益于當下進行“鄉村振興戰略”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