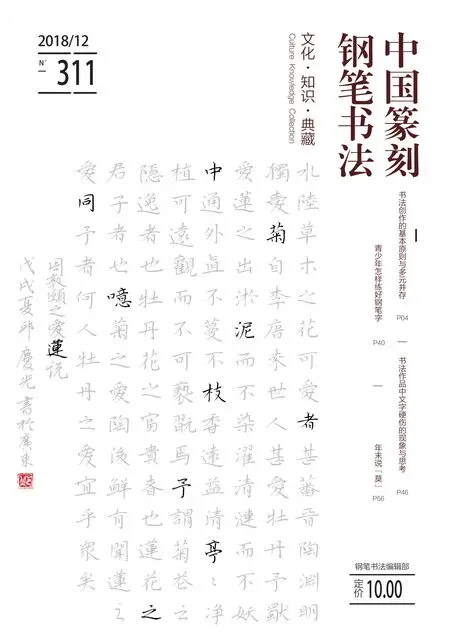人間萬姓仰頭看,“龍”字新探(下)
文︱盛文躍
“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這是清曹雪芹《對月寓懷》的詩句。每一個晴朗的夜空,我們都會舉頭望明月,注視著圓月里的那條“中華龍”;而圓月里的那條“中華龍”也注視著我們,從遙遠的過去到渺遠的未來。
一、《說文》“龍”條新解
除甲骨文“龍”字與月相的形近以外,《說文》對“龍”的釋義也是龍即月的重要證據。
《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徐中舒所編《甲骨文字典》釋“龍”條中引《說文》并解釋稱:“許慎所釋乃附會古代神話傳說而成,不足據。”實則如果徐氏猜測成立的話,該神話傳說像“朦朧”一詞一樣難得地保留了“龍”字即月的證據,并經許慎之手在權威字書中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線索。下逐句詳析之。
“鱗蟲之長”,前已述,說其為“長”是因為月亮每晚從東地平線升起,早晨西地平線落下,在時人眼中,從最東端到最西段的距離是難以想象的,而“月亮”一夜之間即抵達可見其速度之快,月亮又像后面幾句的解釋一樣變幻莫測,陸地上的“蟲”只是對其的不完善的描述和比擬,這就像所有的“蟲”都只是對天上這只“大蟲”的模仿,而月就是完美的原型,就是“鱗蟲之長”。
“能幽,能明”,很難作為一種自然動物的描述,但以其描述月亮則很貼合,這可指月亮不時為云所遮而時暗時明,但這易于推想,恐不確。更恰當的解釋為當時人們等到望日發現滿月并沒有像往常一樣出現,或時隱時現,今天我們知道這天文現象為“月食”——日、月、地球三點成一線并且地球在中間,但在當時人們顯然難以解釋(直到后世人們仍將其想象為“天狗吃月亮”)。
目前已知中國最早的月食記錄在商代,殷墟卜辭中考證得到五次月食記錄,它們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月食記錄。以農耕文明初期人們對月亮的關注程度,他們一定會對異常的“月食”現象有所表示,“能幽,能明”就是流傳下來的對這種現象的歸納。由于“龍”為“月”這一緣起逐漸被淡忘,該描述被嫁接為對動物形象的描述,變為無稽之談,殊不知該動物就是“月亮”。
“能細,能巨,能短,能長”,很顯然這是指當時人看到的月亮大小的變化導致的其中的月相——“龍”的大小長短的變化。 而每月月圓時月亮在人們眼中大小不同的原因是月球繞地球公轉的軌道為橢圓,其中近地點距離地球約為35.6萬千米,遠地點約為40.6萬千米。人們看到月球的大小與地月距離成反比。我們知道月亮的不同位相隨它對太陽的位置而定,望日月亮正與太陽相對,而地球在中間,我們正可看到由于月球的向地面反射太陽光而得到的滿月。由于月球繞地球公轉同時地球繞太陽公轉,所以從前一個望日到下一個望日(約29.5天)的同時地球公轉了約29°,因為望日地球、日、月三點一線,所以兩個望日月球在地月軌道中的相對位置是不同的,后者月球較前者也相應地多公轉了約29°,這個角度需要兩天左右達到,因此一個周期內每個望日地月距離都不同,直觀的反應就是不同月份滿月大小不同,“龍”因之“能細,能巨,能短,能長”。
“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若說前面幾句釋詞其他龍起源說還能勉強附會,這兩句則萬難圓滿解釋了,實則這末兩句正反映了遠古人民對與月亮相關聯的自然現象的想象與解釋。“春分而登天”就是指春分那天太陽還沒有落到地平線以下,月亮已經高懸于空中;同理,“秋分而潛淵”就是指太陽已經落到地平線以下,很久月亮才從地平線升起,就像月亮起初潛藏在深淵里一樣。
經過現代天文觀測得到,上古文明所在緯度范圍內,陰歷8月望日月亮在太陽從地平線落下約40分鐘后從地平線升起,一直到來年一月望日為止都有這樣一段時間間隔,而從一月開始到7月的望日,月亮都在太陽落山前即傍晚就懸于東天,其中以2月望日太陽于地平線落下時月亮升得最高,也就是說每年陰歷上半年月亮“登天”(這正可解釋《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即每年六個月為“登天”),下半年則“潛淵”,而又以2月望日“登天”最高,8月望日“潛淵”最深。春分日就在2月望日前10天左右,秋分日就在8月望日前后。此之謂“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但既然有半年時間月亮會“登天”,為什么唯獨說“春分”呢?
因為古人知道春分日晝夜均分,太陽落下地平線即是夜,而屬夜的月在日的范圍內即出現,在“登天”中是最容易引起好奇和關注的現象;第二,因為龍自古有登天施風布雨的傳說,這正與春分時的自然現象和農人的期望相合。一般春分一到,雨水明顯增多,元稹有詩:“二氣莫交爭,春分雨處行。雨中看電影,云過聽雷聲”,此時正是早稻的播種期,對灌溉需求量大,“二月驚蟄又春分,種樹施肥耕地深”。因此春分時節的雨水對農人的生計至關重要,所謂“春雨貴如油”,“春分有雨是豐年”,“春分雨不歇,清明時節是好天”。
所以龍“春分而登天”正是當時人們對春分時節雨水較多的自然現象的解釋,也是對龍能夠穩定地在春耕時登天施風布雨的期許。
春分日提前三天的二月初二被稱為“春龍節”,“二月二,龍抬頭”,該日也稱“龍頭節”,和春分一樣,敬龍祈雨。其實“龍抬頭”者,同樣也是對當日月象的描述。陰歷初二雖為新月,但初升時已可見“龍頭”上揚(考慮古人視力優越,光線阻礙少和空氣清潔度高),滿月時可以見得分明,到8月滿月時,月相中龍頭正好和春分時相對,整條龍呈向下俯沖之勢。

二月龍頭上揚“登天”

八月龍頭向下“潛淵”
“秋分則潛淵”是對傳說中龍興風作浪的解釋,“淵”古為海,中國再往東是海的事實對尚古時代生活在中東部的民眾來說不會陌生,月亮沒出現時人們自然地認為其在東地平線以下,那就是東海。而既已認為“月—龍”這一動物最為神秘,可作陸地動物的“型相”,又可授時,“神通”極其廣大,那么人們就自然地將這種想象與秋分左右的巨大海浪相聯系——巨浪是“龍—月”在晚上升起前“潛淵”時翻江倒海的結果。這就是后世龍既有施風布雨的正面形象,又有興風作浪的反面形象的源由。
二、文物玉豬龍與月
除以上古文字,文獻的線索外,目前已知的“龍”出土文物也提供了龍起源于月亮的證據。其中最重要的是紅山文化的玉豬龍,該龍形象是東北西遼河流域獨立且久遠的崇龍文化發展史進入成熟期的標志。該系統的龍文化目前可追溯到約8000年前的遼寧阜新查海興隆洼文化的堆塑龍,因其年代最早,體型碩大而被學界稱為“中華第一龍”(時間),而后敖漢興隆溝出土有以野豬頭骨為龍首的豬首龍,發掘者認為“這是中國目前所能確認的最早的豬首龍形態”,另外還有赤峰出土的雙豬首聯體石雕,其形與紅山文化玉豬龍相似,而后還有趙寶溝文化中陶尊上刻畫的豬首龍等,再發展到紅山文化的玉豬龍為其巔峰。因此,西遼河流域的崇龍文化由于年代最早(比中原最早的河南濮陽西水坡的蚌塑龍早2000年左右),分布集中,流傳有序,造型豐富等特點而逐漸被認同為中華龍文化的源頭。
作為該文化成熟期的代表的玉豬龍主要分為“C”形玉雕龍和“玦”形玉豬龍兩類。前者被稱為“中華第一龍”(代表性),后者則被著名文物學家孫機稱為“中國龍標準的原始形象”,此乃卓見,因為正是這件器型蘊含了原始的龍即月的信息。目前已出土的玦形玉豬龍共13件,高度多在10厘米以上,身軀厚實。龍為玦形,環箍狀,首尾間大多數經切割形成玦口,少數玦口內側仍相連,玦口對側龍身皆有圓孔。該形象實為月象之“龍”形與月亮圓盤狀之結合,頭上的突起為“龍頭”上之橢圓的模擬,而身上之圓孔則為月象當中龍身中部所見黑點的模仿,有些玉豬龍有相鄰的兩個圓孔,這正好是因為若仔細觀察會發現,月象當中也在幾乎同樣位置有相鄰的兩個黑點。

需要注意的是比玉豬龍年代稍早的趙寶溝陶尊上的豬首龍呈“S”型,近年來灤河等地也收集到了“S”型的玉豬龍。而到商代婦好墓中還出土了一“C”型,一“S”型兩件玉雕龍(學界也歸于玉豬龍),學者薛志強認為這反映了“龍”的雌雄之分。這正是當時人們將月的形象予以拆分歸并得到的,“C”型(近似圓形)模擬月亮的圓球狀,“S”型模擬月象的“龍”形。

另外需要解釋的是,玉豬龍還常常作為龍的“豬原型”說的證據,實則這種說法和前文述及的“蛇原型說”“鱷原型說”一樣,只是對龍的次原型的辯證。各地先民以當地常見動物來模擬、刻畫、甚至指代空中的“龍—月”是一種自然的認知方式,西遼河一代在距今8000年到5000年為山地森林和草原地帶,野豬繁盛,這從當地出土的大量野豬骨即可佐證,再加上野豬既提供了食物與毛皮,又兇猛可怖,難以制服,與龍既施風布雨,又興風作浪的二元形象相同,因此當地先民就以“豬”為“龍—月”的載體,形成了地域特色濃烈的豬龍文化,前文提到的“朦”字或即受此文化影響而出現。
綜上的各種論證,追本溯源,“龍”即“月”,其他的動物原型都是以當地的崇拜和敬畏對象,來對“龍”進行比附,描述的次原型。再回到上文提到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結合問題,月象本為月球地形的特殊性導致,而于我國中緯度看到的月象又保有了特殊中的獨特性,更奇的是,我們仰頭看那月象,巨口、蜷身、圓冠依稀可辨,這分明就是陸地上常見動物的形象,因此以月觀龍,我們就攫住了最具體,最形象,最顯著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月亮在大地空間上是先民普遍的想望,引用后世的描寫是所謂“千里共嬋娟”。在時間上,我們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民眾和初民時代的人們共享同一個月亮,欣賞同樣的月象,我們繼承遠古以來以月亮陰晴圓缺記時的歷法,其在目前通行的農歷中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以月觀龍我們就體貼了最廣闊,最悠遠,最顯著的普遍性。“龍”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結合,誠不謬也。
三、龍的傳人,“絕龍月通”
崇拜“龍”就是崇拜“月”,而崇拜月就是敬重時間,對時間這一最強大的自然因素的把握是農業的要求,因此也就是農耕文明產生的基礎,所以“龍”最突出地見證了中華文明的起源,也因此代表了中華文明,由此我們就能理解龍文化為何生生不息,歷久彌新;由此我們也就能夠認識到“龍的傳人”這一定位的內涵和分量。但下面我們面臨了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既然龍即月能夠解釋這從具體文獻到抽象意義的一系列問題,那為何這一幾乎每晚都能看到的真相卻隱沒至今,杳無人知呢?為何古來文獻中都從未明確指出,而只余線索留待鉤沉呢?
文明從母系社會進入了父系社會。從田獵時期說起,彼時食物大部分來自與動物的搏斗,男性為占優勢的勞力輸出者,女性則主要進行一些體力要求較低的采集活動,在居住地范圍活動,當捕獲的獵物過多時需要于居住地暫存,女性發現暫存的動物,如野豬等又生出小豬,于是有意識地以采集到的食物加以飼養,作為日后的食物儲備,因此采集的需求量加大,而部分采集到的野谷種子散落在地,來年長出了谷物,于是女性又有意識地對部分谷物進行培育,開展簡單的農業活動,隨著經驗技術的發展,馴化養殖和農業同時發展,成為主要的食物來源,因此在其中占主導地位的女性成為占優勢的勞力輸出者,這也是母系社會的重要特征,屬于母系社會的仰韶文化早期即處于該階段。可見農耕社會初期為母系社會,是不爭的事實。前文已述及農耕的起源和發展關鍵在于掌握農時,而當時主要的授時工具即為月亮,對月亮的關注使人產生了對月象的想象,“龍”形象和概念正誕生于此時,而女性作為早期農業的擔綱者,與“月—龍”共同體的聯系更為緊密,因此有理由認為龍概念誕生之初,是女性的象征。
但很快隨著農業產出占比增加,大部分男性也投入到了農業生產當中,由于身體素質優勢又取代了女性的主導地位,文明從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并且再沒有引起變革。在這一過程中,龍形象因上文提到的突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再加上授時意義,通過控制降水影響農業等因素,從女性的代表上升為了莫測的自然力的象征,即“天”,成為了全部落崇拜,敬畏和意欲加以利用的對象。至顓頊“絕地天通”,天文與人文的溝通由統治階層壟斷,而統治階層為男性,主陽剛,急迫需要“龍,君也”的“政治—文化”論調為統治者的“以德配天”給予合法性。但“龍—月”最初為女性的代表,要打破這一聯系,只有將源頭“月”和女性的關聯取消或者將“龍”和“月”的關聯取消兩種途徑,前者由于月主陰柔的自然聯想而很難達成,相對的后者由于龍概念在單純的月象描繪外,增加了主宰(自然力)狂暴(巨浪)等符合男性特征的符號意義而變得順理成章,所以當時的統治者有意地銷毀了龍與月聯系的證據,隨著龍形象和統治者的關聯日益密切,“龍—月”共同體這一生動的“形象—意義”系統逐漸為人淡忘,只留下一些口口相傳的民間傳說而被許慎聽聞并記錄了下來。所以,“絕龍月通”的過程和“絕地天通”一體兩面,是標記中華文明進展的重要一筆。
綜上所述,“龍”形象來自對滿月月象的描繪,“龍”概念的出現代表以月授時的成熟,進而表征著農耕文明的興起,“絕龍月通”是文明從母系社會發展到父系社會的重要環節。“龍—月”共同體是中華文明發展的濫觴,是中華文化確證的淵藪,它應該使每一個中華兒女興奮,使每一個“龍的傳人”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