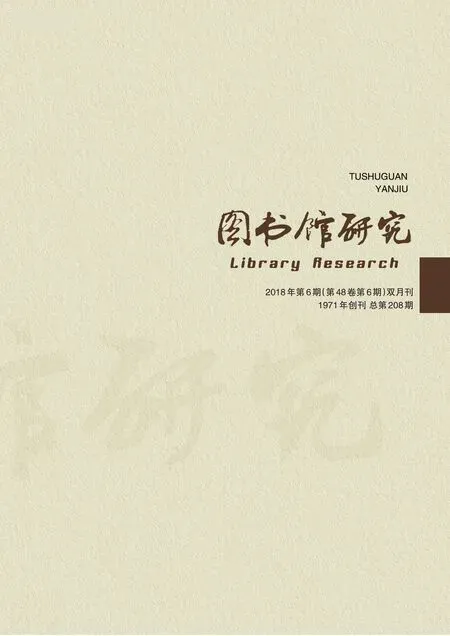高影響力學者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使用行為研究*
——以ResearchGate為例
張耀坤,牛艷霞,汪朝州
(南昌航空大學經(jīng)濟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63)
1 引言
當前,科研人員廣泛地利用社交網(wǎng)絡(luò)進行學術(shù)交流和協(xié)同創(chuàng)新,特別是新近出現(xiàn)的綜合性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如ResearchGate(以下簡稱RG)、Academia.edu、Mendeley等,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科研人員的關(guān)注與使用[1-3]。基于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科研人員可以及時公布和關(guān)注最新科研進展信息、共享科研成果、交流和協(xié)同解決科研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4]。與傳統(tǒng)學術(shù)交流方式相比,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使得科研人員信息共享方式更加多樣化、學術(shù)交流過程更為便捷,創(chuàng)新過程也更趨向于開放式。
高影響力學者在科研創(chuàng)新中處于關(guān)鍵位置,是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的核心節(jié)點,其使用行為往往具有示范帶動作用,能夠為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帶來大量有價值的內(nèi)容與人脈。探索高影響力學者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使用行為,有助于對基于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科學交流行為規(guī)律加深理解,同時也能夠幫助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認識其核心用戶特征并不斷優(yōu)化其服務(wù),提升學術(shù)交流與創(chuàng)新效率。
2 研究過程
本研究旨在探究高影響學者對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使用行為特征與規(guī)律,主要研究其注冊行為、信息共享行為與社交行為,并研究其行為與其影響力之間的相關(guān)性。
2.1 研究對象的選擇
ESI學者,全稱為ESI高被引學者(ESI highly cited scholars)。美國Clarivate Analytics公司(原湯森路透知識產(chǎn)權(quán)與科技事業(yè)部)每年將所屬學科領(lǐng)域論文對應(yīng)年度的他引次數(shù)進行統(tǒng)計排序,排名在前1%的論文為該學科領(lǐng)域的高被引論文,其作者即為ESI高被引學者。目前,ESI相關(guān)指標已被學界所公認,因而本研究選擇ESI學者作為高影響力學者的代表進行研究。
RG創(chuàng)立于2008年,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之一[5]126-127。RG旨在服務(wù)全球科研工作者,通過在該平臺上建立賬號,用戶可以發(fā)布個人最新的科研成果且免費查閱其他科研工作者發(fā)布在平臺上的項目,尋找有相同研究興趣的研究人員。本項研究選擇RG作為研究平臺,對ESI學者的使用行為進行研究。① ESI學者名單數(shù)據(jù)見https://clarivate.com/her/.
2.2 數(shù)據(jù)來源及分析
2.2.1 ESI學者名單的獲取
本研究通過ESI學者官方網(wǎng)站①獲取了2017年度ESI學者名單,該名單中包括3538位學者。我們對數(shù)據(jù)進行了清洗處理,重點對同一學者跨學科的情況進行了合并處理,合并后學者實為3332位。這些學者分別來自58個不同的國家和21個不同的細分學科。我們按照ISI的分類規(guī)則將該21個學科分為5個大類,分別為工程學、自然科學、健康科學、生命科學及社會科學,以進行后期分析(見圖1)。

圖1 ESI學者分布及其RG注冊數(shù)
2.2.2 ESI學者RG行為數(shù)據(jù)獲取
本研究通過以下過程來獲取ESI學者在RG平臺上的行為數(shù)據(jù):
首先,在RG平臺上手工檢索學者姓名。考慮到國內(nèi)外對姓名認知的差異以及學者注冊時可能使用的姓名的差異,其檢索規(guī)則采用Mas-Bleda[6]提出的方案。同時考慮到存在重名現(xiàn)象,應(yīng)結(jié)合學者單位、學位等信息共同篩選,以確定該學者是否已進行注冊。如已注冊,則記錄其個人主頁(Profile)的URL。
其次,利用自主開發(fā)的數(shù)據(jù)獲取軟件,通過URL獲取并解析已注冊ESI學者基本信息,記錄各相關(guān)指標數(shù)據(jù),各指標(見表1)的具體意義可參見RG網(wǎng)站。在研究資料下,列有較多二級類目,如論文、會議論文、報告、全文(Full-text)等,因數(shù)量較多,不一一列舉。值得注意的是,全文并非是指該學者所擁有的研究資料的全文數(shù),而是特指由該學者親自上傳的全文總數(shù)。

表1 RG用戶信息分類及其指標
2.2.3 ESI學者RG行為數(shù)據(jù)處理與分析
本次采集到的行為指標數(shù)據(jù)存在很多指標數(shù)據(jù)特別是二級指標數(shù)據(jù)缺失的情況,為了后續(xù)統(tǒng)計,筆者人工進行缺失值補0。數(shù)據(jù)處理完畢后從三個方面對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一是對ESI學者注冊行為進行分析,重點考察學科對于其注冊行為的影響;二是對ESI學者的信息共享行為和社交行為進行分析,對相應(yīng)的指標數(shù)據(jù)進行描述性統(tǒng)計分析;三是對ESI學者學術(shù)RG顯示度與影響力指標數(shù)據(jù)進行描述性統(tǒng)計分析,并對信息共享行為、社交行為與影響力之間的相關(guān)性進行深入分析。
3 研究結(jié)果與討論
3.1 ESI學者RG注冊行為
本研究中,ESI學者在RG平臺上的注冊率為38.66%(1288/3332)。目前,已有較多研究針對學者對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注冊比率進行了調(diào)查研究。其中,《Nature》雜志社的調(diào)查研究由于樣本量較大而較為具有代表性。該調(diào)查于2014年展開,來自全球的3000多名學者回復(fù)了這項調(diào)查,有接近一半的學者回應(yīng)稱知曉并經(jīng)常訪問RG。而這其中,有29%的學者注冊了RG賬戶[5]127。從注冊比例來看,本研究中的注冊比例遠高于《Nature》調(diào)查中用戶的注冊比例(折算比例約15%)。對相關(guān)研究的綜合分析表明,學者使用RG的目的主要有社交與互動、信息獲取和知識分享、進行學術(shù)合作等[7]。從RG的功能來看,僅有信息獲取比如檢索文獻、下載文獻等不需要進行注冊,其他均需注冊。因而,本項研究表明ESI學者可能比一般學者對于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使用意愿更為強烈。同時,從時間上看,近些年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日益盛行,學者對于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接受度日益提高,這也是ESI學者RG注冊比例較高的原因之一。
當前,研究人員的在線顯示(online presence)已成為提升其學術(shù)影響力的重要渠道。在傳統(tǒng)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研究人員創(chuàng)建個人主頁,或者在機構(gòu)網(wǎng)站上展示個人信息成為通行做法。而在社會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研究人員則廣泛利用社交媒體來“創(chuàng)建、促進和測度學術(shù)聲望”[8],并由此“獲得、保持在線學術(shù)身份”[9]。盡管存有疑問,但仍有部分研究指出,對社交工具的利用能夠幫助研究人員及其研究成果獲取更為廣泛的關(guān)注[10]。RG作為專門服務(wù)于科研群體的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服務(wù),為已注冊研究人員提供創(chuàng)建主頁(Profile)、上傳研究論文、關(guān)注同行、參與主題討論等功能,顯然能夠為研究人員帶來最大限度的學術(shù)影響力提升效應(yīng),因而ESI學者的高注冊率便不難理解。
本文也對不同學科ESI學者注冊情況進行了深入分析,其結(jié)果如圖1所示。圖1顯示,社會科學領(lǐng)域ESI學者盡管在絕對數(shù)量上不占優(yōu)勢,但其注冊比例最高。注冊比例及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數(shù)據(jù)也顯示,社會科學與工程學、生命科學之間注冊率極為接近,并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但與健康科學、自然科學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5)。
以往的研究表明,不同學科學者對于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采納率存在差異,同時對于不同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使用也存在傾向性,比如自然科學學者較社會科學學者更傾向于使用RG[13]。顯然,本文對于ESI學者的研究結(jié)果與上述結(jié)論既有共性,亦有差異。
一方面,本文研究結(jié)論顯示,不同學科之間對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注冊和采納行為確實存在一定差異,而這一點至關(guān)重要,它至少意味著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服務(wù)的設(shè)計與優(yōu)化應(yīng)當遵循“領(lǐng)域?qū)颉?domain-oriented)的基本原則。當前,許多新的針對科研群體的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不斷出現(xiàn),以我國為例,萬方等知名學術(shù)信息企業(yè)均有意涉足該項服務(wù)。但令人遺憾的是,相關(guān)服務(wù)并沒有考慮這一特性,同質(zhì)化現(xiàn)象較為嚴重。
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社會科學領(lǐng)域ESI學者RG注冊率最高,這與以往的調(diào)查結(jié)論有所不同。筆者認為這一結(jié)果反映出社會科學領(lǐng)域的ESI學者相比普通學者群體而言,對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使用意愿更為強烈,同時也隱含著這樣一個觀點,即隨著時間的變化,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服務(wù)和用戶群體都處于變化當中,而學科群體的聚集是對變化最為直觀的反映,這也提示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應(yīng)不斷跟蹤用戶行為模式的變化,以便不斷優(yōu)化服務(wù)。由于研究平臺單一的局限性,筆者無法考察本文的觀察是否是特例。但顯然,以往這種籠統(tǒng)的結(jié)論可能會隱藏某些學科或特殊群體的交流行為特質(zhì),形成固有錯誤觀念并進而可能導(dǎo)致未來服務(wù)的偏差。
3.2 已注冊ESI學者的信息共享行為
科研信息的共享是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重要功能之一。研究表明,獲取科研信息特別是文獻是研究人員使用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重要動機。RG為研究人員共享科研信息提供了十分便捷的渠道,研究人員可以共享研究項目信息和研究資料。這些信息中,一部分已經(jīng)公開出版或公布,如項目、論文、會議論文等;另一部分則沒有公開出版或公布,如報告(Presentation)等。對于已經(jīng)公開的特別是已公開出版的資料,RG能夠較為全面地收錄,并且提供了作者認領(lǐng)機制,允許系統(tǒng)向已注冊用戶推薦與其姓名相符的已公開發(fā)布的研究資料信息,用戶可以確認該資料是否為自己發(fā)表的資料。對于未公開出版或公布的信息,則大多依賴用戶自己手動添加相關(guān)信息進行共享。本文對ESI學者共享的信息進行了統(tǒng)計,其結(jié)果見表2。

表2 ESI學者RG信息共享行為指標的統(tǒng)計(N=1288)
整體上看,各項數(shù)據(jù)均不遵從正態(tài)分布。進一步的數(shù)據(jù)擬合則表明,各項數(shù)據(jù)分布大多近似于冪律分布,說明少數(shù)ESI學者共享了較多的信息,而大多數(shù)ESI學者只共享了為數(shù)不多的信息。進一步地將數(shù)據(jù)進行細分,則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的一些差異。
針對已公開出版或公布信息的共享,ESI學者總體呈現(xiàn)較高的水平:每位學者平均提交了2.74個項目,最高的提交了35個科研項目信息;每位學者平均提交了364.12項研究資料,最高的提交了2962項研究資料。通過數(shù)據(jù)可以確認的是,一方面,RG提供的認領(lǐng)機制是非常有效的。這一機制免除了用戶手工輸入信息的煩瑣,有利于吸引并維系更多的用戶使用,也有利于為用戶提供最大的顯示度。另一方面,ESI學者通過共享信息來擴展自己學術(shù)影響力的意愿非常強烈。在學術(shù)界,學者在個人網(wǎng)站或所在機構(gòu)網(wǎng)站提供自己主持或參與的科研項目信息以及發(fā)表的論文信息等已是慣例。社會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ESI學者可以通過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如LinkedIn等)來公開信息以擴大學術(shù)影響力,而RG作為新型的學術(shù)交流平臺,無疑為這種行為提供了極佳的機會[12]。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們之前觀察到的,全文數(shù)代表了用戶自主(非經(jīng)其他人)上傳的全文數(shù)量,代表了用戶主動共享論文資料的真實意愿。筆者統(tǒng)計分析了全文數(shù)據(jù),其平均值為112.53項,其共享全文的平均比例達30%,可見ESI學者通過共享公開研究資料以擴大學術(shù)影響力的意愿之強。
針對非公開出版或公布信息的共享,ESI學者則總體呈現(xiàn)較低的水平,在可觀測的項目上,預(yù)印本的人均提交量僅為0.048項,最高僅為11項;而報告(Presentation)的人均提交量僅為0.13項,最高提交量僅為10項。除該兩項之外,其他項目觀測水平均非常之低。這一原因主要有二:一是RG對非公開出版或公布信息無法提供認領(lǐng)機制,必須由用戶自主手工錄入相關(guān)信息,對于ESI學者而言,可能并沒有太多時間用于信息的錄入;二是,學者影響力主要來源于公開出版的信息,非公開出版或公布信息對于學術(shù)影響力的提升較為有限,學者共享此類信息的意愿較弱。
3.3 已注冊ESI學者的社交行為
社交也是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重要功能之一。對于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而言,其創(chuàng)立的目的便是經(jīng)由社交關(guān)系進而達到學術(shù)交流的目的。RG為用戶提供了三個細分社交功能:一是對于個人信息的展示,主要包括對個人履歷、研究專長(Skills and expertise)以及所關(guān)注的研究主題(Topics)的展示;二是學者對于其他學者的關(guān)注;三是在平臺提出問題與回答問題。本文對涉及的功能各指標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表3)。

表3 ESI學者RG社交行為指標的統(tǒng)計(N=1288)
RG提供了基于研究主題的信息匯聚機制,在研究主題下,匯聚了最新的項目、論文、問答以及專家等。用戶可以選擇是否擅長于該主題,一旦選擇,則其所有共享的信息都將及時匯聚到該主題下。用戶也可以關(guān)注某主題以獲取最新信息。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ESI學者人均提供了11.78個研究特長點,說明ESI學者對外信息展示、共享研究信息的意愿較強。與此同時,ESI學者人均關(guān)注了6.57個研究主題,與其提供的特長點數(shù)量相比,懸殊較大。事實上,選擇的特長點越多,意味著ESI學者的科研信息可能在更廣的群體中擴散。而關(guān)注的主題越多,則意味其接收到其他學者的科研信息越多,同時無關(guān)信息也可能越多,所以在關(guān)注主題方面,ESI學者尤為謹慎,更傾向于選擇與自己需求密切相關(guān)的主題。
與傳統(tǒng)學術(shù)交流平臺不同的是,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用戶經(jīng)由關(guān)注(Following)與被關(guān)注(Followers)形成社交關(guān)系,并經(jīng)由該關(guān)系形成學術(shù)信息的追蹤與學術(shù)信息的交流。關(guān)注行為代表了學者的主動社交行為,一旦關(guān)注了某學者,可以在系統(tǒng)中得到對于該學者所共享科研信息的自動推送,同時也可能增加與其他學者交流的概率。從表3數(shù)據(jù)來看,ESI學者人均關(guān)注了81.05人。我們與耿斌等人[13]對南京大學學者在RG平臺的平均關(guān)注數(shù)(20.22)進行了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ESI學者關(guān)注的人數(shù)遠超平均水平,其社交意愿總體較為強烈。
除此之外,RG還提供了問答機制,允許用戶提出問題,并回答別人所提出的問題[14]。問答機制是RG提供給用戶非常重要的交流渠道,但已有研究也表明,與微博等社交工具不同的是,研究人員似乎很少使用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站進行非正式的個人交流[9]。表3數(shù)據(jù)顯示,ESI學者平均僅提出了0.03項問題,僅回答了0.51項問題,其整體參與問答進行非正式交流的意愿較弱。這些數(shù)據(jù)也暗示,ESI學者更傾向于進行基于信息共享的正式信息交流。目前,已有相關(guān)研究對研究人員使用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動機進行了分析,結(jié)果顯示學術(shù)性動機比社交動機更為重要[15]。研究人員通過關(guān)注其他學者以跟蹤最新研究進展情況、獲取研究資源,同時也在平臺上分享自身的研究項目、研究資料等,以最大限度地擴大自身學術(shù)影響力和顯示度。顯然,這一行為對于良性的學術(shù)社交生態(tài)系統(tǒng)構(gòu)建至關(guān)重要。
3.4 已注冊ESI學者的影響力測度
在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上,學者的影響力既有傳統(tǒng)的學術(shù)影響力,同時也包含了其社交影響力。RG提供了若干指標以測度用戶的影響力,除了以往業(yè)內(nèi)所熟知的被引次數(shù)、h指數(shù)外,RG還提供了被關(guān)注數(shù)、被閱讀數(shù)、RG指數(shù)等自定義指標。根據(jù)RG對各指標的說明,被關(guān)注數(shù)及被閱讀數(shù)大致可以被視為社交影響力指標,而被引、h指數(shù)則通常被視為學術(shù)影響力指標,RG指數(shù)則兩者兼顧。各相關(guān)指標統(tǒng)計分析結(jié)果見表4。
表4結(jié)果顯示,ESI學者平均得到了520.32人的關(guān)注,平均被閱讀次數(shù)為32700.76次,平均被引次數(shù)為23868.55,RG指數(shù)平均為41.97,h指數(shù)平均值為62.44。總體上看,ESI學者無論是學術(shù)影響力還是社交影響力都非常高,這既是對ESI學者群體影響力的客觀體現(xiàn),同時也說明RG作為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巨大價值所在。盡管如此,數(shù)據(jù)也表明,仍有部分ESI學者在初始注冊后,未能持續(xù)使用RG,說明RG在吸引ESI學者持續(xù)使用方面仍有進步空間。
為了探討ESI學者使用行為對其影響力的影響,筆者對RG中相關(guān)指標進行了相關(guān)性檢驗。根據(jù)K-S檢驗結(jié)果,選取非參數(shù)檢驗中的Spearman檢驗方法,其檢驗結(jié)果如表5所示。

表5 不同測度指標之間的相關(guān)性
注:*相關(guān)性在0.05水平上顯著(雙尾);**在0.01水平(雙尾)上呈現(xiàn)顯著相關(guān)。
3.4.1 ESI學者信息共享行為與影響力的相關(guān)性
表5結(jié)果顯示,ESI學者所共享的項目與研究資料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guān)性(r=0.539>0.5)。一般而言,ESI學者主持項目越多,其研究產(chǎn)出也可能更多,也更愿意將研究資料予以共享。我們重點關(guān)注ESI學者信息共享行為對其影響力的影響。
針對ESI學者RG平臺社交影響力的分析可表明,ESI學者所共享的信息(項目與研究資料)與被關(guān)注、被閱讀之間均存在較強的相關(guān)性(r>0.5),這說明用戶在平臺上共享的信息越多,就有更大的概率獲得其他學者關(guān)注,同時也能獲取更多的閱讀次數(shù),因而可以認為ESI學者共享信息可以提升其社交影響力。
筆者對ESI學者所共享信息與其RG平臺學術(shù)影響力的相關(guān)性也進行了分析。分析結(jié)果表明,ESI學者所共享的研究資料與其被引、h指數(shù)之間均存在較強的相關(guān)性(0.7 相關(guān)性檢驗結(jié)果還表明,ESI學者共享信息行為與RG指數(shù)之間的相關(guān)性均高于其與社交影響力和學術(shù)影響力指標之間的相關(guān)性。在社交網(wǎng)絡(luò)時代,發(fā)展有效的學者影響力替代測度指標已成為一種趨勢。RG指數(shù)作為RG平臺獨有的指標,有效地結(jié)合了社交與學術(shù)影響力,成為衡量學者影響力的重要途徑。 3.4.2 ESI學者社交行為與影響力的相關(guān)性 本研究考察了ESI學者社交行為與其信息共享行為及影響力指標之間的相關(guān)性。數(shù)據(jù)顯示,ESI學者社交行為指標與其信息共享行為指標之間僅存在非常弱的相關(guān)性或不存在相關(guān)性(表5)。筆者重點關(guān)注ESI學者社交行為對其影響力的影響。 數(shù)據(jù)顯示,ESI學者社交行為指標(特長、主題、關(guān)注)與社交影響力指標(被關(guān)注、被閱讀)之間僅存在非常弱的相關(guān)性,僅關(guān)注與被關(guān)注這兩個指標存在較弱的相關(guān)性(r=0.415),同時與學術(shù)影響力指標(被引、h指數(shù))之間幾乎不存在相關(guān)性或存在極弱的相關(guān)性。這充分說明,目前ESI學者在RG上的社交行為對于其社交影響力和學術(shù)影響力的提升極為有限。 本文以2017年ESI學者為研究對象,研究了其對RG的使用行為特征與規(guī)律。本文的主要研究結(jié)論如下: (1)ESI學者在RG平臺上的注冊率高達38.66%,其對于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采納意愿非常強,同時學科的差異性也客觀存在,社會科學領(lǐng)域ESI學者的使用意愿最為強烈。 (2)ESI學者更傾向于共享公開的項目和研究資料等能夠提升顯示度和影響力的信息,對于未公開發(fā)布或出版信息的共享意愿較弱。 (3)ESI學者RG平臺上的社交行為以信息的展示和信息的獲取為主,而對基于問答的信息交流行為參與意愿較弱。 (4)ESI學者信息共享行為能顯著提升其社交和學術(shù)影響力,而現(xiàn)有的社交行為則對其社交和學術(shù)影響提升作用有限。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本研究只考慮了RG這一平臺,而對于其他學術(shù)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的考察則未能進行,這導(dǎo)致研究結(jié)論的推廣上具有一定局限性;其次,本研究對使用行為的劃分較為粗略,同時對使用行為的表征過于強調(diào)量化研究,而對相應(yīng)的質(zhì)性研究缺乏關(guān)注,比如對用戶所提供的個人履歷、問答內(nèi)容的分析等,這有賴于后續(xù)更為深入的研究。4 研究結(jié)論與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