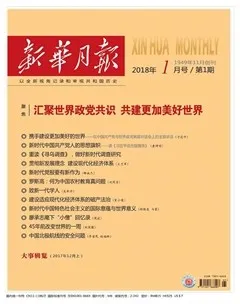致新一代學人
“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制度,于今已四十周年。我們最早幾屆大學生(包括少數工農兵學員)以上世紀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期出生者居多。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一批學人進入學術領域,引發或推動了學術界、思想界的重要變革。四十年過去了,在文史領域里,這批人能橫刀立馬繼續引領學界的尚有人在,但多數學者已不免有廉頗老矣之嘆。生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年富力強的中生代,正值學術高峰期和盛產期,是學術界的中堅力量。
我本人更為關注的是另一批人,就是“文革”后出生的、目前最有活力、最具潛質的一批年輕學者。他們與我們,在年代上有一個交集點,那就是“文革”結束與改革開放。我們在此時進入高校和學術界,而他們則在那個年代出生。這兩代學者具有強烈的對比度,放到一起看,可以說相映成趣。從學術傳承關系來說,這兩代學者是師徒關系。新一代學人基本是老一代學人的學生輩。從社會關系來看,又剛好是父子輩。
人生中,師徒與父子是一種很奇特的關系。一方面關系當然親密,另一方面,有出息的徒弟和孩子往往有一種強烈的叛逆意識和超越感。
人文領域里的一代新學人已悄然崛起。當年,歐陽修讀到后生蘇軾的文章之后慨嘆道:“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我雖然沒有歐陽修那樣的身份和地位,但讀年輕人學術成果時,往往也有類似“不覺汗出,快哉快哉”的感覺。
經常有年輕人問我,能不能超越我們這一代學人。我的回答是:應該超越,期待超越。
古人說,見過于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一般來說,學生應該超越老師,這是常態,然并非鐵律。我之所以說新一代學者應該超越我們,因為他們具備了比我們優越太多的條件。新一代學者所具備的優勢,體現了時代的總體進步。
新一代學者的崛起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標志著中國學術發展出現新的常態,也意味著中國學術正在發生轉折性變化。這具有特殊的學術史意義。
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不一樣,文學創作有“窮而后工”之說,而學術研究則需要長期平靜而安寧的生活環境和較好的物質條件。新一代學者,生于改革開放,長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長期穩定,沒有過大的跌宕起伏。這是從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最快的年代,這種高速發展在全世界都是一個奇跡。而中國從1979年開始全面實施獨生子女政策,出生于城鎮的新一代學者,基本是最早的獨生子女,出身于農村非獨生子女家庭的,往往也是家中掌上之寶,他們集各種關愛和期待于一身,是最早在物質條件方面享受改革開放紅利的一代學人。
從學術研究的環境來看,新一代學人進入學術界,已是21世紀,中國高校與研究機構的硬件有了明顯改善,而著名高校的教學科研條件與國外高校相比,差距已經大大縮小,有些甚至處于世界先進行列。此時中國的高等教育也有了比較規范的體制。他們的導師都受過現代學位制度完整、系統的教育,新一代學人從入門之初就對學術史與學術規范有所認識,并受過比較嚴格、系統的學術訓練,所以很平順而規范地進入學術研究。這是一個開放的時代,中國與海內外的學術交流也極為廣泛,年輕學者都有良好的外語能力,有海外交流經歷,具有更為開闊的理論視野,更為多樣的研究方法。這又是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新一代學者快速地掌握了網絡與大數據方面的技術手段,在世界范圍內大量收集、交流和處理文獻資料,這些都是前輩學人望塵莫及的。這還是一個自媒體時代,善于利用新的傳播方式,也是新一代學者之所長。在自媒體平臺上,每個人都可以及時地發表自己的學術成果,展開公平的討論和交流。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傳統的學術資歷、地位、權威起了消解作用,對年輕學者學術聲譽的獲得與傳播,也是極為有利的。新一代學者在物質與技術層面上,已完全具備超越我輩的能力與條件。
相比之下,我們這一代學者的缺陷是明顯的,總體而言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青少年時期在社會動亂和物質、精神皆極度貧乏中度過。有幸進入大學后,高等教育才剛剛從僵化的體制和落后的水平慢慢地走出來。我曾有個比喻,學術研究如同畫圓圈,圓規兩腳的長短,決定圓的大小。同樣,學者的研究能力決定其研究成就,對于文史研究者而言,須有“舊根底,新眼光”,這兩者就如圓規的兩腳。傳統文史研究者須有特殊的知識結構:對于文、史、哲各學科,必須有較好的基礎;同時對于當代的各種學術思想、研究方法,也要加以吸收,兼收并蓄。坦率地說,我們這一代學者,除少數優秀學者之外,“舊根底”和“新眼光”皆有所欠缺。鑒于此,我們自然對新一代學者有更高期許。
我之所以說新一代學者應該超越吾輩,是比較審慎的說法。因為,老一代學者盡管先天、后天都存在明顯不足,但又獨具特色。他們所親歷的這半個多世紀,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復雜多變的時代。他們經過十年動亂,多數人有過在中國底層社會生活的特殊經歷,因為恢復高考而改變了命運。他們特別珍惜機會,有一種視學術為生命的執著追求。他們又是中國社會變革的親歷者與參與者,對社會、對人生有一種比較深刻而獨到的理解與體驗,有洞察力與整體觀,極富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尤其有一種強烈的人文理想與人文關懷。這些因特殊際遇而形成的精神品質,對于人文學科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些絕對無法靠技術手段或書本知識得來。一代有一代之精神,后人未必嘆贊,也無須摹擬,但它自有一段不可磨滅的光彩。
我在中山大學讀碩士的時候,導師黃海章教授曾以韓愈《答李翊書》中“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這段話勉勵我。后來我到復旦大學讀博士,畢業時,導師王運熙先生也用此語勉勵我。自古以來,名言佳句很多,為什么兩位導師都不約而同地用韓愈的這段話來教導我呢?這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我以前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后來漸漸領悟到,兩位老師忠告我輩切忌“誘于勢利,望其速成”,其實大有深意在焉。我們那個年代,倒是容易做到“無誘于勢利”的,因為那時學術界就不存在什么能誘人的“勢利”。當時有“窮教授、傻博士”“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之類流行語,那些埋頭搞學術的人,實在是不識時務的弱勢或“弱智”群體。但我們這代人,被耽誤的時間實在太長了,時間又是一去不返的,所以自覺不自覺的,不免有“求其速成”之心或之舉。這也是制約我們這一代學人發展的一個原因。前人說,成名要趁早,但學術研究是沒有暴發戶的。快速成名往往等于慢性自殺。我們這代人中,曾有一夜暴得大名的學術明星,就像燃放煙花,瞬間燦爛,頃刻之間,煙消云散,很快就被人遺忘。這就是吾輩“望其速成”的教訓。
到了今天,“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這兩句話,對于新一代學者來說,也未必就過時。
新一代學者中的多數人,從幼兒園開始,一直到博士,都受到不間斷的正規教育。完成了整套教育,也才二三十歲。現在不少人已經是教授、副教授了。本來,對于他們不應該存在“望其速成”的問題,他們完全可以按照學術發展的自然規律,從容不迫地走下去。不過,事實也不完全如此。我們的國家長期處于落后狀態,所以急切追求超常規的快速發展,這是可以理解的。在超出常態的激烈競爭和殘酷的淘汰機制之下,個人若不速成,可能就有被速汰之虞,這使許多年輕學者變得焦慮不安或者變得聰明精致,“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轗軻常苦辛”,這恐怕也是一些年輕人的心態。
其實,“望其速成”的根子就是“誘于勢利”。在當前的學術生態下,“勢利”二字,對于新一代學者的誘惑可能更大。錢鍾書說:“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這句話,現在聽起來,好像是神話。如果說,我們當年處于嚴重的“營養不良”狀態,今天,新一代學者卻處于“富營養化”的生態。名目繁多的科研、教學項目,各種級別的科研獎勵、人才計劃等,數不勝數,令人心馳目眩。學術成果就是榮譽,就是地位,就是金錢。現在,已經有一套非常嚴密和嚴格的績效考核體制,項目、論文、人才與評獎、各種會議成為學者生存的主要方式與評價標準。因此,許多年輕學者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都耗在這些無休無止的俗事雜務之中。但這并非他們所樂意的。我們那個年代,社會處于普遍窮困的狀態,所以個人的安貧樂道倒是比較容易做到的。而現在的年輕學者處于舉目繁華富貴之境,卻要獨自面對著票子、房子、孩子、職稱等重壓,要他們像傳統學者那樣獨守清貧,視名利于敝屣,談何容易!
漢代的司馬相如寫過一段話:“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我絕對相信新一代學者之中,“必有非常之人”,能建“非常之功”。真正能超越吾輩的,正是這些“非常之人”。
新一代學者,要超越吾輩,先要自我超越。一代有一代之所長,一代亦有一代之局限。這一代人,大多以獨生子女之身,處安適裕如之境,浸淫于應試之學,應付乎考核之制,這就使一部分學者容易產生以自我為中心、急功近利之心態與標準化思維。這是新一代學者可能的局限。他們的各種條件雖然比我們優越許多,但所面對的困難和承受的壓力,反而比我們當年大得多。這是特定時代環境所產生的問題。易地而處,我們也難以避免。但新一代學者中必有一批“非常之人”能超越此局限,抗御此壓力:澄懷靜慮、從容淡定。他們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宏大的學術格局,開闊的學術胸襟。他們不以一時之譽、一事之榮為重。他們最在乎的不是發表多少論著,而在于是否在某個領域有大的創見,是否自成一家、獨樹一幟;他們不汲汲于項目的大小、人才的等級,而在乎成果是否能傳世,是否能在學術史上留下一席之地。這就是我們所期待的這一代學者中真正的“非常之人”。我相信,他們必能超越吾輩,而且將創造出世界一流的中國學術。
(摘自2017年11月9日《南方周末》。作者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