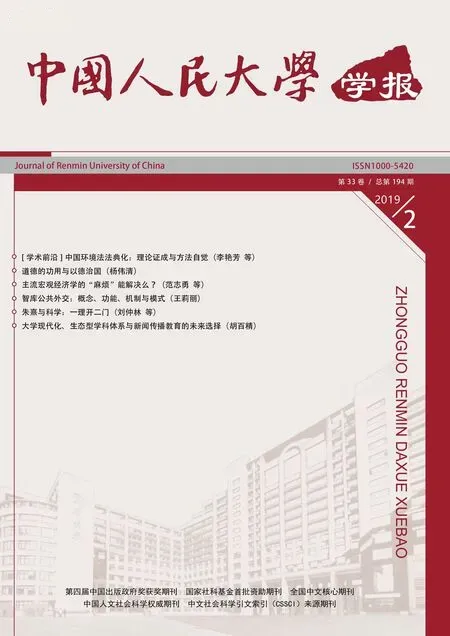自然神學與近代科學的興起
馬建波
科學與宗教的關系是科學史研究中一個具有相當分量和影響力的研究領域。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大體分為內史和外史兩種路徑。外史把宗教作為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外部社會因素來看待,著重考察它對于科學發展的推動或阻礙作用。默頓在其經典名著《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秉持的正是這種思路。內史也即思想史的進路則把宗教思想視為近代科學思想建構的一個內生成分,悉心探討宗教思想如何參與和影響近代科學的演進。相對來說,科學史家吉利思俾(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在《〈創世記〉與地質學》中就更多地采取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兩種路徑具有互補性,對人們理解宗教與科學互動的多樣性都有積極的作用。本文以“近代自然神學”為紐帶,將內史和外史兩種視角結合在一起,以拓展思考科學與宗教關系的深度和廣度。
一、近代自然神學的興盛及特征
在基督教神學思想中,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與啟示神學(Revealed Theology)相對應。前者依靠人的理性來認識和理解上帝,后者則依靠《圣經》和教會認定的權威來宣講信仰。眾所周知,基督教神學思想是古代猶太教的一神信仰與希臘理性精神相結合的產物。因此,自然神學一直在基督教神學傳統中保持著相當強勁的影響力。中世紀神學巨擘托馬斯·阿奎那改造亞里士多德哲學,給出了關于上帝存在的五種證明,是中世紀思辨自然神學的一個極致典范。在近代,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自然神學一度受到思想家們更加充分的關注,進而深刻影響了歐洲近代思想史的運行。
從基督教神學本身的內在邏輯來說,自然神學在近代的濫觴源自宗教改革帶來的思想混亂。宗教改革之后出現的新教諸派別,與羅馬教廷在一些基本教義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加劇了歐洲原本就存在的社會矛盾,從而引發了歐洲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三十年戰爭”(1618—1648)。戰爭中無處不在的暴力和血腥,在促使人們呼吁宗教寬容的同時,也促使他們去尋求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以超越宗派之間的爭執,為信仰找到合理性的根基,從而結束思想混亂的局面。用著名基督教思想史研究者詹姆斯·C·利文斯頓的話來說,在“整個歐洲被宗教戰爭和宗教迫害弄得精疲力竭”之后,人們“產生了一種愿望,想要尋求某種共同的宗教基礎,一切有信仰有理性的人們,不管他們彼此有什么差異,都可以贊同的基礎”[注]詹姆斯·C·利文斯頓:《現代基督教思想——從啟蒙運動到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22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也就是說,其時的人們希望,如果能夠像幾何證明題一樣清清楚楚地證明上帝是存在的,那么關于信仰就不會產生如此多的紛爭,世間也就不會產生如此之多的動蕩。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自然神學被人們寄予厚望。
與中世紀相比,近代自然神學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啟示”以及“奇跡”旗幟鮮明地批判和拒斥。在所有的宗教中,啟示和奇跡都是用來規勸人們皈依的常用手段,基督教在這一點上也不例外。然而,剛剛發生的殘酷宗教迫害卻讓人們意識到,啟示和奇跡只能催生宗教上的狂熱,而無法有效引導信仰。而無所節制的宗教狂熱恰恰是一切混亂和暴力的根源。因此,近代諸多的基督教思想家都不約而同地對傳說和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所謂“奇跡”,自覺地進行了抵制。在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理智健全的人都能夠通過理性認識到上帝的存在,動輒訴諸各種奇跡來渲染上帝的威嚴和無所不能,既不可靠也無必要。英國近代自然神學的奠基人——愛德華·赫伯特(Edward Herbert)在《論真理》(1624年)中就認為:“任何一種對某個啟示大肆宣揚的宗教都不是好的宗教,而一種依靠其權威性來施加教訓的學說也并不總是最為重要的,甚至可能根本就毫無價值。”[注]這種思想顯然來自他對宗教迫害的深刻反省。當宗教信仰脫離理性的指引,僅僅依賴于啟示或者說奇跡的鼓動,只可能陷入盲從而無法自拔。所以,赫伯特強調:“我們應該依靠普遍的智慧來為宗教原則確立根基,以使任何真正來自信仰之命令的東西,都能夠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就像屋頂是由房子所支撐起來的那樣。”[注]愛德華·赫伯特:《論真理》,269、270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同樣,洛克也告誡人們不要寄希望于把宗教信仰的合理基礎建立在奇跡的基礎上,他的自然神學思想集中體現在《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年)一書中。為了避免觸怒保守的宗教信徒,洛克小心翼翼地避開談論奇跡的真假,而是委婉地暗示奇跡不應該成為信仰的核心論題。洛克承認施行奇跡是上帝的權能,他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隨時展示這種權能,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施行奇跡是上帝的慣常的行事方式,更不意味著信仰必須依賴奇跡來保證。相反,洛克認為,除非必要,上帝“倒是經常依照萬物的本性行事以實現自己的目的”[注]洛克:《基督教的合理性》,80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他的意思是,自然按照既定的規則運行,已經是人世間最大的“奇跡”了。對此視而不見,卻對種種怪力亂神孜孜以求,不過旁門左道而已。按照洛克的觀點,奇跡對尚未開化的遠古時期的人來說也許能夠起到作用,但對于今人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人完全能夠通過理性在自然的秩序中發現上帝無處不在的智慧。過多地談論奇跡,不僅無助于堅定人們的信仰,反而會讓他們墮入迷信和虛妄當中。所以,真正的信仰應該通過對自然的理解和認識來達成。
赫伯特和洛克的觀點,在同時代人中引起了廣泛共鳴。在隨后的啟蒙時代,那些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比如伏爾泰、萊辛等人,在對體制化的教會及其僵化的神學體系進行抨擊時,沿襲著同樣的思路。所以,自然神學是啟蒙運動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來源。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近代自然神學對啟示和奇跡的批判,最重要的后果并非是對理性地位的張揚和提升——雖然它毫無疑問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而是從神學的高度確定了自然在認識中的核心地位。中世紀的神學家們也講求理性,然而在他們那里,作為理性認識對象的上帝是抽象而高遠的,因此中世紀的神學主要是由概念推演的玄學思辨模式構成的。近代自然神學在拒斥啟示和奇跡之后,實際上用具體的自然取代了抽象的上帝原本占據的位置。就像洛克所說的那樣,自然本身即是最大的奇跡,它出自造物主的恩賜和創造,所以,能有什么比自然本身的規律性以及和諧完滿更能說明造物主的權能和智慧的呢?人們對一個工匠技巧高低的評判,是通過對他的作品的精巧程度來進行的。既然如此,如果充分揭示出自然內在的秩序,不正好彰顯出創造和設計這一切的上帝的鬼斧神工嗎?自然神學的這種觀點,人們一般稱呼為“設計論”。設計論注重通過發現自然的秩序和規律來窺探上帝的奧秘,客觀上助長了實證精神的勃興。不難看出,占據近代思想史主導地位的機械主義世界觀——那種將自然視為一臺設計精密、運行良好的機器的觀點,背后最大的推手也是自然神學。
近代自然神學放棄了對縹緲的上帝之道的尋求,轉而追索實際的自然之真理;它也不再滿足于從概念到概念的干巴巴討論來證明上帝的存在,轉而通過對自然規律活生生的求證來觸摸上帝的奧秘。這使得自然本身悄然成為新的權威,它不僅是認識的起點和歸宿,也是一切真理的實際仲裁者。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曾經恰如其分地對此進行了概括,他認為在整個啟蒙時代:
基督徒、自然神論者、無神論者——大家全都承認自然界這部大書的權威;假如他們意見不同的話,那也僅只是涉及它的權威的范圍,即涉及它究竟僅僅是肯定抑或是取代舊啟示的權威。在18世紀輿論的氣候下,不管你是尋求對什么問題的答案,自然界總是驗證和標準;人們的思想、習俗和制度假如要想達到完美之境,就顯然必須與“自然界在一切時間里、向一切人顯示”的那些規律相一致。[注]卡爾·貝克爾:《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 》,5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顯然,這樣一種氛圍對于自然科學的發展來說,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二、自然神學為近代科學提供了價值觀基礎
從價值觀的層面看,自然神學對近代科學起到的作用是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其一,自然神學為早期科學的研究者提供了從事科學研究的動機;其二,自然神學為科學自身的合法性辯護提供了理由。人們往往只關注到第一個方面,而忽略了第二個方面;或者把二者混淆起來,忽略了它們之間顯著的區別。我們可以言簡意賅地說明這種區別:前者是科學家說給自己聽的,而后者則是說給別人聽的。
先來看第一個方面。囿于歷史條件,歐洲近代自然科學家大都具有虔誠的宗教信仰。這個客觀事實決定了他們必然會率先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研究工作。從自身的主觀意愿來說,早期的科學研究者們相信,對自然奧秘的探索,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或者,換個說法,他們之所以從事科學研究,相當程度上出自宗教意義上的使命感。
比如,哥白尼在他劃時代的巨著《天體運行論》中,就以一種克制的筆調表達了這一觀點:
雖然一切高尚學術的目的都是誘導人們的心靈戒除邪惡,并把它引向更美好的事物,天文學能夠更充分地完成這一使命。這門學科還能提供非凡的心靈歡樂。當一個人致力于他認為安排得最妥當和受神靈支配的事情時,對它們的深思熟慮會不會激勵他追求最美好的事物并贊美萬物的創造者?[注]哥白尼:《天體運行論》,2頁,武漢,武漢出版社,1992。
相較而言,開普勒的說法則要夸張很多,在提出了奠定近代天文學基礎的行星三定律之后,他用一種飽含濃烈感情的語氣說:
創造我們的上帝啊,我感謝您,您使我醉心于您親手創制的杰作,令我無限欣喜,心神蕩漾。看,我已用您賦予我的全部能力完成了我被指派的任務;我已盡我淺薄的心智所能把握無限的能力,向閱讀這些證明的人展示了您作品的榮耀……如果我因您的作品的令人驚嘆的美而不禁顯得輕率魯莽,或者在這樣一部旨在贊美您的榮耀的作品中追求了我自己在眾人中的名聲,那么請仁慈地寬恕我;最后,愿您屈尊使我的這些證明能夠為您的榮光以及靈魂的拯救盡一份綿薄之力,而千萬不要成為它們的障礙。[注]開普勒:《世界的和諧》,789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
無須羅列過多,我們能夠在近代絕大多數科學名著中找到類似的句子。這很容易理解,在一個宗教氛圍仍然濃郁的時代,科學家們自覺地把自然的規律性歸之于上帝乃是順理成章的,所以在他們看來,在這方面取得的每一點成就,都不過是在為榮耀上帝這項偉大的事業添磚加瓦。
再來看第二個方面。在詳細討論這一點之前,有必要搞清楚一個重要的問題:科學在今天的功能和地位,與近代是完全不同的。
在思考歷史的時候,人們往往不知不覺地陷入一個誤區:如果一個事物在今天具有什么樣的特定功能,那么它在歷史上也理所當然具有這樣的功能;或者,如果它今天被認為非常重要,那么它在歷史上也必定理所當然地被認為重要。拿自然科學來說,它是今天指導人們實踐最有效的知識體系,今天的人們也普遍認為,它是最值得優先發展的事項。因此,很多人也都認為,科學從來就是這樣的,而這也是它自近代以來能夠突飛猛進的原因。不過,事實并非如此,歷史的演進比想象要復雜很多。科學的實用性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展現出來的,它在起初表現得并不那么出色。伏爾泰在一封寫于18世紀20年代的信中就抱怨科學家們對科學的實用性關注不夠,沒能在改善民生上做得更多。[注]伏爾泰:《哲學通信》,132頁,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而是否要支持科學研究,尤其是純粹的理論研究,人們在很長的時間里并未達成共識。英國皇家學會成立于17世紀60年代,但遲至18世紀中期,人們對其意義和性質仍然頗多質疑,這讓該學會一度陷入財政上的窘境。亨利·萊昂斯(Henry Lyons)在《英國皇家學會史》中曾經對此有過精彩的描述。
因而,在科學展現的巨大力量讓所有人膜拜的今天,人們似乎很難理解,宗教上的價值和意義曾經是近代初期科學獲得社會認可的主要理由之一。不過,只要意識到今天與過往歷史情境的巨大差異,理解這一點就不會有什么障礙。在一個宗教信仰仍然被個體視為安身立命之本以及宗教仍然強有力地控制著社會各個方面的時代,著力強調科學的神學功能,在為科學爭取到更高的社會認同度以及關注度方面的作用,當然不可能是無足輕重的。默頓在《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提出所謂“默頓命題”,想要說明的就是這一點。不過他把討論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宗教派別,視野過于狹窄了。實際上,無論出身基督教的何種教派,歐洲近代科學家們都熱衷于宣揚科學在宗教上的意義和價值。
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是科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它的地位和價值在今天當然是毋庸多言的。在當時,該書第二版主編羅格·科茨(Roger Cotes)是這樣為牛頓辯護的:
他把宇宙體系這幅最美麗的圖卷如此清楚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即使是阿爾方索王還活在世上,也不會挑剔說其中缺乏簡單性或和諧性這些優點。現在我們已能更加真切地欣賞自然之美,并陶醉于愉快的深思之中;從而更深刻地激起我們對偉大的造物主和萬物的主宰的敬仰與崇拜之情,這才是哲學的最好和最有價值的果實。如果有誰從事物的這些最明智最具才藝的設計中看不到全能創世主的無窮智慧和仁德,那他必定是個瞎子;而如果它對此視而不見,那他必定是個麻木的瘋子。[注]羅格·科茨:“序”,載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21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
接下來,科茨進一步強調,牛頓體系的最大價值,就在于它是用來對付“無神論者”的強大武器。科茨的這種觀點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里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他研究古希臘哲學同時也是英國國教會牧師,在教堂中的布道便取材于牛頓的這本巨著。為了更好地達到布道的目的,他虛心地向牛頓請教了很多問題,后者也非常熱忱地給予了回應。按照本特利的說法,他的一系列布道取得了很大成功。
三、近代地質學和博物學的自然神學基質
自然科學發展并不平衡,各門學科的成熟程度并非齊頭并進。在近代,像天文學這樣的數學化程度很高的學科,已經日趨成熟,而像地質學和博物學之類的學科才屬起步階段。因而,自然神學對自然科學各學科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對于成熟程度較高的學科,自然神學發揮的作用主要是如前所述的價值觀功能;而對于剛剛起步的學科,除此之外,自然神學還深刻影響到它們的研究內容和形式,構成了這些學科的研究框架。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地質學和博物學在近代其實是特殊形式的實證性自然神學。
1681年,后來成為英王私人牧師的托馬斯·本內特(Thomas Burnet)《關于地球的神圣理論》一書出版,其中充滿了濃郁的自然神學風格。該書以《圣經》為藍本,將地球的歷史分為7個時期,詳細描述了各個時期的特征以及之間的演化。根據《圣經》文本,本內特認為大洪水是影響地球表面形態變化的主要原因,并以一種自然主義的眼光探討了它的由來。在本內特看來,當他把《圣經》中的創世神話還原為一種自然進程的時候,有助于堅定人們對上帝的信仰。本內特很難被認為是一名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家,《關于地球的神圣理論》與《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無論在實際意義還是歷史價值上也都無法相提并論。但不容否認的是,本內特其實提出了后來地質學的研究主題:地球的結構如何?地質演化的主要作用力是什么?[注]在今天,只有視野開闊的科學史家才會把地質學的歷史追溯到本內特。值得一提的是,當代進化論專家、間斷平衡理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提出者之一、卓越的科普作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曾經寫過《托馬斯神父的丑陋的小行星》專門介紹本內特的思想及其影響,該文收入他的博物學隨筆集《自達爾文以來》。等等。更為重要的是,本內特把對地質學的研究視為神學的一部分,以及把大洪水作為地質變化主要作用力的思路,深遠影響到了近代地質學理論的建構。直到19世紀中期,以大洪水為基調的自然神學框架在地質學研究中仍然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科學史家吉利思俾在他的經典作品《〈創世記〉與地質學》中,就詳細分析了這一框架是如何影響到地質學史上歷次重大理論爭論的。因而,近代地質學的發展與自然神學可謂緊密交織在一起。
與地質學相比,近代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有著更加濃郁的自然神學色彩。博物學在西方有著悠久的傳統,是一門對礦物、動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現象進行收集、歸納、分類、記錄的學科。托馬斯·L·漢金斯(Thomas L.Hankins)在《科學與啟蒙運動》中認為,在17世紀存在一場顯著的“博物學的復興”,并認為自然神學的興盛是導致這一結果的重要根源。[注]托馬斯·L·漢金斯:《科學與啟蒙運動》,121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博物學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自然神學,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首先,目的論主導了近代博物學的研究。目的論認為萬物皆有其既定的位置,生物個體結構和功能與生存環境相適應,出自特定的設計而非偶然。雖說目的論思想自古代希臘就有巨大影響力,但近代博物學中的目的論顯然直接來自于自然神學的設計論。物種分類方面的研究之所以成為18世紀博物學的主題,與目的論的強勢影響息息相關。既然物種是按照特定目的被創造出來的,那么它們必然也能被一一對應地放置在恰當的位置,就像人們整理儲物箱。反過來說,如果能夠把物種按照某些特性井井有條地進行分類,那就必然能夠證明它們的確是按照既定目的被創造出來的。林耐的《自然系統》是18世紀物種分類研究方面的最高成就,也是目的論指導之下的集大成之作。
其次,近代博物學的參與者中很多有著正式的神職身份,英語里面有一個專門的名詞“Parson-naturalist”(圣職博物學家)指的就是這類人。他們日復一日嚴謹細致地觀察自然,勤勤懇懇、不厭其煩地描述事物的特征和各種細節,目的是為了論證上帝創造萬物的精妙。在他們愉快地享受這一過程的時候,人們對生物世界的認知和了解也水到渠成地被提高到一個相當的程度。約翰·雷(John Ray)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個典范,他不僅大大推進了植物學研究的水準,也開創了對動物適應現象的研究。他在植物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名為《創世中的神圣智慧》,如果單看書名,人們只會它當成神學著作。
同樣,自然神學在博物學中的影響力到19世紀中期仍然存在。達爾文就坦承他在年輕時深受自然神學的影響。而且有趣的是,盡管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摧毀了舊有的目的論,但他并不排斥有人對他的進化觀點做出自然神學的解釋。
四、結語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論證自然神學是近代科學興起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而只是對歷史進程實事求是地予以客觀描述。自然神學在科學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這些作用,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因為近代自然科學恰好是從基督教文化母體中誕生的。在科學已然昌明的今天,它早已擺脫了自然神學的框架和束縛,更無須借助宗教的力量來獲得認可。然而客觀認識和評價自然神學與自然科學的這段歷史,仍然是不無裨益的。它能夠讓人們充分意識到人類進步之大不易。人類科學的進步和思想的提升,每一次都不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繼承與開拓之間的艱難抉擇中奮勇開辟出來的,其中的蜿蜒曲折、崎嶇逶迤一言難盡。本文所揭示的自然神學與自然科學在近代的互動,直觀地呈現出了人類思想運行的復雜性和曲折性。
自然神學的初衷是論證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但是事實表明,它無法承擔起歷史加之于其上的重擔。在18世紀,自然神學的兩個直系后裔——以霍爾巴赫為代表的樸素唯物論,以及以休謨為代表的哲學上的不可知論,都背離了它的初衷,這頗有些諷刺的意味。
自然神學的設計論與樸素唯物論之間只有一步之遙。設計論預設了一個上帝的存在,并且力圖通過自然的和諧完滿來論證它。但是人們一旦認為自然的和諧完滿足夠充分自洽,那樣一個預設就會越來越喪失其意義和價值,甚至成為一個毫無必要的累贅。因此,當人們毫不猶豫地拋棄掉自然神學中的上帝之后,自然神學就成為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霍爾巴赫在《自然的體系》中就是這樣做的。
與樸素唯物論不同,休謨的不可知論來自對自然神學內在邏輯的批判。休謨從方法論的角度緊緊抓住了自然神學的痛處。休謨指出,自然神學對上帝的設計論證明,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類比。然而類比并非一種嚴格的演繹式證明,而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一種推測。類比的合理性只能建立在相似經驗的基礎上。舉個例子來說,人們看到一部精密的鐘表,推測它必定是某個工匠制造的,這個類比推理很合理,因為人們可以從其他地方看到有人制造過鐘表。但是不管人們發現整個宇宙有多么和諧,推測它必定有一個創造者,也都是錯誤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神創造宇宙的經驗。所以,設計論并不能為信仰提供一個真正堅實的基礎。盡管休謨對自然神學的系統批判集中在晚年的《自然宗教對話錄》中,但在反映其不可知論思想的早期作品《人性論》中,他對因果關系問題的批判性思考,已經深刻體現出對自然神學這種方法論上的駁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