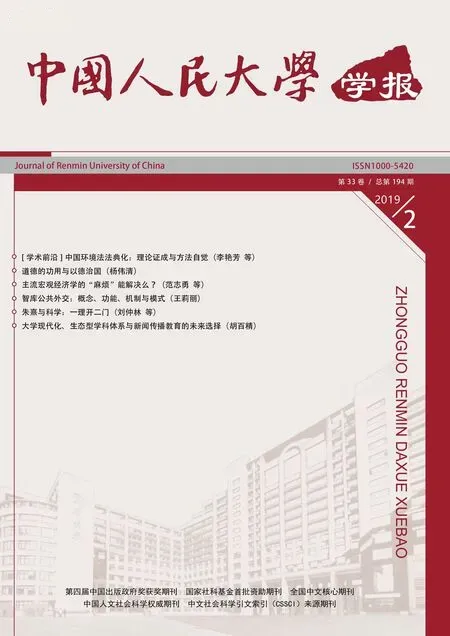大學現代化、生態型學科體系與新聞傳播教育的未來選擇
胡百精
作為傳播學的主要奠基人,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1959年描述了傳播學的歷史方位:十字街頭。[注]① Wilbur Schramm.“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ent”.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59(23).新聞學素來也被公認為雜家之學,向社會和歷史敞開自身。與二者的學術和學科屬性相應,新聞傳播教育一直身處多元交叉地帶,常為時勢、技術和外學科的近鄰所沖擊,以致“邊緣化”“再出發”“整體性否思”甚或“顛覆”之音未絕于耳。持續的身份焦慮和認同危機形成了“領域的騷動”,[注]② 龍強、吳飛:《認同危機與范式之惑:傳播研究反思之反思》,載《國際新聞界》,2008(2)。騷動的實質,便是要走出“十字街頭”,確立新聞傳播學科的自主性和合法性。
及至今日大數據、泛媒介、萬物互聯時代,這種主體性和合法性欲求顯得更加洶涌,遠非“機遇與挑戰并存”“變與不變統一”之類的老話所能平抑。大量論文和演說在檢討新聞理論和實踐的“專業主義”,反思傳播學的主體性、西方進路和中國化,探討新聞傳播教育的改變與改造。十字街頭看起來輝煌又幻滅,前后左右皆可挺進而又令人迷失。這就要以更開闊的觀念、視野來重估新聞傳播教育的歷史方位。本文著眼高等教育現代化進程中三種模式的更迭,從主體性、正當性、有效性等維度切入,辨析多元關系的夾纏、對立和對話,進而提出構建敞開型、生態型學科體系的可能性。生態型的主旨在于強調新聞傳播教育的未來之路是堅守、而非走出“流動的”十字街頭。
一、大學教育現代化與學科合法性危機
在教育思想史領域,人們對現代大學及其知識生產模式的回溯,往往將起點置于洪堡時代和洪堡理想。1809年,深受啟蒙思想熏染的洪堡(Wilhelm Humboldt)創立了柏林大學,他主張大學應出于人的“好奇心”而非功利主義培養人、治學術和服務社會。這一主張后來被表述為著名的洪堡理想(Humboldt ideal):造就自由、自主、平等、心智高貴的人;堅持“純科學模式”,而不必以事功介入社會。大學以涵養純粹心智為中心,舍此便是脫軌或大學精神的墮落。
教育學界將洪堡理想指引下的大學理念和知識生產模式稱為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模式1”。它放棄了中世紀大學的神學本位教育,轉而挺立人的主體地位,開啟了大學教育的現代化進路。“模式1”被認為大抵持續至二戰后,至今仍有人牽念不忘。及至1861年創辦的麻省理工學院已然挑戰了洪堡模式。這所“新式大學”的校徽出現了兩個人物形象:一位是手持經卷的思想者,尚有洪堡理想的余緒;另一位則是工程師,拿著象征工業文明、意在改造世界的工具,大學經世濟用之意昭揭顯現。稍后創辦的霍普金斯大學(1876年)、威斯康新大學(1894年)則被認為是大學真正走向經世濟用、開啟“模式2”時代的標志。及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大學徹底卷入現代化洪流,經受了世俗化和市場化的劇烈改造。學術資本主義和工程師主義逐漸凌駕洪堡理想之上,“模式2”已然成為大學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的主流。
“模式2”主張大學積極介入社會,從專注心智和真理的“象牙塔”轉向一切可能的“應用情境”,解釋和解決國家和時代遭遇的現實問題。為此,大學要生產有用的知識,培養有專業技能的人才。系科和專業分工日趨繁復精細,以契應工業社會的結構與功能之需。模式1向模式2的轉變體現了現代性強烈的進步意志和效率追求,有人認為此乃大學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注]李志峰、高慧、張忠家:《知識生產模式的現代轉型與大學科學研究的模式創新》,載《教育研究》,2014(3)。批評者則指控大學在變得“更現代”“更有用”的同時,背叛洪堡求索高深知識、高貴心智之初心,投靠了學術資本主義。[注]吳洪富:《理性大學·學術資本大學·民主大學——大學轉型的知識社會學闡釋》,載《高等教育研究》,2012(12)。
美國正規新聞教育肇端于20世紀初,正處“模式2”萌芽階段,最早創建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1908年)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1912年)皆表現出強烈的務實和實務取向。1917年,北京大學開設新聞學課程,并于次年組建了新聞學研究會。及至20世紀20年代,芝江大學、上海圣約翰大學、燕京大學等正式開辦新聞系或專業,它們普遍借鑒甚至直接引渡了美國模式。“中國的新聞教育是從美國橫向移植過來的。”[注]張詠、李金銓:《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載李金銓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281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譬如,燕大新聞系素有“小密蘇里”之稱,以提供“急契報界之需”的知識和具有“即戰力”的專業人才為辦學宗旨。[注]張如彥:《新聞教育》,載方漢奇、王潤澤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論文匯編》,第15冊,283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顯然,民國大學的新聞系科因其“美國橫向移植者”身份和救亡圖存的國情而帶有“模式2”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
改革開放后,伴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國新聞傳播學科以產出能夠解釋、解決新聞傳媒和輿論宣傳實踐問題的知識,培養適應新聞傳播實踐需求的人才為導向,并在中西互動中全面擁抱了“模式2”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總體上以生產有用的專業知識生產為職志,重視學生的專業抱負、智識和技能訓練。反映在系科設置上,便是響應、對應傳媒與傳播形態設置精細的專業、方向和人才培養類型。譬如,中國教育部設立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目錄包括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傳播學、網絡新媒體、編輯出版學、數字出版,一些體量稍大的專業之下更依據傳媒生產領域或環節不同而細分若干方向。在理論建設上,即使對新聞傳播問題的哲學反思、范式討論以及對職業理想、倫理的考察,亦強調其實操標準和多元情境下的適用性。
然而,新聞傳播教育對業界和社會的持續主動響應并未真正緩解身份焦慮,至少未能確立學界普遍期待的自主和獨立地位。相反,認同與合法性危機常在教育政策制定與資源分配、跨學科比較與評審、傳媒與傳播實踐變革、技術創新與社會轉型等緊要關頭顯現和發作。所謂合法性危機,即特定主體在核心價值、存在理據和行動正當性上遭遇的挑戰、威脅或顛覆,往往表現為主體性、有效性和正當性等三個方面的缺失、薄弱或偏差。對照工業社會的整體安排和“模式2”原則,新聞傳播學科遭遇如下三重合法性危機實屬必然:
一是主體性危機。“模式2”強調每一學科皆應具足獨特的核心價值和清晰的外部邊界,以在系統分工中確立其主體地位。從學科內部的生成、生長情況看,長期置身十字街頭的新聞傳播學確實存在核心概念、經典理論不足和方法薄弱、專業知識和技能門檻低嵌的窘境。“新聞無學論”從未止歇,傳播學則更像施拉姆所稱的“租界”——很多人來了又走,很多學科穿插而過。[注]Wilbur Schramm.“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ent”.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9(23).人文學科針對新聞與傳播問題的哲學批判、修辭與敘事研究、歷史分析并不遜于新聞傳播學界的努力,甚或在某些縱深領域占據話語霸權;政經法、社會學、心理學和新近崛起的計算科學在介入新聞學、傳播學議題時亦有令人矚目的作為,至少表現出方法上的顯著優勢。對此,凱利(James Carey)在討論“新聞教育錯在哪里”時甚至說,人文和社會學科甚至“以新聞學為恥”[注]James Carey:《新聞教育錯在哪里》,載《國際新聞界》,2002(3)。。而新聞傳播學者一旦將研究議題挺向中心地帶,反而“一不小心”進入了近鄰學科的領地。當喧囂的十字街頭容不下獨立、專屬的理論大廈和知識殿堂,學科主體性危機便呼嘯而至了。
二是有效性危機。按照“模式2”要求,大學分科須與社會系統分工大體匹配,以供給可用、好用的專業知識和人才,而業界對新聞傳播教育最常抱怨的是“理論無用”“理論落后于實踐”。業界的指責在中國新聞教育早期即已存在。1932年4月,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在燕京大學新聞系演講時便提出了“大學何以開展新聞教育”的疑問,他自稱二十年“憑一管筆與社會相見”,“卻未曾讀過一部新聞學的書。”[注]張季鸞:《諸君為什么想做新聞記者?》,載《新聞學研究》,1932。當時很多報界名流都認為大學新聞系未能提供可用、好用的知識和人才,知識難以“契切急需”,人才缺少“即戰力”。實際上,每當社會和技術變革潮起,業界便牢騷熾盛,于今更加甚囂塵上。在大數據、泛媒介、萬物互聯的時代,新聞傳播領域的內容生產、運營管理、技術革新一時由業界主導,大學由觀念和知識的啟蒙者、“立法者”淪為旁觀者和追隨者,學術生產和人才培養面臨整體性重構的挑戰。若全然以有效性的標準度量之,挑戰必然引發危機。
三是正當性危機。正當性亦為合法性的重要范疇,包括經驗和理性兩個維度的正確性與合理性。就經驗而論,正當性表現為行動主體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和尊重;在理性層面,正當性即經過主流道德準則或道德哲學檢驗而獲得信任和確證。新聞傳播教育近年遭遇的正當性批評,主要有學生專業理想黯淡、職業倫理訓練不足、專業主義教育薄弱,以及學界對業界的道義冷漠——譬如當業界遭逢規治上的“艱難時刻”,學界被指認“集體失語”。不唯如此,新聞傳播實踐領域出現的信念缺位、倫理失范或在道德“灰色地帶”的妄言與劣跡,亦常被溯源、歸因于早年新聞傳播教育的虧欠。而在民族國家和人類共同體層面,新聞傳播教育對主流意識形態、公共倫理、共同價值的灌輸方式和涵化效果亦常遭到質疑。
以上指向主體性、有效性、正當性的學科合法性危機,既是實存的,也是建構的,反映了學界的焦慮、自省和改造的決心。惜乎這樣的決心尚未有效解決實存的問題。譬如新聞傳播“中心理論”的創新及其向教學實踐的創造性轉化依然任重道遠,反思仍勝于實績;過度響應業界動態而增設新專業、新方向、新課程的做法難以為繼,馳逐于變化莫測的實踐前沿未免消解大學教育傳統,加劇知識碎片化;專業信念、理想和倫理教育仍主要停留于書本和課堂講授,知識訓練與人格訓練融合的“大培養”格局仍缺少堅固柱石的支撐。當“模式2”框架下的新聞傳播教育還在深受合法性危機之困,大學教育的“模式3”時代降臨了。
二、多元對話與敞開的學科主體性
“模式3”是帶著諸如后現代、后工業、全球化、網絡革命、知識集群、跨界融合等標簽到來的。在2003—2012年間,來自華盛頓大學、斯坦福大學的卡拉雅尼斯(Elias Carayannis)和坎貝爾(David Campbell)等人發表了《創新網絡和知識集群中的知識生產、撒播和應用》《模式3和四重螺旋:走向21世紀分形創新生態系統》等多部(篇)著述,提出并詳述了“模式3”的核心主張和邏輯。新模式直面后工業時代的思想和技術革命,不反對“模式2”對分工和應用情境的追求,但更關切多樣連接、跨界融合、網絡化創新和生態式成長。
“模式3”的核心特征是“多層次、多邊化、多形態、多節點”,強調多元主體在復雜場景下的開放性、包容性對話與合作,以實現“創新驅動”和“協同放大”。[注]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J.“Open Innovation Diplomacy an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Building on the Quadruple and Quintuple Helix Innovation Concepts and the ‘Mode3’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2011(2).循此原則和路徑,學科主體性不再表現為獨善其身的能力、自恃自足的價值、專屬的領地和邊界,而恰為進入多元學科生態、向關聯學科敞開、助益融合創新提供必要性與可能性。換言之,學科主體性走出了傳統上精細分工的自我建構,轉而尋求一種“主體—主體”關系,即培育學科主體間性。理論與實踐、學界與業界的關系亦不再兩廂分立,而是在不同層次、形態和節點上拓展多樣共生、彼此增益的合作場景。
在空間維度,“模式3”主張跨界、跨學科、跨文化的一切可能的鏈接,以建立“全球—在地”的知識集群。與此相應,學科正當性將接受多元主體在更廣闊范圍內的持續檢驗,直到將自身的正當性契入公共性。而公共性乃多元主體通過對話形塑的互為主體性,在經驗和理性上表現為基于多元共識的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和公共倫理。在時間維度,“模式3”是一種動態更新、實時共享、同步反饋的知識生產機制,強調多元主體對應用場景的靈敏響應和適應。為此,學科及其知識生產的有效性首先表現為動態更新、實時共享的能力,進而要在復雜的具體情境中評價其效用。
顯然,模式3的時代標簽今日已打在新聞傳播學科身上,并且具化為算法、大數據、社交網絡、人工智能、媒介融合、萬物互聯等更貼合學科屬性的諸多印跡。按照“模式3”的邏輯,新聞傳播學科應從平衡如下多重關系入手,重構學科主體性、有效性和正當性:
一是重構學科間關系,構建敞開的學科主體性。如是敞開,包括內部融通和外部拓展兩個指向。向內者,即打破學科內部的專業壁壘,人才培養機制由“專業—方向”轉向“項目—任務”或“興趣—專長”,知識生產機制亦然。目前,新聞傳播學科仍主要依照媒介和傳播形態劃分專業領域,每一教師皆歸屬于特定教研室或系科,每一學生皆進入特定專業及其細分方向。這種壁壘分明的專業分工,限制了融媒體、公共傳播時代人才培養、學術創新的想象力和現實選擇。新聞傳播學科理應穿越乃至取消內部的專業邊界,依據學生的興趣和專長,設立承載特定培養任務的人才項目。這些項目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其自由選擇,包容其稟賦和氣質,因材施教,個性化培養,進而將之培育為興趣、任務導向的學術共同體和成長共同體。
向外者,即主動敞開自身,尋求跨學科對話與合作。“模式3”提出的融合創新理念沒用多久便成為高等教育界的共識。新聞傳播教育自然也認識到了學科開放的重要性,卻未免擔憂本學科在邊界突圍、多元融合中持續弱化自身的獨立自主地位——十字街頭的焦慮由來已久。而若將大學現代化視為一個整體性的歷史進程,將模式1、模式2、模式3的次遞更迭理解為這一進程中的必然安排,即可得出兩個基本判斷:新聞傳播學科在“模式2”階段于大學教育中獲得了一席之地,但并未完成自身主體性建構,十字街頭的處境持續引發合法性危機;而在“模式3”時代,學科主體性不再完全源于固守堡壘、看護邊界的能力,而是尋求在多元對話中成就開放、共享的價值,十字街頭恰好可以轉換為對話、合作、融合創新的場景。往昔走出十字街頭的焦慮和沖動,自然亦應轉換為構建敞開的主體性或曰學科主體間性的動力。
二是重構理論與實踐、學界與業界關系,拓展多元、多維、多節點的應用場景。互聯網革命引發了新聞傳播教育和業界的劇烈變遷,二者所遭遇的巨變既有相同的結構和方式,亦有不同的邏輯和進路。除了各自應變,教育與業界的關系也處于調整、重構之中:“人才供給—人才使用”“學術引領—實踐轉化”的傳統關系變得緊張,理論與實踐、學界與業界的鴻溝或有加深之勢。從教育一端看,有效性危機——諸如“理論無用”“理論落后于實踐”、人才缺少“即戰力”的批評再度盛行。所謂有用與無用、引領與落后之爭,一方面表達了人們對教育的憂思,另一方面也犯了簡單二元論的錯誤。學界與業界未必是非前即后的二元關系。在人才培養方面,大學教育有時恰要守在原地,不忘立德樹人之初心,致力于培養有抱負、有德性、有擔當、有美感的年輕人,而不是為業界輸送生產車間的技工;在理論研究方面,學術的也未必領跑業界或尾隨其后做出總結,而應站在高處,或批判其在規律、德性和文化上的偏差。業界及其實踐亦有自己的價值、功能和邏輯,不必成為學界某些概念和理論的操演場,正如大學教育不應成為業界的前置車間或技校。
由于共同面臨著信息傳播技術革命帶來的顛覆性巨變,新聞傳播教育界和業界之間對話、合作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和迫切。對話尊重多樣性和差異性,進而謀求復調和共生的可能性,而非一廂投向另一廂的懷抱,在迎合中喪失自主的憑據。根據“模式3”的主張,教育與業界應基于有效對話,共同創造新型知識生產體系。這一體系承認多樣性和差異性,堅持問題導向,構建創新驅動的關系網絡,針對關鍵節點尋求可能的突破。為此,教育與業界應拓展多維度、多層次合作空間——如共建團隊和實驗平臺、數據與知識產權共享、課程與產品聯合開發,并根據具體應用場景動態調整合作內容和方式。
三是重構公共倫理、大學精神與專業理想之間的關系,確立后真相時代的學科正當性。“模式3”描繪了一個無邊界、全鏈接、開放性、包容性的知識創新網絡,進入其中的多元主體必然面臨價值協商和校準問題。每一主體皆有其價值排序和正當性追求,這就要求基于多元對話尋找共同價值、培育公共倫理。具體到新聞傳播學科,對專業理想、職業倫理的研究和教育亦應契入公共性的價值安排和倫理選擇,持存個性而又不悖公共性。正是在二者的平衡中,學科正當性得以確立。“傳統新聞職業道德的演進趨勢,很可能是兩個方向:一是新聞職業道德要求的公共化、大眾化……二是新聞職業道德進一步窄化、專業化。”[注]楊保軍:《公共化或社會化:“后新聞業時代”新聞道德的一種走向》,載《編輯學刊》,2010(3)。值得深究的是,“模式3”在拓展“模式2”的同時,確乎存在進一步疏離、背叛“模式1”洪堡理想的風險。它更關切知識創新的場景和路徑,而相對忽視傳統大學精神的生成和持守。卡拉雅尼斯等人也承認,“模式3”將引領大學趨向“學術企業”。[注]Campbell D F J.“Guttel W H.Knowledge Production of Firms Research Networks and the ‘Scientification’ of Business 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5(31).那么,洪堡理想所召喚的求真、獨立、自由、平等和批判精神何以安立?這些精神與新聞傳播教育所倡導的專業理想和倫理準則高度契合,也是重振學科正當性的重要價值依據。在今日泛媒介、后真相時代,造就追求真理、獨立思考、自由表達且有批判精神的專業人才,仍為新聞傳播教育使命所系。
每一種模式皆有其局限。“模式1”倡揚的大學理想總能令人生起信念或道德正當性上的“歸鄉感”,但它很難支撐當代大學合法性中的有效性;“模式2”“模式3”逐步推動大學趨向“接地氣”的功利主義效用,而正當性困境則可能持續加劇。在此背景下,今日新聞傳播學科正當性的建構實則面臨兩種選擇:一方面擁抱新時代、新形勢,對外積極介入、參與公共性的培育;另一面則不妨做保守派,無論時勢、技術和知識生產模式經歷何等劇變,皆護持大學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的初心。兩種選擇看似矛盾,而假以融合發展的眼光,未來大學的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未必因循線性更迭模式,亦不應受限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論。三種模式的差異和矛盾正是對話、融合的張力、動力之源。照此理解,未來新聞傳播科學科的正當性培育,既非重返、固守啟蒙時代的洪堡理想,亦非滑向“學術企業”的事功和逐利精神,而是二者的對話、平衡與共創。
三、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國新聞傳播教育改革
以上從三條縱線——模式1、模式2、模式3切入,結合三個平行維度——主體性、有效性、正當性的考察,初步解釋了新聞傳播教育變革與學科合法性問題。若將這一分析框架應用于中國情境下的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和創新,則可得出一些共性結論和特殊判斷。而在討論這些結論和判斷之前,尚須確認一個前提:就歷史方位而論,中國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學新聞傳播教育是否也正在經歷新一輪現代化進程?或者說,是否也面臨由“模式2”向“模式3”的演進?
從歷史和經驗層面回答這個問題并不困難。早在民國時期,新聞教育已經提出服務國家現代化、建設現代社會、啟蒙大眾、促進民主等帶有鮮明現代性色彩的辦學宗旨。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新聞傳播教育及其對應的新聞輿論工作始終是中國現代化事業重要而特殊的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后,新聞輿論工作的地位上升至“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構建現代新聞傳播體系成為國家戰略。及至2018年9月全國教育大會召開,教育現代化、創新驅動、協同發展、“互聯網+教育”成為大會主題詞,并將之寫入“中國教育2035行動計劃”。教育部、中宣部下發“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計劃2.0”則可被視為官方推進“模式3”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行動綱領。從新聞傳播教育近年的改革實踐看,諸如專業融合、跨學科培養、技術導入、創新創業等“模式3”意義上的舉措已取得實績。當然,全國600余家新聞傳播院系、1 200余家學科點發展并不均衡,部分仍處專業初建、資源積聚階段,從“模式2”邁向“模式3”尚有力所不逮處。而一些條件充裕的后來者——譬如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理工科為主型高校創辦的新聞傳播院系,則善用后發之勢,順勢進入了“模式3”情境。
綜上可知,中國新聞傳播教育亦處現代化進路之中,同樣面臨“模式2”向“模式3”的轉換。既確認如是,以下便探討新時代、新模式下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可能方案:
一是學科正當性建設。立足中國國情考察新聞傳播學科的合法性和可持續發展,首先應面對的是學科正當性問題,而這一正當性的首要來源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確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是中西新聞傳播學科建設的根本差異所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新聞傳播教育和實踐奉行新聞專業主義(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強調客觀性、獨立性和自由主義的新聞傳播原則。中國共產黨基于唯物史觀和長期革命、建設經驗提出,應堅持黨的領導與新聞傳播規律、黨性與人民性、輿論引導與輿論監督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據此,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聞傳播教育應構建中國新聞傳播學術話語體系,培養中國新聞輿論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在黨的十九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國家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代之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對新聞傳播教育和實踐的指導、統攝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習近平在關于新聞輿論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指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靈魂”“旗幟”和“定盤星”,事關新聞輿論事業扎根何處、方向何在的大問題。具體到新聞傳播教育,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首要任務是重返大學立德樹人本位,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輿論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這些人堅持黨性原則,以人民為中心,尊重新聞傳播規律,有深厚的家國情懷和開闊的國際視野,在事業發展中能夠高舉旗幟、服務大局、明辨是非、凝聚共識、溝通世界。同時,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傳播的概念、知識和理論體系,把論文寫在中國大地上,解釋、解決中國新聞輿論實踐發展中的重大、基本問題。
事實上,“模式1”的出現乃歐洲啟蒙運動和現代化轉型進程中神學思想退場、人本主義成為時代主流價值的產物;“模式2”的形成與美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實用主義哲學的主流化緊密相關;“模式3”則與全球化、互聯網革命引發的創新思潮相呼應。如是而觀,每一種模式皆有其誕生和發展的時空語境,皆響應了特定時代主題的召喚。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有自己的道路選擇和歷史使命,新聞傳播學科的正當性亦應深植本土情境,反映中國的主流價值和時代主題。同時,隨著中國深度介入全球化和加快推進現代化進程,新聞傳播教育亦應觀照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和共同價值,主動適應、引領“模式3”時代的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機制變革。
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前提下,新聞傳播教育應進一步平衡公共倫理、大學精神和專業理想之間的關系,鑄就“專業之魂”,培養有信仰、有理想、有操守、有仁愛之心、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新聞傳播專業人才,避免出現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中的“重物質輕精神”“重技巧輕操守”“重知識輕道德”“重現實輕理想”。[注]張昆:《鑄魂——新聞傳播教育的天職》,載《新聞與寫作》,2016(9)。在今日人人皆可成為內容生產者、傳播者的時代,信念、德性和專業理想教育更應成為大學新聞傳播教育的本職、底線和正當性基礎。而欲為學生鑄魂,師者及學術共同體則須率先養成崇高的大學精神、學術理想和堪為世范的德性。此外,當公共議題和業界發展需要學界做出響應時,則應擔起“社會良心”之職,以智識的力量探求真理、澄清謬誤,以道義的力量增益公共精神。
二是學科主體性重構。前文論及對內專業融通、對外學科拓展以構建敞開的學科主體性,茲舉數例,以為擴充。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近年逐步突破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和傳播學等傳統的“專業—方向”模式,建立了跨學科、跨界、跨文化的生態型人才培養體系。學院在本科層面創辦了“新聞學—法學”“新聞學—國際政治”、創意傳播、未來傳播學堂、學術拔尖人才成長計劃、明德明新厚重人才成長計劃等培養項目,在碩士層面增設了“大數據與新聞傳播”“戰略傳播”“一帶一路新聞傳播全英文碩士”等培養項目。這些項目以“雙一流”為目標,最大限度尊重學生的自主選擇權,基于學生的個性、興趣、專長因材施教,訓練團隊,培育成長共同體。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推行了跨專業、跨學科的本科人才培養“2+2”模式——本科學習的前2年系統選修某一非新聞傳播學科課程,后2年再重返本專業學習;在專碩層面,復旦新聞學院也實施了跨學科、跨界聯合培養,并著力提升學生的國際化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對外拓展應堅持“固本”優先。人大新聞學院的做法包括:實施“新聞傳播核心課程創新計劃”,每年重點建設5門以上學科基礎課,以通過五年左右時間建成、完善承載本學科核心理論、知識、技能的30余門專業課程建設;裁減傳統專業和細分方向下的部分邊緣、瑣細和重復性課程,以釋放跨學科聯合培養的學分空間;重構課程體系,力圖使全部史論、實務課程整合成完整的知識地圖,以培養學生的整體理解力和判斷力。
三是構建理論與實踐、學界與業界對話、合作的新機制。無論技術引發怎樣的變革,學界和業界首先應各守本位。前者要對知識和人格訓練負責,對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負責,對學術規律、理論創新負責,對中國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基本的理論問題負責;后者要對內容生產、運營管理、技術創新負責,對專業規范和倫理負責,對新聞輿論事業的發展和進步負責。同時,變革也敦促二者建立“模式3”時代的新型對話、合作關系,在知識生產、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諸領域確立創新驅動的生態型合作機制。從麻省理工學院建立跨界跨學科的未來媒體實驗室、斯坦福大學與GOOGLE等硅谷公司的合作經驗看,管理機制設計乃關鍵所在。中國傳媒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傳媒學院在建設產學研平臺、聯合培養人才方面取得了系列標志性成果,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設計了適合國情、校情的有效合作機制。
綜上所述,所謂生態型新聞傳播學科體系可從歷史—邏輯、結構—功能、知識生產—人才培養等維度描述如下:它是“模式1”“模式2”“模式3”三種大學現代化進路在新聞傳播學科的貫通和延展,此中既有縱向的觀念更迭,也有多元邏輯之間的對話與融匯;它強調構建敞開的學科系統,在系統內部打破結構性的專業壁壘、知識邊界和理論閾限,在系統外部參與跨學科共創、介入實踐應用場景,進而基于多樣共生、邊界互通、彼此增益的生態原則,尋求學科主體性、正當性和有效性。顯然,生態型學科體系不再完全按照線性歷史觀鋪展自己的演化進路,也不再徹底服膺工業社會的結構—功能主義,而是主張歷史與現實、系統內部諸要素與系統外部諸主體之間敞開、動態、均衡的對話。正是基于多元對話,學科主體性、正當性和有效性才得以確立和延展。
行文至此,有必要澄清一個歷史細節:施拉姆在論及傳播學的十字街頭處境時,一方面表達了多元交叉、缺少“中心理論”的遺憾,一方面也專門使用了“great cross”這個詞組強調傳播學乃人類研究、人之存在研究的“偉大路口”。這個路口一度為學科主體性、正當性和有效性帶來巨大挑戰,如今則提供了構建學科與學科、理論與實踐、專業性與公共性、中國與世界之間連接、互通、共創生態型學科體系的現實可能性。因此,新聞傳播學科和教育的未來之路不是走出十字街頭,而恰是安身立命于“偉大路口”,于多元生態中自利利他、融合共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