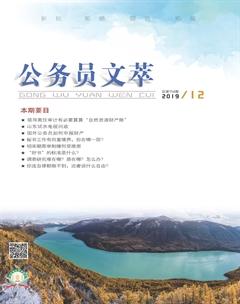和唐代高考比,今人幸福多了
周公子

提起唐代科考,大家可能會紛紛舉手搶答:我知道,我知道!分明經和進士兩科!不錯,不過只說對了一部分。因為嚴格來說,唐代科舉分兩大類:制舉和常舉。
所謂“制舉”,就是由皇帝下詔、以招“非常之才”為目的而不定期舉辦的非常規考試,考什么、怎么考全看皇帝的用人需求。比如初唐四杰中的王勃,16歲就考中幽素科做了官,這個科目就是制舉考試的一種。
有唐一代,設立過的制舉科目大概不下百種,比較常見的有賢良方正科、博學宏詞科、直言極諫科等。此外,還有很多花里胡哨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科目,比如志烈秋霜科、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才廣度沉跡下僚科、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一個個名稱浮夸到令人難以相信這是朝廷正兒八經的招考科目,只能說當皇帝就是好,科考這么嚴肅的事,也能搞得如此任性。
當然,制舉考試畢竟只是人才選拔的一種補充方式,類似現在的藝體特招生。真正的重頭戲,還要看常舉。所謂常舉,又稱貢舉,就是定期舉行的常規性考試。
唐代的常舉每年舉辦一次,主要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法律)、明書(書法)、明算(算數)等五十多種科目。其中秀才科等級最高,但因為太難考,設立不久就廢除了。其他明法、明書之類,都不怎么受待見,所以常科的重中之重就是明經和進士。那這兩科究竟有什么區別呢?首先考試難度不同。
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30歲中明經已經算高齡考生,50歲進士題名卻依然可說是年輕有為。因為明經易考,主要考“帖經”,就是抽取經典古文,遮住關鍵字句,讓考生補充填寫,跟現在做的填充題一樣,純靠死記硬背。
而進士難度就大多了。因為,重點考詩賦。
詩、賦都是對韻律有要求的文體,詩要音韻和諧,對仗工整;賦要文辭華美,駢驪頓挫,還要應題而作,臨場發揮。這就要求考生有相當深厚的文學功底以及獨立思考能力。而我們熟悉的唐代詩人因為個個才華滿格,幾乎都選擇考進士。
唐代的詩賦考試一般放在第一場,出題范圍十分廣泛,什么歷史故事、四季節令、描寫風景等都有,有時甚至是主考官現場即興選題。
比如有一年考試,主考官看到考場的北邊新栽了一棵小松樹,就對考生們說:同學們,今天就以這棵松樹為題作詩吧。所以,這一年的詩賦題目就叫《貢院樓北新栽小松樹》。
堂堂國考,竟然隨性到這種程度,這要是放在八股取士的明清時期簡直就是天方夜譚。而且,不僅考官隨性,考生隨性起來更夸張。
開元年間,有個名叫祖詠的考生,詩賦考試才開場15分鐘,他就突然起身,將詩稿往主考官的案前一放,拎著文具袋揚長而去。剛出考場沒兩步,主考官就舉起考卷,扶著門框,大聲喊:“嘿!這位同學,你還沒寫完呢!”祖詠停步,轉身,微微一笑很傾城,回了主考官兩個字:“意盡”,說完便飄然而去,留下主考官在風中凌亂。
主考官為何說他還沒寫完呢,因為唐代考詩歌有篇幅要求,必須是五言六韻十二句,可祖詠只寫了四句就走人了。
祖詠這首個性的應試之作《終南望馀雪》是這樣寫的:“終南陰嶺秀,積雪浮云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整首詩詠物寄情,意在言外,且清新明朗,樸實自然,是一首難得的佳作。而且,的確已經“意盡”,多一個字都顯畫蛇添足。
清朝王士禎在《漁洋詩話》里把這首詩和陶潛的“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王維的“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等并列,稱為詠雪的“最佳”之作。
在今天,要求800字的高考作文你如果寫200字,估計只能得零分。祖詠卻因這首詩寫得實在太好,被主考官破例錄取,成為有名的科場佳話。
既然明經和進士考試難度不同,學歷含金量也就不同。如果說明經相當于現在的函授本科,那進士就是985、211,甚至對標清華、北大也絕不為過。
在當時的科考風氣中,存在著一股明顯的鄙視鏈:進士出身的瞧不起明經出身的;甚至還沒考中進士的也瞧不起明經出身的。典型例子就是李賀得罪元稹的故事。
李賀十幾歲時,因受到大文豪韓愈的青睞,名揚京洛,據說當時已考中明經的元稹對他十分仰慕,還曾親自登門拜訪。結果,李賀接過名片一看,一聲冷哼道:“你一個明經出身的人,也有臉來見我?”差點把元稹氣到原地爆炸。
這個故事雖然真假難辨,但在唐人眼里,明經和進士聲望的懸殊可見一斑。
看到這里,有人可能想說,唐代的科考還是很美好的嘛。考題范圍那么寬松,答題“半途而廢”也能金榜題名;雖然明經不受待見,那就一門心思考進士唄。呵呵,沒那么容易。
唐朝科舉的第一個特點是:進士錄取率極低。
終唐一代,每年錄取的進士平均不超過25人,錄取率僅百分之一二。所謂物以稀為貴,高中進士在唐朝的尊崇程度,鮮有其他事項可比擬。
比如,有人登第后曾賦詩曰:“元和天子丙甲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進士及第的喜悅如同成仙升天,新科進士們的快意之情與世人的追捧艷羨也就不難想象了。
在唐代,整個官僚體系內都有一種神圣的進士情結。比如一個叫薛元超的宰相,說自己生平有三大恨:一是非進士出身,二是沒娶到五大望族之女,三是沒能修國史。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連君臨天下的唐宣宗都對進士題名一心向往,不能參加科考,他就在宮殿柱子上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過把癮。
然而,這看似風光無限的進士之路,背后卻不知鋪墊了多少落榜考生的血與淚。因為錄取率極低,唐朝甚至產生了一種專門的詩歌類型,叫“落第詩”,比如孟郊寫的《再下第詩》:“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光看詩名《再下第詩》就夠憂傷了,何況內容。
晚唐詩人溫庭筠的兒子溫憲也是屢試不第,筆下也有類似詩篇:“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詩人顧況的兒子更是考了30年,忍不住吐槽:“吟詩三十載,成此一名難。”寫下名句“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詩人曹松一直考到七十多歲,才因年老被特放及第……
當時很多外地學子,為博得一個進士出身,滯留長安多年不得歸家,饑無食,寒無衣。更悲摧的是,有的考生的父母死了,他們卻貧窮到只能賣身為奴,為父母辦喪事,有的夫妻分別十幾載,相見時幾乎不能相認……
不過這還不算完,唐代科考的第二個特點:考試不糊名,且行卷、通榜之風盛行。
不糊名,主考官想針對某個考生放水那就太簡單了。而所謂“行卷”,就是考試前,應考的舉子們把自己的得意之作裝訂成冊,然后奔走于各大王公貴族的門庭下自我推薦。如果得到權貴賞識,向主考官力薦,那就極可能直接內定名次,即為通榜。
比如王維、杜牧,都是這一類的幸運兒。但如此種種,對于出身平凡、沒有靠山的考生們,就顯得十分不公平。比如韓愈,因無人舉薦,一連考了四次才中進士。李商隱也是到了第五次,終于得人舉薦才登科。晚唐詩人杜荀鶴,同樣是詩名遠播卻屢試不就,只能無奈感慨“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貴在朝中”。
接下來,再看唐朝科考的第三個特點:限制考生身份。
唐代民眾大概分士、農、工、商四類,其中只有“士”與“農”的子弟被允許參加科考。而農家子弟大多貧困潦倒,沒什么條件讀書,有資格考也白搭。所以歸根結底,幾乎所有唐代進士都出自官僚階層。
這不得不提下李白。為什么他的家世永遠是一團迷霧?為什么他從不在詩文中說起自己的父母兄弟?答案就是,他家極有可能是經商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李白從不參加科考,才高不屑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沒資格啊!
除此之外,唐朝考進士還是逐級淘汰制,每場定去留。第一場詩賦通不過,后面的帖經和策問直接沒資格考。比如晚唐詩人黃滔第一場詩賦就被刷下來,回到旅館后忍不住哭成了狗:哎,回家怎么跟父老鄉親交代啊……
而且,唐代進士雖然被吹上天,但是考上后不包分配,還得繼續通過吏部篩選才能當上公務員。而吏部的面試環節,考官的自由裁量權極大,有關系、有后臺的世家子弟會再次占盡優勢。
有才如韓愈,因出身普通,居然三選吏部而不得,中進士后又整整做了十年的布衣——就問你坑不坑爹,顫不顫抖!
看到這里,是不是發現古代科舉也沒想象中那么簡單?尤其唐朝,還處于科舉的初級階段,看似一朝登龍門的進士考試,其實只是上層社會少數人才能玩的游戲,還遠不是真正的“廣開才路”。說到底,還是現在的高考制度對我們普通大眾比較友好:不限出身,不用行卷,考試看總分,錄取率還高!
如今,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高考雖然不像古代科舉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卻依然是個體改變命運相對公平的方式。所以,年輕人沒事還是要多讀書啊!那樣才能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摘自《百家講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