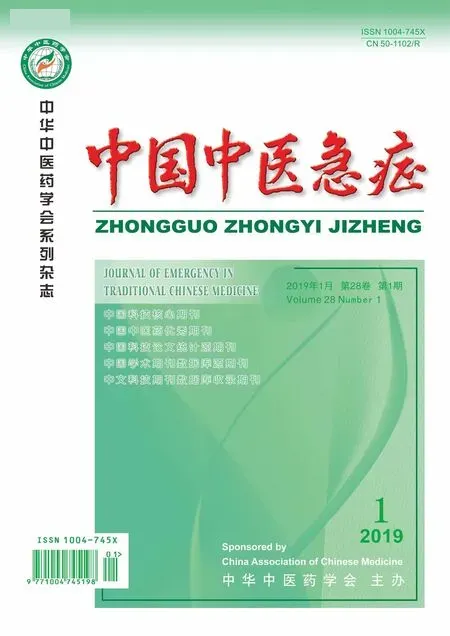中風急救合劑治療缺血性中風急性期的理論探析
周 盈黃 遲趙 楊
(1.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2.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南京市中醫院,江蘇 南京210001)
缺血性中風起病急驟,病情重,變化快,中醫辨證急性期常以標實證為主,少部分患者表現為氣虛血瘀、陰虛風動。在標實為主的證候中,以風、痰、瘀互結,阻滯氣機、損傷脈絡的情況最為常見。尋找有效的治療途徑和治療藥物,減輕腦缺血后的神經功能損傷,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質量,降低缺血性中風的致死率和致殘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目前中醫藥治療中風病已逐漸彰顯出獨特的優勢,成為臨床和科研的主要研究方向。本文立足對中風病“急則治其標”的原則,擬對中風急救合劑治療缺血性中風急性期進行以下闡述和探析。
1 缺血性中風急性期的主要病機
風陽上擾、氣血逆亂是發病的關鍵;風痰瘀互結,閉阻氣機,滯于脈絡是中風病的基本病理環節,三者往往相互兼雜,影響機體的氣血陰陽平衡,病程日久,隨著病機變化,最終導致中風發生。
1.1 肝風內動是發病關鍵 中風之為病,“風”為主邪,唐宋以前多主“外風”,唐宋以后多以“內風”立論,結合現代醫家學者共識,以“內風”立論應更為合理。近賢三張(張伯龍、張山雷、張錫純)上溯《內經》,參以西醫,均強調了中風乃“血菀于上”“血之與氣并走于上”等病機,如張錫純指出,中風雖有外受內生之別,但外中風邪之下,必有主內之虛損,常表現為肝陽上亢致使他臟之氣隨逆,從而引起以氣機逆亂為發病關鍵的諸多證候。內風之產生,多認為與肝相關。風陽擾于上,常認為腎水虧于下,即本虛標實之意,如因氣血衰少,臟腑功能失調,而腎為水臟,肝為風木之臟,各種原因引起的腎中精血漸虧,腎陰不足,則水不涵木,陰不斂陽,肝陽上亢而化“風”,以致虛風。痰瘀閉阻于腦絡則擾亂神機,可出現昏不識人、卒然仆倒等癥,痹阻經絡則可出現肢體偏枯、言語謇澀等癥,是故發為中風。
1.2 痰瘀互結為病理基礎 《內經》中早有痰濁內動。如怒為肝志,《素問》中“怒則氣上”“怒則氣逆”“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等講到暴怒傷肝,易引起氣機逆亂,可表現為肝升太過而上逆化風,抑或是肝陽過亢而化火生風,又如《素問·至真要大論》言“諸逆沖上,皆屬于火”。風火陽亢等熱邪一邊灼液成痰、熬血為瘀,一邊夾帶氣血痰瘀上沖于腦,引起氣血運行不暢、瘀血與中風相關的論述。《素問·通評虛實論》有云“凡治消癉、仆擊、偏枯……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指出常食肥甘厚味者,易致脾運失健,則痰濕內生,或蒙蔽清竅,或阻滯經絡,發為中風,如明·戴元禮《證治要訣》所述“中風之證,卒然昏倒……或口眼歪斜,或半身不遂,或舌強不語,皆痰也”。痰濁黏滯脈絡,影響氣血運行,而易中風者,常元氣虧虛,如清·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云“半身不遂,虧損元氣,是其本源”“元氣既虛,必不能達于血管,血管無氣,必停留而瘀”。血行不暢,瘀滯則生,痰瘀互結,滯于經絡或閉阻腦絡,發為中風。而痰濁和瘀血既是津液代謝失常的病理產物,又是新的致病因素,二者常常是因痰成瘀、由瘀生痰、互為因果、搏結交織為患。
1.3 閉阻氣機乃致病的重要環節 缺血性中風病總屬本虛標實,患者常因先天或后天因素影響,存在機體陰陽失衡狀態,久則引起臟腑功能受損,氣機升降失調,升降失調者,清氣不得以升,濁氣不能斂降,宜藏者反瀉,應行者卻滯。損及中焦者,影響氣、血、津液的正常生化與輸布,則邪風、痰濁、瘀滯內生;痰瘀阻滯,影響中焦樞機不利,脾不升清,胃不降濁,糟粕不傳,腑氣不通,引起氣機閉阻,瘀滯加重,如此負向循環。損及脈絡者,尤數腦絡主要起溫煦、濡養、滲灌腦竅之作用,保持腦絡功能結構的完整是腦竅正常其發揮功能的基礎,如《靈樞·平人絕谷》所云“血脈合利,精神乃居”。故風挾痰瘀,阻閉氣機,氣血不能榮營腦髓、肢體,則可見神識不清、半身不遂等癥狀。
2 治療缺血性中風急性期的重要方法
2.1 平肝息風,急制其動 缺血性中風病機總屬內風引動氣、血、痰、瘀等上行犯腦,閉阻氣機而成,及時制其始動因素顯得尤為重要。西醫對于中風,強調時間窗的診斷及治療,結合腦梗死后的病理改變,自由基的損傷,氧化-抗氧化平衡被破壞,炎性介質及炎癥相關蛋白酶等的過度參與,均促使神經細胞發生凋亡、壞死,增加了血管內皮細胞和血腦屏障的通透性,加重神經細胞毒性損害,加速破壞血腦屏障,加劇腦水腫情況,因此急性期的治療也常與患者康復程度密切相關。中醫辨中風急性期,多以標實為主,常在陰虧不制的本虛基礎上,由肝升過旺或肝陽過亢等因素引起內風擾動,故治療時不忘平肝、清肝,如此,既可調理肝之本身臟腑功能,又可絕其生風之源,如張山雷云“病形雖在肢節,病源實在神經,不潛其陽,不降其氣,則上沖之勢焰不息,神經之擾攘必無已時”,強調中風治療重在及時辨清病源,潛陽息風。
2.2 化痰通絡,速調氣機 內風常挾痰瘀滯于脈絡,阻閉氣機,蓄于腦髓,氣機不暢可又加重痰瘀互阻,影響正常氣血津液的化生與輸布,故快速清除“病邪”,對恢復神機靈巧具有重要意義。然則“百病兼痰,痰瘀同源”,痰濁、瘀血常互為因果,由此引起的痰瘀互結必須通過化痰祛瘀、活血通絡加以疏導,促其消散與吸收,使脈道通利,氣機調暢,腦絡自通。有Meta分析納入以痰瘀同治為主要組方依據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結論表明,在西醫常規治療基礎上,加用以痰瘀同治為主要組方依據的中藥方劑,能有效提高缺血性中風的臨床療效,尤其有利于恢復中風所造成的神經功能缺損[1]。
2.3 通腑降濁,祛邪安正 如沈金鰲所言“中風若二便不秘,邪之中尤淺”。腑實證已被公認為中風急性期中常見證候,并以痰熱性質為主[2]。經多種研究證實,通腑法是為治療急性期腦血管病中重要的環節,重點在于盡早地運用通腑治療,能較早地改善患者腦水腫情況,并減緩病情的加重趨勢,以減輕病損程度和改善患者的意識狀態[3-4]。《素問·五常政大論》有言“病在上,取之下”。中風急性期,氣逆上犯于腦而為發,故氣機的調暢與否成為影響病情的重要因素。通腑降濁法是通過祛除腸道積滯,使濁氣下趨,以通降上逆之氣,引導氣機漸趨調和的方法。氣機升降有序,有助脾胃功能恢復正常,則清氣自升,正氣漸復,有利于病情轉愈。
3 中風急救合劑的具體應用
3.1 制劑淵源 中風急救合劑為南京市中醫院自制制劑(蘇藥制字Z0400084),由南京市中醫院腦病科專家李繼英教授所擬。李教授在繼承前賢的基礎上提出了“中醫為主、中西醫結合、針藥并用、急救和康復結合”的中風臨床治療體系,大力發展了中醫治療中風病事業,并執導研究開發了10種院內自制制劑。其中,中風急救合劑是針對缺血性中風急性期病因病機特點,結合長期臨床運用及觀察,去粗取精,反復推敲所擬得,目前仍廣泛運用于本院臨床。前期臨床觀察亦表明,在西醫常規治療的基礎上,加用合劑,能夠明確改善急性期患者神經功能缺損癥狀[5]。
3.2 組方意義 合劑全方8味,由鉤藤、決明子、全瓜蔞、法半夏、莪術、麥冬、硝枳殼、生大黃組成,主治中風急性期病變。病變期以肝風急挾痰瘀,于內阻滯氣機為患,故擬平肝息風、化痰通絡等為治法。對于鉤藤,《本草綱目》云“通心包于肝木,風靜火息”。《本草述》中又述:治中風癱瘓,口眼斜,及一切手足走注疼痛,肢節攣急。故明鉤藤功能清熱平肝,擅治內風擾動之中風偏癱;決明子亦長清肝熱,疏肝風,兼能潤腸通腑,以二藥為君,上息邪風,下通腑濁;以全瓜蔞、法半夏健脾行氣化痰為臣藥,半夏善治臟腑之濕痰,與清熱滌痰、寬胸散結之瓜蔞配伍,尤去熱與痰結,以防痰瘀膠著,閉阻氣機;麥冬養陰生津,功長潤津枯之腸腑,莪術活血消瘀,又“益氣之功在于疏氣”,同為佐藥,一潤一行,通調脈絡;大黃逐瘀通經、瀉下攻積,合硝枳殼行氣導滯為使,加強調理氣機,更助通腑降濁。本方藥僅8味,然組方科學、配伍嚴謹,針對中風病急性期的病機特點,兼顧安正與祛邪,共奏平肝息風、化痰通絡、通腑瀉濁之功。
3.3 臨床依據 現代醫學表明,缺血性中風的病因常與腦血管血栓的形成有關,其來源可包括血管壁、血液及血流等因素的改變,聯系腦梗死患者情況,通常伴有高血壓、高血脂或者血液黏稠度較高、凝血或纖溶系統功能障礙等基礎狀態,故解決相關致病因素成為治療的關鍵環節。
目前藥理研究表明,平肝息風藥中,鉤藤內含的鉤藤堿對缺血-再灌注損傷大鼠腦組織有保護作用[6-7],還有發現表明鉤藤堿可以減輕腦缺血后發生的炎癥[8],并可以明顯抑制血小板聚集[9];決明子中含有的蒽醌糖苷類化合物也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10]。化痰藥中,藥理證實半夏具有延長凝血時間的傾向,并能明顯抑制紅細胞的聚集,以降低全血黏度[11];瓜蔞亦被證實其研究活性成分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均很強[12]。化痰不忘行氣,有研究表明[13]枳殼的揮發油、水煎劑及生物堿成分有明顯的促進胃腸運動的作用,其水提液亦能抑制血栓形成[14]。活血化瘀藥中,以證實莪術的部分提取物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抗血栓形成的藥理作用[15],還能降低腦梗死體積百分比與腦含水量,有重要的治療作用[16]。通腑藥中,大黃因其大黃素與番瀉苷成分可以反射性地增強結腸蠕動,通過促進排便來加速有毒物質的排泄,從而降低內毒素對機體的損害[17],并有研究證實大黃具有減輕血腦屏障損傷,使腦水腫減輕作用[18]。通腑不忘適量佐以生津潤腸之品,研究證實山麥冬總皂苷不僅可以減少大腦中動脈閉塞模型大鼠的腦梗死灶面積,改善神經功能缺失癥狀,還能明顯延長模型小鼠的凝血時間和出血時間,具備抗凝作用[19]。
4 總 結
綜上表明,中風急救合劑,針對風、痰、瘀為患的缺血性中風急性期發病特點,致力于從平肝息風制其始動、化痰通絡調其氣機、通腑瀉濁祛邪扶正等方面改善疾病癥狀,不僅符合缺血性中風急性期的病機特點,且具現代藥理學的研究基礎,不失為治療本病急性期較為理想的一個中藥復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