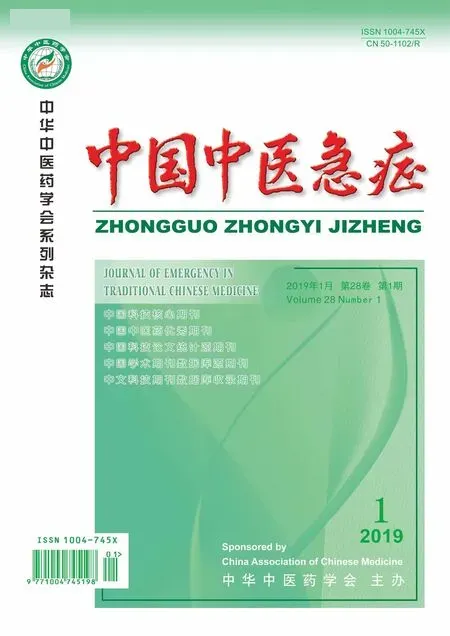從“濕痰瘀”論痛風治法的古今演變*
余怡然 何莉嬌 李海昌 呂惠卿 溫成平
(浙江中醫藥大學,浙江 杭州 310000)
痛風屬于臨床常見病,中醫學對其論述散見于歷代醫籍。《張氏醫通·痛風》云“按痛風一癥,《靈樞》謂之賊風,《素問》謂之痹,《金匱》名曰歷節,后世更名曰白虎歷節”。中醫學認為,痛風的病理基礎為“濕痰瘀互結”,現代醫學證實痛風與高尿酸血癥形成和尿酸鈉鹽結晶積聚有關,為一種反復發作的炎性代謝性疾病[1]。本文欲探討“濕痰瘀”與痛風的溯源以及現代新認識,并以時間為軸梳理 “濕痰瘀”對痛風的治法發展的影響。近百年來,西方現代醫學給中醫學帶來了相當大的影響,因此中醫痛風治法結合現代醫學的進步,有望能進一步指導痛風的中醫診療。
1 痛風病因病機的中醫溯源——從“濕痰瘀”辨證痛風
《素問》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最先指出風寒濕邪為痛風的致病因素。《素問·痹論》闡發了熱痹證的形成機理,“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為痹熱”。痛風患者多為體胖之人,陽氣偏盛,急性痛風發作之初表現為紅腫熱痛。《諸病源候論》曰“熱毒氣從臟腑出,攻于手足,手足則熱、赤、腫、疼痛也”,首次提出痛風與臟腑積熱蘊毒之間的關系。《素問·五臟生成》云“多食甘,則骨痛而發落”,《丹溪心法·附肢節痛》曰“肥人肢節痛,多是風濕與痰飲流注經絡而痛”,皆提及飲食不當損傷脾腎,脾腎功能失常,水谷不化,泌別清濁無權,水濕的輸布、運化與排泄異常,濕濁內生,滯留郁而化熱,注于關節,氣血痹阻不通,而致痛風。《類證治裁·痹證論治》曰“痹久必有痰濕敗血瘀滯經絡”,此處提及痛風久則有瘀滯。
現代醫家認為風寒濕邪等因素是痛風發作的誘因,濕痰瘀才是內因[2-3]。痛風常以濕濁、痰瘀為患,三者往往互相兼夾,或濕熱內蘊,或濕濁內阻,或痰瘀互結。其中濕邪最為關鍵,濕為陰邪,重濁黏滯,極易兼夾他邪,或為濕濁,或為濕熱,或為痰濕。若濕濁逆留、積滯血脈則化為濁瘀,血行郁滯,纏綿難愈,易引起痛風關節炎的反復發作,產生痛風結節。由此,濕邪阻滯是痛風發病的病因,脈絡瘀阻是基本病機,濕痰瘀互結是其最終病理產物。
2 痛風與“濕痰瘀”之間相關性的現代新認識
焦東方、陳黎明等認為,“濕痰瘀交互”為痛風發病的動因,還指出中醫氣血津液運行失常的濕痰瘀產物,類似于現代醫學中尿酸代謝異常導致的尿酸鹽結晶,當其沉積于關節及其周圍組織時易導致痛風關節炎的發作[4-5]。楊培麗認為過量的尿酸屬于中醫學“痰濁”范疇,其痰濁的形成與肝脾功能障礙有關[6]。張忠德認為脈絡瘀阻在外表現為局部的急性炎癥,而濕痰瘀互結形成的病理產物在外表現為尿酸鈉結晶[7]。
現代研究表明由尿酸沉積形成的尿酸鈉鹽結晶具有強烈的致炎性,可與單核/巨噬細胞相互反應,從而趨化中性粒細胞,繼而發生爆發式級聯擴增反應,導致滑膜細胞的炎性反應,引起骨、軟骨的破壞,從而造成痛風關節炎。此研究具體闡釋了濕痰瘀產物——尿酸與炎癥反應之間的關系,用科學語言解釋了濕痰瘀的作用機理[8]。有研究應用雙向電泳聯合質譜技術,比較痰濕質痛風人群和平和質正常人群的血漿蛋白表達后發現,前者人群中有5個表達量上調的蛋白質分子,以及3個表達量下調的蛋白質分子[9]。也有研究表明HLA基因與中醫痰濕體質之間有一定的關聯。以上研究在蛋白、基因的層面用科學語言闡明了痛風與痰濕之間的關系。血液流變學檢測提示,急性期痛風患者APTT、PT、FIB顯著升高而TT值顯著降低,紅細胞和血小板聚集性增強,血液流動性降低,全血黏稠度升高,這與中醫“血瘀”狀態相吻合[10]。此研究借助現代血流指標來定義了痛風與血瘀之間的關聯。
3 痛風治法的古今演變
3.1 秦漢時期:辛溫散寒、祛濕止痛 秦漢時期無“痛風”病名,屬于中醫學“痹證”“歷節病”范疇。如《內經》中以 “痹證”統稱各類痛證,“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明確了痛風病因病機與風寒濕相關,其癥狀以疼痛為主,治療以辛溫散寒、祛濕止痛為主。用藥方面,多用辛溫走竄之品以除濕鎮痛。《神農本草經》詳細記載了治痹之藥,如“附子主風寒……寒濕踒躄,拘攣,膝痛不能行步”“蔓椒,味苦溫。主風寒濕痹,歷節疼,除四肢厥氣,膝痛”等。
《金匱要略》首次提出“白虎歷節”病名,其臨床癥狀與痛風相符。仲景指出痛風病因以濕邪為主,尤重外濕,立祛濕大法。代表方劑為桂枝芍藥知母湯、烏頭湯。此時提出風寒濕邪為痛風形成的關鍵因素,后世醫家在此基礎上認識到風寒濕邪為其誘因,濕痰瘀互作才是痛風的內因所在,并進一步發展了痛風的病因病機。
3.2 隋唐時期:清熱解毒、祛風除濕 隋·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歷節風候》中認為其病機為“此由風毒之氣傷之,與血氣相擊,故痛而結卯不散”。故痛風病機為風濕熱邪和濁毒阻滯經脈。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對于“熱毒流注四肢歷節腫痛者”主張用犀角湯,開始確立了清熱解毒的辨證治療。
《外臺秘要·白虎方》曰“白虎病者,大都是風寒暑濕之毒……經脈結滯,血氣不行,蓄于骨節之間,或在四肢,肉色不變,其病晝靜而夜發,發即徹髓酸疼不歇”,說明痛風亦由內虛而外感風寒暑濕所致,治宜重視利濕。
此時期首次提出了“風毒”“熱毒”的概念,為后世清熱解毒的治法提供了依據,故后世醫家治療痛風的急性期尤為重視清利濕熱。
3.3 金元時期:健脾祛濕,活血化痰 朱丹溪于《丹溪心法》《格致余論》中將“痛風”專列成篇,并首次將該病與“痰”聯系起來。“他方謂之白虎歷節風證,大率有痰、風熱、風濕、血虛”,并認為“彼痛風者……熱血得寒,汗濁凝澀,所以作痛,夜則痛甚,行于陰也”,指出“熱血得寒,汗濁凝澀”是痛風的發病機理,給后世的活血化瘀祛痰治法很大啟示。
李杲擅長臟腑辨證,創造性提出“脾虛致痹”之說。李杲認為臨證治痹當首辨外感與內傷。外感則治以祛風除濕、疏通氣機;內傷則首責之于脾,脾虛運化水濕功能減退,津液代謝失調,痰濁內生,注于關節、浸于經絡,發為痹證,治以健脾利濕除痰,由此開辟了“從脾論治痛風”的先河。
此時期提出“痰”為痛風的病因,并指出痛風的外感內因之說,為后世健脾利濕除痰治法奠定基礎,因此開啟了從脾論治痛風的時代。
3.4 明清時期:活血化瘀、清熱利濕 《景岳全書·風痹論證》認為痹證“有火者宜從清涼”,并指出“有濕熱之為病者,必見內熱之證,滑數之脈,方可治以清源,宜二妙散及加味二妙丸、當歸拈痛湯之類主之。其有熱甚者,如抽薪飲之類亦可暫用,先清其火,而后調其氣血”。王清任繼承《內經》“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澀,經絡時疏,故不通”的思想,在《醫林改錯》中提出“痹證有瘀血”,認為“血瘀”為致病的主要原因,提出以活血化瘀、補氣活血之法治療痛風,創制身痛逐瘀湯等經典方劑。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痹證門》中創“新病濕熱在經,久病瘀熱入絡”之論,立濕熱瘀痹之候,治以清熱利濕、通瘀活絡。對于久治不愈,痛甚無法行走者,善用全蝎、蜣螂蟲等蟲類藥,仿《本事方》麝香原意,搜其剔宣通絡脈之性,對后世用藥影響頗大。活血化瘀中藥注射劑正是在中醫活血化瘀治法指導下,現代醫學基于中藥活性成分的研究,創造出的一種新型制劑[11],可用于痛風的臨床治療,促進了中醫治療痛風的發展。
3.5 近現代分期論治 臨床上大多醫家將痛風歸納為急性發作期和慢性緩解期,治療上急性期提倡清熱利濕,慢性緩解期重視補脾益腎,且活血化瘀貫穿始終。
婁多峰教授在痛風診療過程中,主張根據病情的發展分期治療[12]。活動期多屬濕熱痹阻,治宜祛濕清熱、解毒通絡;早、中期多為寒濕痹阻之候,治宜散寒祛濕、溫經蠲痹;中、晚期脾胃多虛寒,治宜健脾除濕、溫中活絡;穩定期多屬肝腎虧虛,治宜益腎蠲痹、活血通絡。何昱君等根據痛風癥狀和程度的輕重緩急,將其分為無癥狀的高尿酸血癥期、急性痛風關節炎期、間歇發作期、慢性痛風石病變期和腎臟病變期,分別進行用藥規律分析[13]。總的治療原則以祛風通絡、利濕泄濁為主,清熱解毒、活血化瘀為輔,同時兼顧補益脾腎。
中醫對痛風的分期治療,以“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為治療原則,結合患者的病情差異辨證論治。痛風臨床治療提倡利用現代診斷技術,通過觀察患者尿酸水平以及炎性指標的變化等來判斷患者病程,然后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式,取長補短,以便更好地提高療效。
4 結 論
痛風作為臨床常見病,自古有之。基于各時期時代背景以及醫家對于痛風的認識,其治法經歷了秦漢時期的辛溫散寒、祛濕止痛,隋唐時期的清熱解毒、祛風除濕,金元時期的健脾祛濕、活血化痰,明清時期的活血化瘀、清熱利濕,到現代的分期論治。痛風中醫治法在不斷發展,同時有文獻報道了中醫證型跟炎癥指標之間的相關性研究,濕熱蘊結型及瘀熱阻滯型患者血清 IL-1β、IL-4、IL-6、IL-8、TNF-α 水平明顯升高,可根據其升高程度初步區分成濕熱蘊結型及瘀熱阻滯型[14]。另外還有文獻報道,加味四妙湯通過降低急性痛風關節炎患者血清IL-6、IL-8和基質金屬蛋白酶-3水平等,以抑制局部炎癥反應[15]。由此,在總結中醫治療痛風的治法演變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可采用現代醫學技術,用具體指標來明確痛風各期的矛盾點,由此中醫證型及治療效果可以用現代指標進行量化比較,能使結果更為客觀化、具體化、易于掌握,這也是中醫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