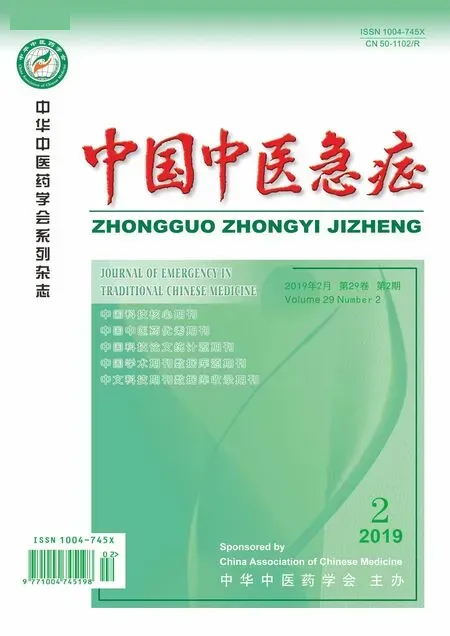膿毒癥的中醫藥診治進展*
李慕云 蘇 和 張雪峰 張瑞芬△
(1.內蒙古醫科大學,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2.內蒙古自治區中醫醫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010000)
膿毒癥的治療和防治是全世界面臨的重要醫療問題,全球每年數百萬人患病且病死人數超過患病人數的1/4,其死亡率相當于多發傷、急性心梗和中風[1]。膿毒癥是多種急危重患者的嚴重并發癥之一,可引起膿毒性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目前臨床治療以西醫常規治療及中醫治療為主[2]。但因西醫常規治療中抗生素的運用易產生耐藥菌,誘發不良反應,臨床救治極為困難[3]。目前,中醫藥治療膿毒癥的有效性、安全性已進一步被證實,單用中醫療法或中西聯合治療均能增強療效、緩解病情、提高生存質量。中醫藥治療本病包括口服方劑、滴注中藥注射液、中藥保留灌腸、穴位貼敷、針灸治療等方法,具有一定的特色并取得一些進展。以下綜述近年來膿毒癥的中醫藥診治現況及展望。
1 膿毒癥診斷標準
膿毒癥是感染引起宿主反應失調導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礙[4]。2015年美國危重癥醫學會(SCCM)、歐洲危重癥醫學會(ESICM)專家提出了Sepsis 3.0的診斷標準,即滿足感染或可疑感染患者SOFA≥2分或qSOFA評分≥2分可診斷膿毒癥,此診斷標準比全身炎癥反應診斷膿毒癥更能反映預后[5-7]。
2 膿毒癥的中醫認識
盡管中醫典籍中尚未見膿毒癥的概念,但因其具有發熱、厥脫、腑氣不通等癥狀,現代醫家普遍將本病歸入“傷寒”“外感熱病”“溫毒”“走黃”“內陷”等疾病之內[8-9]。
3 膿毒癥的證機特點
膿毒癥病位涉及諸多臟腑,病機復雜。《金匱要略心典》云“毒,邪氣蘊結不解之謂”[10]。 劉清泉教授將誘發膿毒癥的毒邪分為“外來之毒”和“內生之毒”。所謂外來之毒,即六淫之邪、疫癘之氣等侵入機體;內生之毒即機體不能抗邪外出,內郁日久而釀生熱、瘀、痰等病理產物,由于邪氣亢盛,正氣漸衰,無力抗衡而突然起病,故歸納其病機為“正虛毒損、絡脈瘀滯”[11-13]。王今達認為,膿毒癥是因外界邪毒入侵機體,激發體內正氣抵抗,正邪交爭于內,日久正氣逐漸損耗,而邪毒仍阻滯不出,導致出現正氣虛弱邪氣亢盛[14]。張云松等認為膿毒癥的發病是邪毒內蘊、正氣虧虛、瘀血內結三者共同作用、相互為患的結果[15]。綜上,現對于膿毒癥的病機認識主要包括外邪入侵、邪蘊成毒、正虛邪亢、痰瘀熱毒壅滯不出,交互為患等觀點。
諸多醫家提出,膿毒癥可參照衛氣營血辨證方法進行辨證,且其臨床表現與衛氣營血辨證各階段具有相似性[16]。現代醫家通過臨床觀察發現,膿毒癥的證候要素主要包括“熱毒”“痰”“瘀”“虛”。膿毒癥初起易虛易實,而后往往表現為正氣耗傷而邪氣未出,虛證與實證并見的虛實夾雜證,最終大多演化為虛證或虛實夾雜證。內科膿毒癥患者中,虛實夾雜證占比重最大[17-19]。
4 中醫藥診治膿毒癥現狀
中醫藥治療本著“祛邪扶正”的原則,辨證論治。對于實證,以祛邪解毒、通腑瀉熱、活血化瘀為法;對于虛證,則以回陽救急、大補元氣、滋陰溫陽為法;對于虛實夾雜者,祛邪與扶正兼顧。另外可以通過針灸、穴位貼敷等方法減輕炎癥反應和免疫損害,改善胃腸功能障礙和凝血功能紊亂,進而提高生活質量。
4.1 辨證施治 對于熱毒內盛,氣分實熱者,需外以宣肺透邪,內以瀉陽明熱結,方用麻杏石甘湯合大柴胡湯加減;對于瘀毒損絡、氣營兩燔,營分證偏盛者,需清營解毒、透熱轉氣,方選清營湯加減,而血分證偏盛者,則需涼血解毒,泄熱存陰,方選犀角地黃湯加減;對于膿毒癥高凝期氣血功能失調者,需調理氣血,予紅參30 g,三七15 g,濃煎頻服,每2小時1劑,每劑20 mL,同時予血必凈注射液活血化瘀,扶正通絡;對于膿毒癥休克期正氣欲脫,瘀毒未除者,應以益氣扶正固脫為要,并兼用活血解毒之法,方用獨參湯大補元氣,或用參附湯合生脈散回陽救逆,配合使用參麥和參附中藥注射液靜脈滴注[18]。王林等收集膿毒癥患者(熱毒型)115例進行隨機對照試驗,發現加用黃連解毒湯可使患者急性生理與慢性健康情況評價Ⅱ(APACHEⅡ)評分、器官功能障礙評分、生命體征指標和相關生化指標[白細胞計數 (WBC)、C反應蛋白 (CRP)、降鈣素原(PCT)、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IL-6)等]相比常規治療顯著改善,治療有效率提高20%以上,說明黃連解毒湯對于膿毒癥(熱毒證)患者確有臨床療效[20]。任鈺鑫等收集118例膿毒癥(熱毒熾盛證)患者進行隨機對照研究,觀察加用血必凈注射液靜脈滴注、清瘟敗毒飲合涼膈散辨證施治的臨床效果,結果顯示觀察組與對照組的有效率分別是77.97%、42.37%,且觀察組相關炎性和凝血指標及預后指標明顯優于對照組,證明了中藥注射液血必凈注射液靜滴、清瘟敗毒飲合涼膈散辨證治療,對于膿毒癥(熱毒熾盛證)患者有確切的臨床療效,具體體現在對早期炎癥反應的控制、微循環和凝血功能的恢復、細菌和毒素移位的控制上[21]。此外,有研究表明單味中藥或其提取物,如大黃、黃芪、連翹等,可改善膿毒癥患者胃腸功能障礙,保護心肌,改善心功能,糾正免疫紊亂與凝血異常,解決多系統功能障礙,值得臨床上進一步的借鑒和應用[22-25]。
4.2 中藥灌腸 藥物可經結直腸直接被機體吸收,可避免口服湯劑的諸多限制。劉佳麗等收集60例嚴重膿毒癥(severe sepsis)進行隨機對照試驗,大承氣湯保留灌腸與清潔灌腸有效率分別是86.82%和46.35%,證明此法可明顯提高療效[26]。徐震宇收集64例膿毒癥初期(熱毒內蘊證)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和治療組各32例,所有患者均以常規治療為基礎,治療組加用清熱解毒灌腸方灌腸,觀察干預后肛溫恢復所用時間、中醫證候積分、相關生化指標(WBC、CRP、PCT、TNF-α 等)變化,結果顯示,兩組患者相關指標經治療后均有所改善,且治療組各指標改善程度更大,無不良反應,治療組總有效率(87.10%)較對照組(63.33%)顯著提高,證明在西醫常規治療聯用清熱解毒灌腸方灌腸的臨床效果顯著,能減輕炎癥反應,安全有效[27]。
4.3 穴位貼敷 宋麥芬等將69例severe sepsis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對照組33例予常規治療,治療組36例加用消脹貼貼敷神闕穴,結果發現,此干預方法可使患者胃腸耐受性顯著增強,同時使腸功能障礙評分減少[28]。王芳芳等也進行了類似研究,證明了中藥(酒調吳茱萸粉和丁香粉)貼臍法可提高腸內營養耐受率,促進胃腸功能恢復,從而起到改善預后的作用[29]。
4.4 針灸療法 針灸是中醫治療膿毒癥的特色之一,基于人體經穴學理論,對腧穴施以一定刺激,疏通經絡,調動全身氣血運行,祛邪扶正,從而改善膿毒癥患者的臨床癥狀,且對其胃腸功能恢復、炎癥反應減輕等方面均有良好的效果。楊廣等選取58例膿毒癥患者進行了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結果證明通過電針刺激足三里、關元穴的方法,可有效緩解炎癥反應,增強療效[30]。卓劍豐通過對70例老年嚴重膿毒癥患者的臨床試驗觀察發現,在常規療法中加入針灸干預,可有效緩解患者胃腸道功能障礙[31]。
5 討 論
膿毒癥的發病機制復雜,引起局部、全身性反應的病程迅速,目前尚無特異性治療方法,且因感染、細菌耐藥等問題,使得臨床的診治難度大大增加。中藥湯劑、中藥注射液、中藥灌腸、穴位貼敷、針灸治療等有效避免了抗生素的使用中耐藥菌的產生、不良反應的出現等問題,并且在整體治療中起到一定效果,特別是針對胃腸功能障礙、凝血功能紊亂、炎癥反應等方面的顯著作用已逐步得到證實。
然而,由于膿毒癥證候多樣,分型紛雜,各醫家治法相殊,用藥各異,難以形成較為一致的辨證治療體系,且中醫藥治療方案干預本病的作用機制仍不清晰,何種方法更為有效亦不明確,這將成為日后研究的重點。如何發揮中醫學辨證論治、整體觀念的獨特優勢,根據辨證分型和患者個體間的差異制定個性化、精細化治療方案仍需進一步研究。目前,膿毒癥治療上仍存在諸多難點:如何有效減少耐藥菌的產生?如何改變耐藥菌的耐藥性?如何防止出現多重感染?對于炎癥反應、免疫損害及凝血功能紊亂等相關病理過程是否能形成針對性、特異性治療方案?這些問題仍需要中、西醫兩方面共同解決。
此外,在臨床研究方面,仍缺乏大樣本、多中心、隨機對照臨床試驗,且在實驗過程中是否能做到患者隨機分配,是否選用負性指標作為結局指標之一等仍存在許多問題。隨著循證醫學科研思路的普及以及科研方法的不斷完善,希望能有更多高質量的研究出現。同時,隨著更深入的研究,針對性、特異性的治療方案和策略有望被提出,中醫藥發揮療效的機制將會更加明晰,中醫藥將會為膿毒癥的治療做出更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