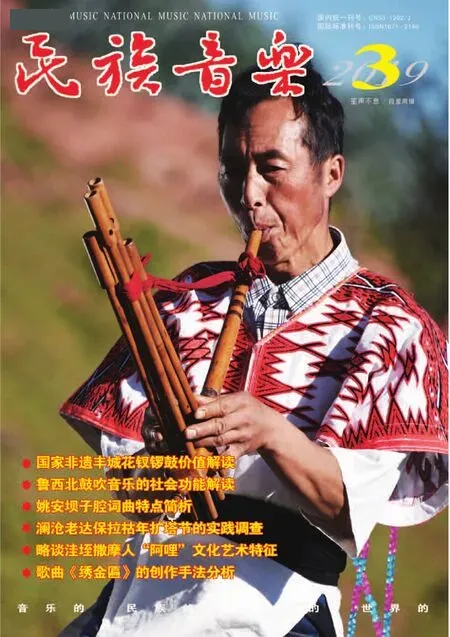悲離中的音聲觀照
——評《悲歡離合—長江流域漢族聚居地區喪葬儀式音聲個案與比較研究》
■班富寧 蔣 燮(廣西藝術學院)
談及死亡,人們往往對其心生畏懼,但又無法回避。死亡作為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站,為死亡舉行的喪葬儀式是人類各種生命禮儀中最為繁雜隆重的儀式活動,人們通過一系列程序來追念死者,安撫生者。喪葬儀式往往與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與喪葬儀式相關的文化藝術研究也是近年來許多學者著力探究的內容。其中齊琨博士主編的《悲歡離合——長江流域漢族聚居地區喪葬儀式音聲個案與比較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年出版,下文簡稱《悲歡離合》)正是筆者近期有幸拜讀的著作。
《悲歡離合》是齊琨繼《儀式空間中的音聲表述——對兩個喪禮與一場童關醮儀式音聲的描述與分析》后新推出的一部學術成果。其個案之詳細、論點之新穎、視角之獨特,無疑是儀式音樂研究領域又一力作。全書分“綜述篇”“個案篇”“比較篇”三大部分,對長江流域漢族喪葬儀式現象進行詳盡調查與研究,為讀者展現長江上、中、下游十地漢族喪葬儀式與音聲的豐富樣貌。該著結合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等研究視角與方法,透視喪葬儀式中的儀式程序,為讀者勾勒了一幅喪葬儀式音聲表達的生動圖景。筆者通讀全書,收獲頗豐,遂從以下方面論述淺聞拙見。
■《悲歡離合》之特點
(一)思想碰撞:國內多位學者的傾情合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關于漢族喪葬儀式研究在人文社科界早有探路者,不同學科、學者、視角的研究思路,使漢族喪葬儀式研究呈現枝繁葉茂、相映成輝的發展態勢。《悲歡離合》“綜述篇”中,主編秉承學科交融、理論互通的理念,約請國內相關領域優秀學者,就西方學界中的華南漢人喪葬儀式研究、近三十年中國古代喪葬史研究、漢族喪葬儀式民俗研究、漢族喪葬儀式音樂研究等議題進行述評。這一篇章在從歷史學、民俗學、人類學等視角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時,也指出漢族喪葬儀式研究的現狀和問題:首先,描述性、資料性的著述占多數,闡釋性的深入研究較少;其次,國內對于“音聲”概念領域雖引用較多,但在具體研究中,其形態分析還是停留在一般意義的“音樂的聲音”;最后,宏觀的喪葬文化史研究較多,但對當代活態喪葬習俗的田野調查還不夠,地方性喪葬文化研究有待加強。“綜述篇”是第二篇章“個案篇”進行個案研究的理論參考和角度借鑒,對音樂學者進行田野調查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研究思路和觀察視野。“個案篇”中十篇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研究成果,在顯現出長江流域漢族喪葬儀式音樂文化整體豐富性的同時,也體現了不同地方喪葬儀式音樂文化的個性特征。第三篇章“比較篇”中,作者對長江流域漢族聚居地喪葬儀式音聲進行整體比較,篇幅設計雖少,卻力圖通過長江流域漢族喪葬儀式結構、音聲類型、音聲過程等的分析歸納,闡釋漢人喪葬儀式音聲所表述的宇宙觀。
《悲歡離合》融合了不同學者對長江流域不同省市漢族聚居地喪葬儀式音聲的學術觀點和思想表述,不同學科背景、知識結構的作者展開多元匯集的智慧碰撞。相對其他儀式音樂研究著作而言,本書不僅在研究領域上較為寬廣、觀察視角上多維參照,而且善于統合不同學者的觀點來看待同一類音樂事象,繼而摩擦出不同的思想火花,較好地做到了思想的凝聚和學理的統一。
(二)有機整合:彰顯漢族傳統文化保護意識
整合,即是把零散的東西彼此銜接,從而實現信息系統的資源共享和協同工作,形成有價值有效率的一個整體。在《悲歡離合》中,7名項目組成員分別前往上海南匯、江蘇揚州、浙江富陽、安徽徽州、江西寧都、湖南湘陰、江西宜春、湖北石首、重慶萬州、四川石邑等地展開實地考察。這些田野點漢族人口較多,分布地域較廣,其族群特點必然呈現差異性,對其進行儀式音樂文化研究,工作量可想可知。個案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因為通過對局部現象的收集整理,可以透視族群整體的運行規則與邏輯。《悲歡離合》在這方面做出了表率:首先,個案篇中的考察點具有代表性,能夠從儀式背景、儀式行為、儀式音聲分析等方面整合當代長江流域地區漢族喪禮的生存圖景;其次,不同的儀式場域、不同的儀式程序、不同的儀式音聲,始終貫穿著漢人慎終追遠,重孝厚葬的觀念,表達著漢人對逝者的深切懷念。與其說此書是對長江流域漢人喪禮音樂的收集和整理,不如說是對漢人自身人文情懷和信仰觀念的深入解讀,其必將對我國喪葬儀式研究形成較大的推動作用。
族群傳統文化的整理與歸納,將有利于促進族群內部的自我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形成與延續。《悲歡離合》匯聚長江流域不同省市喪葬儀式音樂文化于一部文本之中,在熱鬧又飽含人情味的音聲中展現出漢人的審美情趣與人生觀,不僅有益于促進社會對漢人族群傳統文化保護的關注,也能夠為相關部門制定傳承、保護和弘揚我國優秀民族民間儀式音樂文化的決策帶來一定的參考。
(三)多維交互:儀式音樂研究三重模式等方法的融入
曹本冶先生提出的“信仰—儀式—音聲”儀式音樂三重研究模式,成為許多學者研究和分析儀式音樂的理論依據和研究思路。隨著學界對儀式音樂研究重視程度的不斷深入,學者在承襲前人研究理論的同時,也在不斷總結和歸納符合自身考察對象特質的理論范式。如《悲歡離合》“個案篇”齊琨《上海市南匯縣喪葬儀式音聲調查與研究》一文將儀式空間分為“物質空間”“關系空間”“意識空間”三個層面,并就此展開研究分析;姜潔《江蘇省揚州地區喪葬儀式音聲調查與研究》在進行儀式音聲分類時借鑒楊民康先生“核心層次”“中介層次”“外圍層次”三個層次的風格分析模式,指出在揚州地區喪葬儀式中,“瑜伽焰口”超度儀式是最直接與神靈接觸溝通方式,超度儀式音樂屬于儀式音樂的核心層次;儀式過程中的嗩吶吹打曲牌,多出現在迎來送往的儀式環節中,雖與喪儀中的民間信仰關系稀疏,但在連接儀式結構與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屬于中介層次;揚州地區喪葬儀式中加入流行歌曲部分,多是為了娛人,起到營造氣氛的作用,屬于外圍層次。
綜上可知,《悲歡離合》的作者們立足前人成果,探尋出一系列新的視角和方法,并將其應用于研究實踐,不僅豐富了民族音樂學學科的研究內容,也為后來者開辟出一條新的前行之路。
■《悲歡離合》之商榷
(一)音樂形態分析有待深入
喪葬儀式音樂具有其獨特的本體特征和風格樣式,彰顯出該儀式類型特有的藝術意涵和文化表達。喪葬儀式程序繁雜多樣,其中的音樂更是豐富多彩,它與儀式相伴相隨,對推進儀式的有序進行起到重要作用。《悲歡離合》偏重對儀式個案的音聲描述與忠實記錄,缺少對儀式音聲本體層面的深入分析與比較研究。倘若書中能繼續深入分析儀式音聲中的旋律體系、空間組織、動力系統、詞曲配合等方面的特點,則將更為形象、全面地展示喪葬儀式音聲的整體風格構成。
(二)全書篇幅安排有待完善
《悲歡離合》分為“綜述篇”“個案篇”“比較篇”三部分,其中綜述篇含納四篇文章,個案篇有十篇,比較篇收錄一篇。書中對個案篇的篇幅安排十分充足,而比較篇則內容較為單薄,形成較大反差,若能在比較中予以引申,將長江流域漢族與該地區少數民族喪葬儀式音樂進行社會結構、信仰體系、儀程進行、儀式用樂等不同側面的比較,則整本書篇幅安排會更為平衡,也更能凸顯不同民族喪葬儀式音樂觀念與行為的“同”與“異”。
(三)研究視角尚待拓寬
民族音樂學主要研究當今依然存活的音樂事象,口頭傳統是其研究主體。近年來,受到歷史人類學的影響,民族音樂學的歷史研究方興未艾。其關鍵點在于,在“新史學”視野的影響下,在以新的方式來“重構”歷史的過程中,文化意義的闡釋成為民族志寫作的核心。通過對闡釋的方式來建構不同歷史時期、社會環境和個人心中所認識的歷史“真理”。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美譽,喪禮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先秦《周禮》中將“五禮”分為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其中兇禮中即包含喪葬禮儀。閱讀《悲歡離合》后,筆者認為,該著對長江流域漢族聚居區喪禮音樂個案的田野考察非常扎實深入,但卻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對儀式音樂歷史脈絡的把握。實際上,喪葬儀式音全息反映了多重疊合的動態的社會文化變遷的時間歷程。如果能借鑒民族音樂學歷史研究的相關研究視角,把共時性的實地調查與歷時性的文獻解讀相結合,將儒學經典、地方史志、民眾口述與當下活態傳承的儀式文本接通并相互印證,在宏觀把握下進行微觀個案研究,則可能對長江流域漢族喪葬儀式音樂文化的精妙之處會有更為立體的認知和體悟。
另外,著述也可考慮引入“國家”這一分析維度。區域性儀式音樂的存在,是蘊含于國家制度和國家話語的深度理解之中,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民間喪儀中相當多的音樂觀念與行為,體現出了整體一致性中的地方差異性,其實質是歷史上的國家禮制被民間接續之后的俗化體現。如果忽視國家的存在而僅僅談論儀式音樂個案,難免會產生“隔靴搔癢”的偏頗。
■總結與思考
一聲嗩吶,奏起生離死別;一曲挽歌,唱盡悲歡離合。行走于田野之中,體驗他者的離別哀傷;穿梭于音聲之間,徹悟生命輪回的深刻寓意。每一聲哀泣,表達對逝者深深眷戀之情;每一聲樂起,吟訴對生命的依戀之情。當再捧起厚重的《悲歡離合》,細心品味,仿佛置身于人聲與器聲交織的儀式現場,靜靜觸摸那段人生禮儀的最后送別時光。人生如歌,有始有終。喪葬儀式宛如一條河流,它流淌著生者祈望死者福蔭后人的情懷,傳達著對生命的敬重和生活的新希望。
《悲歡離合》是一部詳盡記載長江流域漢族聚居地區喪葬儀式音樂的民族志,不同學科理論、不同觀察視角、不同學者思路的有機融合,其較為全面地描述、分析了該區域喪儀音樂的整體樣貌。數十位作者一起深入田野調研,專心案頭寫作,尋音談樂,愛于此,樂于斯,他們不僅僅是在深入探究音樂事象,也是在表達自己對民族音樂學學科發展的情愫與美好愿景。透過作者們細膩的筆觸和溫潤的情感表達,筆者讀懂了他們在田野考察中的所得所悟,也對他們高尚的人文情懷、求善求美的學術品格心生贊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