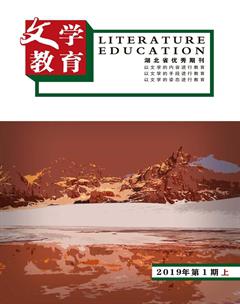高中語文學科新面向:整本書
內容摘要:在“整本書”教學問題上,無論是闡述的廣度和深度,還是對師生的要求,《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都遠遠高于2003年版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對應于課程目標和內容,新版課程標準中的“讀物”建議也做了修改、調整,包括種類、數量和深廣度等。雖然新版課程標準讓教師感到有些繁難,但如果能夠以“整本書”尤其是經典名著的閱讀教學來促進學生“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提高,就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有全面實施各個學科“核心素養”發展戰略,才有可能讓利于國、利于民的“整本書”教學落地生根,才有可能讓“整本書”教學這棵幼苗在校園里長成參天大樹。
關鍵詞:高中語文學科 課程標準 整本書 名著閱讀教學 核心素養 閱讀理念 教學理念
跟2003年版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以下簡稱“舊版課程標準”[1],凡出自該標準的引用文字只在正文括號內注明頁碼)相比,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以下簡稱“新版課程標準”[2],凡出自該標準的引用文字只在正文括號內注明頁碼)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如“學科核心素養”(第4-5頁)、“整本書閱讀與研討”(第11-13頁)、“學業質量水平”描述(第35-39頁)等,對語文教師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對此,筆者以為,雖然新版課程標準讓教師感到有些繁難,但如果能夠抓住“學科核心素養”和“整本書”的聯結點,以整本書尤其是經典名著的閱讀教學來促進學生“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提高,就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整本書”在新版課程標準中的突出地位
在語文學科教學中,整本書尤其是經典名著歷來為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所重視。雖然我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因過分重視應試教育而未將其落實好,但在頂層設計的舊版課程標準中,我們仍能看到并未完全被忽視,只是相比之下,新版課程標準賦予了它很突出的因而也是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整本書”問題上,舊版課程標準“一、必修課程”中“閱讀與鑒賞”部分的表述是:“10.具有廣泛的閱讀興趣,努力擴大閱讀視野。學會正確、自主地選擇閱讀材料,讀好書,讀整本書,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文化品位。課外自讀文學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讀物,總量不少于150萬字。”(第8-9頁),而新版課程標準的“課程內容”則把“整本書閱讀與研討”列為18個“學習任務群”中的第一個來加以闡述(第11-13頁)。通過對比分析,可知新、舊版課程標準之間存在著多個方面的差異。
第一,新版課程標準明確規定,作為第一個“學習任務群”的“整本書閱讀與研討”,必須貫串到高中教學的“必修、選擇性必修、選修”三個階段中(第11頁),而舊版課程標準則泛泛而談,雖然強調了要讀“整本書”,但沒有對高中三個年級提出具體的“整本書”教學要求。從性質上講,“整本書”教學在舊版課程標準中仍屬于“隱性課程”,而在新版課程標準中則轉變為舉足輕重的“顯性課程”[3]。
第二,在新版課程標準的“學習目標與內容”中,“必修課程”不僅明確規定了要有“一部長篇小說”的教學,而且還明確要求須有“一部學術著作”的教學(第11-12頁),而按舊版課程標準中關于“讀整本書”的倡導和要求,既可以不是學術著作,也可以不是長篇小說,而可以只是中短篇小說集、詩集或散文集。
第三,新版課程標準“必修課程”不僅有“整本書閱讀”要求,而且還有難度更大的“整本書研討”要求,但舊版課程標準的教學則未明確提出要對整本書進行“研討”,更沒有新版課程標準中的諸如“研究小說的藝術價值”、“閱讀與本書相關的資料,了解本書的學術思想及學術價值。通過反復閱讀和思考,探究本書的語言特點和論述邏輯”之類的已近乎大學教學要求的高端說法(第12頁)。當然,舊版課程標準也有“文化論著研讀”的提法(第12-13頁),但其要求只在“選修課程”內(第10-13頁),在“必修課程”里卻完全不提。另外,“文化論著”不同于“學術著作”,“研讀”也與“研討”有別,前者在檔次和要求上都低于后者。
第四,新版課程標準對學生“各類文本的閱讀量”的要求是必修階段不低于150萬字(第32頁),選擇性必修階段不低于150萬字(第34頁),也就是說,兩個階段的閱讀量合計不能低于300萬字,而舊版課程標準的要求則只有“必修課程”中所說的“總量不少于150萬字”(第9頁)。
由此可知,在“整本書”教學問題上,新版課程標準無論是闡述的廣度和深度,還是對師生的要求,都遠遠高于舊版課程標準。
二.“讀物”建議在新版課程標準中的顯著變化
對應于課程目標和內容,新版課程標準中的“讀物”建議也做了修改、調整。
首先是“建議”的提法有新意。舊版課程標準的提法是“關于課外讀物的建議”(第28頁),而新版課程標準則改為“關于課內外讀物的建議”(第57頁)。雖然這里只加上了一個“內”字,但這一字之差卻有著重要的意義,可謂是天壤之別。它表明了,高中語文課程不僅要重視課外閱讀中的整本書尤其是經典名著,而且還必須把“整本書”尤其是“經典名著”的“閱讀與研討”納入課內教學的軌道,這讓原本似乎有些另類甚至還被一些人視為是不務正業的課外閱讀教學尤其是經典名著教學變得很重要。
其次是“讀物”的種類有明顯的改動。舊版課程標準里有“課外讀物包括適合高中學生閱讀的各類圖書和報刊”的說法(第28頁),而新版課程標準里則沒有提及“報刊”(第57-58頁)。這樣的“刪改”,表明建議的“讀物”是整本書尤其是經典名著,而不是時效性較強的“報刊”。或者說,在新版課程標準里,對于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應該重視”的“報刊”[4],雖然處于高中階段的學生也很喜歡[5],但由于其相對的“短、平、快”,所以就沒有再推薦閱讀的必要了。
再次是“讀物”數量、范圍有不小的變化。除籠統的“讀物”類型的推薦外,“建議”中有具體作品名稱或具體作家名字的,舊版課程標準為30部(位),而新版課程標準為50部(位)。新版課程標準里,語言、文學理論著作方面未有增減;文化經典著作方面,增加了《老子》《史記》等作品;詩歌方面,增加了毛澤東、戴望舒、艾青、藏克家、賀敬之、郭小川、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小說方面,增加了《儒林外史》《彷徨》《四世同堂》《暴風驟雨》《平凡的世界》《約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散文方面,增加了葉圣陶的作品;劇本方面,增加了《竇娥冤》《牡丹亭》《屈原》等作品。
最后是“讀物”的厚度和深度也有較大的改變。同樣是狄更斯的長篇小說,舊版課程標準中的《匹克威克外傳》有67萬多字,新版課程標準則換成了稍長一點的74萬多字的《大衛·科波菲爾》。同樣是雨果的長篇小說,舊版課程標準中的《巴黎圣母院》只有40多萬字,新版課程標準則換成了長達120多萬字的《悲慘世界》。同樣是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舊版課程標準中的《復活》只有40多萬字,新版課程標準則換成了長達130多萬字的《戰爭與和平》。
對比可見,新版課程標準中推薦的“讀物”變得厚重。僅從新添加的作家作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80多萬字)、路遙的《平凡的世界》(100多萬字)、《約翰·克利斯朵夫》(120多萬字)等,就可看出其對高中生提出了必須多讀鴻篇巨制的要求。此外,新版課程標準推薦的“讀物”不僅篇幅變長,而且變得更有深度和廣度。比如,《悲慘世界》內容的深刻性和豐富性,遠非《巴黎圣母院》可比。再如,《戰爭與和平》主題的深邃、豐富程度,也在《復活》之上,其接受難度,恐怕連那些語言文學專業的大學生都不一定個個能理解好。雖然有學者認為:“今天已經進入到了一個相對‘厚重些的書籍難以對絕大多數人的閱讀起決定性作用的年代”[6],但新版課程標準卻表明了,閱讀“厚重”的書籍對于學生的成長來說仍然是很重要的。
綜上所述,在“讀物的建議”問題上,新版課程標準的改變不可謂不大。而這種改變,實際上與“整本書”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是一脈相承的,也可以說是新版課程標準的相關內容必須相稱所使然。
三.“學科核心素養”與“整本書”教學的關聯
新版課程標準的一大亮點,是把“素養”這個頗為寬泛、籠統的概念提煉概括成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若干個“要素”。作為一個整體,“語文學科核心素養”包括語言建構與運用、思維發展與提升、審美鑒賞與創造、文化傳承與理解四大方面(第4-5頁)。對于“語言、思維、審美、文化”這四大方面,課程目標還進一步地細化,將它們都劃分為高低不同的三個目標層次(第5-7頁)。大體而言,每個方面的三個不同目標依次升高,即第一方面的目標層次為:①語言積累與建構→②語言表達與交流→③語言梳理與整合;第二方面的目標層次為:①增強形象思維能力→②發展邏輯思維→③提升思維品質;第三方面的目標層次為:①增進對祖國語言文字的美感體驗→②鑒賞文學作品→③美的表達與創造;第四方面的目標層次為:①傳承中華文化→②理解多樣文化→③關注、參與當代文化。一般地說,要實現高層次的教學目標,就必須建立在低層次的教學目標已經實現的基礎上。而如果教學只是達到低層次的目標,則不能說教師已經完成了“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培育任務。
關于“學科核心素養”不同層次的劃分,新版課程標準中“學業質量水平”的描述顯得更為具體、更為清晰。其中,低級“學業質量水平”(以第1級為代表)的描述主要為諸如積累、感受、理解、欣賞之類的行為水平,而高級“學業質量水平”(以第5級為代表)的描述則主要為諸如批判、發現、創作、解決問題之類的行為水平。
像新版課程標準這種細分為五個等級的“質量描述”,意味著學生必須擁有廣闊的閱讀視野和深厚的閱讀積累,意味著學生必須走大量的整本書閱讀尤其是經典名著閱讀的道路[7]。如果不是這樣,學生就難以達到較高級別的“學業質量水平”。如果不是這樣,學生就無法做倒“有探索語言運用規律的興趣,能主動收集、整理、探究生活中常見的語言現象;能發現所學的語言文學作品中的各類聯系”;無法做倒“在表達時,講究語言運用,追求獨創性,力求用不同的詞語準確表達概念,用多種語句形式表達自己的判斷和推理;喜歡嘗試用多種文體、語體、多種媒介,多樣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追求表達的準確性、深刻性、靈活性、生動性”;無法做倒“能比較多個不同作品的異同,能對同一作品的不同闡釋發表自己的觀點,且內容具體,依據充分……有文學創作的興趣和愿望……追求正確的價值觀、高尚的審美情趣和審美品位”;無法做倒“寫相關調查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組織專題討論和報告會;嘗試用歷史眼光和現代觀念,辯證地審視和評論古今中外語言文學作品的內容和思想傾向,對當代文化建設發表自己的見解”(第38-39頁)。可以說,在語言、思維、審美和文化等四個方面都能夠同時達到上述中第5級水平的成年人并不是很多。若從高中生培養角度講,要達到第5級的水平那就更加不容易。而能夠真正實現的途徑與辦法,是以整本書尤其經典名著的教學為基石,而非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整本書閱讀只是語文課程整體架構中的一項也許并非核心的具體內容”[8],更不能像以往那樣只依靠“單篇短章”的教學,在方法上也不能是老一套[9]。
像這樣規定性的“質量描述”,意味著教師必須更新閱讀理念、教學理念[10],意味著教師必須探索新的教學策略和教學方法,以培養高漲的閱讀熱情、掌握正確的閱讀方法和養成“自動化”的“讀書習慣”為宗旨[11],除把單篇課文教好外,還要特別地重視整本書的教學,尤其是那些“由于歷經考驗而變得難以動搖甚或不可動搖”的經典名著的教學[12]。
眾所周知,我們的高中語文教學長期以來注重基礎知識的積累,包括詞語解釋、名句摘抄、詩詞背誦、段落分析和掌握各類文體的作文法等等,并且特別重視采取各種措施和方法來對學生進行應考能力的強化訓練,包括月考和周測試以及跨校聯評、聯考等等[13],至于學生在課外讀了多少本書、讀了什么書,不是漠不關心,就是走過場地檢查一下讀書筆記,或者要求他們寫一點讀后感。而學生們,多數沒有“正確的閱讀觀念和良好的閱讀行為”[14]。他們為了應付老師的檢查,相當一部分不是在網上復制或剪輯同題文章,就是找一本有導讀的名著摘抄幾段,至于原著則不讀,更未認真讀,甚至于老師要求讀的名著,有些連摸都沒摸過,有些則陌生到把書名都記錯了。
在新版課程標準頒布的背景下,像這樣過于功利性的教學現狀是到了該改過來的時候了。
與幾千字以內的單篇課文不同的是,整本書尤其是那些鴻篇巨制無法在課堂上讀完。故而,學生在課外有沒有興趣閱讀、采用什么方式閱讀至關重要。而要使學生在課外讀整本書更有成效,就必須竭盡全力激發他們的閱讀興趣,教給他們閱讀的方法,并盡最大的可能減少他們不得不完成的作業量,使他們擁有充足的自由閱讀時間而不必用“求速度”、“求效益”的方式來應對有厚度和深度的整本書[15],以便在書中流暢的語言、和諧的結構、曲折的情節、生動的形象、激越的情感、深邃的思想的陪伴下享受審美和探究的樂趣。如果學生能跟書中廣袤的世界擁抱在一起,能與書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能站在經典名著中的精神高地上來“看世界、看時代、看自我”[16],能借先賢圣哲的書來深化自己的思考,能由經典名著中的原創力量來激發自身探索的欲望和創造的潛能,那么,他們的語文學科核心素養水平的真正提高就將不期而至。
四.“整本書”教學展望
早在七八十年前,老一輩語文教育家葉圣陶先生就有過用“整本的書”來推進“國文教學”的設想,他在《論中學國文課程的改訂》中這樣寫道:“國文教材似乎該用整本的書,而不該用單篇短篇……退一步說,也該把整本的書作主體,把單篇短章作輔佐。”[17]不過,由于社會資源的匱乏,“整本書”的教學很難在那個時候扎根。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和學校圖書資源的日益豐富,學生人手一部名著或多部名著并非是什么難事。也就是說,名著閱讀教學走進課堂,如今在物質條件方面應該是不會有什么大的問題了。而新版課程標準的頒布,則使這項雖繁難但對真正提高語文教學質量有莫大好處的工作有了更加充分的理據。進而言之,只要把新版課程標準中的“整本書”貫徹落實好,學生“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全面提高也就指日可待。
然而,理想不等于現實,貫徹落實好新版課程標準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是一項可能需要用很長的時間來進行建設的系統工程。
首先,起著“指揮棒”作用的高考命題[18],應指向整本書閱讀尤其是經典名著閱讀,并且其分值不能過低。筆者認為,分值的幅度可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之間。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所以命題時應該特別地注意能夠考出學生是否真正閱讀過該經典名著的情況,并盡最大可能避開各式各樣教輔書中列出的所謂“知識點”,讓那些浮光掠影的閱讀者無法輕易得分。就整本書的“命題覆蓋范圍”而言,以新版課程標準所列的50部(位)為最低限度,讓押題者難以猜對,久而久之,猜題的現象就會減少,甚至于消失。
其次,起著強力調控作用的教育管理者,應改變已經扭曲了的急功近利的教育觀念,“竭盡全力”“糾正‘考試至上主義傾向”[19],主動順應素質教育的大潮流。由于“整本書”教學尤其是鴻篇巨制的教學是一項“報入多而產出時間長”的工作,或者說其效果并非立竿見影,所以,教育管理者除了應該給教師創設良好的條件外,還應該有足夠的耐心,而不能像以往那樣搞“分數掛帥”[20],不能老是盯著學生的語文考試成績不放,更不能把期末考、期中考甚或是月考的成績拿出來說事,以免舍本逐末,誤了真正提升學生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大事。
最后,起著直接作用的高中語文教師,應改變教學理念,銳意進取。一篇課文講兩三個學時的“精細法”還會保留,“字、詞、句、段、篇”的蝸牛般前行的教學方法還會存在,因為選文式的教材仍有相當大的分量。但是,“整本書”進入課堂已經大大地改變了高中語文教學的格局,它需要語文教師釆用新的教學策略,構建新的教學模式,探尋新的教學方法,這當然是一種不小的挑戰。不過,這種策略上、模式上、方法上的挑戰再大也是容易應對的,因為可以閱讀指導手冊[21],可以請專家指導,可以觀摩學習,可以集體備課,也許一年半載就上手了。對于多數的高中語文教師來說,更為嚴峻的挑戰是來自于自身的“讀書少”[22],因而也就無法成為學生“多讀書,多讀整本書”的好榜樣[23]。
長期的應試教育,讓許許多多曾經很熟悉或較熟悉“整本書”的語文教師已經變得不知道“整本書”是什么味道了。現在要讓他們來教“整本書”,能行嗎?新版課程標準已經出臺,不行也得行,解決的辦法之一是“惡補”。但是,“整本書”閱讀素養的提升是一種內力的提升,沒三五年的浸淫功夫難以見效,而不像諸如教學方法之類的套路那樣,可以借助外力在短時間內習得。所以,能夠預測得到,剛開始實施的“整本書”教學,多屬于花拳繡腿。不過,只要武者有決心和恒心,花拳繡腿最終還是會變成“真功夫”的。
另外,我們還應該看到,高中語文教師最為艱難的適應可能并不是自身“閱讀素養”的提升,而是由“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之間的矛盾沖突所導致的嚴重心理負擔問題。如果只是自身“整本書”閱讀素養的提升問題,只是“整本書”教學需要探索適宜的路徑問題,那么,語文教師就還可以通過不懈的努力來解決。但如果一方面要不斷地提升自身的“閱讀素養”,不斷地提高在學生有效閱讀“整本書”方面的“引領技巧”[24],而另一方面又要符合現有的教育行政管理者所釆用的以學生考分作為業績評價標準的要求,那么,任何人都難以解決好。在兩難困境下,作為一個普通的語文教師,最終不是顧此失彼,就是心力交瘁。顯然,這樣的擔心并非是多余的,因為在新舊交替的社會轉型期,包括外部、內部和個體自身的各種各樣的矛盾沖突會經常發生,而“整本書”教學作為高中語文學科的一種新面向,其承擔者也不會例外。
由上述可知,只有教育行政管理者能夠充分地認識到“考試制度”是“目前制約著學生多讀課外書的首因”[25],也是讓中學生“經典名著閱讀量”比小學生更遠離理想的最主要因素[26],并能真正地以提升學生“學科核心素養”為重,全面實施各個學科“核心素養”發展戰略,杜絕各種各樣以追求考分為主要目標的投機取巧行為,才有可能讓利于國、利于民的“整本書”教學落地生根,才有可能讓“整本書”教學這棵幼苗在校園里長成參天大樹。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訂.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3]鄭惠生.影響中學生課外閱讀的五個因素[J].教學與管理,2007(34):37.
[4]鄭惠生.城鄉小學生最喜歡哪些雜志和報紙——小學生課外閱讀調查研究之五[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7(02):87.
[5]鄭惠生.“視聽時代”中學生最喜歡閱讀的紙質讀物探討——中學生課外閱讀調查研究之五[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6(08):110.
[6]鄭惠生.“圖像時代”大學生最認同的讀物的探討——大學生課外閱讀調查研究之八[J].美與時代(下),2005(12):89.
[7]姚佩瑯.以提升素養為導向的名著閱讀教學實驗[J].文學教育(上),2018(11):71
[8]管然榮,陳金華.整本書閱讀教學的“冷”思考[J].語文建設,2017(04):66.
[9]姚佩瑯.名著閱讀教學的條件創設[J].文學教育(上),2018(12).
[10]姚佩瑯.校辦讀書節的閱讀理念[J].語文教學通訊·D刊(學術刊),2016(07):21.
[11]鄭惠生.小學生課外閱讀認知、行為與相關條件的調研[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06):86.
[12]鄭惠生.文藝學批評實踐[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381.
[13]姚佩瑯.略論當前中學文學教學的“八重八輕”[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9(02):84.
[14]姚佩瑯.德育視野中的校辦讀書節[J].現代中小學教育,2017(04):28.
[15]鄭惠生.論雅文學的困境與出路[J]. 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02):11.
[16]姚佩瑯.例談學校讀書節的功用、運作及局限[J].中學語文教學參考,2015(33):11.
[17]葉圣陶.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5:60.
[18]姚佩瑯.高中語文中文學作品的定位——以《課標》、教材、高考的分析為基礎[J].語文教學通訊·D刊(學術刊),2014(05):29.
[19]鄭惠生.中學生最欣賞與最反感的作家作品有哪些?——中學生課外閱讀調查研究之三[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6(02):63.
[20]鄭惠生.中學生離經典名著有多遠——中學生課外閱讀調查研究之二[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5(12):88.
[21]吳欣歆,許艷,主編.書冊閱讀教學現場[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6.
[22]鄭惠生.關于大學生課外經典名著閱讀原因的調查研究[J].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5(05):47.
[23]鄭惠生.論影響小學生課外閱讀五因——從城鄉小學生的心里話談起[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10):95.
[24]鄭惠生.經典名著留給大學生的印象探討——大學生課外閱讀調查研究之六[J].美與時代(下),2005(09):83.
[25]姚佩瑯.校辦讀書節對學生課外閱讀認知與行為的影響——以汕頭市東廈中學為例[J].中國校外教育,2016(04):7.
[26]鄭惠生.城鄉小學生離經典名著有多遠——小學生課外閱讀調查研究之二(上)[J].湖北教育學院學報,2006(11):103.
(作者介紹:姚佩瑯,汕頭市東廈中學語文教研組長,汕頭市名教師,廣東省特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