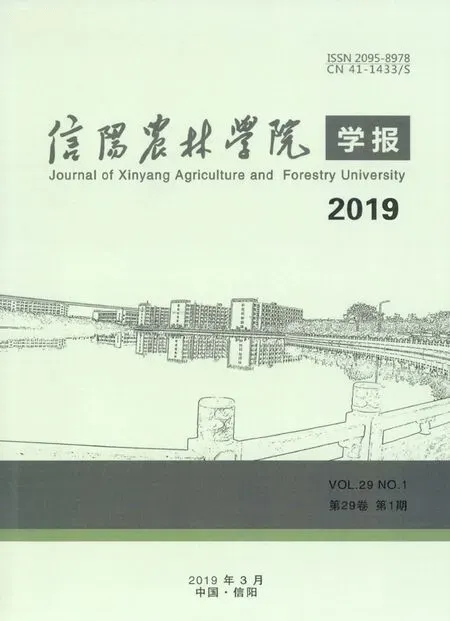《活著》的生與死探析
趙 娟
(呂梁學院汾陽師范分校 中文系,山西 汾陽 032200)
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會受到早期經驗的影響,著名心理學家榮格曾說心靈有與之相應的生理器官并繼承多種特性,而這些特性又決定這個人對于生活經歷作出的多種反應,甚至這些特性還決定了他之后要面臨的生活經歷,因此可以說人體與過去的經歷是密切相關的,而且與人體相連的不僅是童年的經歷還有往昔歲月。余華出生于浙江杭州,之后又遷移到海鹽,父母都是醫生。幼小的余華有很多異于常人的舉動,他曾由于疲憊而躺在醫院太平間,與尸體一同午睡,而且還故意裝著肚子疼被切除盲腸,余華的個性在他的創作風格中也有所反映,二者呈現出一致性。余華也認為一直以來自己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現實的那一層比較緊張的關系,這種緊張感越來越明顯,也真實地體現在他的作品中。余華是我國著名的先鋒派作家,在上世界80年代已經成為文壇名人,1990年代隨著文學進入轉型期,他的作品也出現一定的轉變。外界曾評價余華是冰渣子文學青年,但后來他選擇用溫情的方式開始新的文學之旅,轉型后的代表作之一《活著》從不同的視角對生存展開深入思考,描繪出人類在苦難、死亡、貧困等一系列困境下的真實生存狀態。
1 對死亡的描述
雖然《活著》這部小說的主題是活著,但是在字面背后卻一直潛伏著指向死亡的人生苦難,這部作品充滿著死亡的氣息,也是作者上世紀80年代先鋒創作風格的延伸。《活著》這部作品中的第一人稱敘述人是一個在民間喜愛收集民謠的文人墨客,有一次在田間聽福貴講述了他坎坷的一生。小說中的死亡是如此真實,濃重的死亡氣息讓讀者難以承受,因此在此基礎上改編成的電影版本《活著》并沒有向觀眾展示小說中全部的死亡事件,只拍到女兒難產而死就終結了。電影的處理方式溫情了許多,結尾的長鏡頭表現了仍然活著的福貴和他的妻子、外孫,其生活常態顯示了生命的延續和生活的希望,讓人心生慰籍[1]。而余華的小說《活著》卻讓讀者看到生活的殘酷和讓人難以接受的死亡,作家用純凈的語言不斷講述著一個個的死亡故事,從他的筆下卻感受不到一絲悲傷的氣息,他并沒有對小說中人物的遭遇表示出態度,而是站在非人間的立場,將這種人間苦難細微地描繪出來,在對死亡的表現上顯得格外真實客觀。
縱觀余華的創作,尤其是他創作于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小說,其中很多都是描寫死亡的,他用冷漠的筆法對死亡進行細致的描繪,細節刻畫令人毛骨悚然,比如在《死亡敘述》中,一個卡車司機先后兩次出車禍撞死了年輕的生命,之后司機被人打死。在《古典愛情》這部作品中,赴京趕考的柳生在科舉落榜之后尋找曾與自己有過一夜柔情的女子,但當兩人相見時,女子的腿正被切下,而被賣的另一少女還未被殺死。大量的死亡與暴力被充實在作者的筆觸之下,讓人不禁感受到余華對于生命的承受力[2]。
2 活著與死亡的關系
《活著》中的人性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呢?小說《活著》講述了主人公福貴的人生故事,以時代劃分,福貴的人生可以分為民國時代和共和國時代兩個階段,從福貴的內心欲望和個人身份定位方面可以分為紈绔子弟和作為父親的福貴。僅從時代背景理解這篇小說,很容易發現作品中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民國時代福貴被抓去當壯丁,是戰爭的炮灰,自然可以理解為是當時那個黑暗社會的體現;共和國時代的福貴經歷了大躍進、文革,同樣可以理解為對社會時代的抗議,針對第二個時代的故事反映出余華是個勇敢的作家,能夠直面現實[3]。毫無疑問,小說中最觸目驚心的就是死亡和災難,《活著》是一篇僅僅十萬字的小說,便講述了福貴的父母、妻子、子女、女婿、孫子等七個人的非正常死亡,而在福貴的家庭之外,讀者還目睹了龍二、縣長春生等人物的非正常死亡,可以說小說的故事就是由一個接一個的死亡事件連綴而成的。福貴一家包括兒子有慶,女兒鳳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孫子苦根之死都發生于共和國時代,尤其是有慶之死,直接原因便是縣長太太需要輸血搶救,這個情節強化了小說的現實批判功能,然而我們的閱讀不能如此粗放,深思會發現社會批判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因為認真追究會發現福貴父親實際上是死于福貴的嗜賭成性,而福貴的這一賭徒天性又來源于父親的遺傳,父親在一定程度上是死于自己的賭徒基因。同樣,母親的死是由于疾病,福貴妻子家珍死于軟骨病,女兒由于發燒成為聾啞人,文革時代又死于產后出血,這些死亡雖然有貧困、醫療落后等原因,但從本質上來說,這些疾病主要是天災,不能過多追究于人禍,而能夠體現對于人禍的揭露的部分也不過是女婿二喜因為勞動事故逝世,這里固然有現實中勞動條件差的原因,但根本上說屬于意外事故,而現實主義更傾向于描寫人的死亡必然性,必然性是體現現實主義的深刻保證,而偶然性的書寫是現實主義不夠深入的證明[4]。
從另一個層次來看,這本書講述的是死亡,敘述的重點卻是活著,小說中的死亡都比較突然,大多沒有任何征兆,通過死亡來表現活著,讓我們感到內容之絕。在《活著》的翻譯本出版時余華曾說,活著,從字面上看,我們國家的語言充滿著力量,并不是來源于喊叫,也不是進攻,而是一味的忍受,我們只能不斷忍受生命賦予的責任,忍受時代給我們的苦難與幸福。在主人公福貴身上,我們看到活著的人必然要遭受多重苦難,經歷多種磨難,但我們仍然要堅強活著,勇敢面對生活帶給我們的苦難,主人公福貴的身上體現了一種頑強不息、百折不撓的精神。
3 死亡中的重生
在《活著》這本小說中我們發現余華從對死亡的絕望描寫中蘇醒,正如他在前言中所寫,美國民歌《老黑奴》中的主人公經歷了畢生苦難,家人都相繼離開,而他仍然對世界抱有友好的態度,并且沒有任何抱怨。余華寫下這部小說主要是希望體現人類對于苦難的承受,對于世界保持的樂觀態度。在寫作過程中,他認為人是為活著而活著的,并不是為了活著以外的事物而存在,這句話雖然簡單,卻讓人感受到生命的高貴,隱含了作者的個人思想和精神層面的上升。《活著》雖然密集地鋪陳著人間的苦難,向讀者展示出死亡的一幕幕場景,但并不是單純地描寫暴力,也不是因恐懼而對死亡過分夸大,而是在死亡背后蘊藏著心理學、社會學等多角度的思考,可以說死亡是人類最集中的苦難,也是苦難生活的極致。《活著》這本小說描繪了生離死別,寄托著余華對幾千年來中國農民在生存和命運層面上的思考,飽含著他對農民的同情與憐憫。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是最弱小、最無能為力的群體,他們永遠是被動的,想好好活著只能忍受身邊接踵而至的苦難。《活著》的主人公福貴在自己的田地中辛苦勞作,雖然掙扎在饑餓的邊緣,生活一直比較貧困,但是一些戰亂和運動接踵而至,才是社會對他最可怕的壓抑。屬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時代雖然過去了,但是很多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卻依然能夠體會到那種不堪回首、令人窒息的感覺。福貴不僅僅是一個人物,而且是一種符號代表,是我國歷經苦難的人民的縮影。正如余華所說,中國人就是這樣在幾十年的歷史長河中慢慢煎熬過來的,福貴見證了歷史,也是那個時代背景下農民的代名詞。余華描寫的就是那個時代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最無力的中國農民。死亡是一種極端的書寫,多少年來,人類對死亡都保持回避態度,利用溫情的詞匯進行描述[5]。而在余華的筆下,死亡如此接近我們,但正是由于死亡的貼近才讓人真正感受到生命的執著,沒有什么是比活著更重要的,雖然這句話很樸實,卻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中能夠綿延不絕發展下去的動力。《活著》這部小說的結尾雖然是悲劇,但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從悲劇中也看到了希望,死亡并不是最終的結局,而是新的開始,小說中也表明了民族性格的延續,這正是余華獻給讀者的最好的慰藉。
4 從《活著》品味余華的轉變
從1987年到1989年間,余華創作了多部作品,譬如《1986》《世事如煙》等,作為先鋒派代表作家之一,在這段時間余華的很多小說主要是利用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手法,向人們展示非理性的世界以及人性的兇險。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余華的創作發生一定程度的偏移,他認為創作的使命不是為了發泄,也不是控訴,而應當向人們展示性善的一面,也就是高尚,這是對事物理解之后的一種超然[6]。對待善與惡,要一視同仁,用同情的態度來看待這個世界,正是由于創作理念的改變,使他從過去憤懣不平以及先鋒孤僻的封閉中逐步走出來,越來越看重客觀的世界,也正是由于他對現實生活的態度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使他更加注重客觀評價世界,客觀看待人類生存的價值和意義。《活著》這部小說主要闡述了人類的命運,作家對小說中人物命運和生存困境的刻畫不再像往常一樣呈現過多的暴力,或者黑暗世界,而是著重展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主人公生活的坎坷,并對他們的生死存亡和艱難困苦進行細微描述。余華創作的風格逐漸向現實主義方向發展,這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國文學的時代背景與文化轉型所致。上世紀80年代,我國很多先鋒作家借鑒西方文藝創作的基本理論,但這種理論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而且有些態度比較偏激,使得先鋒作家最終只得將創作理念回歸現實主義;其次是余華個人的成長環境導致他的創作理念轉型。年輕時的余華對現實世界充滿了激憤,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反叛心理逐漸消失,他的心中多了些許溫情,開始用同情和客觀的目光來看待身邊的一切。最終他發現最好的生活就是活著,在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余華寫下了《活著》這部偉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