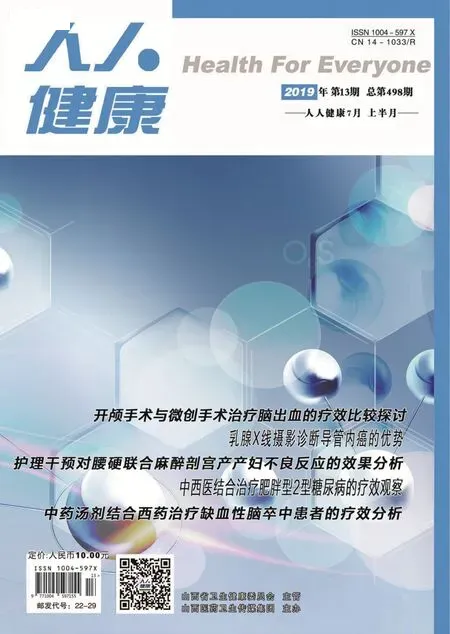衛生與健康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與對策分析
陳 芳
(安徽醫科大學附屬阜陽醫院 安徽 阜陽 236000)
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人們的健康需求越來越多元化和層次化。與此同時,經濟、社會與科技發展帶來的新業態諸如中醫藥健康養生、健康旅游等也激發了大眾一系列的潛在需求[1]。在社會轉型時期,應優化衛生與健康服務業的供給結構,最大程度滿足大眾的衛生與健康需求。本文旨在通過分別厘清衛生與健康領域當前存在的和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癥下藥地提出衛生與健康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對策建議。
1.衛生與健康領域目前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1.1 衛生與健康服務供給能力不足引發“碎片化”趨勢
當前,一個完整、連貫的衛生與健康服務流程被分割成各個片段,且大部分資源被集中在醫療服務供給上,供給側內部結構呈現出“碎片化”狀態[2]。同時,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雖然內部結構單一,總體服務和供給能力低下,卻承擔著衛生與健康服務的預防、宣傳、教育等前端工作,其供給能力不足的問題更是擴大了“碎片化”趨勢[3]。
從人力和床位的角度來看,近幾年我國醫生數、護士數以及床位數有一定的上升,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在一定程度上凸顯出我國衛生與健康服務供給總量不足[4]。在外部結構方面,政府管制也對衛生與健康服務供給產生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在產權和資本結構方面,我國衛生與健康領域供給主體多為政府主導的國有資本。這有利于國家對于衛生與健康領域的管理與調控,但也形成了我國衛生與健康行業的國家壟斷,從而導致資源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組織管理效能不高。
1.2 需求持續轉變,但供給相對滯后
從疾病譜的角度看,腫瘤、心腦血管疾病和心理疾病等慢性病成為影響健康的最大威脅。從人口結構的角度看,截至2016年底,我國老年人口已經達到2.3億人,占總人口的16.7%。孕產婦保健、新生兒護理等相關衛生服務的供需矛盾進一步突出。2.7億慢性病人和0.8億殘疾人對于長期管理、康復護理的衛生服務需求。上述人群不斷增長的需求對本就“供不應求”的衛生資源產生了嚴峻挑戰。
1.3 養老、康復需求不斷增加
有關機構預測,到2050 年,中國老年人口的消費潛力將從2014年的4 萬億左右增長到106 萬億左右。而當前我國養老機構的從業人員數不足100 萬,存在巨大缺口。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養老服務產業尚處在萌芽階段,不少地區的健康養老、智慧養老等服務產業仍在試點階段甚至還未出現,養老服務產業在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較發達國家偏低。
2.衛生與健康領域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改革進程逐漸邁入深水區,許多重難點問題集中顯現,需要進一步明確改革側重點。一是全民醫保體系建設有待進一步健全完善,醫保控制醫療費用過快增長的機制還不完善,醫保基金收支不平衡的矛盾開始顯現,需進一步深化支付方式改革。二是基層醫改成果還需進一步鞏固;基層醫療衛生資源較為薄弱,人才短缺問題十分突出,區域衛生發展格局有待優化。三是社會辦醫療機構數量雖多,與公立醫院相比,社會辦醫機構規模偏小,服務能力較弱,衛生人力質量和數量有待改善,床位使用率低。
3.衛生與健康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建議
3.1 明確問題,做出正確的系統性診斷
在進行衛生與健康領域的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時,需要找出存在的哪些體制性、結構性的深層次矛盾。以整合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IDS)為例,其由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和醫療機構組成,向特定的人群、提供或安排整合和連續的醫療服務的一種組織網絡,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可以包括家庭保健、療養院服務、初級和專科的門診治療和手術治療、預防保健、健康教育和融資,通常采取管理式醫療護理的形式。由此可知,進行系統性診斷,明確存在的問題對改革的進行至關重要。
3.2 多措并舉,給衛生與健康領域供給側“去行政化”與“去中心化”
衛生與健康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必須從“去行政化”入手,改“審批制”為“備案制”。鼓勵公立醫院逐步形成以理事會制度為核心的新型法人治理結構,從性質上實現“去行政化”。目前衛生與健康領域所提的“去中心化”主要集中在綜合性醫院的建設思路上。而對于宏觀的衛生與健康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去中心化”更應該體現在各級醫療衛生機構之間的合作和整合上。大型公立醫院應當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密切整合,促進醫療衛生資源逐步下沉,實現總體供給能力的提升。
3.3 多方協調,注重各子系統及各要素之間的協同改革
要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相關部門協同改革,同時在系統診斷的基礎上,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分類,分輕重緩急,重點問題優先改革。對此可以借鑒芬蘭的“多部門委員會制度”,將現有的針對特定問題不定期召開的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上升為長期設立的多部門委員會,由國務院直接領導,多部門負責人參與,并加快各部門健康影響評估體系的研究制定,為日后改革經多部門委員會討論,結合健康影響評估結果,最終確定改革措施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