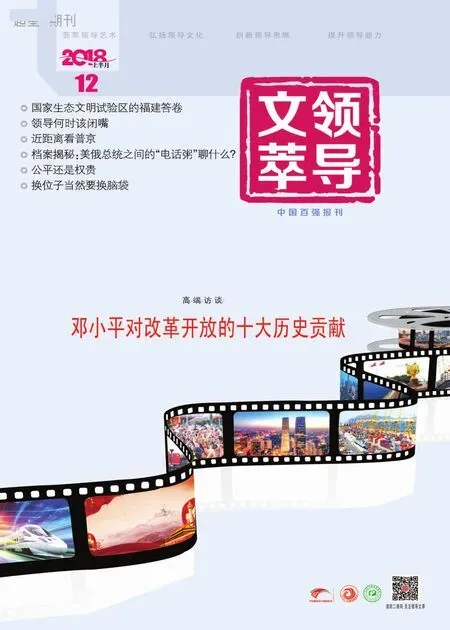厲以寧:無悔今生不自愁
陸正明
“股份制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減員增效從宏觀來說,是根本錯誤的”“道德是僅次于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的第三種力量”……近40年來,厲以寧的聲音總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節拍傳入人們耳中。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厲以寧“改革先鋒”稱號。在獲得褒獎時,厲以寧說:“作為讀書人,總有些正心、齊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這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
北大時光
1951年8月,厲以寧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
第二年,傳來了院系調整的消息。北大經濟系大部分并入新成立的中央財經學院,小部分留在北大,政治經濟學是唯一專業。當時有人提出厲以寧不適合學這門學科。代理系主任陳振漢教授和張友仁老師講了好話,他才得以留在北大。
厲以寧說:“陳振漢先生在聽課的學生中注意到了我,要我有空到他家里去坐坐。也許是因為我課間課后喜歡提問吧!”厲以寧“有空去坐坐”的還有趙迺摶先生的家。趙先生又推薦厲以寧結識了專攻西方經濟史的周炳琳先生。周炳琳曾言:如果沒有經濟史基礎,經濟理論是學不好的;如果沒有對西方經濟史的研究,工業化會走彎路。厲以寧說:“這兩句話影響了我一輩子的研究和學習。”
1977年,厲以寧正式登上講臺,很快成為大受學生歡迎的教師,有時連走廊上也擠滿了人,以至有學生提前領號,憑號入場。
人稱“厲股份”自稱“厲非均衡”
20世紀80年代初,就業成為經濟、社會的突出問題。1980年夏,厲以寧在全國勞動就業會議上提出,可以用民間集資的方法,組建股份制企業,為解決就業問題開辟新路。他的意見沒有被采納。
1986年,價格“雙軌制”的負面影響日趨顯現。4月26日,厲以寧在北京大學紀念“五四”學術討論會上,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9月,厲以寧在《人民日報》發文,再次為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大聲疾呼。有海外中文報紙給他起了“厲股份”的外號。
數十年后,厲以寧在談到這個外號時說:“有人稱我是‘股份制的首創者,這不符合事實。如果要有外號,我認為應該是‘厲非均衡。”
“非均衡”是指在市場不完善、價格體系不靈敏條件下達到的均衡。20世紀80年代末,厲以寧提出了“兩類不均衡”的觀點。他認為,按照市場主體是否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均衡”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企業能夠自主經營、不受干預情況下的“非均衡”。在傳統和雙軌制下的計劃經濟體制里,企業難以擺脫行政的干預,是第二類“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才能轉化第一類“非均衡”。這是他堅持經濟改革必須從產權改革入手的學理依據。
厲以寧說,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國的股份制改革經歷了試點、暫停、重啟,主張股份制的學者一度面臨被否定、被批判,直到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才有了變化。
2004年,《關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連同厲以寧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國務院。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問世,即著名的“非公經濟36條”。厲以寧又成了“厲民營”。
無悔今生不自愁
1980年,厲以寧第一次提出以“股份制”匯集社會資金興辦企業、解決就業問題的設想,未被采納且受到質疑。厲以寧寫下“七絕”:“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這首詩成為一代改革者心路歷程的寫照。
如今,在北京中關村的一處教授公寓里,89歲的厲以寧和夫人何玉春過著平淡日子。客廳仍是十幾年前的裝修,家具也有些陳舊,唯有一對略新的沙發,是學生送的。厲以寧每天早晨6點起床,堅持寫一小時文章,7點做兩個人的早飯,然后看書、寫作,直到11點,開始做午飯。做飯,是夫人何玉春為了讓他有機會歇歇腦子、動動身體。
何玉春是電氣高級工程師。厲以寧的文章總是先給她看,何玉春滿意了,厲以寧才放心,這樣,一般讀者讀起來也不會太難。
從1957年兩人重逢、為何玉春寫第一首詞起,厲以寧“情詩”多多。2008年,是他們金婚,厲以寧以“凄風苦雨從容過,無悔今生不自愁”的詩句總結50年婚姻,也可視作作者自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