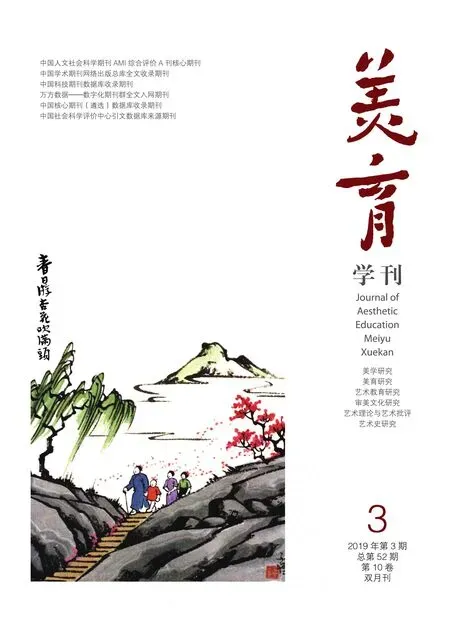《斷背山》中的“藝格符換”:從小說到電影的張力地帶
王 豪,歐 榮
(杭州師范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斷背山》(BrokebackMountain)是美國作家安妮·普魯克斯(Annie Proulx,1935—)于1997年在《紐約客》上發(fā)表的短篇小說,描述1963年至1983年美國懷俄明州兩個西部牛仔之間情愛與性愛的復(fù)雜同性戀情。小說發(fā)表次年,即獲歐·亨利短篇小說獎和全美雜志獎。小說在發(fā)表之初,便受到電影界的關(guān)注,很快被改編為劇本,歷經(jīng)8年時間籌備,被搬上銀幕。事實(shí)證明,華人導(dǎo)演李安執(zhí)導(dǎo)的《斷背山》獲得了成功與認(rèn)可。在電影上映次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斷背山》奪得了包括最佳導(dǎo)演、最佳改編劇本和最佳原創(chuàng)配樂在內(nèi)的3項(xiàng)大獎。
筆者通過檢索國外各大文獻(xiàn)數(shù)據(jù)庫后發(fā)現(xiàn),小說《斷背山》在發(fā)表之初,很快斬獲了一些獎項(xiàng),但在學(xué)界卻少有評論或研究;李安執(zhí)導(dǎo)的電影上映于2005年,探討電影和小說中“同性”情理緣由的文章此后集中涌現(xiàn),從性別角色、酷兒性向、同性悲劇、男性氣概、酷兒人格、同性戀凝視等角度加以闡發(fā)。筆者發(fā)現(xiàn),這些文章盡管角度明確,主題明晰,但在論述觀點(diǎn)時,往往將小說和電影統(tǒng)而論之,在小說與電影之間跳轉(zhuǎn)不定,鮮有探尋從小說到電影的蛻變過程中所生發(fā)的文藝符碼轉(zhuǎn)換的現(xiàn)象。與國外的熱度話題不同,迄今為止,國內(nèi)少有探討《斷背山》小說本身內(nèi)容及思想意義的研究成果,卻有不少文章或評論集中于肯定并剖析《斷背山》電影的藝術(shù)技巧與思想價值,這些研究為本文的討論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盡管《斷背山》小說和電影牽扯同樣的現(xiàn)實(shí)命題,為何在電影上映之后,所謂“同性”話題才呈現(xiàn)出井噴式集中爆發(fā)的趨勢?筆者認(rèn)為,這些“同性”問題在電影的源文本(小說)中是既定的存在,但正是因?yàn)榻?jīng)歷了從小說到電影的“藝格符換”,從單一文本到復(fù)文本(包括圖像、音樂)的跨藝術(shù)拓展,在全球范圍以更加直觀、更加生動的形式與觀眾見面,才引發(fā)人們更廣泛的共鳴與討論。時至今日,電影本身成為經(jīng)典,“斷背山”一詞已成為隱喻性的暗指。文藝的符碼,究竟經(jīng)歷了什么樣的轉(zhuǎn)換,才愈發(fā)引人關(guān)注與思考?本文旨在探尋,《斷背山》從小說到電影的“藝格符換”中,“視覺建構(gòu)”“敘事調(diào)整”“配樂新增”這三重文藝符碼的變化,并試圖探尋符碼變化背后的意義生成。
一、“藝格符換”
“藝格符換”是筆者據(jù)“ekphrasis”一詞所譯。本文雖不再作ekphrasis概念流變梳理以及中文譯名考量,但要指出,以往對ekphrasis的一些界定,如司各特(Grant Scott, 1991),米歇爾(W.J.T. Mitchell, 1992)以及赫弗南(Heffernan, 1993)所認(rèn)同的“對視覺表征的語言再現(xiàn)”[1](the verbal representation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或國內(nèi)學(xué)者所謂“藝格敷詞”或“繪畫詩”等,主要關(guān)注從視覺文本到語言文本的單向轉(zhuǎn)換。而本文所探討的,顯然是一種逆向的ekphrasis(從語言文本到視覺文本的轉(zhuǎn)換),中文譯名“藝格符換”就包含了將研究范圍擴(kuò)大、文藝符碼無特定方向轉(zhuǎn)換的學(xué)術(shù)意涵。
盡管“藝格符換”這一舶來的文藝概念,對于很多國內(nèi)學(xué)者來說,仍相對陌生,但將其應(yīng)用于文藝轉(zhuǎn)換研究的實(shí)踐,卻大有可為。“藝格符換”關(guān)注不同藝術(shù)媒介之間的互動和不同藝術(shù)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可以應(yīng)用于更廣泛的跨藝術(shù),甚至跨學(xué)科研究中。[2]作為一種文藝現(xiàn)象的存在,不僅豐富了觀賞層次,不同藝術(shù)媒介形式的轉(zhuǎn)換亦擴(kuò)大了受眾范圍,使藝術(shù)作品的傳播更廣,生命力更長久。
美國最重要的視覺藝術(shù)批評家和圖像理論家之一米歇爾,在其著作《圖像理論》(PictureTheory)一書中,回答了“圖像是什么?圖像和語言有什么關(guān)系?上述問題為何具有理論意義或者實(shí)際意義?”等若干問題。他指出,圖像與語言再現(xiàn)之間存在著一個張力地帶,摻雜著“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場域內(nèi)的角力,性別、種族和階級、政治恐懼以及真善美等問題都交匯在再現(xiàn)問題上。[3]由是觀之,從語言文本到視覺文本的“藝格符換”,同樣處于一個張力地帶,有著豐富而復(fù)雜的政治和文化內(nèi)涵。
而具體到探討“藝格符換”的跨藝術(shù)研究中,瑞典學(xué)者隆德(Hans Lund)在其著作《作為圖像的文本:圖像的文學(xué)性轉(zhuǎn)換的研究》(TextasPicture:StudiesintheliteraryTransformationsofPictures)[4]中提出了文本之于圖像轉(zhuǎn)換的三種主要類型:組合型(combination)、融合型(integration)以及轉(zhuǎn)換型(transformation)。
隆德指出“組合”意味著“共存”,即語言和圖像和諧并生的最佳狀態(tài),語圖兩種媒介彼此補(bǔ)充、互文共釋,如英國詩人兼畫家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和但丁·羅塞蒂(Dante Rossetti)以及德國作家兼畫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一些詩畫并置的作品即屬于此范疇。
在“融合型”作品中,圖像性因素是文字作品視覺形態(tài)的一部分。比較而言,在“組合型”作品中,圖像性因素?fù)?dān)負(fù)相當(dāng)獨(dú)立的功能,而在“融合型”作品中,一旦移除圖像性因素,語言的結(jié)構(gòu)勢必遭受破壞,即,語言和視覺因素共筑整體、缺一不可,像高腳酒杯狀或沙漏狀排版的詩節(jié)、巴洛克詩歌中的圖案詩(pattern poems)以及現(xiàn)代主義的具象詩都是典型的“融合型”作品。
而在“轉(zhuǎn)換型”作品中,沒有任何圖像因素與語言文本的組合或彼此融入,這個時候,關(guān)涉圖像中一個因素或組合因素的文本并不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傳遞給讀者的關(guān)于圖像的信息有且僅由語言文字給出的。當(dāng)詩歌或散文是基于繪畫的創(chuàng)作時,這種“轉(zhuǎn)換”即被視為“藝格符換”。
隆德和米歇爾的觀點(diǎn)啟發(fā)我們,在“藝格符換”的過程中,關(guān)注文藝符碼的變化,是研究的應(yīng)有之義,而進(jìn)一步探尋符碼變化所蘊(yùn)含的意義生成,更是研究重心之所在。
此外,在涉及文藝作品的媒介轉(zhuǎn)換的問題上,國內(nèi)外研究往往使用“改編”(adaption)一詞加以指代,但本文更偏向于使用術(shù)語“藝格符換”而不是“改編”。誠然,電影基于小說創(chuàng)作,此種現(xiàn)象固然可以“改編”一詞概之,但筆者認(rèn)為,就探究同題姊妹藝術(shù)的關(guān)系而言,“改編”一詞顯然只是普遍意義上的籠統(tǒng)概述,且單向度地指代從此媒介到彼媒介的靜止描述,而“藝格符換”則更加強(qiáng)調(diào)文藝符碼轉(zhuǎn)換的流動與多變。因此,筆者使用“藝格符換”一詞,更便于探尋文藝符碼的跨藝術(shù)轉(zhuǎn)換。
二、《斷背山》中的“藝格符換”
在《斷背山》從小說到電影的“藝格符換”中,我們關(guān)注“視覺建構(gòu)”“敘事調(diào)整”“配樂新增”這三重文藝符碼的變化,并試圖探尋符碼變化背后的意義生成。
(一)視覺建構(gòu):斷背樂土中的東方意涵
相對于小說的文字載體,電影給予受眾最為直接的是聲色并茂的視聽呈現(xiàn)。通常,在小說的閱讀過程中,文字畫面與場景的搭建,是通過作者的語言描述,讀者得以在腦海中借由形象思維搭建還原場面,“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種頭腦中的想象,會因?yàn)樽x者的生活閱歷和生命體驗(yàn)而千差萬別。電影,作為一種認(rèn)真而嚴(yán)謹(jǐn)?shù)乃囆g(shù)再創(chuàng)作,其畫面呈現(xiàn)往往在尊重原作的基礎(chǔ)上,通過實(shí)景拍攝或數(shù)字化處理,進(jìn)行具象的視覺建構(gòu)。
小說對于“斷背山”著墨不多,只在敘述兩人在山間放牧?xí)r對景物有非常簡略的描寫,讀者需要仔細(xì)品讀琢磨,才能夠體會包含其中的美感。這里試舉兩處:
黎明時分,天空漸漸透出透明的橙黃色,天際線呈現(xiàn)出凝膠般的淡綠色。黝黑的山色漸漸轉(zhuǎn)淡,直到和恩尼斯煮早飯時的炊煙渾然一色。凜冽的空氣變得溫和起來,曙光在山巒間投下了細(xì)長的影子,山下的黑松林郁郁蔥蔥,生長茂盛。
茶褐色的河水,帶著融化的積雪,匯成一股股急流,撞擊在山石上,濺起朵朵水花。河堤上楊柳輕拂,黃色的柳絮漫天飛舞。馬在河邊飲水,杰克跳下馬背,掬起一捧冰水暢飲,晶瑩的水滴從他指間、嘴巴和下巴上滑落,閃閃發(fā)亮。[注]引自Annie Proulx , “Brokeback Mountain”, New Yorker , October 13, 1997 issue.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1997/10/13/brokeback-mountain,筆者自譯,下文引用原文時,不再加注。
而電影《斷背山》通過視覺化的呈現(xiàn),非常直觀地展示了“斷背山”的自然風(fēng)光,藝術(shù)地完成了從語言文本到視覺文本的轉(zhuǎn)換演繹,以至于電影的真實(shí)拍攝地——加拿大亞伯達(dá)省的落基山成為關(guān)鍵詞“斷背山”旅游廣告宣傳的熱門景點(diǎn),而小說的背景地——美國懷俄明州——反而淪為一個文本設(shè)定的抽象的地理概念。
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電影《斷背山》的畫面呈現(xiàn)頗有“生態(tài)敘事”的味道,小說中的情節(jié)發(fā)展與風(fēng)景之間的關(guān)系緊密,斷背山是主線故事的發(fā)生地和見證者,與兩位主人公生命體驗(yàn)中的悲歡離合關(guān)系密切,毫無疑問,是二者生命體驗(yàn)中的帶著缺憾的樂土。導(dǎo)演綜合運(yùn)用電影的藝術(shù)手段及認(rèn)真的制作態(tài)度,是成功呈現(xiàn)視覺上“缺憾樂土”的關(guān)鍵。電影制作成本有限,但是導(dǎo)演李安在取景拍攝上頗為考量,他拒絕了數(shù)字化的處理方式[5],全部采用真實(shí)場景拍攝。在拍攝過程中,電影在畫面構(gòu)圖、色彩呈現(xiàn)、借光布光等方面堪稱教科書般的典范。如果說攝制組在技術(shù)上已經(jīng)達(dá)到了高水平的制作,真正在背后起主導(dǎo)作用的導(dǎo)演的“東方意涵”藝術(shù)之思則是需要被認(rèn)真關(guān)注的。
有學(xué)者指出,電影《斷背山》在視覺建構(gòu)上,注入了東方文化的美學(xué)意蘊(yùn),這點(diǎn)筆者十分贊同:
《斷背山》采用了中國山水畫的意像技法,描寫含蓄卻澎湃的暗流激情,借寓美洲山林予以表現(xiàn)。但入眼的不是雄峻偉大的山勢,卻是朗朗晴空、清風(fēng)明月、密林煙樹的意像,更加諸流水、羊群等等包含東方色彩的陰柔事物,即使是杰克在山區(qū)放牧、恩尼斯在湖邊飲酒的鏡頭都籠罩著一種“寒山頂上月輪孤”的幽謐氛圍。這些景物的選取,直接根源于中國傳統(tǒng)畫論中內(nèi)斂隱約的美學(xué)觀念……[6]
除了意象技法與意境營造,電影畫面對中國藝術(shù)中“留白”手法的借鑒也令人回味無窮。
還有評論指出,《斷背山》以東方美學(xué)的內(nèi)斂特征、敘事風(fēng)格、悲天憫人的基調(diào)為導(dǎo)向,以清新唯美的影像風(fēng)格,融進(jìn)了西方愛情電影的傳統(tǒng)和特色,再現(xiàn)了美國西部的兩個牛仔細(xì)膩、凄涼的同性戀情,完成了從小說到電影(思維角度、影像風(fēng)格、隱喻特征)的成功轉(zhuǎn)換[7]。這種“滲透了東方美學(xué)的含蓄內(nèi)斂”,除了在氛圍營造上有了高度的可觀賞性,同時在媒介傳播與受眾接受上,“大大降低了有悖社會常態(tài)性規(guī)范的題材可能令普通人產(chǎn)生的厭惡與不解,讓小眾化的情感適合主流大眾的口味”[7]。
借助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斷背山》這個由華人導(dǎo)演執(zhí)掌西方文化題材的典型案例中,東方美學(xué)的注入使得“藝格符換”相較于以往——同一文化體系內(nèi)姊妹藝術(shù)的轉(zhuǎn)換,擁有了新的文化層次,即跨文化表達(dá)。同題藝術(shù)的轉(zhuǎn)換,可以不再是一個文化體系內(nèi)的兜兜轉(zhuǎn)轉(zhuǎn),而是在跨文化體系內(nèi)的優(yōu)勢互補(bǔ)、交相輝映,而且這種趨勢,也勢必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藝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得越來越明顯。
(二)敘事調(diào)整:雙線程與家庭敘事
導(dǎo)演作為講故事的人,往往擁有自己敘述故事的方式。
在敘事結(jié)構(gòu)上,電影基本依循小說的架構(gòu),但是做出了一些細(xì)微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電影的劇情舍棄了小說開頭兩段的倒敘,而是按照“正敘”手法直接演繹故事的開端—發(fā)展—高潮—結(jié)尾,這樣處理的好處是方便觀眾對于劇情的理解。觀眾可以從短暫的兩個多小時的觀影過程中,擁有強(qiáng)烈的代入感,仿佛和主人公一樣經(jīng)歷了二十余年的情感糾葛。其次,小說側(cè)重于以恩尼斯作為敘事主體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寫作手法,電影在敘事上采用了較為均衡的雙線平行敘事,劇情在雙方主人公身上分配較為均勻,并且借助真人出演、主角直接對話的方式,大大增加了劇情感染力。
家庭敘事,即增加的“家庭”元素在調(diào)整后的雙線程敘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事實(shí)上,杰克和恩尼斯都是雙性戀者。故事伊始,二人在斷背山牧羊時墜入情網(wǎng),下山后他們依然循規(guī)蹈矩地選擇了異性戀生活,娶妻生子,在經(jīng)營各自家庭生活的同時,保持著秘密的關(guān)系。所以,作為承載社會常規(guī)和傳統(tǒng)約束的容器,家庭在影片中起到了探討自由和責(zé)任、欲望和倫理沖突的重要作用。
《斷背山》的小說原作者曾這樣描述兩位主人公的肉體關(guān)系:“杰克和恩尼斯在斷背山特殊條件下用身體凝聚成的男性之間不亞于婚姻的牢固關(guān)系,使他們在以后各自的婚姻中一直無法快樂起來。”[8]
電影劇情合理增添并補(bǔ)足了二人的戀愛求偶情節(jié)以及娶妻生子后的家庭狀況,尤其是杰克的家庭情況(小說中對杰克的家庭生活沒有正面描述,僅通過杰克的三言兩語加以交代)。不管是恩尼斯還是杰克, 雙方在戀愛或婚姻初期,表面上看起來美滿幸福,但實(shí)則危機(jī)重重,難以為繼。在增加的戲碼中,無論是恩尼斯攜妻女在國慶煙火下與陌生人發(fā)生沖突,還是杰克在感恩節(jié)的餐桌上與岳父的口角之爭,都表現(xiàn)出二者家庭生活的不如意。但正是這樣的“失意”敘事才為時不時地“出逃”——斷背山的屢屢相約重逢埋下伏筆。其實(shí),這也是電影在暗示二者缺憾悲情的境遇,敘事線程一分為二,兩廂苦悶糾纏;敘事線程合二為一,兩情相悅,但短暫的朝朝暮暮卻無法天長地久。
(三)配樂新增:敘事輔助與情感渲染
所有從文學(xué)作品到影視的“藝格符換”中,電影配樂是全新的“符碼”,《斷背山》也不例外。在第78屆奧斯卡金像獎的頒獎典禮上,該電影配樂獲得了最佳配樂的大獎。在利用配樂作音樂性的輔助敘事與情感渲染方面,新的“符碼”表現(xiàn)出色。
電影的配樂由阿根廷音樂家古斯塔沃·桑托拉拉(Gustavo Santaolalla)制作。桑托拉拉擁有扎實(shí)的技術(shù)功底和開闊的音樂眼界,在電影《斷背山》中根據(jù)小說提供的文字意象完成了大部分創(chuàng)作。在電影開場,伴隨著暮色與風(fēng)聲,最簡約的吉他撥弦勾勒出懷俄明州廣漠的草原景色,為故事的敘述奠定了一個悲涼哀傷的基調(diào)。
電影中的所有配樂都不是隨意安插,往往與劇情或主題緊密配合,無縫銜接,起到了輔助敘事、渲染情感的作用。如劇中當(dāng)杰克得知恩尼斯離婚之后,興沖沖地長途駕車而來,滿心期待著他們未來的共同生活,這時候,車內(nèi)播放的是溫布賴特(Rufus Wainwright)的《公路之王》(KingoftheRoad),杰克小調(diào)輕哼,瀟灑自足,儼然是個“公路之王”,他的怡然快活,溢于言表。當(dāng)杰克經(jīng)歷長途疲勞駕駛,終于見到心上人,但恩尼斯卻告訴他這周他要陪伴女兒,不能和他去斷背山。三言兩語之后,秋風(fēng)落葉之中,杰克怏怏而歸,這時,車?yán)锊シ诺氖敲绹l(xiāng)村民謠女歌手哈里斯(Emmylou Harris)演唱的《永不老去的愛》(ALoveThatWillNeverGrowOld),圓潤飽滿的歌聲與主人公的心境形成共鳴。而這“永不老去的愛”更成為二者關(guān)系的隱喻和暗示,一方面,二者的愛戀只能永遠(yuǎn)定格在年輕的歲月(杰克英年早逝),另一方面,這份情感也成為恩尼斯永遠(yuǎn)的憑吊。
與劇情巧妙縫合銜接的配樂,不勝枚舉。在電影片尾處,由納爾森(Willie Nelson)翻唱、鮑勃·迪倫(Bob Dylan)編曲的民謠《他是我的朋友》(HewasaFriendofMine)隱約呼應(yīng)結(jié)局,幾乎道出了這部電影所蘊(yùn)含的全部感傷,讓人不勝唏噓,歌詞“a friend of mine”的多次重復(fù)有力烘托和渲染悲情,表達(dá)出恩尼斯睹物思人的悲情哀挽。而另外一首片尾曲,由溫布賴特演唱的《一切天成》(TheMakerMakes)在淺吟低唱中以鏈條之喻,拷問現(xiàn)實(shí),直抵人心。
當(dāng)我們再次回顧隆德所提出的文本之于圖像轉(zhuǎn)換的三種主要的類型,我們恰好可以發(fā)現(xiàn)本文所舉出的“視覺建構(gòu)”“敘事調(diào)整”“配樂新增”三重變化中的文藝符碼,可以使用這三種類型加以闡釋,盡管一開始隆德提出的這三種類型只是基于語言文本之于圖像轉(zhuǎn)換的研究。
其一,新增的配樂,發(fā)揮了輔助敘事與抒情渲染的功能。音樂性的符碼,不僅與源文本,更與從源文本轉(zhuǎn)化后圖像形成了共存的“組合”關(guān)系,讀者可以在完全安靜的情形下閱讀小說,觀者可以在沒有配樂的情形下觀看電影,盡管電影的呈現(xiàn)力會受到削減。然而正是借助音樂性符碼的魅力,音樂與動態(tài)圖像彼此補(bǔ)充,互文共釋,大大增強(qiáng)了影像感化人心的表現(xiàn)力。
其二,盡管電影在敘事層面做出了一些調(diào)整,借助于動態(tài)影像,其敘事在主干上仍然基于小說情節(jié)建立。語言文字的敘事和動態(tài)人物影像的敘事,二者在電影媒介中是相互“融合”的,二者共筑整體,不可剝離。這種在新媒介的巧妙融合,無疑是帶給了文字文本更多文藝的光彩和展演的空間。
其三,在視覺建構(gòu)的層面上,呈現(xiàn)給電影觀者(尤其是那些完全沒有讀過小說的電影觀眾)關(guān)于斷背山的視覺印象,則完全是由圖像給出,《斷背山》的語言文字的描述已經(jīng)“轉(zhuǎn)換”為影像的視覺呈現(xiàn)。絕大多數(shù)的電影,在呈現(xiàn)圖像時,一般不會給出大段的語言作為說明,因?yàn)橛跋癖旧砭褪菄H通行的最佳“語言”。而這也是電影這種影像媒介的魅力所在,它可以跨越國別和民族語言的藩籬,用影像的力量感染觀眾。
三、符碼的變化背后:從“恐同”到“真愛”的重心位移
無論是敘事的調(diào)整,還是全新的視覺建構(gòu)和新增配樂的“組合”“融合”以及“轉(zhuǎn)換”,都反映了《斷背山》在從小說到電影“藝格符換”過程中的種種變化,而這些符碼的變化,又指向了什么樣的意義表達(dá)呢?
普魯克斯說,創(chuàng)作《斷背山》的靈感,源于其在懷俄明一處酒吧的經(jīng)歷。那個夜晚,普魯克斯在酒吧里留意到一位上了年紀(jì)的老牛仔,“他表情里的某種東西,某種悲傷的渴望,讓我懷疑他是不是鄉(xiāng)村同性戀者” 。不過,普魯克斯強(qiáng)調(diào),她完全憑想象力來完成對兩個沒受過多少教育、風(fēng)格粗獷的年輕牛仔的刻畫。小說中的主人公,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人沒有任何關(guān)系。她稱,長年來在美國農(nóng)村地區(qū)尤其是西部地區(qū),她觀察到美國鄉(xiāng)村人對同性戀者極端憎惡,這促使她寫下了這個故事。[9]她著重申明:“《斷背山》沒有牽涉到任何一樁具體的事件,而是基于多年來,我在這里或那里聽到或看到的眾多小事的拼貼組合。”[10]
而作家在訪談中提到的“眾多小事”,卻包孕在沉重的社會語境之中。作為一個主要由清教徒建立起來的基督教國家,因?yàn)樽诮毯驼卧颍绹跉v史上對同性戀并不寬容,對于同性戀者的歧視、毆打甚至仇恨殺戮屢屢見諸報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同性戀一直被認(rèn)定為一項(xiàng)罪名,同性戀活動只能暗藏于地下。1951年,同性戀活動組織馬特辛協(xié)會(Mattachine Society)在洛杉磯成立,因?yàn)槠浞欠ㄐ裕蓡T之間只能用暗號聯(lián)絡(luò),防止被警察抓捕。1966年在紐約裘力斯酒吧,在知道幾位顧客是馬特辛協(xié)會成員后,酒保倒掉了他們的酒,拒絕為他們服務(wù)。1978年11月27日,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選任政府職位的公開同性戀傾向的政治人物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其主要的職責(zé)是負(fù)責(zé)推動同性戀權(quán)益的法令)被射殺身亡,其同性戀身份與此次刺殺不無關(guān)系。20世紀(jì)末,21歲的大學(xué)生同性戀者馬修·謝巴德(Matthew Shepard)在懷俄明州的拉萊米市郊被殘忍地毆打,最終因傷勢過重死亡。馬修的死引起全美同性戀和反同性戀兩大陣營的“對抗”。而《斷背山》故事設(shè)定的地點(diǎn)——美國的懷俄明州在歷史上有憎惡同性戀的傳統(tǒng),并且是全美大齡單身男性自殺率最高的地方;小說與電影也都提及了主人公恩尼斯幼年目睹同性戀農(nóng)場主被恐同者凌虐致死的心理陰影。
故事內(nèi)外的創(chuàng)痛記憶總是令人難以釋懷。囿于悲傷的故事結(jié)局,在電影上映10年后,不少讀者仍然致信作者,要求重寫故事結(jié)局。普魯克斯在接受一次采訪時表示,“大家似乎不了解,這個故事不是在講杰克和恩尼斯(兩位男主角名字)這二個人,而是在講‘恐同癥’(同性戀恐懼癥),以及他們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一種不同的心態(tài)和不同的道德觀念……”[11]
而在李安執(zhí)導(dǎo)的電影《斷背山》中,其敘述與探討的重心悄然移至了“真愛”。而“真愛”問題也恰恰是米歇爾所提的“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角力場域內(nèi)性別、種族和階級、政治恐懼以及真善美問題中的重要內(nèi)容。電影上映時的多款宣傳海報上,宣傳標(biāo)語“Love is a force of nature”(愛是與生俱來的力量。)標(biāo)識顯著,一以貫之。李安本人也秉持“真愛無關(guān)性別”的觀點(diǎn),執(zhí)導(dǎo)電影的拍攝以及主打后期的宣傳。
李安曾說:“《斷背山》雖然是個悲劇,但它給我很多愛的感覺,給這個世界很多愛的感覺。我本來都要退休了,它等于把我救回來了。”[12]影片《斷背山》將同性關(guān)系的糾結(jié)描述得淋漓盡致,但是李安則認(rèn)為這部電影不是為同性戀權(quán)利呼喊,也不是對同性戀保守的觀察;他自己是一個電影藝術(shù)家,更關(guān)注的是愛情主題。由此可見,李安看重的,恰恰是一種可以大力宣揚(yáng)并萬無一失的普世價值理念:愛是可以超越文化差異的,當(dāng)愛降臨時異性之愛與同性之愛是毫無差別的。[13]李安旨在忽略性別表象,感受愛本質(zhì)上的真摯與純凈,喚醒世俗對愛的寬容,這才是其表達(dá)的初衷。[14]
結(jié) 語
從《斷背山》這一從小說到電影的典型現(xiàn)代“藝格符換”示例中,李安導(dǎo)演頗為成功地完成了文藝符碼的轉(zhuǎn)換,正是這種成功的轉(zhuǎn)換,有力表達(dá)出藝術(shù)作品的現(xiàn)實(shí)叩擊與拷問,小說作者也對電影的藝術(shù)效果表示完全的認(rèn)同和贊賞。201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同性婚姻合法。筆者認(rèn)為,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離不開像《斷背山》這樣的作品所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力及觀念表達(dá)。
2008年美國音樂家瓦瑞能(Charles Wuorinen)與普魯克斯合作(前者作曲,后者改編劇本),經(jīng)過6年時間的準(zhǔn)備,2014年將小說搬上歌劇舞臺,在西班牙馬德里首演,獲得成功。由此可見,在當(dāng)代全球化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中,“藝格符換”作品的完成,不僅可以豐富同題文藝作品觀賞的層次,更可以借助于彼媒介不同于此媒介的差異性,體現(xiàn)出跨媒介跨文化的互補(bǔ)性優(yōu)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