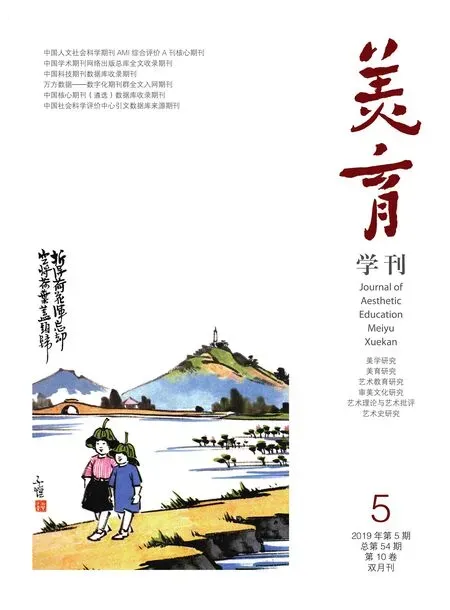復古何為
——傳統藝術中的復古現象及其現代意義
周 敏
(北京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1)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復古現象,可謂由來已久。早至上古殷商,經漢唐,到宋元明清,言必稱古的現象非常常見,尤其唐宋轉型以降,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主流的認同基礎。(1)如“行先王之教”“奉先王之制”“祖宗圣訓”“祖宗之法”等理念,在古代歷史上廣泛存在,并被統治者引為法令規矩,裁斷準則,亦可說是復古觀念在政治文化中的體現。可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1頁。每一民族的藝術之花必定開自于本民族文化之土壤,中國傳統藝術中的復古現象亦是極為常見,巫鴻曾敏銳地指出:“復古是中國藝術中一個源遠流長的機制,從三代的禮制藝術到晚近的繪畫書法不絕如縷。”[1]Ⅳ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書則魏晉,畫則宋元,既是學統,也是道統。古典生活中的人們似乎所有的努力都是在繼承前人的傳統,解釋古人的遺訓,恢復往昔的理想。那么復古與創新,古人與今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斷裂如何理解?“復古”究竟要復到多古才算古?“古”的又何以就是好的?本文從時間觀念的角度對古代與現代的本質不同展開討論,揭示古代“復古”與現代“創新”觀念的沖突所在。首先,我們有必要對傳統藝術中的復古概念及復古現象進行梳理。
一、何為復古
《說文解字》里說:“復,行故道也。”段玉裁補充說:“故者,凡事之所以然,而所以然者皆備于古,故曰古,故也。”可見復古即復其故,也就是恢復其本來的樣子。復古的前提在于有所中斷,正在于失落了某種東西,才需要去恢復。所以任何“復古”的嘗試都必須跨越年代和心理上的距離來重新親近“古”的價值與品味,并將己身融入其中。[1]4李零也曾敏銳地指出復古實踐透出一種“自覺”意識,其特征在于“失而復得、斷而復續”。(2)“失、斷”是排除從前人直接因襲下來的情況;“得、續”則是排除與古人的全然無關聯,其中一定有一個脫離現代的時空距離,又保持了現在與過去的某種聯系。他強調中斷后的再生和復興,模仿、依托、再現和重構是“復古藝術”的總特征。我們認為這一強調對復古藝術的“自覺”意識有特別的觀照。參見李零:《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9頁。那么是什么樣的宗教、社會意識形態系統為往后的“復古”探索提供了一個基礎呢?巫鴻認為是祖先祭祀的信仰,祖先崇拜不但為“復古”實踐提供了直接的場合(祭祀禮儀),而且也在普遍意義上規定了中國文化中“現在”和“過去”之間的關系。[1]4
《禮記·祭義》中說:“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文錦釋之曰:君子反思遠古,追懷本始,不忘自己生命的由來。[2]考古發現從西周晚期到戰國時期,大量的復古青銅禮器是專為葬禮特制的“明器”。[1]10其動機應當是來自“返古復始”的觀念,以此岸世界想象、推及彼岸也有祖先祭祀的需要,制作的復古隨葬器物則被賦予了具體的功能性價值,在極為重視祭祀禮儀的背景下,類似于周朝青銅仿商朝,春秋陶器仿上古陶器形式等禮器的制作可以說是最早的復古實踐活動。
此外,復古觀念也深入到后來的文人畫藝術創作及品評當中,文人畫論中的復古現象俯首即是。“以李嘗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米芾《畫史》);“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趙孟頫);“豈有舍古法而獨創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他們紛紛以古為尚,以得古意自屬。然而應該注意的是文人所謂的“古意”并非一個固定的樣式類型,而是一種可以自由闡釋的理想概念。在前人闡釋學書路徑的時候也常看到“學古貴能變通”“古而能化”之類的說法,表示他們并非照搬古人,學古之目的乃在“變化”,在于重開“我”所理想中的古代之淳厚風氣。這種復古乃是一種以復古而開新。
復古實踐還不僅局限于此,在古代社會的其他領域也能看到一種復古原則的貫徹。如在制度建設的層面,宋人崇尚的“祖宗之法”體現著士大夫群體基本的認識與共識,新舊各派對此都相當熱忱,共同參與著這種“塑造”的建構過程。(3)關于“祖宗之法”原則被建立起來和在制度實踐中具體落實之間的運作過程,鄧小南做過非常詳細的史學實證梳理,如她所說,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逐漸形塑的過程。士大夫們的熱忱和信念,深深根植于那個時代的傳統之中,影響著當時的行為、制度乃至社會觀念,并在此之中,體現出“祖宗之法”精神原則的存在。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14頁。新舊黨爭的雙方都可以引用“祖宗之法”的原則來攻擊對方,因為宋人所謂的“祖宗之法”并非一個事先就固定好的條目,各方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靈活解釋這個原則。本文認為這些亦是一種廣義的復古實踐活動。
二、復古現象的類型
前面提到復古藝術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其明顯的“自覺”意識,它表現出一種刻意脫離當下的意圖,當然,任何稱得上是藝術的作品都會具有某種“意圖性”,與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及資源相連,但仿古器物,都反映了對自身政治、社會及藝術目的的強烈的自我意識。這是任何復古設計中的必然成分,這一前提性設問對藝術史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1[16]由此,我們可以對歷史上的復古現象進行類型模式的分類,大致可分為三類:禮儀、收藏、借古開新。
“禮儀”模式下的復古制作,主要在國家政治層面,其意義重在確立政治權力繼承的合法性,如王莽的復古活動,一個克己復禮的儒生,以制作禮樂為重要方面,將漢代制度的設計推向理想極致。他以儒家正統自居,復周公之禮,廢漢武帝之禮,這對后世的禮制改革,包括唐禮和宋禮,在格局上和精神上都有很大影響。[3]63他根據《考工記》的文字描述而制作典型復古嘉量,以及根據古人留下的實物制作銅方斗、銅升等度量衡器,其制作之初是與禮制改革相配合使用的。后來宋徽宗大量制作政和、宣和禮器,以出土真器或金石著錄為參考對象,開宋以來復古風氣之源,這都和王莽的復古意義類似。
“收藏”模式下的復古活動主要在個人層面,意在凸顯擁有者的高雅身份,以區隔于其他低俗階層。關于對古物的好尚問題,柯律格有不少精彩論述,他對明代物質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敏銳地注意到往昔之物以及單憑其物理形態就能喚起往昔之感的物品,在古人的世界里占據了特殊的地位。他指出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士紳精英作者的文字,絕沒有涵蓋明代物品的所有類型,與那些面向低端市場的著述,不僅表述詞匯相異,而且有著完全不同的側重點,例如,居家手冊中通常稱物品為“時樣”,其意顯然為“時尚的”,而這個詞在文震亨的書中卻并未見到。[4]83可見,文人士紳階層對所謂“時樣”多取一種拒絕的姿態。柯氏運用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關于“趣味差異”對維系社會和文化階層所起作用的理論,非常巧妙地剖析晚明的社會結構。“對古物及其所包含的象征價值的擁有是對財富和名望的最佳體現。”[4]93柯氏犀利地指出收藏、好尚古物——這種看起來無功利的審美趣味背后的階級性,另一方面,也是好古者對自身高貴身份的彰顯。
在宋代之后,收藏模式下的復古現象出現了新的轉向,一種為了學術研究和藝術鑒賞的傾向開始突顯,文人學者的參與,直接推動了宋代金石學的發展,使古物研究成為歷史學的一個新分支,從而很大地刺激了人們仿造器物的嘗試。宋時出土殷周銅器日多,逐漸形成收藏、著錄和研究的高潮,出版了不少圖文資料。(4)李零在其書中列出了于史可考的八種主要吉金圖錄,可參見李零:《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79頁。這一轉向預示著一個重要趨勢——復古型器物開始超越禮儀的限制,進入一個新的語境:文人的書齋和其他空間。“復古”越來越多地成為文人的一種品味,甚至變成大眾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明清江南地區經濟富庶,文人好金石古物,事雅鑒收藏,蔚然成風,這既是一種高雅品位的表現,也是高貴身份的標識。文震亨《長物志》卷七器具篇:“今人見聞不廣,又習見時世所尚,遂至雅俗莫辨,更有專事絢麗,目不識古,軒窗幾案,毫無韻事。”對“古”的認識乃是雅俗之尺度,目不識古,即落俗了。再如清代金石考據背景下的文人們極好古物,陳介祺、吳大澂等皆有畫工為之描繪坐擁古器物的寫實圖像,以“與古為徒”自況,另外在金石全形拓上描繪折枝花卉的“博古圖”形式在晚清也是非常流行,其中都顯示出親近古物所呈現的高雅不俗之氣,我們將此歸為復古現象“收藏”模式的深化。
隨著收藏模式的深化發展,復古觀念同時也逐漸滲透到文人的藝術創作中,這就形成了第三種復古模式:借古開新。文人畫論中的復古現象歷來能看到很多,如前述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例。高居翰說,對前朝和當下都不滿意,元初士大夫畫家選擇了綜合復興古老傳統和創造嶄新風格的道路。[5]如趙孟頫之“復古”、激進如康有為者大倡崇碑抑帖之論,當然有很強烈的政治、文化上的動機,但從藝術本體上看也是對南宋院畫的糾正,對晚清帖學敗壞的反撥,重開一代風氣。趙孟頫所說“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看上去是批評別人水平不夠,實則不過是文人給自己營建的審美趣味壁壘,[3]101高居翰曾指出,“關于中國繪畫的傳統問題,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當某個中國畫家宣稱他師法古人時,你不必太信以為真——這種宣稱只是為了使他們的創作在觀眾眼里顯得名正言順而已”。[6]在“必也正名乎”的傳統語境中,名正言順是那么重要,即使在文人的藝術創作中,亦難脫此框架。
三、復古與創新
“借古開新”的問題在傳統藝術觀念中非常重要,其中具有極為豐富的哲學意味。古人復古,是否就意味著一味泥古、錙銖必較于前人具體瑣碎的細枝末節?當然不是,前面我們就說到,他們所謂的“古意”并非一個固定的樣式,而是一種可以自由闡釋的理想原型。用現代解釋學的說法來理解,這種復古也是一種視域融合——古人與今人的經驗融合,將己身融入其中,離不開自我意識的參與滲透。所以需要質疑的不是復古中有沒有“變”,而是這是怎樣的一種“變”,與現代人所理解的有何區別。
古人關于新變的論述常能見到。“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王羲之);“天之為道,生生相續,新新不停”(孔穎達);“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王夫之)。中國哲學的開端是“生生”,生生之謂易,易即變,變無重復故常之道,變就是新變,無新則無變,即生即新,即新即變,新變必然與過往相關聯。故有學者指出中國哲學和美學新變思想的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復中趨新,在連續性的變化中,主會通和合,而非西方文化主標新立異;二是即故即新,新雖與故相對,但新不脫離故,兩者構成極富魅力的張弛關系,若即若離,不即不離,如同太極的力道,連續往復,綿綿不絕,這種新不是外在表象的更替,而是心靈對生命的發現。(5)對此思想具體的闡述,詳見朱良志《中國美學十五講》第三講的“新變”一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62-70頁。
以上復古特點在現代傳統(6)在此有必要說明一個問題,本文所說的“現代”是指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所謂“現代性”也是從這一脈絡中產生的。對于中國自身有沒有產生“現代性”這一問題,學術界依然具有爭議。本文不欲對此過多展開,在此只選擇接受一種觀點作為論述的基礎,即認為中國自身并未發展出西方意義上的“現代性”,至20世紀初隨著西學東漸的沖擊,古代舊學的瓦解,“現代中國”才逐漸形成。換言之即,現代中國的“現代性”其實來自西方,故后文直接將中國古代時間觀念與西方現代時間觀念對比,乃是因為本文論述的基礎在于接受現代中國的時間觀念來自現代西方這一論斷。中則變得截然相反,現代傳統中的“新奇”“創新”則丟失了這個“古故”的維度,它要求切斷與故舊的連續,并視之為過時、落后,而以一種全新的、轉瞬即逝的鮮活姿態出現,它強調差異、分割、新奇、進化等等特性,這是與古代復古傳統反差極大的地方。現代繪畫一般而言開始于后印象派,印象派將畫室搬到大自然中,直接對景寫生,捕捉自然光線的瞬息變化,強調那種轉瞬即逝的鮮活感,后印象派則拋棄對外在客觀世界的描寫,轉而探索內在的抽象表現。現代藝術發展到20世紀,出現先鋒實驗的傾向,達達主義、立體主義、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等,形式及觀念上都非常前衛,以否定自身,新奇、獨創為藝術的生命。所以帕斯深刻地指出:現代性是一種爭議性的傳統,它驅逐當下的傳統,無論那是什么,但卻在一剎那之后又將其位置讓渡給隨之而來充當現代性的一個瞬間表現的又一個傳統,“現代性”從來不是自身,它始終是異類。[7]6后印象派以筆觸等形式語言表現主體內在情感,的確在一些方面和中國文人畫有某些相通之處,但絕對不能夸大這種相似,因為兩者處在不同的傳統背景中。方聞曾指出過其中的區別,他說在模擬形似階段終結之后,西方現代畫家于19世紀之后轉向了無休止的新實驗,而宋代以后的文人畫家則堅持古意,通過書法化抽象以復興古代風格。(7)方聞認為中國模擬形式的終結論由蘇軾提出:“君子之于學,百工之于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書至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西方則由漢斯·貝爾廷(Hans Belting)和亞瑟·丹托(Arthur Danto)提出。蘇軾的結論是:一切可能的風格都已盡善盡美了,如要復興藝術,必須回返到早期大師的古代語匯。所以我們在宋代以后中國藝術見到的循環不已的變遷與歷史性復興。而在西方藝術中卻見到無休止的實驗。詳見方聞:《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255-257頁。
為了更好地說清兩個傳統關于“變”的不同點,筆者以為古代傳統更準確地說應該是“通變”,而現代傳統則可以稱為“創新”或“新變”,它更強調變中之新的異質性。劉勰《文心雕龍·通變》曰:
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茜;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8]550
將此“通變”簡單理解為繼承與創新的辯證關系是時下頗為流行的說法,祖寶泉對此即有批評,并指出劉氏的“通變”論實乃“會通”“適變”論,以此觀點解釋《通變》全文,通而無礙。[8]564“會通”者,“參古”又“望今”,指融匯古今而貫通之;“適變”者,適應時勢需要而有錯綜變化。這意在強調古今之間的連續、同一性,與現代意義上創新、新變論之斷裂、異質性的差異不可不辨。
四、復古的現代意義
古人以復古方式求通變的意義何在?或者說為何一定要通過復古來求變?而現代卻為何恰恰相反,要以中斷、否定過去的連續來求變?要講清楚這個問題,本文認為需要涉及古代和現代兩種不同的時間觀念。
《周易》是中國古代宇宙觀的總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六十四卦,以此六十四卦推衍復雜的宇宙世界。這一體系本身是一個完美不變的模型,所有的變皆在這個模型內部被模仿,所謂“周流六虛,唯變所適”。這一體系前后排列又有一定的內在邏輯,《序卦》就是對這種邏輯的解說,當整個體系完成一遍后將又重新開始。這里體現了古代宇宙觀的兩個特點:一是對超越變化的把握,所謂“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周易·系辭上》),以把握變化不測為神明;一是對超越時間的把握,因為循環時間本質上是對時間不可逆的直線流動的否定、超越,其實是一種無時間的永恒時間。《周易》的“剝卦”之后接“復卦”,乃取群陰剝盡陽氣后,一陽來復起于地下之象,復卦辭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非常生動地揭示出古人的循環時間觀。
古人對于時間的流逝所隱含的難以預測的變化是恐懼的,其逃脫變化的方式之一是循環重生,以此將自身從歷史的變化中拯救,然而重生帶來的只不過是一個暫時的喘息而已,隨之又被拋入另一個開始。歷史的展開是原初時間的貶值,一個緩慢的,無可阻擋的,以死亡為終結的傾頹過程。[7]18原初時間的意象一定是在“過去”——不是最近的過去,而是一個超乎所有過去的過去,那“過去”可被稱為“開端”。何為“開端”?對此海德格爾在其《藝術作品的本源》中有精辟論斷:
真正的開端絕不具有原始之物的草創特性。原始之物總是無將來的,因為它沒有贈予著和建基著的跳躍和領先。……開端總是包含著陰森驚人之物亦即與親切之物的爭執的未曾展開的全部豐富性。[9]
“開端”并非歷史進步論語境下的原始草創、落后荒蠻,其中包含著有待展開的全部豐富性,那是藝術作品的意義(價值、真理)得以一躍而出的源泉。這個過去的“開端”永遠在場,它充當一個模仿的原型,定期在儀典中再現而保護著社會免于變化。這種“開端”是一個亙古不變的時間,且不是發生一次,而是一直在發生的當下。它既逃脫了意外也逃脫了偶然,盡管它是時間,然而也是對時間的否定,以此化解了過去和現在之間因變化而產生的矛盾和裂痕,也正是壓制了差別,從而確保了社會常規性和自我同一性的獲勝。[7]16中國古代社會的“三代理想”“致君堯舜禹”“西周之于孔子”“祖宗之法”等都充當了作為“開端”的時間原型,這些原型無一例外都是“復古”的。
但是現代與古代的思維方式突兀地決裂了,說“突兀”并非意在現代傳統毫無繼承而憑空生出,乃是側重在其時間觀念的一種突破。“現代”是西方希伯來猶太教(上帝和啟示)和古希臘哲學(存在和理性)兩大文明之間矛盾無可消解的結果。這兩者之間的斗爭最終是以神性被驅逐——“袪魅”為代價,理性獲勝,所以上帝死了。現代時間繼承了基督教時間的直線不可逆特點,但是否定了基督教的時間有限性——當全部時間用盡接受“大審判”之后則是永恒的當下。現代打開了無限未來的大門,無限且不可逆時間觀的確立也意味著拯救的不可能,因此上帝必須死。從古希臘繼承而來的理性則傾向于從自身中分離出去,每當它反省自身,它便分為兩半,這是一種批判理性。所以帕斯指出,“現代傳統”這一短語意味著不止一個邏輯和語言的矛盾:它表達了我們(現代)文明的戲劇性狀況,它不是在過去或是某些萬古不移的原理之中,而是在變化之中尋找自身的基礎。[7]14以變化不居為基礎,即以不可測的深淵之虛無為奠基,這就是海德格爾所謂的“淵基(Abgrund)”,也是我們所謂的“突兀地決裂”之所在。
在此,與古代不同的是現代文明第一次肯定并贊揚變化本身,時間(歷史)才是我們通往完美的必經途徑,人的所有活動的意義也發生轉向,不再具有宗教性的意義,其意義首先是歷史的和社會的。所謂完美,在現代被引入了時間維度,現代社會的時間(完美)原型必定指向未來——這個和差異、分割、異質、新奇、進化、未知、變化等幾乎同義的詞,它尚未存在并且永遠將來。對于現代的我們,時間是變化的載體,對于古人則是壓制變化的媒介。古人的過去不只是時間的一個范疇,還是一個超越時間的現實。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再來理解文人畫中“高古”的價值就會容易很多。朱良志在解讀陳洪綬的作品時提出一對范疇——超越和還原:
就超越而言,高古境界旨在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有限性,將人的精神從窘迫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就還原而言,現實的、當下的、欲望的世界,包含著太多的矯飾、虛偽,太多與人的真性相違背的東西,要在無限的高古世界中,還原人質樸、原初的精神,讓生命的真性自在彰顯。[10]
超越乃是從現實的變化沖突中解脫出來;還原則是恢復到原初開端的境域——無時間的永恒之中,這是古人所追求的完美境界。本文所謂的“復古”不可簡單理解為歷代復古思潮的以古律今,或者以古代今,這只是復古觀念支配下所呈現的表象,復古之本質恰恰是無古無今,通過此在和往古的轉換而超越時間,是一種無時間的時間,它體現的是中國藝術家對永恒感的思考。[11]
古人通過復古而求變,其內在意義乃是求與古人心靈會通,真正的古意即是兩顆古今的心靈超越時空的妙相契悟,所謂“一朝風月、萬古長空”,古人以此獲得一種連續、同一性的確認,并從現實的變動窘迫中解脫。而現代人通過未來求新變,則已經失去了這種頗有宗教性意味的救贖,理性批判不是為了某種真理,它就是真理本身。時間原型的不同決定了古人與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必然如此,對完美范式的理解也截然相反。
五、余論
復古在現代社會的不合時宜,讓現代人對古人的復古觀念抱有一種保守、落后的刻板印象。即便時尚界將古代的某些樣式作為復古元素流行一季,這種方式依然是現代的,它利用具有時間距離的陌生化樣式,制造出新奇的獨特感。本文著力于闡釋“復古”的價值內涵并非意在一種鄉愿式的懷古或者主張回到古代社會,而是試圖激活傳統文化藝術中非常重要的“復古”觀念,將之帶到現代語境中,讓它重新獲得生長力。
“現代”打開了未來之門,這未來盡管是“完美”的倉庫,卻既不是安身之所也不是盡頭;相反,它是一個不斷持續的開始,一場永遠向前的運動,未來之門打開的既是天堂也是地獄:天堂,因為它是欲望的國度;地獄,因為它是不滿足的家園。未來以最痛切的方式呈現出構成現代性的矛盾。[7]43“五四”以來,現代西方全面征服古老的中國,近一百年過去了,深受現代西方影響的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現代人”,但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注定成了異類、孤獨的。我們忘卻了自己的傳統,又終究是一個西方傳統的“他者”,徘徊、游離于兩者之間的現代中國有必要重新探索屬于自己的現代之路,開出屬于自己的“中國現代性”,一種“中國現代性”的可能,必須同時回應“現代性”(即西方現代性)和激活中國古代傳統資源,從中國自己的古代傳統中汲取養分。
“復古”之于古典生活背景下的人們,猶如空氣,“人心古樸”是說風俗淳厚,“人心不古”幾乎就是時風敗壞的衰世之嘆,“再使風俗淳”的理想狀態乃是“致君堯舜禹”恢復三代之“空氣”。在一味求新求奇求異的現代、后現代語境下,筆者激活傳統藝術中的“復古”概念,意在賦予它一種現代價值,“復古”不只是一個概念,也是一種方法,對“過去”的重新激活,但目標是指向“未來”的,這一過程始終發生在“當下、此刻”,因此,“復古”不意味著對“當下”的否定,它恰恰是對“當下”的肯定。在這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的開放世界圖景中,復古何為?或許就是為“真性”的再生備好一個居留之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