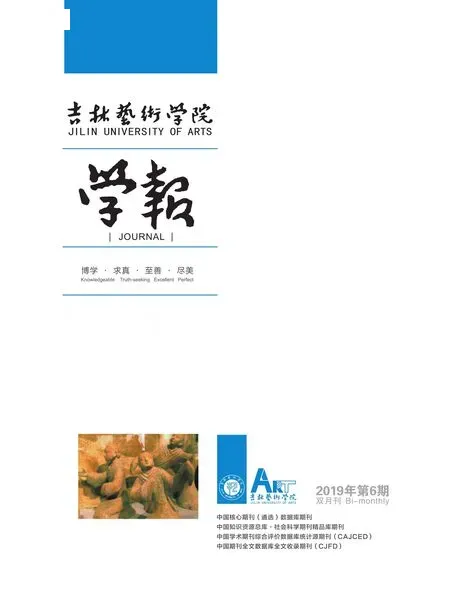《大神布朗》的假面游戲與倫理身份的危機
黃暉 黃夏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 武漢,430079)
《大神布朗》(1925)是美國戲劇家尤金·奧尼爾創作的一部四幕假面劇,也是他在戲劇革新方面較為成功的一次實驗。該劇當年在紐約連續上演八個月,而且幾乎是在百老匯劇場內,曾獲得評論家和普通觀眾的一致好評。[1]285相比于《榆樹下的欲望》《天邊外》等知名戲劇,目前國內對于《大神布朗》的關注甚少,已有文章基本集中于研究面具的使用技巧,并未對其中涉及的倫理問題展開深入討論。《大神布朗》看似只是講述了一個關于三角戀愛的情感故事,實際上該劇涉及不少殺人奪妻、策劃假死等挑戰倫理規范的情節,證明其內核是一個倫理悲劇。《大神布朗》最大的創新之處在于塑造了一個信奉假面社交的倫理空間,劇中主要人物利用面具掩蓋真實的自我,不惜在朋友乃至愛人面前上演一場偽裝游戲。由此,本文運用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以主人公的倫理身份為切入點,分析其身份焦慮和身份迷失的具體表征,進而探討身份危機的現實意義及其倫理意蘊。
一、假面社交與身份焦慮
作為一部頗具實驗色彩的假面劇,奧尼爾的《大神布朗》響應了20世紀的戲劇復興潮流。事實上,在戲劇表演中使用假面并非是奧尼爾首創,而是一種古老的表現技法,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祭祀酒神狄奧尼索斯的慶典活動。據學者研究,隨著時代的變遷,面具在文學作品中亦經歷了“從‘原型’到‘變形’,從‘面目缺失’到尋找‘真我’或‘本我’”的演變,其文化含義、符號功能等方面皆發生了根本的變化。[2]在奧尼爾看來,假面劇可以塑造更為真實的人物,是“一種靈魂的戲劇和一種被面具所控制并構成他們命運的‘自由意志者’的歷險。”[1]284-285在《大神布朗》中,奧尼爾對面具的使用是有選擇性的,主要人物迪昂、瑪格麗特和西比爾從一出場就有專屬自己的面具,而前期的布朗并未佩戴。為了掩飾真實的自我,他們三人不惜戴上面具,在朋友乃至愛人面前表演著另一個人,為布朗上演一場偽裝游戲。身處這樣一個假面社交的倫理空間,以真實面目示人的布朗不免產生了嚴重的身份焦慮。其中,兼具朋友和情敵身份的迪昂對布朗的影響無疑是最突出的。
聶珍釗教授認為,“在文學文本中,所有倫理問題的產生往往都同倫理身份相關。”[3]263布朗的身份焦慮正是因其倫理身份而起的。倫理身份的種類多樣,包括職業身份或以倫理關系為基礎的身份。就其職業身份而言,作為一名建設師和商人,布朗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人士,擁有著許多令人艷羨的資本。但事實上,這一職業選擇是父母為兒子做的人生規劃,并非出于布朗自身的意愿或能力,這就給布朗的職業焦慮埋下了禍根。在日后的職業實踐中,盡管接受了良好的大學教育,但布朗卻經常很難交出令人滿意的建筑設計。對比迪昂,自打兒時起便表現出超強的創作天賦,首先就讓布朗察覺到自身的資質平庸。而當迪昂戴上了象征著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潘神形象,實現了從人到神的身份想象,擺脫了人性的孱弱,更是給布朗帶來了莫大的壓力,加劇其職業焦慮。據此,布朗利用商人的優勢,將經濟窘迫的迪昂收歸到自己的公司,表面上為了接濟朋友,實際上是為了緩解自身的職業焦慮,趁機將迪昂的設計創意據為己有。
在倫理關系方面,布朗原本成長于一個衣食無憂、父母恩愛的幸福家庭,后因為向瑪格麗特求婚失敗和父母的逝世,他在情感上成了無人依靠的“孤兒”。一方面,人到中年,無妻無子的“單身漢”身份使得布朗對重建家庭的渴望與日俱增,陷入嚴重的婚戀焦慮。另一方面,看似“一事無成”的迪昂,不僅借助藝術家的面具獲得了瑪格麗特的青睞,完成了布朗最渴望的倫理身份的轉變——成為瑪格麗特的丈夫及其孩子的父親,甚至還能越過婚姻獲得西比爾的情感慰藉。迪昂在情場上的無往不利使布朗心生嫉妒,其婚戀焦慮指數隨之急劇上升。從兩個女性角色來看,瑪格麗特和西比爾利用面具分別表演著天使和魔鬼,對布朗則構成了截然相反的性吸引力。從少女到少婦,瑪格麗特從未向布朗展示其真實面目,每次相見皆以面具為偽裝,一直在布朗面前表演著“賢妻良母”的理想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布朗將瑪格麗特視為情感伴侶的最佳人選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同于瑪格麗特,西比爾戴著丑陋的面具出場,即“涂胭脂、抹口紅、畫著黑眼圈的狠心的妓女的面貌”[4]129,留給布朗則是一個誘人墮落的魔女形象。在長期苦戀瑪格麗特而不得回應的情況下,布朗退而求其次,選擇以金錢換取妓女西比爾的陪伴,但這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其婚戀焦慮。因為不管是深愛的瑪格麗特,還是情人西比爾,她們皆表示心向迪昂。在這兩個三角戀愛的倫理結構中,布朗始終處于下位,他所擁有的經濟資本,與才華橫溢的迪昂相比顯得毫無優勢。
隨著主要人物的出場,面具在劇中所起的作用逐漸具象化。面具可以為人物提供了另一種與自我相悖的身份,是擺脫人性之弱點的一種有力偽裝或反抗社會的一種自衛機制。譬如迪昂,安東尼的姓氏所代表的“自我虐待、否定生活的基督教精神”。[1]335因為兒時遭遇布朗的欺凌,迪昂對世間萬物乃至自身存在懷有強烈的質疑和恐懼,并開始用面具來偽裝和保護自己。但透過面具,迪昂給布朗呈現的是一個才華橫溢、美滿幸福的假面形象,掩蓋了自身的貧窮、孱弱、敏感。可以說,在假面社交的倫理空間內,人和人之間的交往隔著一張面具,相互偽裝,相互隱瞞,面具前后的人格形象發生了錯位。榮格在《心理類型學》中提出一個人格面具的概念,即“人格面具是由于適應或必要的便利的原因而進入存在的一種功能情結。”[5]面對自身存在的問題,迪昂等三人選擇戴上面具,將真實的自我封閉起來,過著一種身份表演的“非我”生活。對于以真實面目示人的布朗而言,他們三人尤其是迪昂夫婦通過面具塑造超越自我的理想形象,實則構成了一種社交泡沫,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和虛幻性。受其影響,布朗產生了嚴重的身份焦慮,其倫理意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無形之中已被卷進了身份表演的泥沼里。
二、雙重人生與身份迷失
出于緩解自身焦慮的目的,布朗將自我放逐在假面游戲之中,不曾想卻因此加劇自身的身份危機。前期的布朗以真實面目示人,并未在社交泡沫中迷失自我,但在殺死迪昂后,布朗戴上他的面具,主動以身份表演作為新的生存策略。為了徹底占有迪昂的身份,布朗不惜策劃一場“自殺”,徹底掉進了他者身份的陷阱。在雙重人生的生存壓力之下,布朗在自我與他者身份之間來回切換,深陷身份迷失的倫理困境而無法自拔。
布朗與迪昂的身份置換是劇中最精彩的情節。迪昂等三人只是利用面具來改變自我的形象,實質是為滿足一種身份想象,而布朗的身份表演卻是頂替另外一個實際存在的個體,這是現代法治的倫理規范所不容許的。在假面社交的倫理空間內,“偷龍換鳳”的操作實踐顯得十分簡單:只要戴上迪昂的面具,布朗便可以完成從自我到他者的身份置換。而當布朗自以為能實現事業與愛情兩得意之時,現實卻給他當頭一棒。他非但沒有解決自身的身份焦慮,反而迷失在雙重人生的生存困境之中,被迫過上了自我分裂的生活。“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規范聯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變就容易導致倫理混亂,引起沖突。”[3]257倫理身份的轉變對布朗構成了新的道德約束。首先,布朗戴著迪昂的面具,如愿獲得瑪格麗特的愛情。作為一家之主,布朗必須承擔迪昂的倫理責任,接受瑪格麗特溫柔的“規訓”,真正成為一名勤懇賺錢養家、戒掉酗酒惡習的好丈夫、好父親。而為布朗所不知的是,迪昂和瑪格麗特的結合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瑪格麗特自始至終迷戀的只是迪昂的面具,而非迪昂的真實形態。為了滿足瑪格麗特的期待,迪昂戴上潘神面具扮演著完美丈夫,其真實自我早已被面具摧殘得不成人形,就連面具自身也染上了梅菲斯特的魔性。在此情況下,布朗不僅需要扮演迪昂,更重要的是,他必須以謊言彌合謊言,去成就一個不曾存在卻極具魅力的迪昂。
與此同時,為了在世人面前維持其成功者的形象,布朗戴上了專屬自己的面具,這是極其無奈的選擇。由于受到魔鬼面具的反噬,布朗原來的面孔變得既憔悴又扭曲,成為最不受人待見的第三張“面具”。正如奧尼爾所說,“他以為他獲得了創造性生活的能力,而事實上他偷到的只是因完全失望而變成自我毀滅的那種創造力。這個喜愛嘲諷懷疑的惡魔使他很快喪命。”[1]336更有甚者,受害者與殺人犯身份之間的相互沖突,使得布朗長期處于精神的“修羅場”,既享受著逍遙法外的自由,同時也承受著自我譴責的折磨。定期以迪昂的面具活動,布朗是可以完美遮蔽其殺人犯的身份。但布朗十分清醒地知道——在假面社交的倫理空間里,“靈魂”不死是可以實現的。肉身之死并不代表生命的徹底終結,他無時無刻不在感受著迪昂面具帶來的致命性威脅。猶如其呼:“你死了,威廉·布朗。死后連復活的希望都沒有!是你埋在花園里的迪昂把你給殺了,而不是你殺了他!”[4]158當布朗摘下迪昂的面具,再次試圖以真實面目告白之時,換來的卻依舊是瑪格麗特冷冰冰的拒絕。這一身份實驗的失敗,實際構成了壓倒布朗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催生他的“自殺”計劃:抹除自我的存在,并將全部的“遺產”留給迪昂。
回到人物自身,一個是擁有矚目的商業財富,一個是擁有出眾的創作才華,布朗與迪昂在事業和藝術方面各有其成就。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及了兩種精神:一為沉湎于物質外觀的幸福幻覺的日神精神,二為迷醉于個體內心的痛苦本質的酒神精神。[6]在某種意義上,這兩種精神可以分別對應布朗和迪昂的人生選擇。然而,在看似迥然不同的兩項選擇之后,實際有著極其相似的人生境遇,皆因其欲求不得而痛不欲生——事業有成的布朗苦于求愛失敗,而家庭美滿的迪昂則毫無出頭之日。就此而言,他們的關系與其說形成了一組絕佳的對比,不如說是一種吊詭的鏡像。如同福柯所言,“從鏡子的角度,我發現了我對于我所在之處的缺席,因為我在那兒看到我自己。”[7]。迪昂的存在,真切地折射出布朗最熱烈的內心渴望和最現實的人生缺憾。正因為如此,布朗才會無法抗拒迪昂身份的誘惑,企圖遁入他者的人生去尋求解脫,從而走向了抹殺自我身份的極端。殊不知,這出自導自演的“死亡”使“迪昂”成為萬人通緝的殺人犯,布朗被迫拾回自我身份。從自我到他者,又從他者返回自我,布朗在雙重人生之間不斷徘徊,卻始終無法獲得相對穩定的身份認同,最終喪失了對倫理身份的正確判斷。
從認同假面游戲到將其付諸實踐,布朗對自我身份的認知出現嚴重混亂。在殺人之后,布朗以迪昂的身份活動,試圖掩蓋自身的罪行,甚至不惜策劃一場“自殺”來成全自己。而令其始料未及的是,在迪昂婚姻美滿的表象之下,潛藏著如此之多的不為人知的傷痛與謊言。縱使布朗借助面具得到理想的愛情,他同樣沒有能力扭轉迪昂人生的悲劇性。倫理身份的置換并不只是倫理關系的簡單變動,還牽扯著身份背后的倫理責任與生存壓力轉移。從這個意義上說,布朗在自我與他者身份之間來回切換,深陷身份迷失的倫理困境而無法自拔,其實是無法平衡雙重人生的生存壓力。換言之,為了取代他者的自我“犧牲”,終究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三、“斯芬克斯之謎”的現代變奏
聯系劇本創作的歷史語境可知,《大神布朗》所塑造的假面社交的倫理空間并非奧尼爾的天馬行空,而是基于美國20世紀20年代普遍繁榮卻暗藏危機的時代語境的合理想象。在此背景下,主人公布朗由假面游戲引起的一系列身份危機,具體指涉的是現代社會的倫理問題。從這個角度上講,布朗的身份危機實際是“斯芬克斯之謎”的現代變奏,體現了現代人對于“我是誰”的追問與思索,具有深刻的倫理警示意義。
在解讀和闡釋文學作品時,文學倫理學批評要求研究者回到特定的文學空間,即“進入文學的歷史現場,而不是遠離歷史現場的假自治環境”。[8]以此推論,奧尼爾筆下信奉假面社交的倫理空間,其實是20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在文學領域的一個變形。傳統史學界將這一時期定義為咆哮的二十年代,據美國學者重估,認為普遍繁榮的美國形象繞過了最貧窮的社會階層。這種過度宣傳在很大程度上歸咎于電影和電視媒體,因為它們往往將富裕、魅力四射描述為美國形象的規范。[9]28在此話語體系下,當時社會存在的貧富分化嚴重等不穩定因素是避而不談的。通過奧尼爾的戲劇創作,今日的我們大體可以窺測其中一些蛛絲馬跡,如破產落魄的迪昂、任人擺弄的西比爾。
在眾多人物中,“相貌漂亮、衣著講究、辦事能干”[4]124的布朗身份最具有典型的美國性。布朗所從事的建筑行業是20年代經濟繁榮的標志之一,其事務所承接的業務主要是反映美國現代氣派的市政廳、州議會大廈、商業住宅等建筑。研究顯示,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建造了570萬套新式住房,現代建筑大師弗蘭克·勞埃德·萊特的草原式住宅尤為風靡。[9]38正是建筑行業這潛在的利益空間,導致了布朗的事業野心膨脹。換言之,布朗的職業焦慮與其說是因迪昂而起,不如說是由于無法應對日益龐大的建筑市場。在故事結尾,布朗撕毀了設計生涯中最成功的議會大廈作品,不僅是拒絕“迪昂”成為下一個被利欲熏心的自己,更是對建筑行業之商業化大勢的強勢反擊。巧合的是,在《大神布朗》開展巡演后不久,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爆發了房地產泡沫,首先戳破了咆哮年代的瑰麗美夢,在幾年后,另有一場更為浩大的經濟危機席卷全美。由此可見,奧尼爾以布朗的悲劇性結局,預見性地宣告了美國黃金二十年代的終結。
從更深層的倫理意蘊來看,布朗的身份危機反映出人類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在現代社會的較量與博弈。聶珍釗教授指出,從倫理意義而言,人類是一種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斯芬克斯因子是由人性因子和獸性因子構成的,并通過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發揮作用。”[10]對于布朗而言,迫切渴望成功的物欲和為瑪格麗特執著的愛欲構成了人生中最難攻克的兩重關卡。為了解決自我的身份危機,布朗曾一度受欲望和自由意志的蠱惑而放棄了自我的底線。正如現代社會的浮士德,布朗以出賣靈魂的代價與魔鬼共舞,徹底掉進了倫理犯罪的深淵。他利用商人的經濟優勢強取豪奪,不僅將迪昂的設計創意及其情婦西比爾占為己有,更是不惜實施殺人奪妻、“自殺”計劃等倫理犯罪來滿足自我的欲望。
布朗最后的死亡是基于理性做出的倫理選擇。面對警察的追殺,布朗最后一次戴上迪昂的面具,選擇接受倫理犯罪的懲罰。“奧尼爾意在表明,渴望同時戴上成功者和藝術者的面具,是人類自我斗爭的一部分。”[11]在迪昂身份的誘惑面前,布朗曾經試圖用面具扮演一個事業和愛情兩得意的人生贏家,不曾想就此陷入身份危機的僵局。在最后的理性懺悔階段,布朗赤裸上身匍匐在地,祈求上帝的寬恕,結果靠自己參透了身份表演虛無性的實質。假面游戲所能實現的只是一種想象性建構,并非實質性的轉變。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中指出:“表演者可能完全為自己的行動所欺騙;他能真誠地相信,他所表演的現實印象就是真正的現實。”[12]當日常生活完全變成假面游戲,表演他者身份成為一種常態,主體對于自我身份的認知便會出現錯亂。甚至可以說,假面游戲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把戲,不過為布朗提供一個逃避現實的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假面社交的倫理空間里,同一樁死亡事件實際發酵出不同的故事版本。面對布朗的死亡,事務所委員們悼念的是面具形態的布朗,而瑪格麗特眼中只有面具形態的迪昂。唯有西比爾看到了布朗真實狀態的死亡,并最終肯定了他作為“人”的姿態和尊嚴。據奧尼爾所說,西比爾既是“古希臘大地母神茜貝勒的化身”,同時也是“注定會受到隔離”的棄子。[2]336由于身處社會底層,西比爾很早以前便洞穿了假面社交的游戲規則,曾試圖以其覺醒者的身份將迪昂從泥沼中拉出來。反觀瑪格麗特,一直抗拒赤裸的真相,不知不覺中變成加劇迪昂和布朗走向幻滅的推手。據此,瑪格麗特和西比爾之于布朗的角色定位已經發生了明顯的反轉。“瑪格麗特開始時是光明女神,實際代表著更具破壞性的魔女;而西比爾最初是傳統意義的黑暗女神,卻成為布朗和迪昂的最終救贖。”[13]在布朗死后,瑪格麗特同樣沒有覺醒,而是選擇與迪昂面具度過余生,永遠沉迷在幻象與假面之中。
廖可兌先生在《論〈大神布朗〉》中認為奧尼爾批判的是布朗所代表的商人形象,其特征是“只知道追求物質財富,沒有靈魂……都是物質富有但精神空虛的人。”[14]在筆者看來,布朗的身份危機不僅指涉富裕的資產階級,而應與現代社會的個體皆有關聯,隱射的是整個現代社會的倫理生態問題。布朗的悲劇真正在于將自我放逐在假面游戲之中,企圖在他者期待與真實自我的夾縫中尋求生存的空間,實際是在自由意志與理性意志的博弈中喪失了自我的本真。
四、結語
基于美國20世紀20年代的社會現實,奧尼爾認為單純反映生活的現實主義是不夠的,而應該關注現代人內心的精神危機。在此期間,奧尼爾轉向假面劇的實驗創作,嘗試以假面拓寬人物的表現維度。這不僅是為了借鑒古老的面具技法經驗,更是試圖通過鉆研古希臘悲劇崇高的文學傳統,進一步確立自我的戲劇理想,書寫人類在光榮偉大又具毀滅性的自我斗爭之中的永恒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