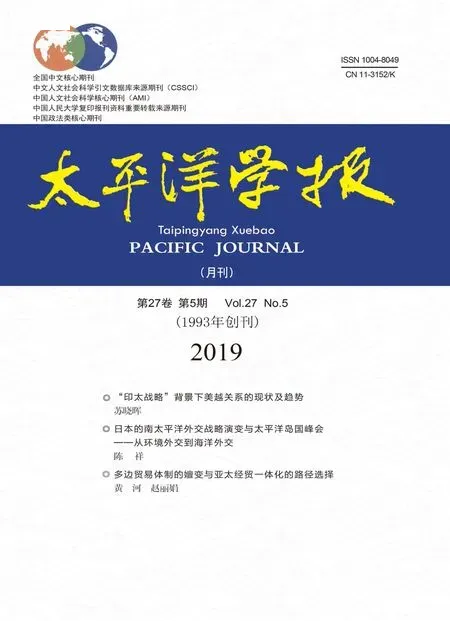東亞地區安全架構中的同盟政治與領土爭端
——以中日釣魚島爭端和中菲南海爭端為例
李 途
(1.南京大學, 江蘇 南京 210093)
領土爭端是否解決以及如何解決是影響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因素。除了與印度及不丹之間的陸地邊界問題尚未解決外,中國在東海和南海方向還面臨著海上領土爭端,其中既包括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也包括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南海主權爭端。這兩個爭端的相似之處在于:二者都屬于二戰以來的歷史遺留問題,與20世紀70年代海底油氣資源的發現和爭奪密不可分,美國均牽涉其中。1951年9月,旨在解決日本戰后政治地位以及日本戰爭責任的國際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美國聯合英國等國家單獨與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以下簡稱“舊金山和約”),其中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對臺灣、澎湖的所有權利、權利根據與請求權”。①“Peace Treaty with Japan”,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September 8, 1951,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36/volume-136-i-1832-english.pdf.但是,日本拒不承認釣魚島作為臺灣的附屬島嶼,屬于“舊金山和約”規定的日本應當放棄的領土,反而主張釣魚島作為美國戰后托管的“日本領土”,隨著《歸還沖繩協定》一并“歸還”給了日本。“舊金山和約”第二條還規定,“日本放棄對南威島及西沙群島之所有權利、權利根據與請求權”,但未明確規定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主權歸屬,這也為后來的南海爭端埋下了隱患。菲律賓據此主張,“舊金山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南沙島礁的主權權利后,南沙便成為國際法意義上的“無主地”①Mark E.Rosen,JD,LLM,“Philippin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Legal Analysis”, Center for Navy Analyses, August 2014, https://www.cna.org/cna_files/pdf/iop-2014-u-008435.pdf.,為其后來非法侵占南沙島礁提供依據。
此外,美國還因與爭端當事國日本和菲律賓存在正式的同盟關系而進一步牽涉其中。作為日本和菲律賓最為重要的盟友,美國在這兩個主權爭端問題上的態度值得特別關注。在中日釣魚島問題上,美國公開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多次表示《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關于“共同防御”的規定適用于釣魚島,美國還一再聲稱其立場始終如此,從未發生改變。但在中菲南沙島礁爭議問題上,美國刻意在《美菲共同防御條約》是否涵蓋南沙爭議島礁的問題上保持模糊態度,一再拒絕在是否協防南沙的問題上向菲律賓作出明確的安全承諾。
同樣作為美國的亞太地區盟友,同樣針對中國,為什么美國愿意向日本做出明確的同盟承諾,而拒絕向菲律賓做出明確的同盟承諾?對此,吳志成與陳一一提出,可以從美菲與美日同盟條約、美國戰略目標差異以及菲日兩國對美政策影響力等制約雙邊關系的基本因素來進行分析,這為理解美日、美菲同盟差異提供了一定的思路。②吳志成、陳一一:“美國在黃巖島與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緣何不同?”《現代國際關系》,2013年第4期,第35-40頁。但是,從更普遍的意義上來說,同盟關系的存在如何影響同盟一方與第三方的領土主權爭端?一國會在什么情況下介入同盟國與第三方的領土爭端?同盟的介入或者不介入又會對爭端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同盟政治與領土爭端
領土爭端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對同一塊領土均宣稱擁有主權從而造成的沖突和糾紛。領土爭端一般都涉及敏感的主權問題,如果爭議領土還具有重要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價值的話,爭端當事方很難在這一問題上進行妥協和退讓,因領土而起的爭端也就具有持久性和破壞性的特征,容易引發國家間的敵對和沖突。為了獲得令人滿意的爭端解決結果,爭端雙方都會試圖提升本國的軍事實力,加強對爭議領土的控制,威懾對手不要采取進一步侵占行動。
軍事實力的提升,既可以通過加強軍事部署來完成,也可以通過強化同盟來實現。同盟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之間所作出的關于相互進行軍事援助的承諾。③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1,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68, pp.268-271.同盟關系一旦組建,當盟國與其他國家發生爭端或沖突時,一國就有義務對其盟國提供必要的援助和支持,這種援助既可以包括外交方面的支持,比如積極聲援或嚴守中立,也可以包括軍事方面的支持,比如提供武器裝備或直接軍事介入等。同盟國一旦違背自己的援助義務,不僅會對盟友及同盟一方的生存與安全利益造成損害,還可能對本國的國際聲譽造成不可挽回的負面影響,以至于將來在本國受到攻擊時不能獲得其他盟友的援助。
關于同盟關系如何影響領土主權爭端,主要分為兩種情況,其中一種是同盟內部的領土主權爭端。根據保羅·胡思(Paul Huth)的研究,領土爭端分為三個部分:產生、升級和解決。盡管同盟關系的存在并不足以阻止領土爭端的產生,也就是說,即使是同盟國家之間也可能存在領土糾紛,但是,同盟關系能夠緩和彼此之間的對立,加強相互的溝通與協調,防止領土問題發展成為長期的、嚴重的軍事沖突。此外,同盟關系還有助于領土爭端的解決。因為雙方存在著共同的安全利益,而領土問題上的妥協是維持同盟關系與加強安全合作必須付出的代價。①Paul K Huth, Standing Your Grou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160-163.
當然這也意味著,一旦共同的威脅消失,同盟一方不再認為對方對本國的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時,領土問題上的合作需求就會大大降低。比如,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力支援越南的抗法、抗美斗爭,中越兩黨結成了“同志加兄弟”的友誼,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也多次表態支持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主張,公開承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是中國的領土。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美軍撤出越南,蘇聯加強對越援助,中越矛盾越來越突出,實現統一的越南很快背離了原來的立場,派軍占領了原為南越當局侵占的南沙島礁,并進一步擴大到對中國西沙和南沙全部島礁提出主權要求。②相關研究參見唐慧云:“1950—1979年間中越同盟中的蘇聯因素”,《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第7-12頁。
另一種是同盟一方與第三方之間的領土主權爭端,這種情況更為復雜,既包括同盟內部的分歧,也包括同盟與爭端第三方之間的沖突。這種復雜性體現在:爭議領土是否屬于同盟義務規定的范圍?雙方在這一問題上是否存在著共識?同盟雙方在如何解決領土爭議問題上是否存在著一致的看法?是通過武力實現還是主張和平談判?同盟一方是否會介入盟友與第三方的領土爭端?同盟一方如何平衡受盟友牽連的風險與被盟友拋棄的風險?同盟的介入,以及通過何種方式介入又會對領土爭端的未來走向產生怎樣的影響?是激化爭端還是緩和沖突?
傳統威懾理論認為,同盟關系本身便是一種威懾,同盟關系的存在可以向對手傳遞彼此合作的信息,增加威懾的可信度,減少領土沖突的風險。托林·懷特(Thorin Wright)和托比·賴德(Toby Rider)指出,防御性同盟能夠有效地威懾敵對方的侵略行為和進攻意圖,因為同盟的存在增加了敵對方挑起沖突和戰爭的成本。即使是在領土爭端這種涉及重大利益、極易引發沖突的問題上,防御性同盟也能夠對敵對方的進攻行動起到有效的威懾作用。③Thorin M.Wright and Toby J.Rider, “Disputed Territory,Defensive Alliances and Conflict Initia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31, No.2, 2014, pp.119-144.但在保羅·胡思看來,在領土爭端問題上,同盟關系的威懾作用非常有限。因為爭端國一旦在領土問題上遭到挑戰,其盟友很難在短時間內向其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爭端對方的意圖并不是發起大規模的、全面的軍事進攻,而只是為了實現有限的領土目標。④同①,pp.118-119.換言之,如果爭端另一方的目的只是為了占領特定地區的爭議領土,那么,除少數情況外,這種行為一般不會對同盟的生存與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軍事介入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就不會那么強烈。
除威懾作用外,同盟關系的存在還可能激化現有的領土爭端,提升沖突與戰爭的風險。一方面是因為,當爭端當事國在領土問題上尋求外部聯盟的援助時,容易造成爭端另一方的不安全感,從而產生安全困境,提升了威脅的感知和沖突的風險。⑤John Vasquez, The War Puzzle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68.另一方面,同盟關系的存在還可能會鼓勵盟友主動采取武力升級措施,或是在領土談判中要價過高,因為它會期待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獲得盟友的支持,從而進一步加劇沖突與戰爭的可能性。同盟國家也因此受到牽連,被迫卷入與自己無關、但涉及盟友的領土主權爭議中。
但是,也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因為同盟的功能除了共同抵御外部威脅外,還包括約束盟友的行為,約束的目的在于防止盟國采取有損本國安全利益的行為。比如,在詹姆斯·莫羅(James Morrow)認為,國家間結盟是安全(security)與自主(autonomy)之間的交換。大國在向小國提供安全保證前,會要求對小國的行為施加一定的控制,從而減少同盟牽連的風險。⑥James D.Morrow, “Alliance: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No.1, 2000, p.79.金(Tongfi Kim)也提出,同盟陷阱(entrapment)在現實政治中是很少見的事情,受到同盟連累的國家往往是小國和弱國。因為在不對稱同盟中,大國如果擔心受到小國盟友冒險軍事行動的牽連,因其本身具備更多討價還價的能力,所以它會在同盟條約中對同盟義務的性質和啟動同盟的條件進行明確的規定,以避免日后受到連累。①Tongfi Kim, “Why Alliances Entangle But Seldom Entrap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Vol.20, 2011, pp.350-377.
從上述分析來看,同盟在領土爭端問題上的影響是復雜和多重的,同盟關系的存在,無論在威懾對手方面還是在鼓勵盟友方面都存在著不確定性,其效果取決于同盟介入的程度和介入的意愿。而同盟介入的程度和意愿又取決于其如何權衡以下三方面的問題:第一,領土爭端是否屬于同盟義務規定的范圍?第二,同盟一方能否從介入爭端中獲益,特別是在同盟條約沒有明確規定援助義務的情況下?第三,同盟一方如何評估介入爭端可能產生的同盟牽連風險?只有當盟友的領土爭端涉及本國重大的安全利益時,同盟一方才會介入爭端,主動承擔同盟牽連的風險。
首先,同盟具有不同的類型,同盟條約規定的差異決定著一國是否有義務介入盟友的軍事沖突。②Brett Ashley Leeds, “Do Alliance Deter Aggression?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Alliances on the Initiation of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47, 2003, pp.427-439.如果同盟條約對領土爭端問題上的援助義務進行了明確規定,那么該國介入領土爭端的可能性會更高,在領土問題上支援盟友的可能性也越大。因為同盟的建立和維持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這意味著只有那些愿意履行同盟承諾的國家才會組建同盟。③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7, No.4, 2003, p.805.另外,根據布雷特·利茲(Brett Leeds)等的研究,在大多數情況下,盟友都會履行援助義務。同盟的可靠性基于同盟條約明確規定了啟動同盟義務的條件以及應當采取的行動。④Brett Ashley Leeds,Andrew G.Long and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 Reevaluating Alliance Reliability: Specific Threats,Specific Prom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4, No.5,2000,pp.686-698.如果一國在條約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拒不履行同盟義務,它將面臨著較高的違約成本,這對大國和小國來說都是如此。大國擁有更多的盟友,一旦失信于某一盟友,它將付出極高的聲譽代價;小國高度依賴大國的安全保護,一旦不履行同盟承諾,容易面臨被大國拋棄的風險。
反之,如果同盟條約沒有對領土爭端問題上的援助義務進行明確規定,即存在著較大的自由行動空間,那么該國介入領土爭端的可能性會降低,在領土問題上支援盟友的可能性也會減少,這點對于大國來說尤其如是。比如,王石山等基于其研究提出,美國是否援助危機中的盟國是附帶條件的,當危機并不直接涉及美國的同盟義務時,或者說美國在是否履行同盟義務的問題上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時,美國援助盟友的可能性會大大降低。⑤王石山、韓召穎:“美國為何援助國際危機中的盟國(1946—2006)”,《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8期,第107-134頁。
其次,同盟一方是否會介入盟國的領土爭端取決于它能否從介入爭端中獲益。一般而言,一國是否會履行同盟承諾介入盟國的沖突,主要取決于介入的收益是否會超過介入的成本,具體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如果軍事介入的成本較低,也就是說,介入能夠輕易地幫助盟友取得勝利,那么該國介入的意愿就會越高。二是,如果介入的收益越高,該國介入的意愿也會越高。三是,如果不介入的損失較大,比如同盟關系遭到破壞甚至失去盟友,那么介入的必要性也會增強。⑥James D.Morrow, “Alliance: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No.1, 2000, pp.63-83.
如上所述,如果同盟條約對援助義務進行了明確規定,那么盟國介入領土爭端的可能性越高。這不僅僅是因為不履約將面臨較高的聲譽損失,還因為履約有助于維持和強化同盟關系,鞏固雙方在爭議問題上的合作。如果同盟一方違背其同盟義務,拒絕在領土爭端問題上援助盟友,可能會承擔損失盟友的風險。同盟關系越重要,盟國履約的意愿就越強烈,介入爭端的積極性也越高。
反之,如果同盟條約沒有對援助義務進行明確規定,但是同盟一方認為維持同盟關系至關重要,或是介入爭端能夠獲得顯著的收益,且不介入的損失較大,那么該國介入爭端的可能性也越高。以美國出兵朝鮮戰爭為例,二戰結束之際,美軍從朝鮮半島撤軍,并將南朝鮮劃在美國的太平洋“環形防線”以外,南朝鮮一旦遭到攻擊,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和聯合國的集體行動”,即否認了美國對南朝鮮的援助義務。但是,朝鮮戰爭爆發后,在冷戰思維的影響下,美國認定北朝鮮的進攻是由“蘇聯發動、支援和慫恿的”,因此改變了原來不予援助的立場,決定立即進行全面軍事干預以防止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①牛軍:“朝鮮戰爭中中美決策比較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36-55頁。
最后,在介入領土爭端的問題上,同盟一方除了能夠獲得一定的收益外,還需要承擔必要的成本,特別是同盟牽連的風險。同盟一方最終是否介入爭端,取決于其如何評估同盟牽連的風險和成本。同盟牽連指的是一國因為同盟義務不得不援助盟友從事代價高昂、但獲益甚少的事業。②Tongfi Kim, “Why Alliances Entangle But Seldom Entrap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Vol.20, 2011, p.355.同盟牽連的實質是一國出于道德、法律或聲譽上的考慮選擇維持同盟承諾,卷入盟友的軍事沖突,通常以犧牲本國利益為代價。③Michael Beckley,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S.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4, 2015, p.12.
一般而言,如果盟友的領土爭端與本國的利益關涉不大,或者說盟友的重要性不夠突出,那么為了減少同盟牽連的風險,同盟一方會盡力逃避同盟義務,或是盡可能地維持同盟承諾的模糊性,避免直接介入盟國與第三方的領土爭端。這點對于擁有更多資源的大國來說尤其如此。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提出,大國可以通過在盟約中設定規避性條款、逃避代價過于高昂的同盟義務(比如只提供外交而非軍事援助,只提供空中掩護而非地面部隊)、維持同盟的多元化(一國的挑釁性行為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共同約束),以及使用明確的同盟承諾來威懾對手并阻止盟國主動挑起沖突等,降低本國卷入盟國軍事沖突的風險。但是,他也指出,這并不意味著大國不會因為同盟而卷入軍事沖突。只是表明,大國在選擇軍事介入時,同盟義務并不一定是其主要的考慮,大國之所以這么做主要是為了本國的國家利益。以美國為例,二戰以來的六十余年間,美國一共與60多個國家簽署了同盟協定,但只有五次清楚地表明美國被卷入盟國的軍事沖突中,分別是1954年和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越南戰爭、20世紀90年代的波斯尼亞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在這些屈指可數的案例中,美國援助盟友都是出于美國的國家利益而非對同盟的義務。④同③,pp.7-48.
反之,當盟友的領土爭端涉及本國重大的安全利益時,即當爭議領土的價值或者同盟的重要性超越了同盟牽連的成本時,那么無論盟約是否規定或者如何規定,該國都會選擇介入爭端,主動承擔同盟牽連的風險。比如一戰前夕,德國向俄國宣戰后,法國履行其對俄同盟義務也向德宣戰,但作為協約國的一方,英國遲遲未能宣布參戰。直到德國違背《倫敦條約》入侵低地國家比利時、直接威脅英吉利海峽的安全時,英國才最終下定決心向德國宣戰。戰爭態勢的變化對英國國家利益的影響決定了英國參戰態度的轉變。
以中日釣魚島問題和中菲南海爭端為例,盡管美國一再表示在主權爭議問題上持中立立場,主張各方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但美國事實上對日本和菲律賓采取了不同的態度,一方面,多次公開承諾《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另一方面,拒絕將南沙島礁及黃巖島納入《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的范圍。美國之所以在兩個海洋領土爭端問題上采取截然不同的態度,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因素:第一,同盟條約規定的差異。《美日安保條約》和《美菲共同防御條約》均規定美國共同防御的義務為日本/菲律賓管轄下的領土,但是美國基于“第27號令”和《歸還沖繩協定》承認釣魚島為日本管轄下的領土,從而將釣魚島納入美日共同防御的范圍。相反,美國從未正式承認菲律賓對其主張的部分南沙島礁①菲律賓稱“卡拉延群島”。和黃巖島擁有主權或管轄權,從而將它們排除在美菲共同防御的范圍之外。第二,同盟的性質以及利益上的差異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在領土爭議問題上支援盟國的意愿。在南海問題上,由于菲律賓實力較弱,在分擔美國全球及地區戰略重任方面有限,美國并不愿向菲律賓做出明確的安全承諾,以免日后承擔過于高昂的同盟牽連風險。相反,從當前來看,無論是美日同盟,還是釣魚島本身,對美國的戰略價值都遠遠超過了美菲同盟和南沙島礁。這也意味著美國介入釣魚島問題的意愿和程度都遠遠超過中菲南海爭端。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以及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利益,都促使美國自愿承擔同盟牽連的風險,甚至隨著局勢的變化進一步強化在釣魚島問題上對日本的支持態度。下文將分別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具體說明。
二、美日同盟與中日釣魚島爭端
釣魚島問題原本是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和主權爭議,但是釣魚島問題的出現與美國二戰后的對日政策不無關系。甚至可以說,美國是釣魚島爭端的“直接參與者”。②M.Taylor Fravel, “Explaining Stability in the Senkaku (Diaoyu) Islands Dispute”, in Gerald L.Curtis, Ryosei Kokubun and Jisi Wang eds., Getting the Triangle Straight: Managing China-Japan-US Relations,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10,p.147.盡管美國一再淡化它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角色,認為這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問題,但是美國“深度介入”了釣魚島爭端。正是因為美國占領琉球群島后,有意通過行政管轄和相關軍事活動將釣魚島和琉球群島捆綁在一起,才造成了今天的中日釣魚島糾紛。③Jean-Marc F.Blanchard, “The U.S.Role i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1945-1971”,the China Quarterly, No.161, 2000, p.120.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還多次承諾《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公然違背其在主權問題上的中立立場。
美國承諾釣魚島屬于美日共同防御的范圍,首先是源于同盟義務的規定。因為從同盟條約內容的解讀來看,《美日安保條約》規定共同防御義務涵蓋日本行政管轄下的領土,而美國承認釣魚島為“日本行政管轄下的領土”,因此《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這一看法不僅得到了學界的廣泛共識,也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正式承認,這也是美國無法在釣魚島問題上置身事外的重要原因。
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雖未明確提及釣魚島問題,但二戰結束后釣魚島作為美軍的訓練基地一直處于美國的軍事托管之下。到了1953年12月,美國代表琉球民政府發布“關于琉球列島地理界限的公告”(即“第27號令”),錯誤地將釣魚島劃入美國托管琉球群島的地理范圍。這一公告將釣魚島問題與琉球群島的未來不可避免地聯系在一起,也成為后來中日主權糾紛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0年1月,美日兩國在華盛頓簽署《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U.S.and Japan,以下簡稱《美日安保條約》),修改了兩國曾于1951年簽訂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美日安保條約》除了確認美國繼續享有在日本駐軍和保留軍事基地的權利外,還廢除了美軍干涉日本內部事務的條款。其中第五條還規定,雙方認為,在日本行政管轄下的領土上針對締約任何一方的武裝進攻,都是對本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雙方承諾將根據本國憲法規定的條款和程序采取行動以應對共同的危險。④“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nuary 19, 1960, 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q&a/ref/1.html.
與此同時,隨著國際地位的提升,日本國內要求“沖繩歸還”的輿論呼聲也越來越高。1971年6月,經過近兩年時間的談判,美日最終達成《歸還沖繩協定》(Okinawa Reversion Agreement),規定美國將琉球群島及大東群島的行政管轄權歸還給日本,并在《諒解備忘錄》中按照琉球民政府“第27號公告”的內容,以經緯度坐標的方式將釣魚島明確標識在歸還的地理范圍內。面對中國方面的強烈反對,美國國務院稱,雖然美國將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交還日本,但是美國在島嶼主權爭議問題上持中立立場。美國將行政管轄權交還給日本并不表明美國偏向爭端中的任何一方①Mark E.Manyin, “ The Senkakus ( Diaoyu/Diaoyutai)Dispute: U.S.Treaty Oblig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2761,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October 14, 2016, https://fas.org/sgp/crs/row/R42761.pdf.。美國國務卿威廉姆·羅杰斯(William Rogers)還表示,《歸還沖繩協定》并不影響這些島嶼的法律地位。協定生效之后,這些島嶼的法律地位與協定簽署之前的法律地位保持一致。②Jean-Marc F.Blanchard, “The U.S.Role i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1945-1971”,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1, 2000, p.120.
盡管美國做出了上述中立表態,但是美日同盟條約所確立的美國援助日本的義務明確將美國與釣魚島問題聯系在一起。由于美國通過“第27號令”以及《歸還沖繩協定》承認釣魚島為日本行政管轄下的領土,因此符合《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規定,一旦有第三方使用武力奪取日本實際管轄和控制的釣魚島,美國就有義務援助日本。而從實際情況來看,美國也沒有逃避其對日同盟義務,多次公開表態承認《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
有分析稱,美國自小布什政府時期才開始承認釣魚島為美日共同防御的范圍③郭永虎:“關于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美國因素’的歷史考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1-117頁。,但事實上早在1971年美日簽訂《歸還沖繩協定》時,美國就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表態。1971年10月,美國國務卿威廉姆·羅杰斯在參議院關于“歸還沖繩協定”的聽證會上明確表示,1960年《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歸還給日本的領土,其中包括釣魚島。④Tongfi Kim,“US Alliance Obligations in the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Issues of Applicability and Interpretations”,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Report, No.141, th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2016, p.8, https://www.hsfk.de/fileadmin/HSFK/hsfk_publikationen/prif141.pdf.
在隨后出現的數次釣魚島危機中,美國的上述立場一再得到確認和證實。1996年7月,日本右翼組織“日本青年社”登上釣魚島,建立了一座太陽能燈塔,并要求日本政府承認其為正式的航標。8月,日本另一右翼組織登上釣魚島,在燈塔附近豎立一面日本國旗。9月,中國香港和臺灣民間群體多次組織赴釣魚島的保釣運動。這一系列行動引發了新一輪的中日釣魚島紛爭。9月,《紐約時報》引用美國駐日大使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的話表示,美國軍隊沒有義務因為《美日安保條約》的規定介入釣魚島的爭端。這一表態引發了日本方面的擔憂。隨后,美國國防部長威廉姆·佩里(William Perry)和美國國防部亞太事務副助理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均對此作出了反駁,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問題。⑤同④。
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國漁船在釣魚島海域先后與兩艘日本巡邏船相撞,日本海上保安廳隨后以“涉嫌妨礙公務”為由逮捕了中國漁船船長。中國對此提出嚴正抗議并與日方多次交涉,兩國關系陷入緊張局面。10月27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會見日本外相前原誠司(Seiji Maehara)后公開表示,《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這是美國對日承諾的一部分。⑥Hillary Clinton, “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Seiji Maehara”, U.S.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7,2010,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 /10 /150110.htm.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后,中國隨即采取反制措施,在釣魚島海域開展定期巡航,并公布釣魚島及其附島嶼的領海基線,中日關系急劇惡化。2014年4月,奧巴馬在訪問日本時表示,美國對日本的同盟承諾是毋庸置疑的,《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于日本管轄下的所有領土,其中包括釣魚島,這也是美國總統首次就釣魚島問題作出這樣的公開表態。
其次,美國承諾《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不僅是美日同盟條約的規定使然,也是因為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存在著廣泛的利益,無法對中日糾紛置之不理。具體來看,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優勢,有賴于日本提供軍事基地和各種輔助設施,其中琉球群島的作用不可忽視。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就開始在日本駐軍,將琉球群島視為其遠東戰略防線的重要環節,并私自將釣魚島也納入其中。朝鮮戰爭爆發后,日本作為美國軍事后勤基地的作用更為突出,也加速了美國對日媾和的進程,“舊金山和約”確立了美國對琉球群島等島嶼的托管制度。在美國看來,將這些島嶼置于戰后美國的托管之下而不是交給日本或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戰略安全利益極為重要。為此,美國需要獲得對琉球等群島的“排他性戰略控制權”。因為“一旦琉球落入蘇聯或共產主義中國手中,將會危及美國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基地網絡。”①Jean-Marc F.Blanchard, “The U.S.Role i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1945-1971”,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1, 2000, pp.102-109.美國軍方還認為,這種排他性的控制權應當包含整個琉球群島。任何一個小島一旦被分割出去,都會對美國在關鍵島嶼的軍事存在構成嚴重的威脅。②同①,p.104。這也是戰后美國將釣魚島劃入琉球群島地理范圍的重要原因。
20世紀60年代,美國之所以同意與日本就“歸還琉球”問題進行談判,也與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利益密切相關。因為面對日本國內不斷要求“歸還沖繩”的輿論壓力,美國意識到沖繩問題的解決可能會對美日安全合作造成負面影響,特別是《美日安保條約》將于1970年到期,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去留將成為問題。為了防止日本本土及沖繩島內的反美情緒影響到《美日安保條約》的存續以及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美國同意盡快歸還沖繩。1969年11月,尼克松與佐藤榮作發表聯合聲明,約定美國將在其軍事基地功能不受損害的前提下歸還沖繩。③王新生:“佐藤政權時期‘沖繩歸還’的政治過程”,《日本學刊》,2012年第3期,第154頁。
1971年6月,美日簽訂《歸還沖繩協定》,事實上肯定了日本對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這明顯是偏袒日本的表現。美國之所以這么做是為了繼續維持美日安保體制。盡管當時尼克松政府已經在謀求改善對華關系,但是日本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并沒有改變。事實上,美日在簽署《歸還沖繩協定》的同時還秘密簽署了《諒解備忘錄》,規定美國在歸還島嶼的“行政管轄權”后還可以繼續使用日本的軍事基地,其中就包括釣魚群島中的黃尾嶼和赤尾嶼。④崔修竹、崔丕:“美日返還琉球群島和大東群島施政權談判中的釣魚島問題”,《世界歷史》,2014年第5期,第19-22頁。
其二,美日同盟是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基石,日本對美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釣魚島問題也成為美國拉攏日本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與美菲同盟不同的是,美日同盟不再是冷戰初期“美國提供安全保護、日本提供軍事基地”這種單向的依附性同盟,日本對美國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日本能夠為美國提供東亞的軍事基地,還體現在日本能夠積極配合美國在地區和全球范圍內的聯合軍事行動。⑤朱鳳嵐:“論冷戰后日美同盟關系的調整”,《國際論壇》,2005年第5期,第12-13頁。這從冷戰結束以來美日同盟經歷的三次大調整中就能看得出來。每一次調整都擴大了美日同盟的適用范圍,從最初的專守防衛擴大到“周邊事態”,再擴展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⑥陶文釗:“冷戰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調整”,《美國研究》,2015年第4期,第29頁。,日本在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的重要性得到進一步強化,在同盟內部的影響力也得到進一步提升。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威脅的消失使得冷戰期間被共同安全利益掩蓋的美日經濟矛盾逐漸突出,克林頓政府奉行貿易優先政策,在貿易和市場問題上頻繁向日本發難,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一度遭到質疑。然而,朝核問題和臺海形勢的發展,促使美國重新審視日本的戰略價值。1995年2月,美國國防部出臺了《美國亞太地區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美日關系是美國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對實現美國太平洋地區安全政策和全球戰略目標具有重要的價值”,并強調“美日同盟是美國推行亞太安全政策的關鍵”。①“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5, 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003052174.1996年4月,美日發表《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面向21世紀的同盟》,重新定義了兩國安全合作的范圍,將美日同盟的目標從冷戰時期的“遏制蘇聯擴張”發展為“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②“Japan-U.S.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pril 17, 1996,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ecurity.html.1997年9月,兩國公布了新版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提出了“周邊事態”的概念③“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Defense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September 23, 1997, http://www.mod.go.jp/e/d_act/anpo/19970923.html.,大大擴展了日本軍事力量在日本周邊地區活動的范圍和方式。
小布什政府時期,日本積極支持美國的全球反恐行動,通過修改國內立法,突破了“和平憲法”關于直接參與海外軍事行動的限制。此外,日本還積極配合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日本國會先后通過了《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等“有事三法案”。2004年2月,日本向伊拉克派遣550人組成的陸上自衛隊以執行人道救援任務,這也是“二戰”結束以來日本首次向海外派兵。通過反恐合作,美日同盟得到進一步提升和強化,美日安全合作的范圍也從日本的“周邊事態”擴大到印度洋和中東地區。
奧巴馬上任初期,美日同盟曾因為普天間機場搬遷、民主黨追求對等外交等問題出現過短暫的“漂流”,但安倍晉三再次出任首相后,積極向美國靠攏,全力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美日同盟得到進一步強化和升級。④陶文釗:“冷戰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調整”,《美國研究》,2015年第4期,第26頁。與此同時,在金融危機和財政預算削減的情況下,美國也鼓勵盟友日本分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以減輕自身的戰略負擔。2015年4月,美日公布了新版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解除了日本自衛隊行動的地理限制,將美日軍事合作的范圍擴展到全球,并強調了兩國從和平時期到緊急事態各個階段的無縫合作,其中就包括日本極力主張的“灰色地帶事態”,這也意味著美國幾乎無法在中日釣魚島沖突中置身事外。⑤Ian E.Rinehart, “ New 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 Deepen Alliance Cooperation”, 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 Reports,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April 28, 2015, https://fas.org/sgp/crs/row/IN10265.pdf.
其三,除了安撫日本外,中國因素也是美國介入釣魚島爭端的重要考量。盡管釣魚島問題與美日同盟強化并不存在著直接的對應關系,但是中國崛起無疑是美日同盟強化的重要誘因。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釣魚島問題是“重塑美日同盟的外在動力”。⑥苗吉:“日本釣魚島政策及其走向”,《太平洋學報》,2016年第11期,第50頁。釣魚島是中國突破西太平洋島鏈的咽喉⑦史春林、李秀英:“美國島鏈封鎖及其對我國海上安全的影響”,《世界地理研究》,2013年第2期,第6頁。,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維持介入的態勢,將對中國形成有效的制衡。此外,美國還擔心,一旦在釣魚島問題上置身事外,美國的安全利益將受到極大的損害。
按照詹姆斯·莫羅(James Morrow)的觀點,一國在決定是否介入盟國的軍事沖突時,除了需要考慮介入的成本與收益外,還需要考慮不介入可能造成的損失。如果不介入的損失較大,那么該國介入的必要性也會相應提升。⑧James D.Morrow, “Alliance: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No.1, 2000, pp.63-83.從美國的角度看,如果美國沒有在釣魚島問題上向日本提供支援,就會引發地區國家對其同盟承諾可信度的擔憂以及對其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能力的質疑。一旦地區國家對美國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失去信心,就可能拋棄美國,選擇追隨中國。美國還擔心,如果不對中國在東海地區的行為及時采取針對措施,就會鼓勵中國在南海地區也采取類似的“過激”行動。⑨Bonnie Glaser, “US Interests in Japan’s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s wi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Discussio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7th Berlin Conference on Asian Security, Berlin, July 1-2,2013,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projekt_papiere/BCAS2013_Bonnie_Glaser.pdf.因此及時表明美國的立場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是為什么近些年來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強化對日承諾的重要原因。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對日援助承諾存在漏洞,日本對此也深感擔憂。因為按照同盟條約的規定,美國對日同盟義務包括“日本管轄下的所有領土”,但是美國要求日本承擔保衛其領土的首要責任。也就是說,一旦日本失去了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權,美國就可借此逃避對日援助義務。①Yoichiro Sato, “The Senkaku Dispute and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Pacific Forum, No.57, 2012, p.1.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后,中國大幅增加了釣魚島附近的海上巡邏和海上執法行動,實現了在釣魚島附近海域的常態化護漁巡航。中國這一做法意在挑戰日本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是對美國對日同盟承諾可信度的一種考驗。②Mrak E.Manyin, “The Senkakus(Diaoyu/Diaoyutai) Dispute: U.S.Treaty Oblig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2761, October 14, 2016, p.7, https://fas.org/sgp/crs/row/R42761.pdf.
為了緩解日本方面的擔憂,美國一再偏離其在主權爭議問題上的中立立場,進一步強化了在釣魚島問題上對日本的安全承諾,多次聲明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領土現狀的行動,針對中國的意圖明顯。2012年,美國國會在“201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明確表示,任何第三方的單邊行動都不會影響美國承認日本對釣魚島擁有行政管轄權的立場,美國遵守《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規定的對日同盟義務。③United States Congress,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3, Public Law 112-239, January 2, 2013, U.S.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https://www.gpo.gov/fdsys/pkg/PLAW-112publ239/html/PLAW-112publ239.htm.2013年1月,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在會晤到訪的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時明確表示,美國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行政管轄,反對任何損害日本行政管轄權的單邊行動。④“Remarks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fter Their Meeting”, U.S.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19, 2013,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3/01/203050.htm.2013年11月,美國批評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行為是在“改變地區現狀”,只會“引發地區危機和沖突”。⑤“Statement on the 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U.S.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23, 2013,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11/218013.htm.
三、美菲同盟與中菲南海爭端
菲律賓對南海島礁的侵占始于“二戰”結束之后。1956年,菲律賓人托馬斯·克洛馬(Tomas Cloma)宣稱“發現”了南沙群島并占領了其中33個島礁,將其命名為“卡拉延群島”(Kalayaan Island Group)。自1970年開始,菲律賓政府先后占領了南沙群島中的馬歡島、費信島等8個島礁。1978年,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發布第1596號總統令,正式將南沙33個島礁納入菲律賓的“領土范圍”,置于巴拉望省行政管轄之下。同釣魚島問題一樣,美國在南沙主權爭議問題上持中立立場,支持各方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然而,在同盟義務問題上,盡管菲律賓多次主張將南沙島礁納入美國對菲同盟義務的范圍,但是美國一再拒絕做出類似于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所獲得的同盟承諾。一方面是因為美菲同盟條約的模糊規定,賦予了美國在同盟承諾問題上的靈活操作空間。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菲律賓在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的重要性不及日本,美國協防南沙群島的意愿并不強烈,不希望為此承擔同盟牽連的風險。
1)課堂互動系統主要是建立教師計算機與學生手機之間的通信聯系,實現對手機的屏幕廣播、手機屏幕監看、教學互動、答疑指導等功能,達到對課堂教學的組織與實施[3]。
首先,從同盟條約的解讀來看,《美菲共同防御條約》是否適用于南沙爭議島礁存在著模糊性。⑥Tongfi Kim,“US Alliance Obligations in the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Issues of Applicability and Interpretations”,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Report, No.141, 2016, p.3, th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https://www.hsfk.de/fileadmin/HSFK/hsfk_publikationen/prif141.pdf.美國國會研究報告也指出,《美菲共同防御條約》并沒有明確規定美國必須在爭議海域問題上援助菲律賓。⑦Thomas Lum and Ben Dolv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U.S.Interests-2014”,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May 15, 2014, p.12,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s://fas.org/sgp/crs/row/R43498.pdf.這也意味著,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著逃避同盟義務的空間。從實踐來看,無論是1995年的“美濟礁事件”,還是2012年的“黃巖島事件”,美國給予菲律賓的只是有限的外交支持,拒絕將美菲共同防御義務擴大到南海爭議島礁。
1951年,美菲締結《美菲共同防御條約》(U-nited States-Philippines Mutual Defense Treaty),其中第四條規定“在太平洋地區對締約任何一方的武裝進攻會被視為對本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雙方承諾將根據本國憲法規定的程序采取行動以應對共同的危險”。從內容上看,《美菲共同防御條約》與《美日安保條約》相差不大,但是細節的差異決定了美國在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和中菲南海主權爭議問題上的不同態度。《美日安保條約》將共同防御的范圍限定為“日本行政管轄下的領土”,由于美國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因而自然將釣魚島納入美日共同防御的范圍。但是,《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第五條將美菲共同防御的目標限定為太平洋地區“對締約國本土的進攻”“對締約國管轄下的太平洋島嶼的進攻”,以及“對締約國在太平洋上的軍隊、船舶或飛機的進攻”。
由于美國從未認可菲律賓對南沙爭議島礁或黃巖島擁有主權或管轄權,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菲律賓主張的南海島礁并不符合《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第五條中前兩項“菲律賓的本土”或“菲律賓管轄下的太平洋島嶼”的定義。特別是菲律賓直到1978年才正式宣布將其主張的“卡拉延群島”劃入菲國土范圍內,而《美菲共同防御條約》于1951年簽署,所以美國完全可以主張它的條約義務不包括南海爭議島礁。至于第五條的第三項,即菲律賓駐守在南海爭議島礁上的軍隊遭受攻擊時,美國也對此進行了嚴格的限定。1975年6月9日,基辛格在發給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及美駐菲使館的電報中明確表示,只有當這些軍隊是出于集體防衛的目的并符合國際法的規定,美國才會進行援助。基辛格還進一步指出,《美菲共同防御條約》并沒有給予任何一方絕對的安全保證,也就是說,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當其部署在太平洋任意地區的軍事力量受到第三方攻擊時都能獲得對方的援助。①Jay L.Batongbacal, “EDCA and the West Philippine Sea”,Rappler, December 12, 2014, http://www.rappler.com/thoughtleaders/77823-edca-west-philippine-sea-america.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隨著美國對華制衡力度的加大,美國進一步明確了在第五條第三項上的立場。2019年3月1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在與菲律賓外長洛欽(Teodoro Locsin)會晤時表示,由于南海是太平洋的一部分,任何對菲律賓在南海的軍隊、飛機或船舶的武裝進攻,都將觸發美菲同盟條約的共同防御義務。②Michael R.Pompeo, “ Remarks With Philippine Foreign Secretary Teodoro Locsin, Jr.”, U.S.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2019,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9/03/289799.htm.這也是美國高層官員首次做出這樣的表態,但是這一表態并不意味著美國會為菲律賓在南海的行為“廣開綠燈”。只有菲律賓在南海遭受其他國家的“武裝進攻”時,美國才會根據國內憲法規定的程序啟動同盟援助義務。因此,只要中國避免首先在南海問題上對菲直接使用武力,美國是否協防南沙、如何協防南沙就是未定數。鑒于此,洛欽在同一場合也表示,“太過模糊的承諾會導致人們質疑承諾本身的可靠性。目前來看,幫助菲律賓發展自我防御能力才是正解。”③同②。
鑒于條約規定的模糊性和可操作空間,美國一直拒絕將菲律賓主張的南海島礁納入美國對菲同盟義務的范圍,這從歷次南海爭端升級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比如,1995年“美濟礁事件”發生后,菲律賓加強了在其主張的南沙島礁上的軍事部署和附近的軍事活動,中菲南沙爭端明顯升級。美國國務院隨后發布了“南沙及南海政策聲明”,表明美國在南海主權爭議問題上的中立立場,強調其利益在于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和航行自由,絲毫沒有提及美國對菲同盟義務的問題。④Christine Shelly, “U.S.policy on Spratly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U.S.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Press Briefing, May 10,1995,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5/9505/950510db.html.2012年4月,中國海監船和漁政船與菲律賓海軍護衛艦“德爾皮拉爾”號在黃巖島附近海域發生對峙事件。在中菲對峙期間,正值美菲舉行首次“2+2”會談,菲律賓希望借此獲得美國在黃巖島問題上援助菲律賓的承諾,但是這一努力顯然沒有成功。①Tongfi Kim,“US Alliance Obligations in the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Issues of Applicability and Interpretations”,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Report, No.141,2016, p.21, th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https://www.hsfk.de/fileadmin/HSFK/hsfk_publikationen/prif141.pdf.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在會后重申了美國的利益在于航行自由與地區和平穩定,她還表示美國將與菲律賓就這一事態進行緊密磋商,但仍然沒有提及軍事援助問題。②Hillary Clinton, “Remarks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 Philippines Foreign Secretary Albert Del Rosario, and Philippines Defense Secretary Voltaire Gazmin After Their Meeting”, U.S.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30, 2012,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4/188982.htm.
事實上,菲律賓方面也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菲律賓學者稱,菲律賓很難從美國那里獲得像釣魚島問題上對日本那樣的安全承諾。因為如果美國想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得更為積極和堅定,它早就會與菲律賓制定出類似《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那樣的文件來明確其承諾。③Maria Ortuoste,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Out of Time, Out of Options?”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1, 2013,p.244.
其次,如上文所述,當領土爭端超出同盟義務的規定時,美國是否介入取決于風險與收益的考量。只有當介入的收益超過牽連的成本時,美國才會考慮將同盟承諾擴大到南沙爭議島礁。菲律賓由于軍事實力較弱,在美菲同盟體系中一直居于從屬地位,并沒有向日本那樣發展出與美國逐漸對等的同盟關系。菲律賓過去不僅嚴重依賴美國的外部安全保護,甚至在內部安全問題上也需要美國幫助打擊國內的恐怖主義和叛亂勢力,比如美軍曾協助打擊菲律賓南部城市馬拉維的極端主義組織等。在不對稱同盟中,只要美國掌握更多討價還價的能力,如何解釋它的同盟義務就取決于美國的利益需要。
從美菲同盟演變的歷史來看,菲律賓在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的重要性逐步下降,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甚至一度將軍隊撤出在菲律賓的基地,直到2014年才通過輪換部署的形式重新回到菲律賓。即便如此,美菲軍事合作的水平和程度也遠不及美日合作。此外,菲律賓憲法還禁止外國軍隊在菲律賓設立軍事基地,也進一步限制了美菲軍事合作的深化。因此,與美日同盟和釣魚島問題相比,美國協防南沙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并不強烈。
具體來看,冷戰期間,菲律賓的軍事基地曾是美國西太平洋戰略部署的重要一環,在遏制蘇聯在亞洲地區的擴張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菲律賓還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菲關系日漸走向疏離,雙方的戰略目標也出現分歧。美國希望借助菲律賓的軍事基地抗衡蘇聯的勢力,但在馬科斯及其繼任者阿基諾看來,美國的軍事存在更像是一種要求美國援助的籌碼,而不是維護菲律賓國土安全的保障。④Richard D.Fisher, Jr., “ Rebuilding the U.S.-Philippine Allianc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No.12, 1999, p.3.同時由于忙于應對國內的叛亂和政變,菲律賓越來越難以在軍事上向美國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分擔美國地區和全球戰略重任方面作用有限。
冷戰結束后,菲律賓對美國的重要性大為降低。1990年,菲律賓政府借“美菲軍事基地協議”到期需要重新談判之際,要求美國提高駐菲軍事基地的租金和對菲律賓的軍事援助。但事實證明,菲律賓錯誤地高估了冷戰后它在美國全球軍事部署中的重要性。⑤Renato Cruz De Castro, “Special Relations and Alliance Politics in Philippine-U.S.Security Relations, 1990-2002”, Asian Perspective, Vol.27, No.1, 2003, pp.144-146.美國拒絕了菲律賓的要求,將軍隊完全撤出了菲律賓,結束了在菲律賓近一個世紀的軍事存在,美菲同盟也陷入停擺狀態。
1995年“美濟礁事件”發生后,菲律賓重新認識到美國的軍事存在對維持東南亞地區均勢的重要性。1998年2月,經過兩年多的談判,美菲達成《訪問部隊協議》(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這一協議允許兩國舉行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并準許美國軍艦訪問菲律賓港口。雙方還借此恢復了中斷數年的“肩并肩”聯合軍事演習。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菲律賓公開支持美國的全球反恐行動。2002年11月,美菲簽訂《后勤支援互助協議》(Mutual Logistics Support Agreement),規定菲律賓可以為在菲領土范圍內外行動的美軍提供后勤支援保障。2003年6月,菲律賓向伊拉克派出人道主義救援團隊。然而在2004年7月,阿羅約政府因“伊拉克人質事件”決定提前撤軍,遭到了美國政府的嚴厲批評,美菲關系再次受挫。“伊拉克人質事件”凸顯出美菲同盟的利益分歧。這也從側面說明,菲律賓由于受到國內政治和實力不足的限制,對美國全球戰略的開展和推進助益有限。①Mely Caballero-Anthony, “Beyond the Iraq Hostage Crisis:Re-assessing US-Philippine Relations”, IDSS Commentaries, July 28,2004.
直到奧巴馬政府宣布將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之后,菲律賓對美國的重要性才再次得到凸顯。阿基諾三世政府積極配合美國的“再平衡”政策,美菲同盟關系得到強化。2014年4月,美菲簽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規定美軍可以通過輪換部署的形式進駐菲律賓的軍事基地,強化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也正是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與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利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契合,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介入程度不斷加深,公開聲明南海航行自由關乎美國的國家利益②“Speech of Hillary Clinton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larger ASEAN Regional Forum”, U.S.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2010,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 /07 /145095.htm.。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也拒絕在協防南沙的問題上向菲律賓做出明確保證,充分說明菲律賓重要性的提升程度還不足以讓美國擴大對菲的安全承諾。
與釣魚島問題不同的是,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和興趣是近些年來在美國“重返亞太”以及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的背景下才逐漸變得突出的。美菲同盟強化以及菲律賓重要性的提升是奧巴馬政府亞太政策調整的結果而非原因。美國介入南海爭端主要是因為擔心中國的“斷續線”主張和南海島礁建設會損害其在南海地區的航行自由和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海上霸權,而非對菲同盟義務。當前,美國主要通過“航行自由行動”來挑戰中國的南海主張,并不愿意因為同盟義務而被迫卷入中菲之間的領土沖突。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并沒有完全排除通過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條約》介入南沙爭端的可能性。因為一旦美國認為中國在南海地區的存在危及美國的航行自由和海上霸權地位,美國就有可能借助美菲同盟的名義擴大對菲律賓的軍事援助和安全承諾。正如蓬佩奧近期在美菲同盟義務上的最新表態③Michael R.Pompeo, “ Remarks with Philippine Foreign Secretary Teodoro Locsin, Jr.”, U.S.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2019,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9/03/289799.htm.所顯示的那樣,隨著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全面開展,以及菲律賓“疏美親中”傾向的加劇,美國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對菲同盟義務,以試圖拉攏菲律賓配合美國在地區范圍內制衡中國的行動。但是,美國未來將如何履行這一同盟承諾,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結 語
美國的海上霸權地位依賴于全球公共海域的開放及其軍事力量的自由投射。東海和南海作為重要的海上戰略通道,美國自然不會置之不理。美國時任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拉塞爾(Daniel Russel)在參議院作證時指出,美國在東海和南海地區具有重要的利益,包括航行和飛越自由、暢通無阻的合法貿易、尊重國際法以及和平解決爭端。他還表示,美國在主權爭議問題上不持立場,但是爭端解決的方式影響著美國的國家利益。④Daniel R.Russel,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U.S.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5, 2014, https://2009-2017.state.gov/p/eap/rls/rm/2014/06/228415.htm.盡管做出了上述中立表態,美國還是通過對日和對菲同盟義務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釣魚島爭端和南海爭端。
美日同盟和美菲同盟均起源于冷戰初期,后來逐漸發展成為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美國在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上的介入程度卻不盡相同。美國在承認釣魚島為日本行政管轄下的領土,承諾《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的同時,拒絕將菲律賓主張的南沙島礁和黃巖島納入《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的范圍。美國之所以在盟國的海洋領土爭端問題上采取不同的協防態度,一方面是因為美菲同盟條約留下了不同的解釋空間,美國完全可以借此逃避其在南海問題上的同盟義務;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同盟利益和安全利益要遠高于美國在中菲南海爭端問題上的利益,這也意味著,盡管存在同盟牽連的風險,美國介入東海爭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要遠高于南海爭端。
那么,美國的同盟承諾以及同盟承諾的差異又是如何影響釣魚島爭端和南海爭端呢?傅泰林(Taylor Fravel)提出,美日同盟的威懾效應,是中日圍繞釣魚島爭端沒有發生軍事沖突的關鍵原因。①M.Taylor Fravel, “ Explaining Stability in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Dispute”, in Gerald L.Curtis, Ryosei Kokubun and Jisi Wang eds., Getting the Triangle Straight: Managing China-Japan-US Relations,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10, p.160.萊謝克·布斯恩斯基(Leszek Buszynski)也認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是維護南海局勢穩定,防止領土爭端升級的主要原因。②Leszek Buszenski, “ASEAN, the Declaration on Conduct,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5, No.3,2003,pp.343-362.但是,這種觀點過于夸大了同盟在領土爭端問題上的威懾效應,低估了爭議領土問題上同盟牽連的風險,也忽視了同盟承諾的差異可能造成的不同影響。安迪·葉(Andy Yee)就指出,美國在領土爭端上對盟友的支持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即在促進南海爭端當事國加強談判與合作的同時加劇了東海地區的軍事和外交沖突。③Andy Yee,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No.2, 2011, p.189.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Delfin Lorenzana)也表示,美菲同盟條約的模糊和含混,不僅不會對對手構成有效的威懾,反而會在危機出現時制造困惑和混亂。④Paterno Esmaquel II, “Lorenzana-Locsin Clash over Mutual Defense Treaty Heats up”, Rappler, March 5, 2019, https://www.rappler.com/nation/224962-lorenzana-clashes-locsin-philippines-us-mutual-defense-treaty.
事實上,同盟在領土爭端問題上的威懾作用存在著諸多不確定因素,盡管同盟條約進行了相關規定,但是一國是否會介入盟友與第三方的領土爭端取決于其如何權衡介入的收益與風險。在不對稱同盟中,只要主導國家掌握更多的權力和資源,如何解釋它的同盟義務就取決于其利益和偏好。無論是美日同盟還是美菲同盟,其建立的目標都不是為了幫助日本或菲律賓實現它們的領土主權主張,而是為了實現共同的安全利益。因此,除非美國的利益牽涉其中,否則美國會盡量避免介入爭端,防止同盟牽連的風險,保持承諾的模糊性。
盡管不應過分強調同盟在領土爭端問題上的威懾作用,但是美國出于自身利益,利用其亞太同盟體系介入地區事務,的確改變了地區安全格局,進一步激化了地區海上爭端。南海問題的升級正是發生在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背景之下,阿基諾三世仰仗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在南海問題上頻頻挑釁中國,造成中菲關系嚴重惡化,南海局勢驟然緊張。而美國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鼓勵日本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只會推動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采取更為強硬的政策。相反,無論是“美濟礁事件”后中菲達成“磋商聯合聲明”,中國與東盟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還是杜特爾特上任后中菲關系全面轉圜,中國與東盟就“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取得突破性進展⑤“王毅:‘南海行為準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形成,證明中國和東盟國家有能力達成共同遵守的地區規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8 年 8 月 2 日,http://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 /gjldrhd_674881 /t1582564.shtml。,以及中菲簽署《關于油氣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等,都說明地區國家和相關當事國完全有能力管控和解決好地區問題。域外大國出于自身利益介入地區爭端只會推動問題走向多邊化和國際化,加劇爭端解決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