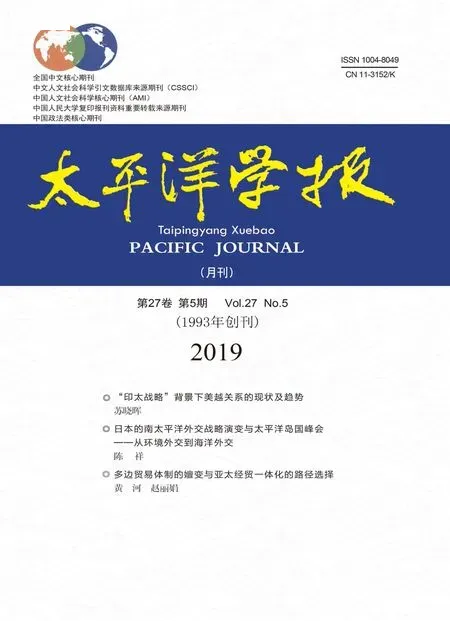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路徑、極限與對策思考
葛漢文
(1.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江蘇 南京210039)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后,因其愈發突出的地緣政治意義連同其所激發的地區國家間甚至世界主要大國間關系的復雜變動,南海問題已經愈益成為影響中國國家安全、地區形勢發展甚至全球權勢格局變動的關鍵變量之一。特別是,作為當前國際體系中的頭號強國和域外國家,美國近年來在南海問題上的戰略調整,不僅在外交領域持續推動區域內國家間的猜忌與不和,更在軍事領域不斷推升既定區域安全形勢的總體緊張,甚至急劇增加了中美兩國爆發武裝沖突的風險。其后果使得南海問題在領域上早已大幅突破了原定議題,在范圍上亦已遠遠超越了區域地理概念,成為當下中美戰略博弈的關鍵戰場和決定兩國當下乃至未來關系走向的重要風向標。①Lyle Goldstein,“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An Abundance of Noise and Smoke,but Little Fire”,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3, No.3, 2011, p.320.
一、美國南海政策的演進與基軸
冷戰后美國對南海問題的直接介入大致開始于克林頓政府時期。在所謂“美濟礁事件”發生后,1995年5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提出包括“和平解決爭端”、“保持和平穩定”、“航行自由”、“在主權問題上保持中立”及“尊重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為代表的海洋規范”等五點聲明,首次較為完整地表述了美國在既定問題上的政策立場。①Enrico Fels and Truong-Minh Vu, eds., Power Politics in A-sia’s Contested Waters: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New Yor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393.隨著區域地緣政治格局的進一步變化、部分聲索國在南海島礁歸屬及海洋資源開發等問題上立場的日趨激進以及隨之而來的聲索國之間主權、權益爭端的不時激化,主要在2006年之后,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注程度開始顯著加大。2009年,美國以中國制裁參與越南非法開采的美國石油公司及“騷擾”對華抵近偵察的美海軍艦只(即所謂“無暇號事件”)為由,開始著手制定一項“全新的、清晰的和全面的”南海政策,以應對美國利益在該地區所受到的“危險和挑戰”。②Nicholas D.Anderson, and Victor D.Cha, “The Case of the Pivot to Asia: System Effects and the Origins of Strateg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2, No.4, 2017, p.604.2010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公開發表聲明,在重申1995年政策諸項核心要素(尤其是所謂“航行自由權”)的同時,再次強調美國在南海爭端中“不持立場”,主張通過“司法渠道”解決爭端,聲稱反對任何聲索國在地區爭端中“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③同①,p.394。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后,主要在中國國家綜合實力不斷上升、地區權勢結構向有利于我方向演進背景下,南海問題很快便成為美國亞太政策重點關切的議題,甚至成為部分美國決策者心目當中足以阻滯中國戰略崛起的“絕佳助力”。2012年美國務院以我維護黃巖島主權及設立三沙市為由發表聲明,首次明確指責中國“破壞地區現狀”、“激化緊張局勢”,重申美國將該地區的“和平、穩定”視為其國家利益的組成部分。④同②。2014年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拉塞爾(Daniel Russel)以中國“圍困”仁愛礁、海軍艦只抵達曾母暗沙甚至“可能”在南海設立防空識別區(ADIZ)為由,指責中國“有計劃的、采取堅實的步驟控制‘九段線’內區域”,甚至明確聲稱中國的“九段線”主張“既不符合自然地貌,也不符合國際法”,并宣稱支持菲律賓向國際海洋法法庭(ITOLS)提起仲裁,甚至將之稱為以“和平”而非“施壓”手段解決爭端的“范例”。⑤同①,p.397。美國對中國的權益主張(“九段線”)及正常維權行動的直接攻擊,實際上標志:美國已然放棄早先一再強調的所謂“中立”立場,將南海安全形勢緊張的根源歸因為中國合法的主權權益訴求和正常的維權行動,實際上開始“選邊站”。
尤其在2015年,以美國時任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在香格里拉對話會公開指責我南海島礁建設為“過度主張”、嚴重破壞地區軍事平衡、宣稱將針對性展開“航行自由行動”(FONOPs)為標志,美國在南海問題上開始由外交介入正式開始升級為軍事介入階段。⑥Ashton Car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allenges to Asia-Pacific Secur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30 May 2015, https://www.iiss.org/events/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15.2015年和2016年,美海軍艦只在中國南海共計執行了4次進入我南海島礁12海里內的所謂“航行自由行動”。⑦分別為:2015年10月美驅逐艦“拉森”號駛入我渚碧礁鄰近12海里水域;2016年1月美驅逐艦“威爾伯”號進入我西沙領海;5月美驅逐艦“勞倫斯”號駛入我永暑礁鄰近12海里水域;10月美驅逐艦“迪凱特”號進入我西沙領海。Axel Berkofsky,“U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FONO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Able to Keep Chinese Territorial Expansionism in Check?” in Marco Clementi,Matteo Dian, and Barbara Pisciotta, eds., U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llenging World: Building Order on Shifting Foundations, 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2018,p.341.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執政末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南海問題為其政策依據和關注重點,強調主要依賴外交等所謂“巧實力”(smart power)加強其地區同盟體系、提升盟國和伙伴國能力、更大程度參與地區事務,以求強化遏阻中國在該地區“專斷”(assertive)行動的國際網絡。①Nicholas D.Anderson, and Victor D.Cha, “The Case of the Pivot to Asia: System Effects and the Origins of Strateg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2, No.4, 2017, pp.597-598.
作為域外國家,2015年后美國深度介入南海問題的緣由,在于宣稱在南海存在兩大重要利益。一是所謂“自由通行權”。美國宣稱,考慮該區域對于全球經濟、貿易、能源、軍事的重要地緣價值,直接關乎世界經濟尤其是美國及其亞太主要盟國的經濟發展和外部安全,因此所有國家在該區域均應享有充分的海洋“航行自由”(FON)。二是所謂維護“地區穩定”。隨著亞太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南海及其周邊地區已經成為當前世界經濟中最具活力且具備相當規模的區域之一。維持該地區安全形勢的總體穩定,被認為是涉及美國及其地區盟國、伙伴國的重要利益。與此同時,其他被列入到美國國家利益范圍的相關問題還包括:美國對地區盟國、伙伴國所謂“安全承諾”;處理與中國的總體關系等。②Enrico Fels, and Truong-Minh Vu, eds., Power Politics in Asia’s Contested Waters: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New Yor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p.391-392.
總的來看,1995年至2016年的二十年時間里,美國的南海政策主要存在四大特征:①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注程度存在明顯的不連貫性。特別是前期,主要是對所謂的“突發事件”做出政策回應;②美國至少在政策宣示上對南海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不持立場”;③同②,pp.389-390.美國將維護所謂“秩序和準則”作為其南海政策的基軸;④葛漢文:“‘拒絕衰落’與美國‘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戰略”,《國際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第92-93頁。美國的南海政策與其全球戰略相聯系并存在內在機理的一致性。③然而應當看到,在該階段行將結束之際,美國南海政策正醞釀著大變動。尤其是以2015年為重要節點,美國開始一改早先主要以政策宣示和外交手段插手南海問題的戰略路徑,開始將我正當維權行動視為中國“挑戰”其地區霸權地位進而“主導”地區事務的先聲,傾向于綜合運用外交攻勢和軍事力量正面挑戰我主權權益主張,阻礙了兩國關系的正常發展,加劇了地區相關國家在既定議題上的猜忌與不和,推動了地區緊張局勢的不斷升級。
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邏輯與實踐
2017年1月20日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大戰略開始出現較大調整。在“美國優先”口號下,特朗普政府將應對“大國競爭”、尤其是中俄等所謂“修正主義”大國的競爭視為政策重點;在經濟上撤回對全球自由開放經濟的支持,為被全球化“削弱”的美國制造業提供保護性關稅;在軍事上加大投入、進一步強化實力、保持軍事實力的絕對優勢地位,同時又強調遠離是非,軍事力量只限于保衛美國自身安全;置疑戰后美國的國際機制設計、尤其是國際安全機制設計,強調獲得單方面的優勢或好處;淡化美國傳統的全球安全視角,在鼓勵盟國擔負更多責任同時,部分撤回海外安全承諾。這與以往美國力圖通過維系其主導之下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進而實現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傳統思路存在較大的差異。④
盡管就任當年特朗普政府的亞太安全戰略重點在于以所謂“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政策以求盡快解決朝鮮核問題,但在應對“大國競爭”邏輯指引下,特朗普政府在短暫停止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動”約3個月后,很快便在南海問題上重新保持相當的政策關注力,以此向中國持續施壓。2017年6月,美時任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的講話為美軍的軍事行動提供了解釋:“尊重航行自由,維護國際規范,對印太地區的和平和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美國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區進行飛越、航行與行動,并通過在南海及其他地區的持續性行動以表明決心”。⑤James Mattis, “First Plenary S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ne 3, 2017, https://www.iiss.org/events/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17.當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發布,更為特朗普政府行動提供了系統的理論和邏輯指引。該報告稱,在“印太”(Indo-Pacific)區域內存在所謂“自由”世界秩序觀與“壓迫”世界秩序觀的地緣政治競爭:“中國對前哨(南沙島礁)的建設和使之軍事化,威脅了貿易的自由流通、威脅其他國家的主權、破壞了地區穩定”。在南海問題被提升至中美兩國地區競爭、甚至是全球秩序競爭的邏輯下,美國宣稱將在軍事上“保持前沿部署,懾止及(如需要的話)擊敗任何敵手”;外交上“將擴大與印度的防務合作,重振與菲律賓、泰國的同盟關系,強化與新加坡、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伙伴關系及海上合作”。①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17,pp.46-47.
在此指導下,2017年5月美國恢復其在南海的所謂“航行自由行動”,驅逐艦“杜威”號擅自進入我美濟礁鄰近海域12海里;7月“斯坦塞姆”號導彈驅逐艦進入中國西沙群島領海;8月美“麥凱恩”號導彈驅逐艦進入美濟礁鄰近海域12海里;10月美“查菲”號驅逐艦在西沙群島海域巡航。2018年,美海軍于1月(“霍珀”號導彈驅逐艦)、3月(“馬斯丁”號導彈驅逐艦)、5月(“希金斯”導彈驅逐艦和“安提塔姆”導彈巡洋艦)、7月(“斯坦塞姆”號)、9月(“迪凱特”號導彈驅逐艦)不斷派遣主戰艦只進入我中沙群島黃巖島、南沙群島美濟礁、南薰礁、赤瓜礁、西沙群島鄰近海域進行所謂“航行自由”。進入2019年后,美軍此類行動頻次繼續提升:1月7日“麥坎貝爾”號導彈驅逐艦擅自進入我西沙島礁12海里內巡航;2月11日“斯普魯恩斯”號、“普雷貝爾”號進入我南沙美濟礁12海里內巡航。②Ryan Browne, “ US Warships Again Challenge Beijing’s Claims in South China Sea”,CNN, February 11, 2019, https://edition.cnn.com/2019/02/10/politics/us-ships-south-china-sea/index.htm.特別是2018年9月30日,美艦“迪凱特”號在執行此類行動時,于南熏礁附近與我維權艦只險些發生碰撞事故,大幅加劇了雙方沖突風險。③Luis Martinez, “Chinese Warship Came within 45 Yards of USS Decatur in South China Sea: US”, ABC News, 1 October 2018,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chinese-warship-45-yards-ussdecatur-south-china/story? id=58210760.
在外交領域,至少在南海議題上,特朗普政府一改在其他場合和議題上對多邊外交的消極態勢,反而開始積極致力于在該區域構建更廣范圍和更高層次的政治、軍事合作機制,以期借南海議題對我形成群體性壓力。尤其以推進“印太”戰略為牽引,特朗普政府以中國在南海“填島、建設前哨基地、將爭議海上地物軍事化”為所謂“依據”,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域外國家不斷強化軍事安全聯系,甚至有組建將中國排除在外、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地區軍事安全框架之勢。在美國要求下,包括日本、澳大利亞、印度、英國、法國等西太、印太、甚至更遠地域的南海爭端非當事方不斷就中國南海所謂“航行自由”和“軍事平衡”等問題指責我國,部分國家甚至直接參加美軍“航行自由行動”,以反對中國的“過度”領土主張、確保南海的“航行自由權”。④“France, UK Announce South China Sea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Naval Today, 6 June 2018, https://navaltoday.com /2018 /06 /06 /france-uk-announce-south-china-sea-freedom-of-navigation-operations/.
值得關注的是,與奧巴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現在開始更多地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合法主張和維權行動視為對美國區域軍事存在的直接挑戰,甚至視為崛起中的中國對美國主導下的全球秩序乃至其“全球領導地位”的破壞,是當前“大國戰略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是一個特定的、孤立的、對美國利益影響有限的國際爭端。2018年10月,美副總統彭斯在其發表的著名演講中就公然聲稱中國“當前已經在人工島礁上部署先進的反艦和防空導彈,使之成為軍事基地”,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其權力。為此,美國“將繼續根據國際法允許和國家利益要求的任何地方繼續飛越、航行和行動。我們不會被嚇倒,我們不會屈服!”⑤“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White House, 4 October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正是在此類說辭的渲染和指導下,美軍近兩年來在南海針對我方的軍事活動數量規模大幅上升,行動方式日漸頑固、露骨,對我國家安全和周邊安全施壓力度不斷加大。
但是應當看到的是,當前美國的南海政策實際上與特朗普的大戰略存在邏輯上的內在緊張。一方面,特朗普大戰略調整的關鍵在于,在極力強化自身實力的同時,慎重使用武力、注意節省資源,而非在地球的遙遠一端(如阿富汗、伊拉克及敘利亞)“虛耗”國力。這種思路顯然與當前美國在南海愈發激進的軍事冒險存在明顯的邏輯沖突。與此同時,特朗普大戰略調整的又一重點,則是在“美國優先”口號下放棄奧巴馬時代格外推崇的多邊外交努力,削減長期以來對國際機制的戰略性投入,尤其強調再度審視其早先顯然過于寬泛的海外安全承諾,這又與當前部分美國高官(特別是前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所力推的、構筑主要針對中國南海問題的“印太”戰略同盟存在精神上的矛盾。因此,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稱要盡力減輕海外安全負擔,另一方面卻在全球范圍內(尤其是南海)繼續顯示和運用美國超大規模的武力;一方面希望擺脫多邊機制約束及壓力,另一方面卻又重回構筑同盟、繼續擴大其安全承諾的傳統思路。此類看似矛盾的現象,可能印證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的基軸,已從奧巴馬時代范圍異常廣泛的海外利益關切轉向了集中“應對大國競爭”,特別是與中國的大國競爭。美國在努力強化自身經濟與軍事實力同時,撤出(或努力撤出)其在中東、歐洲等地區的防務義務和軍事負擔,根本目的就是將注意力進一步轉向東亞,采取多種手段,以爭取在應對中國上取得較以往更加顯著的戰略與軍事優勢。
三、美國的南海戰略① 筆者認為,就概念而言,“政策”意為一國政府已經確定并在執行當中的措施、手段的實踐;而“戰略”則為就某一宏大問題所進行的總體籌劃,觀念思想因素占多,當然也有戰略實施過程。此處之所以用“戰略”一詞,主要談美國戰略學界就相關問題所進行的戰略籌劃,這與前兩節論述的政府的具體舉措存在不同。:困境與選擇
近年來,隨著南海爭議各方利益博弈日趨明顯、域外大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和行動愈發具有挑釁性、連同由此引發的地區安全形勢空前緊張,美國戰略學界圍繞南海問題的討論日益激烈,對2011年以來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政策表達出相當程度的不滿和批評。部分美國學者指責,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正在用“切香腸”(salami slicing)戰略以求強化在南海的地緣政治地位,“不斷侵蝕美國長期以來保衛的國際規范和國家利益”;②Hal Brands, and Zack Cooper, “Getting Serious about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71,No.1, 2018, p.13.尤其是2013年開始在南沙群島的島礁建設,使得中國在南海這個極其關鍵性的戰略要道已逐步占據壓倒性優勢。與之相比,盡管奧巴馬、特朗普兩屆政府不斷努力試圖采取“有效”的回應,但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政策應對大體上是失敗的:奧巴馬政府在中國進行島礁建設之初(2013年到2015年)反應遲緩甚至坐視不理,后期(2015年到2016年底)則舉止失措以至收效甚微;③很多美國學者批評道:奧巴馬政府的南海政策實際上就是其著名的對朝“戰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政策的延續。但這個政策不僅無法解決朝鮮問題,類似的思路也導致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無所作為,最終成為了“戰略靜默”(strategic silence):“既沒有阻止中國填島,之后又沒有阻止中國將之軍事化’,‘航行自由行動’開始地既遲緩,數量亦有限,美國政府的重視程度也不夠”。 Donald K.Emmerson, “South China Sea: US Bargaining Chip or Key Interest?” YaleGlobal Online, 1 June 2017,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south-china-sea-us-bargaining-chip-or-key-interest.特朗普執政之初(2017年1月到5月)對南海問題選擇性遺忘,之后(2017年5月至今)政策又驟然激進。這些學者由此認為:近十年以來,美國實際上并沒有一項全面的、連貫的、有效的南海戰略,其倉促的應對,效果可疑,實質于事無補。而美國政策的數次搖擺和重心轉移,使其不僅已經并將繼續經受長時間的“戰略透支”,更在南海遭受了反復的政策失敗。④同②。
為此,當前不少美國戰略學者認為,隨著中國的“前進”和美國動機空間的“減少”,南海形勢正處在一個極為關鍵的階段。他們建議,美國的南海戰略,必須在“推回”、“遏制”、“抵消”與“接納”等四種路徑之間做出大致明確的選擇,以改善美國面對的愈發“嚴峻”的戰略困局。①Hal Brands, and Zack Cooper, “Getting Serious about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71,No.1, 2018, p.14.
(1)所謂“推回”(Rollback)戰略,即建議美國政府立即采取“強制行動”迫使中國放棄其在南海的既有所得,包括放棄對南沙人工島嶼、西沙群島的控制、甚至迫使中國放棄“九段線”要求。最少也是放棄在南沙島礁上增設的軍事設施,恢復2013年前的狀態。這個最野心勃勃的選項,要求美國不僅是“簡單阻止中國的冒險”而是要將局勢扭轉,為此不惜接受軍事沖突的損失。這種戰略的“好處”在于,能夠最快地消除中國在該區域對美國利益的“威脅”,恢復美國的“可信度”,采取最激進的手段會取得最佳效果;缺陷是危險性極大,美國必須準備戰爭(包括軍事襲擊和軍事封鎖),準備承擔相當嚴重的報復和損失以及戰爭升級的風險。同時,地區國家由于擔心被卷入,會強烈反對。②特朗普政府前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就表達出這種傾向,他曾要求美國不僅需要阻止中國進一步的島嶼建設和將其“軍事化”,甚至還要使用美軍將這些已建島礁進行“隔離”或“封鎖”,以防止中國“接近這些島嶼”并將之逼退。Nicholas Borroz, “How Trump Can Avoid War with China”, Asia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4, No.3, 2017, p.614.
(2) “遏制”(Containment)戰略。 其要義,在于接受中國在南海的當前所得,但強調美國必須立即“劃出紅線”,防止中國再次“得寸進尺”。這種戰略比“推回”風險要小,執行難度也稍低,但是同樣嚴重依賴軍事手段,包括威脅使用武力。這個戰略主要靠軍事威懾來“阻止”中國在南海采取進一步行動,但由于不是讓中國“屈辱地吐出所得”,因此相對會引發較小的反彈。該戰略執行,必然是長期性的,花費高昂,同時困難重重,存在爆發軍事沖突的風險。與“推回”戰略一樣,“遏制”戰略成功的關鍵在于美國必須有在南海同中國開戰的決心,“這個決心是該戰略不需打仗并取得成功的關鍵”。③同①,p.21.然而,該戰略同樣存在巨大風險:隨著中國實力和信心的不斷增強,美國在南海的軍事行動會面臨更大的困難,會付出更高的代價,甚至必然將導致軍事摩擦。同時,該戰略在外交上困難重重,美國盟國和伙伴國看似不大可能冒公開得罪中國的風險而支持美國。④地區很多國家均在擔心這種前景,即在南海發生局部武裝沖突時被迫要在其最大經濟伙伴(中國)與長期的軍事盟友(美國)之間“選邊站”。見 William T.Tow,“President Trump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Australia-US Alliance and Australia’s Role in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9, No.1, 2017,pp.50-51。
(3)“抵消”(Offset)戰略。 同奧巴馬的南海政策存在精神上的共通之處,該戰略不尋求阻止中國在南海的進一步“進攻性舉動”,但強調采取其他措施(如外交、經濟和其他手段)對中國行動進行“懲罰”,使中國遭受損失、抵消其在南海空間“擴張”所導致的后果影響,以強化美國在地區的總體態勢。這個戰略的所謂“益處”,在于不用同中國直接軍事對抗,而在于使用其他手段以包圍、孤立中國。這種戰略相信,中美兩國在南海乃至亞太、甚至“印太”區域的斗爭,最終勝利不在于誰控制南海的若干島嶼,而在于誰能通過更好地爭取、編織和強化地區的同盟國和伙伴國網絡,從而最終贏得區域主導權。然而,美國學者同時認為,這種“戰術悲觀”但“戰略樂觀”的戰略,總體上是被動的,對現狀于事無補:既無法阻止中國鞏固既得成果,甚至繼續造島或奪島,還會因其效力難以及時彰顯而動搖地區國家對美國的“信心”。另外,采取外交、經濟等手段能否取得預想成果,把握不大,戰略執行難度卻極大。這種戰略實際要求,美國“必須學會走鋼絲”:“它必須足夠強硬使地區國家相信美國沒有放棄南海,但也須避免過于強硬從而嚇倒那些不想被直接卷入中美沖突的地區盟國和其他國家”。⑤同①,pp.22-25.
(4)最后則是“接納”(Accommodation)。 與以上三種路徑不同,這種戰略承認美國在“中國后院”與中國競爭之花費高昂、曠日持久并存在巨大危險,因此美國應避免用軍事、外交和法律手段挑戰中國,承認中國對南海甚至亞太地區的實際主導地位,當下則是力爭確保中美之間能夠“相對平穩地”交接對該地區的主導權。這種戰略的益處在于:美國不會與中國產生沖突,花費較少,能夠保持盟國和伙伴的大體安全(不包括它們對爭議島嶼的主張)。美國還可借此同中國進行利益交換,從而能夠讓美國將戰略重心放在其他關鍵性區域或領域,如朝鮮、伊朗、俄羅斯,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但是,該戰略的代價是會使盟國和伙伴國對美國“信心破產”、地區同盟體系解體以及美國在這一關鍵地區整體利益的“大挫敗”。另外,該戰略雖在短期內會減少軍事對抗風險,但美國的“退縮”及其在效果上對中國的“鼓勵”和“縱容”,會在未來更長的時段內實際加大同中國發生“終極決戰”的可能性。①Hal Brands, and Zack Cooper, “Getting Serious about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71,No.1, 2018, pp.25-26.
在不少美國學者看來,當前特朗普的南海政策實際上是排除了兩個最為極端的戰略選項(“推回”和“接納”),而將“遏制”與“抵消”列入可選范圍。或者說,采取了一種混合式戰略,即以“遏制”手段對抗美國戰略學界最為擔心的“奪島”(如2014年仁愛礁)、進一步“建島”(如2013年后的島礁建設)和劃設防空識別區(類似東海);而以“抵消”戰略對抗中國不那么“激進的”行動(如非軍事力量活動)。當然,很多美國學者也承認,這種混合戰略不一定確保成功,因為并不會削弱中國已經取得的“軍事—地緣政治成果”,也無法消除中國未來可能的“施壓”和“進攻”。同時,這種戰略說易行難,難以精確執行,無法避免危機爆發和消除安全兩難,并且隨著中國力量的進一步增長,實際效果將被進一步削弱。但考慮到美國在南海問題上長期沒有一項清晰連貫的戰略,特朗普當前所采取的此類混合戰略,即以更大的力度繼續“軟硬兼施”,可能是在諸多利弊皆有的戰略類型中的一個次優的選擇。②同①,pp.28-29.
四、對中國應對策略的幾點思考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后,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總體上已出現顯著變化:綜合國力的發展與國家發展利益的拓展,使得中國對外戰略的關注點在地理空間上大幅前移,不論是在陸地抑或海洋,均是如此。尤其在海洋方向,在國家實力高速發展的驅動下,中國國家利益(島礁主權歸屬)、發展利益(海洋貿易、漁業生產和資源開發)、安全利益(確保海上軍事安全)的現狀甚至窘境,均嚴重落后于中國現實意義上和心理意義上的整體需求。與此同時,域外霸權國家、地區部分利益攸關國家和南海沿岸既得利益國家,出于維持對其有利(盡管遠非公正、合法、合理)之現狀目的,對中國的海洋權益主張存在近乎天然的敵意。上述兩種情勢相結合,使得南海方向的海洋權益之爭和部分國家眼中的地區主導權之爭,在當下及未來一個較長歷史階段內存在進一步激化趨勢,南海問題的復雜性、重要性及對地區安全的影響程度均顯著提升。
作為域外國家,美國以軍事和外交手段長期介入這一具有“非凡”地緣政治價值的空間區域,甚至在部分時段實際主導了該區域的軍事—安全架構。然而,隨著近年來諸多事件、事實或趨勢的急速發展,在實力相對衰落的情勢或預期下,美國在地區權勢結構體系中的絕對優勢地位,顯然已非二戰結束與冷戰結束之初那般牢固。盡管如此,不可低估所謂“霸主誘惑”(hegemony’s temptation)對美國政策的顯著影響。同時必須看到,雖然特朗普政府政策與奧巴馬執政后期的南海政策在精神邏輯乃至路徑選擇上實際差別有限(均注重以軍事和外交兩手以反對中國的權益主張及維權行動),但特朗普極端現實主義的政策思路、求變求快乃至存在極大“不確定性”的決策風格、力圖一改奧巴馬時期“無所作為”的勃勃雄心、對應對“大國戰略博弈”的極強看重,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南海問題重視程度的上升及對美國軍事干預時機、力度和方式的不斷試探,均導致美國在南海采取進一步軍事冒險的可能性有所增強。幾乎可以肯定,美軍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短期不會停止,甚至還將更加頻繁;我國在未來幾年里采取進一步維權行動時,將不得不面對美國愈發加大的軍事壓力、甚至是直接的軍事干涉。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隨著中美兩國國家實力對比的發展變化,有關“中美之間必有一戰”的觀點在美國戰略學界甚至特朗普執政團隊當中已然成為熱門話題。①特朗普前首席顧問、普遍被認為是其政治謀主的斯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在2016年預言:未來十年美中之間必有一戰。 Nicholas Borroz, “How Trump Can Avoid War with China”,A-sia&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Vol.4,No.3,2017,p.613.而作為兩國間重要的博弈議題之一,奧巴馬在2015年便正確提醒道:“南海的緊張局勢提醒人們注意升級的風險。”②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5),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15, p.10.正如上文所述,如果美國戰略學界乃至決策界放任這種自2015年以來便已初顯端倪、當下已經異常凸顯的危險情勢(特別是有關美國應在南海準備戰爭、準備承擔嚴重損失、準備將中國“推回”的熱烈討論)繼續發展的話,那么幾乎可以肯定: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爆發于海上、尤其是南海的可能性無疑將大幅增加。而一場當前世界最大的海洋霸主國家同新興的海上強國之間的較大規模武裝沖突,其后果必然對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延續至今的地區安全架構、國際秩序與全球權勢格局造成顛覆性的影響。
面對美國南海政策調整的逐步深入,在南海問題上必須要有危機意識。長期以來貫穿美國決策界的兩大精神思路(即“國際自由主義”與“國際政治現實主義”),均可在南海問題上覓得發難的理由:“國際自由主義”指責我在南海的正常維權是對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規則”、“原則”和“價值”的破壞,甚至是對現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與國際安全架構的顛覆;而所謂“國際政治現實主義”,則將我對南海的權益主張視為是“主導南海、進而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區域”進而將美國影響逐出這一地區的先聲,而對這一地區的控制長期以來被認為構成了美國全球地緣戰略的兩大柱石之一。③見[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頁。因此,在中國“加快”南海維權活動預期下,那種認為美國在南海“讓步”便意味著美國開始放棄其對外政策“核心與原則”、意味著美國主導下國際秩序崩壞、甚至“美國治下和平”就此終結的看法,在部分美國決策界和戰略學界精英當中已經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識。南海問題也不再被認為僅僅事關“世界另一端的幾塊無人礁石”④美國參聯會主席約瑟夫·鄧福德(Joseph F.Dunford)語。據《紐約時報》報道,2016年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鄧福德詢問時任太平洋總部司令哈利·哈里斯(Harry Harris):“你是否會為世界另一端的幾塊無人礁石(指中國黃巖島)而戰?”轉引自瓦西里·卡申:“中國南海領土爭端”,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16年4月6 日,http://sputniknews.cn/opinion/201604061018738992/。,而是被視作了地區主導權之爭、國際秩序之爭甚至是世界霸權之爭。
但同時,我們要更加具備戰略信心:在國家權勢相對衰落的背景下,尤其是考慮到當前美國戰略重點在空間和議題上的廣泛性與異常復雜性,特朗普政府實質已經無力在所有議題上全面開戰,唯冀集中力量一個接一個解決,這從2017年初特朗普就任之后美國政策重點(朝鮮、中東、伊朗、俄羅斯、經貿摩擦、移民、邊界安全)的不斷轉移(甚至不斷受挫)中便可以得到極為明顯的體現。即使是在亞太地區,美國面對的地緣政治難題,范圍廣泛、嚴重牽涉戰略精力且短期內顯然無法解決。⑤Thitinan Pongsudhirak, “Southeast Asia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6, No.1, 2017, p.9.中國則不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由之而來的國家軟、硬權勢的大幅躍升,為中國在與美國的戰略博弈、尤其是在南海的戰略博弈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特別受益于地緣距離的鄰近、巨量的可用資源、求合促和的政策訴求,使中國已經開始實質性改變所在地區安全形勢的整體面目。⑥根據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一份調查,有56%受訪者認為美國未來在東南亞的介入將會減少。在被問及哪個國家或組織在該地區影響力最大時,74%受訪者認為中國,18%認為是東盟,僅4%受訪者認為是美國。Donald K.Emmerson,“South China Sea:US Bargaining Chip or Key Interest?” YaleGlobal Online, June 1,2017,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south-china-sea-us-bargaining-chip-or-key-interest.
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以來,由于在議題、范圍上內生和衍生的極端復雜性和廣泛關聯性,在當前國際形勢顯著變動背景下,南海問題對我國國家安全、地區形勢發展乃至全球地緣政治演進的關鍵性意義進一步凸顯。①不少美國學者判斷:隨著中美兩國發展速度的差距,2030年可能是雙方力量平衡的“破界點”。而在此時間點之前,中國南海甚至可能演變成為“21世紀的西柏林”。Hal Brands,and Zack Cooper, “Getting Serious about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Vol.71,No.1,2018,p.22.特別是2013年以來,中國在南海的維權斗爭所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成果,一舉改善了中國在該地區總體的地緣政治態勢。②美國國防部2015年指責,雖然南海權益各聲索方均在進行填島作業,但均無法與中國島礁建設規模相提并論:“中國填島2 900英畝,越南80英畝,馬來西亞70英畝,菲律賓14英畝,中國臺灣 8 英 畝”。 Richard Q.Turcsányi, Chinese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ower Sourc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Reactive Foreign Polic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p.51.未來,我國南海戰略應在鞏固現有成果基礎上,重點與相關各方一道,加快推進真正適合東亞國家安全利益的區域安全機制建構。③蘇浩:“中國是維護南中國海和平穩定的負責任大國”,《太平洋學報》,2016年第7期,第46頁;周士新:“關于‘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前景的分析”,《太平洋學報》2015年第3期。在此過程中,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和利用地區各國之間在既定問題上關注點及政策實質的不同、分歧和搖擺,充分運用我國在地區愈發增長的軟、硬和巧實力,抵制域外霸權國家試圖借南海問題構筑反華、遏華戰略同盟、進而全面阻斷我和平發展的企圖,全力防止美國南海政策變為“遏制”為主甚至升級為“推回”,在堅定維護在南海的主權和相關權利基礎上,塑造南海安全形勢的總體戰略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