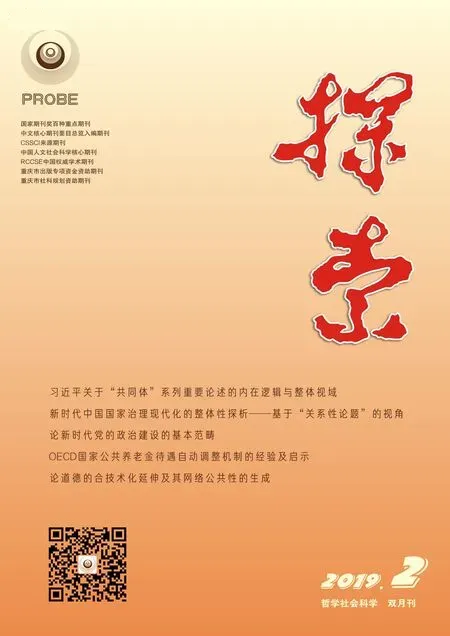新興風險下的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胡尚全
(重慶財經職業學院,重慶402160)
公共安全一頭連著經濟社會發展,一頭連著千家萬戶,是社會安定有序、人民安居樂業、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隨著我國發展進入新時代,人民對安全的需求不斷增長,對安全的要求日益提高,必然對公共安全建設及其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時,公共安全領域內的各種風險亦是當前我國社會轉型發展過程中要應對的突出問題。圍繞各種利益關系的博弈以及多元化社會因素造成的影響,使公共安全治理持續性地面臨各種安全風險的威脅。
基層社區既是社會治理重心下沉的落腳點,也是承托整個公共安全的基石。正確認知社區公共安全的問題本質,合理解釋和分析社區公共安全治理經驗表象背后各種結構要素系統性的邏輯關系、演變機制和發展進路,重視風險領域內新興風險的形成及其演變,避免由風險屬性和特性變化帶來的諸多衍生性的、棘手的、新的公共安全問題,對于在安全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更好地把握新時代社區公共安全治理的內涵要求,探索基層公共安全治理的新路徑、新舉措,提高應對風險和提供公共安全保障的能力,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1 新興風險的類型與特征
1.1 新興風險的內涵
“新興風險”,顧名思義,即“新興”的“風險”。“新興”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里定義為“新近出現的”[1]1459;百度詞典則將其解釋為最近才興起的;英語里對“新興”一詞沒有對應的單詞,含義較為接近和貼合的主要有“rising;burgeoning;new and developing;newly developing”等,翻譯成中文有“崛起、萌芽、新發展、新的發展”等含義。雖然不同詞典、不同語種對“新興”的定義不完全一致,但都從時間維度上對“新興”作出了解釋,即最近才有的,而且是以前沒有的。
關于什么是“新興風險”,2013 年7 月4 日,瑞士再保險有限公司中國業務發展負責人熊耀華在北京舉行的“創新引領保險業蛻變論壇”的發言中提到,“新興風險”可以是新出現的風險,也可能是不斷變化的風險。“新興風險”還包括“被低估的自然巨災風險”“網絡攻擊風險”“新型交通風險”“人工智能風險”“新的診斷工具和個性化醫療”“金融安全風險”等。這些風險有的是原有風險的延伸,例如自然災害、交通工具等,還有一些諸如網絡化、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的風險。馬寧和劉瑋根據熊耀華的觀點,進一步將其解釋為原有風險的新變化與新興領域的風險[2]。張海波從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角度將“新興風險”定義為“新近表露的風險”[3];李曉翾和趙綽翔從企業管理的角度認為“新興風險”主要是指“網絡風險”[4];潘頔則認為“金融風險”是“新興風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5]。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新興風險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和闡釋,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認識和研究新興風險。同時,人們更應該看到,隨著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內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國際形勢更加復雜多變。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各種矛盾疊加,風險隱患集聚。”[6]2018 年4 月17 日,在十九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指出,“前進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認識和有力應對一些重大風險挑戰。要聚焦重點,抓綱帶目,著力防范各類風險挑戰內外聯動、累積疊加,不斷提高國家安全能力”[7]。
根據目前的安全形勢,結合國內已有的研究,筆者認為,“新興風險”主要是指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新近出現的風險及其發展和演化。具體包括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新近出現”的風險,指的是風險出現的時間不長,現有的風險識別技術和識別手段還無法對其特征、特點、屬性等進行比較充分的描述,對其存在的載體、形成條件等還缺乏較為全面和準確的了解,因此,它既對立于傳統(舊)的風險,又區別于已知的風險。二是對公共安全治理而言,新興風險包含著更多的不確定性,是在人們認識能力和認知范疇以外的風險,相較于已知的風險,新興風險的性質、存在的場域、醞釀的土壤、發生的條件、轉化的因素等都不明了。特別是新興風險在何種情況下會發生量變、質變,發展演化的規律是什么,影響要素有哪些,是短期存在還是長期存在等,對于公共安全治理,都難于把握,也是公共安全治理在新的風險態勢下面臨的新挑戰。
1.2 新興風險的類型
根據不同的標準,風險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按照風險存在的領域,可以分為自然風險、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生態環境風險等;根據風險所產生的影響,可分為基本風險、特定風險;根據風險的性質,可分為已知風險和未知風險;根據風險的可控程度,可分為可控風險和不可控風險等。對新興風險的劃分亦是如此。筆者根據公共安全治理所對應的領域,將新興風險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網絡安全風險。網絡安全風險是基于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所形成的一種新興風險。一方面,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催生了互聯網金融、網絡負面輿情、電信網絡詐騙、網絡信息安全、網上意識形態斗爭等各種各樣的網絡安全風險具體形態,互聯網技術在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便利、創造許多機遇的同時,也給社會的安全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另一方面,網絡安全風險涉及政務、金融、能源、環境、衛健、民生等社會運行與發展的方方面面,各種社會風險借助網絡空間傳導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今后還將更加突顯。網絡既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保證,也成為信息泄漏、信息竊取、數據篡改、數據刪添、計算機病毒等攻擊的主陣地。同時,網絡實體還要經受諸如水災、火災、地震、電磁輻射等方面的考驗,網絡發展所產生的安全問題以及互聯網自身的安全問題已經成為全世界共同關注的焦點。
第二,生產安全風險。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今后一個時期,生產安全領域內的新興風險可能會不斷突顯。正如《關于推進城市安全發展的意見》中所指出的,“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人口、功能和規模不斷擴大,發展方式、產業結構和區域布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藝廣泛應用,新產業、新業態、新領域大量涌現,城市運行系統日益復雜,安全風險不斷增大”。礦山、道路交通、水上交通、軌道交通、危險化學品、特種設備、人員密集場所、城市地下管網等重點行業、重要領域,傳統風險與新興風險還將相互交織、相互轉化,產生出新的風險。
第三,民生事項風險。民生是社會發展之基,安全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底線,民生安全是公共安全的紅線,安全也是最大的民生之一。民生事項涉及住房、醫療、衛生、就業、教育等方方面面,一直是風險的高發領域,潛藏著各種風險。隨著我國民生事業的發展,民生領域內的各種新興風險也在不斷涌現,如公共衛生領域的各種突發性傳染疾病,食品安全、假疫苗、房地產價格波動所引發的各種訴求,校園不良網絡借貸引發的極端安全事故等[8],都與社會公眾個體的生存與發展息息相關。隨著青年失業上升為全球性的社會問題,且表現出不同層面的消極影響,青年正淪為“風險中的一代”[9],有效應對青年失業風險,在當下尤為重要。
第四,社會矛盾風險。改革開放不僅帶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在客觀上拉大了社會成員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差距,社會分化呈現加速狀態,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開始顯化和尖銳起來。由于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與社會、單位與個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開始全面重構,而社會保障體制建設相對滯后和不健全,既削弱了社會成員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增大了一部分社會成員在發展中的個體風險。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社會公眾對安全的需求以及對政府公共安全治理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以環境類鄰避事件、小區物業管理和物業權益糾紛、非法集資等為代表的基層社會矛盾和糾紛問題日益增多,社會領域內的新興風險也在不斷顯露、發展和演化。
1.3 新興風險的特征
不管是哪一類的新興風險,從其表現形式看,主要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未知;二是不確定。未知就是人們對風險沒有一個方法來分析和預判它;不確定就是人們對風險的性質、風險的屬性、風險的發生條件、風險的發展及其演化、風險可能造成的損害程度等可能有多個判斷,但無法作出明確的描述和判定。同時,新興風險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只要社會在向前發展,就會有新的風險出現,它因時而生、因事而興,有其自身的特征與演化發展態勢。
第一,已知性與未知性交織。從目前已經涌現出的新興風險來看,其來源主要有兩類:已知的事物和未知的事物。對于已知的事物,雖然人們對其有一定的了解和認識,但在風險承載主體本身的復雜性和外部環境的多變性面前,就如同人生病一樣,人體自身結構的復雜性和人所處環境的多變性會導致疾病發生的時間以及病發程度的未知性,如果來源于未知的事物,新興風險的未知性就更加明顯。加之風險本身是動態變化的,變化之中也蘊藏著未知。已知性和未知性相互交織,既有已知的風險,又有未知的風險。對于風險的這種未知性,人們很難進行判斷并作出預測,也很難找到相對應的解決方法,成為公共安全治理中的難點。需要在弄清楚風險來源的基礎上,創新治理工具、提高社區韌性、完善安全網絡來加以應對。
第二,陌生性與不確定性共存。新興風險具有很多不確定性,為此,當前社會中出現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和一些始料未及的風險可以視為一個新的風險社會來臨的表征[10]。另外,由于是新出現的風險,人們對其尚缺乏足夠的認知,有時甚至都無法準確地感知,傳統的公共安全應急管理的相關做法,如突發事件的分類、分級、風險預測、預判、預警、預控等在新興風險面前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很難具有操作性,這就增加了新興風險應對與現行的公共安全治理體系之間的沖突。同時,也正因為新興風險的陌生性,人們對其特征、特性以及產生、發展、轉化和演化的要素和規律都缺乏充分認知和足夠把握,較之傳統風險,存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對于行為主體來說,可能風險的基本信息都難以捕捉,增加了決策的難度。因此,新興風險的陌生性與高度的不確定性并存,成為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又一難點。
第三,關聯性與耦合性并聯。風險的關聯性最初源于金融機構與相關產業或相關市場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在現代社會,各風險主體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聯結的關系更加復雜,任何一個環節受到損壞,往往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引起整個社會的連鎖反應,導致公共安全失序。多因素的復雜耦合作用是公共安全事件誘發過程中的強大動力[11]。風險耦合性是指系統活動過程中某一類個別風險的發生及其影響力依賴于其他風險的程度和影響其他風險發生及影響的程度,這種風險間的依賴和影響關系稱為耦合,風險間的依賴和影響程度越大,則風險耦合度越大,反之風險耦合度越小[12]。
新興風險雖然是新出現的風險,但作為風險的一種,和傳統風險一樣,有著較為明顯的關聯性和耦合性。比如新發明出來的危險化學品,在其生產、儲存、運輸、轉運、投用、治污等一系列過程中,每個環節都會在生產系統內部和外界環境之間產生高度的關聯,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爆炸、泄漏、污染等較大的生產安全事故,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等嚴重社會危害,因此,既是公共安全治理的難點,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隱患的重點。
第四,發展、轉化、演變的模糊性。新興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和高度關聯性使其發展、轉化與演變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模糊性。一方面,和傳統風險一樣,新興風險呈現出線性與非線性兼有的發展演變規律,如金融領域里的互聯網金融風險等;另一方面,其轉化和演變規律又很難在短時期內被發現和總結出來,特別是社會安全方面的新興風險,由于社會因素和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很難說自然領域、生產領域的風險不會向社會領域延伸和蔓延。加之一些新興風險本身就是傳統風險經過發展和演變而來,在一定條件下,還有可能發生新的轉化,因此,在目前的技術手段和技術水平下,新興風險的演變規律很難得到系統全面的總結。如各類社會風險借助網絡空間傳導的趨勢正在突顯,網上與網下風險相互交織、同頻共振,風險形態將更加敏感和復雜,同樣給公共安全治理帶來不小的挑戰。
2 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架構對新興風險的適應性
基于新興風險的特性及其發展演化態勢,城市社區作為公共安全治理的基礎,在其自身治理中應該如何準確把握風險屬性和風險特性的變化所帶來的挑戰,是構建新的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架構以適應新興風險及其發展演變非常重要的環節。
2.1 治理邊界的模糊性與新興風險的陌生性不相適應
隨著我國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化與安全發展要求的提高,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正在興起。但這種治理又主要依托于社區治理,社區公共安全治理與社區治理之間的邊界并不清晰。
一是治理主體向多元化裂變。在一些新型的城市社區,居民地域來源廣泛、人員結構多元,由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社會,復雜多元的社會階層結構,陌生人群的信任缺乏,“租客”等流動人口的“過客”心態,以致社區居民的融合度不高。即使面對傳統風險都存在治理對象多元分散的困境,在陌生的新興風險面前,更難明確治理的主體責任。
二是利益訴求多元。不同人群對包括公共安全產品供給、公共安全問題解決、社區心理輔導等社區公共安全服務的個性化需求呈現出多樣化、多層次、差異性特征。各種利益訴求交織,社區組織可控功能弱化與群眾較強的自主性形成鮮明對立,對社會資源整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公共安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很難有效應對新興風險。
三是社會矛盾交匯。不同群體之間的職業背景、文化素養、生活習慣各異,特別是以各自利益摩擦為核心的矛盾交匯疊加,磨合難度大且易產生“共振效應”,從而引發新的安全風險。這就使得社區的公共安全治理面臨治理邊界的拓展和延伸以及治理體系需要加速轉型的現實問題。
2.2 治理資源的分散性與新興風險的關聯性不相適應
如前所述,新興風險具有較強的關聯性,因此,需要各治理主體的統籌與協同。但目前的治理主體多通過各自的渠道和途徑開展相關的安全治理工作,不但延誤了寶貴的處置時間,而且由于渠道途徑的不統籌,往往導致信息、數據等不一致,增加了風險研判的難度和誤判幾率,影響處置決策的準確性。
一是現有城市社區安全治理“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的現象較為普遍。社區要面對政府職能部門延伸下來的應急、藥監、質監、綜治、城管、住建、公安、信訪等多個部門,部門與部門之間協調溝通不夠,部門與社區之間信息共享不暢,“屬事”與“屬地”兩個方面相互交織,常常導致治理過程中相關部門和相關人員相互推諉、各自為政,極大地降低了治理的效率。如在住建領域糾紛中,住建部門掌握了建筑商與開發商之間的協議,但社區卻沒有掌握或沒有準確掌握相關協議,一旦發生矛盾糾紛,勢必影響處置決策,甚至為新的風險的出現埋下隱患。
二是職責權限的定位不清晰。重視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是實現公共安全問題預防與處置重心下沉、關口前移的重要舉措。但多數安全問題的處置權限都在屬事的職能部門,社區既沒有法定授權,又無相關專業人員,更難以協調級別和層次比自己高的部門,導致一些矛盾糾紛和安全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同時,由于社區職責權限界定模糊不清,一些部門和街道習慣于將各類任務隨意下派社區。如有城市社區清理出安全工作任務435 項,其中40 項存在“協辦變主辦”現象,導致城市社區對安全風險的防范與化解流于形式,嚴重影響對新興風險的及時識別與精準研判。
2.3 治理結構的穩定性與新興風險的動態變化性不相適應
從目前我國城市社區治理的過程來看,主要還是以行政為主導的治理結構,強化基層政府的功能,主要運用政府及其所掌握的行政資源進行包括社區在內的自上而下的社會整合,較為典型的就是20 世紀90 年代上海提出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落實”。這種層級式的治理結構到今天仍在全國許多城市社區被借鑒和引用。
而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又寓于社區治理,不管是在治理資源的配置上、治理的組織安排上、治理的方式上、治理機制的運行等方面,都以政府為主導,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即使如沈陽的以社區自治為導向,強化了基層社區的自治功能,呈現出以單位為聚集點的“蜂窩狀”治理結構,仍難免帶有“行政”的烙印。
但新興風險是動態變化著的,這意味著風險主體由單一向多元轉變,風險的主體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以單位為聚集點的“蜂窩狀”治理結構應該向多層次、多主體、多場所的復合治理結構轉變。但在目前相對穩定的治理結構下,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的單位可能職責交叉、各自為政,運行效率不高,難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治理策略、治理方式、治理機制都亟待改進。
2.4 治理模式的確定性與新興風險的不確定性不相適應
目前,我國城市社區治理主要采取政府主導、市場主導、社區自治、專家參與等形式[13]。每種形式各有優勢,也各有不足。但總的來說,四種形式從治理的過程來看,都具有相對的確定性,人們對其治理所需的要素、治理的路徑、治理所需配置的資源等比較明確,能夠在城市社區的實際治理過程中被相對固定地持續加以運用,從而構成今天我國城市社區治理的總體格局。
但新興風險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一是就個體而言,風險發生幾率不確定,發生的時間和場域不確定,爆發的烈度也不確定;二是個體風險是否會演化為整體風險、小風險是否會演化為大風險、域內風險是否會演化為域外風險、局部風險是否會演化為整體風險、單一風險是否會演化為綜合風險,都難于確定。雖然有些新興風險必然會發生,如新的傳染性疾病,但什么時候會爆發、在哪些人群身上會發生,甚或傳染程度等都難以預測。一旦發生會對個體、群體乃至整個社會帶來多大影響無法進行準確預測。因此,在現有的治理框架和模式下,很難對新興風險進行識別,并在此基礎上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防范和化解;當新興風險爆發出來,常規的風險應對方式就會失靈,需要人們從技術手段、應對策略、應急機制構建等方面綜合創新來應對。
3 基于新興風險的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創新
基于上述新興風險下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的困境,需要從風險認知、參與動因、互動機理、溝通網絡等環節對治理渠道、治理方式進行優化,對社會參與程度進行深化,對治理工具進行創新,以最大程度整合城市社區內不同主體對新興風險及其轉化發展態勢的正確認知,消除認知差異所導致的治理分歧,形成安全需求—風險辨識—治理網絡—目標共識之間的互動連續體,從風險控制轉向風險溝通[14],在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與社區治理之間以及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之間實現有機銜接和融合,使城市社區真正起到承托經濟社會發展“小社區、大安全、新風險、共治理”的基礎性功能和作用。
3.1 加強制度供給,促進條塊契合
對城市社區而言,公共安全治理資源條塊分割的現象仍然較為突出。由于新興風險產生及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不確定因素,各行為主體出于理性考慮,就需要具有強制性的行為規則來加以規范,否則只會加劇風險對公共安全的威脅程度。這就需要加強制度供給,進一步理順“條”與“塊”的關系,并促進“條”與“塊”之間的契合,實現協同治理。
作為制度供給主體的政府,應該在社區公共安全治理方面加強制度供給,如出臺推行社區大黨委制的指導意見。通過出臺實施意見,明確推行大黨委制的指導思想、目標原則、主要內容、方法步驟和保障措施,打通行政隸屬壁壘,成立社區大黨委,把基層黨組織和駐區單位融合起來,把各類群團組織、社會組織動員起來,推動基層黨建制度與基層治理機制有機銜接、良性互動。同時,在社區黨支部牽頭成立社區大黨委。黨委書記由所在社區黨支部書記擔任,轄區內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的黨組織負責人原則上為大黨委委員。制定黨委議事規則和黨委會會議制度,通過定期召開社區與轄區單位黨組織聯席會議,研究包括安全治理在內的社區重大問題,分解落實責任,促進各方主體責任和社會責任的落實,著力解決社區統籌協調難的問題,激活公共安全治理的“神經末梢”。
比如在食品安全領域,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政府運用公權力對食品安全監管,在立法、執法、法律救濟、法律監督等方面加強食品安全法律法規的供給,從檢驗標準、檢測體系、認證體系、協同監管等方面做好制度上的設計[15],則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政府職能部門內部、職能部門與社區所屬的鎮街之間,社區內的學校、企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等相關的多元主體之間就可以形成更加良性的合作。
3.2 整合優化資源,促進功能彌合
應對新興風險是我國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中的重點,圍繞各種利益關系的博弈以及多元化社會因素造成的影響使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持續性地面臨各種安全風險的威脅。而城市社區自身所擁有的各種內生性資源,如社區居民、轄區單位、社會組織、社會力量等都是社區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力量。在目前社區治理資源結構性分散的情況下,需要社區加大資源整合的力度,使各項安全功能能夠在面對新興風險時“擰成一股繩”,形成應對的合力,從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
一是加強部門資源整合。基層黨委、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整合的時機,進一步加強公安、城管、藥監、質監、應急、綜治、住建、衛健等公共資源的整合和下沉,加強對街道辦事處的指導協調,共同做好風險隱患排查、安全問題動態監管、突發事件應急處置等方面的工作。同時,系統梳理社區建設、社區公共服務、社區發展的需求事項,搭建以需求為導向的資源整合平臺,建立服務需求和資源供給有效對接的良性機制,促進政府資源和社區資源有效對接互動,讓社區資源成為社區服務的有機組成部分,構建社區資源共同生長的生態圈[16],充實基層社區綜合監管防控力量,真正讓新興風險的隱患化解在社區。
二是加強社區之間資源整合。街道要加強統籌規劃,切實發揮對轄區內社區安全資源的整合功能。根據社區事務多少和人員配置情況,對計生、社保等部分社區公共服務職能實行劃片和信息化管理,騰出更多人手,專心從事社區安全工作。同時建立和完善社區各項安全工作制度,逐步規范各項社區工作,著力解決安全治理中的行政化、機關化傾向問題,整合完善居民代表會、居民議事會、居民委員會、居民議事小組等機構,充分調動公共安全公眾治理的積極性,以解決好新興風險源頭治理與防控的難題。
三是加強社區內部資源整合。在全面清理社區各項公共安全職能的基礎上,整合社區內人、財、物資源,特別是整合社區居委會低保、社保、醫保、信訪、殘聯、安保、綜治、治安協管等“八大員”和網格員、樓棟長、業委會等,使社區公共安全服務與管理人少事多的問題逐步得以解決。切實整合社區內部的綜治、司法、信訪、民政、應急等資源,統籌發動轄區內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服務力量,建立協同聯動機制,做到風險隱患聯排、聯查、聯控、聯治,以更好適應新興風險的關聯性和發展演化。
3.3 豐富治理工具,促進要素融合
公共安全的治理離不開多種方式的綜合運用,新興風險下尤其如此。而城市社區參與公共安全治理,就是對以政府為主導的治理方式的豐富。同時,圍繞著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安全目標、公共關系、安全訴求、組織體系、內生動力等多要素的促進與整合,城市社區還應該進一步豐富公共安全治理的方式,促進各種要素的融合。
一是探索市場力量的參與。通過投資入股、吸收民間資金等形式,積極發展應急產業,針對比較突出的風險識別技術、隱患動態跟蹤等新興風險應對中的具體事項,使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工具得到延伸和拓展,從而能夠更加充分地調動市場資源做好應對新興風險的準備[17]。
二是以公共安全服務為杠桿,撬動整合社區各類自治組織、社會組織和市場主體的資源,開展安全服務、物業管理,形成安全隱患整治、安全服務管理、治理能力提升“三位一體”治理新格局。大力培育和發展專業化的公共安全治理機構,如建設社區應急服務中心等,通過向社區居民提供專業化的安全服務,建立比較完善的治理網絡,以更加充足地應對新興風險下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多樣化、個性化的治理需求。
三是全面分析安全治理機制與社區公眾參與之間的邏輯關系,厘清社區公共安全治理的價值因素,充分把握社區居民的安全訴求,形成共同的公共安全治理目標,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選擇治理工具并靈活使用,使社區的治理潛力能夠得到充分激活。
3.4 強化網絡構建,促進點線面結合
面對新興風險,處于多要素交相構建場域中的社區應以公共安全治理的目標與價值為導向,充分考慮安全資源分配的困境、安全產品供給的困境、風險主體利益碎片化的困境、治理工具選擇的困境,從加強治理網絡的構建上來應對新興風險及其轉化與演變。這就需要以現有部門職責分工和網格化管理服務格局為基礎,設計多主體、多層次、多階段、綜合性、適應性、協同式的社區公共安全治理架構。如重點加強社區安全基礎數據信息采集、社區重點區域領域管控、社區重點行業安全監管、社區重點人群服務管理、社區網絡安全保障等五個重點環節建設,明確社區公共安全治理優化的具體舉措。
加強和創新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還要在傳統“三基”(基層、基礎、基本素質)的基礎上,與“新三基”緊密結合。即以社區網格為治理基本單元,以結構網絡化、服務差異化、內容項目化、參與社會化、技術現代化、價值同構化為基點,以大民生、大安全、大風險、大治理為基線,以點連線、以線連面,采取源頭化治理、網絡化管理、專業化支撐、社會化參與的總體思路,最終形成資源整合、要素融合、條塊契合、手段綜合、功能彌合、點線面結合的城市社區公共安全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