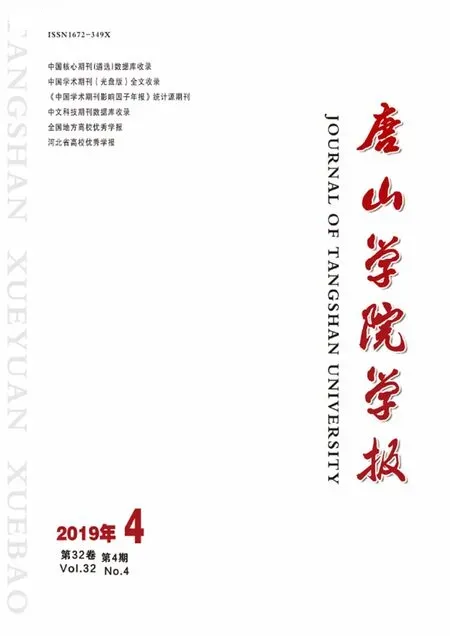古代法中的兒童:規范描述與價值分析
段立章,賈 維,徐曉靜
(唐山學院 文法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在現代社會,兒童作為人類未來的主宰、作為權利的擁有者,享有與成人同樣的人格與尊嚴。然而,兒童的這種定位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歷史發展和建構的產物,“兒童和兒童權利是歷史和社會建構的產物,‘兒童’并不是一個純粹由生物學所決定的自然或普通的范疇。它也不是具有某種固定意義的事物,讓人們可以借助其名義輕而易舉地提出各種訴求。相反,童年的概念在歷史上、文化上,以及社會上都是不斷變化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社會群體中,兒童曾被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有關兒童的定義乃是社會過程與話語過程造成的結果。”[1]歷史是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元素的復合體,而這些又通過法律規范得以集中展現,規范將不同時代人的形象與面貌通過權利與義務的形式描繪出來,“對于一個法律時代的風格而言,重要的莫過于對人的看法,它決定著法律的方向”[2]。那么,在古代社會,兒童的規范樣貌是怎樣的呢?本文通過對古代代表性法典的考察,試圖對此做一大略的描述與分析。
一、古代法中兒童的規范描述
(一)《漢謨拉比法典》中的兒童法律地位
《漢謨拉比法典》是古巴比倫第六代國王漢謨拉比“為使強不凌弱,為使孤寡各得其所”而頒布的一部法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較系統的法典,約公元前1772年頒布,其中多有涉及兒童的規定。
其一,父親主權。法典規定:“倘自由民因負有債務,將其妻、其子或其女出賣,或交出以為債權,則他們在其買者或債權者之家服役應為三年;至第四年應恢復其自由。”法典還規定:“倘自由民之配偶為之生有子女,其女奴亦為之生有子女,而父在世之日,稱女奴所生之子女為‘我之子女’,視之與配偶之子女同列,則父死之后,配偶之子女與女奴之子女應均分父之家產;當分產時,配偶之子得優先選取其應得之份。”該法典規定:“倘父于生前未稱女奴為之生育子女為”我之子女“,則父死之后,女奴之子女不得與配偶之子同分父之家產。女奴及其子女應解放,配偶之子女不得要求將女奴之子女變成奴隸。”
其二,父債子(女)償。法典規定:“倘人質因遭毆打或虐待,死于取之為質者之家,則人之主人應檢舉塔木卡之罪;倘[被取為質者]為自由民之子,則應殺其子,倘為自己民之奴隸,則被應賠償銀三分之一名那,并喪失其全部[貸款]。”法典還規定:“倘自由民打自由民之女,以致此女墜胎,則應賠銀十舍客勒。倘此婦死亡,則應殺其女。”
其三,父親尊嚴不可侵犯。法典規定:“倘子毆其父,則應斷其指。”
其四,撫護幼童。法典規定:“倘自由民意圖離棄曾為之生子之妾,或曾使之有子之不育婦女,則應將此婦女之嫁妝歸還,并應給她一部分田園及[動]產,使她能撫養子女。”“倘自由民淫其女,則應將此自由民逐出公社。”該法典還規定:“倘自由民已為其諸子娶妻,而未為其幼子娶妻,則父死之后,兄弟分產之時,應就父之家產中,除此未娶妻之幼弟應得的一份外,再給以婚姻聘金之銀,使之娶妻。”“已有幼年子女之寡婦,倘欲入他人之家,則非通知法官,不得前往。當其入他人之家時,法官應調查其前夫之家事,并應將其前夫之家委托其后夫及此婦,并向他們索取文書。他們應保存房產。撫養幼年子女,并不得將家具出賣。購買寡婦子女之家具者將喪失其銀;[子女之]財產應歸還其主人。”
其五,子責減免。法典規定:“倘自由民欲逐其子,而告法官云:‘我將逐吾子。’則法官應調查其事,如子未犯有足以剝奪其繼承權之重大罪過,則父不得剝奪其繼承權。”法典還規定:“倘子對父犯有足以剝奪其繼承權之重大罪過,則法官應寬恕子之初犯;倘子再犯重大罪過,則父得剝奪其繼承權。”
其六,此法典最早規定了人類兒童收養制度。法典規定:“倘自由民收養被遺棄之幼兒為子,并將其撫養成人,則[他人]不得向法院申訴請求歸還此養子。”“倘自由民收養幼兒為子,而在收養之時,彼已認知其父其母,則此養子得歸還其父之家。”法典另外規定:“倘自由民撫養其所收養之幼兒,但未將其視同自己之子女,則此受養育者得歸還其父之家。”法典第一九一條規定:“倘自由民撫養其所收養之幼兒,至其成家生子之后,欲將此養子逐出,則此子不應空手離去;撫養彼之父應就其財產中給他以繼承份額的三分之一,而后他可以離去;但養父可不以田園房屋給之。”另外法典還對宮廷閹人、神妓、手工業者收養幼童做了規定。
(二)《摩奴法典》中的兒童法律地位
成于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摩奴法典》[3]是古印度法典,內容涉及禮儀、習俗、教育、道德、法律、宗教、哲學等諸方面,其中有些條款涉及到了兒童。
其一,《摩奴法典》規定了嚴格的種姓不平等制度,這種不平等在兒童權利的規定中也有所體現,如該法典規定:“教師的兒子,勤奮可教的學生,能傳授其他知識的學生,正直的學生,清凈的學生,熱誠的學生,能力強的學生,慷慨好施的學生,道德高尚的學生,有血緣關系的學生,乃是依法準許學習吠陀的十種青年。”“同一城市的市民間,不以十歲之差而失其平等;藝人間不以五歲之差;精于吠陀的婆羅門間不以三歲之差;同一家庭成員之間,平等只存在不多的時間。”“十歲的婆羅門和年達百歲的剎帝利應該被視為父子,兩者中婆羅門為父,且應該被尊敬如父。”
其二,兒童和青年有尊敬和服從師長、父母的義務。法典規定:“青年要經常在各種情況下做可以博得父母、師長歡心的事情,三者都滿意時,一切苦行也就順利完成而獲得果報。”“恭敬地遵從三者的意圖,被稱為最卓越的苦行;學生未經他們許可,不得做任何善行。”“父親是由家長永遠維持的圣火;母親是祭儀之火;教師是供物之火。這三圣火應該受最大的尊敬。”“尊敬這三者的人,必尊敬其一切義務,而獲得其果報;但不尊敬這三者的任何人,其一切善行都無果報。”“當他們三者有生之年,不應該任意從事其它任何義務,但要始終表示尊敬的服從,一意承歡,奉事他們。”法典還規定“和父親有爭論的兒子”同“令人代己賭博者,酒徒,象皮病人,聲名狼藉者,偽善者,植物液商人”一樣無資格分享敬禮諸神或祖靈的祭品。
其三,法典規定要保護、憫恤兒童。如:“兒童、老人、被保護的窮人和病人應被認為是太空之主;長兄等于父親,妻子和兒子有如自己的身體。”“眾奴仆好像他(父親)的影子,女兒是最值得疼愛者;因而,如果這些人中的一個人得罪他,他要經常忍受而無慍怒。”“如果兒童沒有保護人,其繼承財產應該置于國王保護之下,直到他完成學業,或達到成人期,即達到十六歲時為止。”“欲靈魂得享安寧的國王,要不斷寬恕那些怒罵自己的訴訟者、兒童、老人和病人。”“國王應該始終尊敬知識淵博的神學家、病人、苦于憂患的人、兒童、老人、窮人、出身高貴的人和德高望重的人。”法典禁止殺嬰:“殺嬰兒者、以怨報德者、殺害請求庇護者或殺害婦女者,雖已根據法律進行自贖,也不可和他交住。”另外,該法典還規定了特殊情況下兒童的有限作證能力。“遇此情況,沒有適當證人時,可聽取婦女、兒童、老人、學生、親族、奴隸或仆人的供述。”“但因為兒童、老人和病人所述情況可能不實,法官應該將他們的證據看作是無力的,精神失常者的證據亦然。”
(三)古羅馬法中的兒童法律地位
古羅馬法是西方法律的源頭,從其中的一些規范中也大致能窺見早期西方兒童的存在狀態。
其一,在古羅馬法中,父親是一家之主。父親有種種權力,如,承認或不承認兒子的權力;嫁女的權力,也就是將他對女兒的權力轉讓給他人;為兒子擇偶的權力,因為兒子的婚姻與家庭的延續有關;出繼兒子的權力,由此而逐兒子于家庭和家祭之外;承嗣兒子的權力,由此而讓某一外人加入到本家的祭禮中。兒子與婦女的地位相同:他不能有財產,他工作的收入、經商的獲利都歸父親所有;他從外人那里獲得的贈與或遺產,承受者仍為父親,而不是他本人。古羅馬法禁止父親與兒子訂立買賣契約,因為兒子所得的財產均須交歸父親,所以若父親賣與兒子,就等于是賣給他自己一樣[4]81。
其二,兒童是父親的私有財產。據古羅馬與雅典法的規定,父親都有賣子女的權力。如《十二銅表法》就明確規定:“家屬終身在家長權的支配下。家長得監察之、毆打之、使作苦役,甚至出賣之或殺死之;縱使子孫擔任了國家高級公職的亦同。”而這種做法的理由是,父親是支配全家產業的主人,兒子可以被視為是他的財產,兒子的雙手勞動也是父親獲得收入的手段。所以父親有權或將這一手段留為己用,或出賣給他人。
其三,兒童被視為國家的工具。《十二銅表法》規定:“對畸形怪狀的嬰兒,應即殺之。”說明國家有不寬容殘疾人的權力。它可令人不要生下殘疾者,或將生下的殘疾兒殺死。之所以這樣規定,顯然是因為殘疾兒童被看作是國家、家庭的無用的累贅。在亞里士多德及柏拉圖所設想的理想法律中也包含將兒童視為國家之物的規定。柏拉圖曾說:“父母不能隨意令子女去還是不去國家指定的老師家讀書,因為兒童與其說屬于父母,不如說屬于城邦。”[4]295
其四,家長權在一定情形下有受限性。《十二銅表法》規定:“家長如三次出賣其子的,該子即脫離家長權而獲得解放。”這體現了古羅馬法第一次對父權權力的削減。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雅典法,兒子到了一定的年齡,就可以不再受父權的支配。另外雅典法律規定兒子必須瞻養他年老或不能自理的父親,由此可推斷,兒子可以擁有私產,以及他可以脫離父權的管轄。
其五,兒童刑責有減免情形。《十二銅表法》第8表第9條規定:“在夜間竊取耕地的莊稼或放牧的,如為適婚人,則處死以祭谷神;如為未適婚人,則由長官酌情鞭打,并處以賠償雙倍于損害的罰金。”
(四)中國古代法中的兒童法律地位
首先,中國古代法確立了長幼尊卑有序的身份等級秩序,不容僭越。如《大清律例》將“惡逆”“不孝”作為十惡不赦之罪。“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七曰不孝,謂告言咒罵謀殺祖父母父母……”“凡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斬,已殺者皆凌遲處死。”“其尊長謀殺卑幼已行者各依故殺罪減二等。”“凡子孫毆祖父母父母……皆斬,殺者皆凌遲處死。”“其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毆殺者,杖一百;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凡子孫違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者杖一百。”
其次,中國古代立法確認了家長主權原則。如《漢書·食貨志》載,漢高帝頒布詔令:“民得賣子。”《大清律例》亦規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辦理,不必審訊。”
再次,我國古代立法規定了兒童犯罪的刑事減免,中國古代《禮記·曲禮上》載:“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唐律》規定:凡年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反逆”殺人等死罪,可以上請減免,而“九十以上、十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大清律例》亦規定十五歲以下犯流罪以下收贖;十歲以下犯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盜竊傷人者亦收贖,余者勿論;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
最后,中國古代立法有保護幼童的條款。如《大清律例》:“凡收留人家迷失子女不送官司而賣為奴婢或為妻妾子孫者,受杖刑徒刑。”“凡鰥寡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如應給衣糧而官吏克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奸幼女十二歲以下者,雖和同強(奸)論。”“老幼不拷訊。”
二、工具化:古代法中兒童的價值分析
“童年的歷史幌如一場我們剛剛醒來的噩夢。我們越向前追溯這一歷史,就會發現照顧兒童的水準越來越低,而且兒童被殺害、遺棄、責打、恐嚇和性虐待的可能性越大。”[5]這樣一個描述對于整個兒童權利發展的歷史而言可能有點夸大,但對古代社會的兒童地位來講該敘事基本是準確的,這一點在上述文明古國的古代法中已有集中體現。在漫長的古代社會,兒童的社會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們被工具化、財產化或附屬化,被要求履行義務卻不享有權利。
首先,總體而言,在漫長的古代社會,兒童的價值被工具化,兒童僅僅被看作是國家或部族的財產和工具。在許多遠古時代的原始部落中,新生嬰兒不被當作人,而被視作父母或氏族的隸屬品。在這些部落中流行殺嬰、棄嬰(特別是殘疾嬰兒)或殺嬰獻祭等現象。在古希臘斯巴達,兒童屬于國家所有。嬰兒剛一出生,就受到國家長老的檢查,凡是身體畸形或孱弱的就被拋到峽谷墓地,檢查合格的則交給父母代替國家撫養。實際上,人類第一部禁止殺害嬰兒的法律直到公元374年才在歐洲出現[6]。在古羅馬時期,如果國家處于危機時刻,14歲以上的兒童也要像成年人一樣參加戰爭,在戰爭中殺人或被殺[7]。
其次,在古代社會兒童被作為權利的客體而非權利的主體。古代社會是等級森嚴的身份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處于社會金字塔頂端身份高的人擁有各種特權,而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則只能履行義務,甚至不被當人看。兒童在古代社會就處于社會金字塔的底層,在那個時代,兒童僅僅被看作是父權制家庭中的私人財產和家長的附屬物,是一種可以向其他成人自由轉讓的財產利益[8],其實質上是父權制的一種客觀對象物。在此種觀念主導下,父母特別是父親可以像支配私人財產一樣隨意處分自己的子女,對此國家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法律對父母虐待、遺棄或盤剝子女的行為不但不做禁止性規定,反而授權他們可以對自己的子女進行嚴厲的管教、懲罰或責打,乃至隨意買賣、扼殺。《圣經》中就有亞伯拉罕把兒子作為獻祭的記載。
在古代,作為他權人,兒童在家長主權之下,毫無法律地位可言。“法律止于家的邊界”,古羅馬法學家蓋尤斯就說:“要知道,人們不能將正義轉讓給在權力之下的人,即妻子、兒子、奴隸。就像他們沒有什么東西屬于自己的一樣,他們也不能要求得到正義。如果在你管轄下的兒子犯了罪,那么法律就將你告上正義的法庭。兒子針對他父親犯下的罪,不具備任何的法律效果。”[4]81由此顯然看出,在古羅馬兒子在法庭上既不能做訴訟人和辯護人,也不能做原告、被告及證人。家中只有父親可以上城邦的法院,公義只與他一人有關,全家人一切罪責均由他一人肩負。在家庭內部,家長是審判官,憑著他擁有的夫權和父權,在家神的監視下可以以家庭的名義進行審判。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家庭的屬性是個人與私人生活的一種現象,兒童是家庭或者父母的一種延伸。這種觀點流傳久遠,甚至在啟蒙時代霍布斯還主張兒童完全處于父母的支配之下,父母依據自己的選擇來維護或是毀滅他們的孩子[9]。與此類似,中國古代也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極端主張。
再次,在古代家長、成人中心論下,兒童的特質泯滅不彰。在歐洲中世紀,“預成論”曾大行其道,該觀點認為,兒童與成人僅有尺寸大小、知識多寡的區別,而否認二者在身心特征上的重大差異,因此主張用對待成人的標準對待兒童[10]。甚至到了中世紀社會依然不存在童年觀念。阿里斯主張,在中世紀童年和成年之間幾乎看不到什么區別,人們意識不到兒童的不成熟,兒童一到七歲就完全參與成人生活[11]。在兒童面前,成人百無禁忌:粗俗的語言、淫穢的行為和場面,兒童無所不聽、無所不見。兒童一脫離尿布,馬上就穿得和成人一樣[12]。諾伯特·埃利亞斯也認為在中世紀,“成年人與兒童之間的差距很小”[13]。兒童及其童年在此失去了自身獨特意義。
基于兒童的此種定位,對兒童的體罰在古代是被普遍認可的。在古代社會操控兒童命運的有“兒童原罪說”。“原罪說”的兒童觀認為,由于人類的祖先亞當及夏娃不聽上帝的話,偷吃了伊甸園的禁果,因此染上“原罪”(original sin),并遺傳給子子孫孫,兒童生來本性傾向邪惡,故須嚴加管束。如基督教會《舊約》里就有這樣的話:“不可不管教孩童,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靈魂免下陰間。”一份中世紀的德國布道書中的觀點是:“就像貓天生愛抓老鼠,狐貍愛抓小雞,狼愛吃小羊一樣,剛出生的嬰兒在他們的內心中也有一種天生的不良傾向,如對奸邪、不道德行為的渴望,對偶像的崇拜,對魔法的迷戀,對敵意、爭吵、激情、憤怒、沖突、紛爭、結黨營私、仇恨、謀殺、酗酒、貪吃等等行為的嗜好。”[14]一個叫約翰·羅賓遜的牧師曾寫道:“可以確定地說,在每個兒童心中都有一股源自天性的執拗和堅決,但在它們剛冒頭的時候父母就必須堅決打擊和粉碎掉這種性情。這樣才能在謙遜和溫順的基礎之上對他們實行教育,他們那個時代的其他品格也才能夠養成。”[15]于此類似,中國古代也有“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育兒觀。
當然,古代社會對兒童而言雖有冷酷的一面,但亦有溫情的一面。體弱恤幼及差別化對待的思想在古代盡管不是社會的主流意識,但卻確確實實存在著——是古人留給今人的一大精神財富,亦是后世兒童權利得以生發的一塊沃土。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代世界各國都有類似的思想,如基督教經典告誡人們“不可挪移古時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兒的天地”;伊斯蘭經典《古蘭經》亦訓誡道“要照顧孤兒。待他們不得殘忍,必須善待”[16]。當然,“古人慈幼的思想基點并不在于兒童本身,而在于國與家的政治經濟利益,被用作齊家治國、富國強兵的政治手段,作為社會政治倫理維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倫常關系。此外,還被作為鼓勵人口增殖的措施,服務于富國強兵的財政目的和軍事目的”[17]。
三、余論
有人說:“西洋在16世紀發現了人,18世紀發現了婦女,19世紀發現了兒童。”[18]誠哉斯言,在漫長的古代社會,兒童一直被作為一種有用的工具、一種可易的財產、一種家長的附屬物來看待。兒童被作為人來看待、作為獨立的人格主體來看待,是近現代特別是二戰后社會發展的產物。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兒童的發現——兒童被社會作為平等的人格主體來看待——要遠遠晚于人(成年男人、女人)的發現。因此,時至今日,兒童權利觀念、兒童平等主體觀念在整個社會觀念場域中遠未牢固地樹立起來,根深蒂固的古代兒童觀在現代社會依然還有殘存,還在影響著成人世界的價值選擇,還在制造著現代兒童悲劇——如現實生活中時有發生的虐待兒童、拐賣兒童、選擇性墮胎等丑惡行為的發生往往與此有關。因此,關愛兒童、保護兒童不但需要在規范上建章立制,還需要在觀念上清除古代社會遺留下來的有關兒童的一些錯誤觀念,使兒童權利觀、兒童平等主體觀真正在全社會樹立起來,從而為兒童的健康成長構筑起制度和觀念雙重支撐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