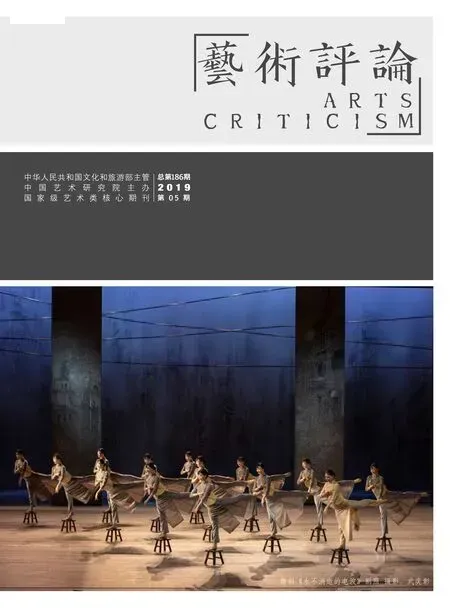近代華南繪畫的洋風演變
[內容提要]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東南沿海首先開放了通商城市,受此影響,那里的繪畫逐步產生西洋風特色,題材與內容也更多地反映商業發展情況。畫工努力展現他們理解的西洋技法,并將中國民間題材的畫面與西洋畫的氛圍協調起來。這類民間繪畫采用“西方的眼鏡、東方的情趣”的方式,來展現獨特的繪畫語言,是日后西洋藝術技法的普及與藝術創作大眾化的重要過渡。那一時期形成的民間洋風畫給20世紀中國繪畫的發展帶來了一定影響。
在歷史研究中,普遍以鴉片戰爭的開始,即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或“晚清”的開端。筆者依據華南沿海民間美術的演變,曾建議把“近代”定為1780年至1910年。再將整個時段以1850年為界,劃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中國人帶有一種主動和西方交往的態度,清宮廷仍供養著傳教士畫家,宮廷之外西洋畫家由寓居澳門逐步在華南沿海城市移居寫生,并影響中國南方沿海的民間繪畫,中國民間繪畫也開始出口歐美。然而到了1856年,即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飽受戰爭的煎熬,尤其是英國人對廣州、廈門、定海等城市的破壞,西方列強的侵略行為已經昭然若揭。在十分被動的情況下,中國北方與長江沿岸開放了更多的通商城市,來華的西方報刊紀實畫家增加了,中國民間繪畫逐漸發生洋風演變,并且由南向北擴展。
本文所探討的對象是19世紀中期以降具有西洋風特色的中國民間繪畫,論述它們受西方影響的源頭、畫面基本內容與洋風特色,及其給20世紀中國繪畫進程帶來的影響。筆者認為,當中國人認識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必要性時,民間繪畫則采用“西方的眼鏡、東方的情趣”的方式,來迎接新的社會變革。
一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早以圖像為主的畫報,該報將赴華西洋畫家、新聞插圖家所繪的素描或水彩原作,以趨于成熟的細密木刻版畫(wood engraving)刊載出來,這種細紋利刃制作的木版畫,以及后來采用的平版石印套色版畫,都具備精湛高超的表現力。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隨后的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各國報刊的插圖,都將真實性的紀錄放在首位,完全寫實,這些報刊的插圖內容反映了中外關系或中國國內的重大事件,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等,也在中國間接傳播了西洋繪畫及技法。當時報刊中的許多插圖并沒有注明作者,有些插圖是對早期西洋畫家來華寫生或創作的作品加工,有些則是由各國特派畫家完成的。沃格曼(Charles Wirgman)1857年始作為特派中國的畫家與通訊員,發表了大量有關戰爭與社會生活的圖文,他的《中國畫家們》記錄了一家在香港的中國畫室的內部,展現了畫工作畫的場面。一些報刊發表的作品則明確注明“依據中國畫家的繪圖”,如《采茶的中國婦女》《絞死罪犯》《押罪犯赴刑場》等。1843年出版的畫冊《中國:那個古代帝國的風景、建筑和社會習俗》載有英國畫家阿羅姆(Thomas Allom)繪制的128幅版畫,更加完整地反映晚清社會,再現外國使團拜見中國官員、官員招待外使、戲臺、表演以及花嫁和出殯等場景,地域則從北京城郊到澳門海島都有涉及。以上畫作彌漫著西方人遺留下來的東方美好印象,顯示畫家的素材不僅來自赴華畫家的速寫,還包含早年所收集的有關中國的圖像。此類書刊既為西洋藝術在中土的推廣開辟了廣泛的渠道,同時為華人模仿與學習西洋畫技法提供了有利條件。至19世紀中期,華南沿海繪制外銷畫(trade pictures)形成風氣,且區域持續擴大。此前外銷瓷繪畫——主要是廣彩瓷器開南中國沿海西洋畫法之風——還只是少量的仿西法繪瓷面,后來大規模的中國藝術圖像載體是瓷器、絲綢、扇子、漆器、壁紙,這些不同材料上的中國民間工藝,向西方展示了東方繪畫技巧與神奇迷人的文明。隨著東西方經濟交往的擴大,為迎合西方的欣賞品位,廣東珠江口的畫家轉向以草紙水彩、布面油畫、玻璃背畫等材料繪制的各種西洋技藝,外銷畫從復制西畫到模仿洋技,進入創作性批量制作,逐步演變為一種以本地畫工為創作主體的民間洋風畫。如紙本水彩《廣州商館區》描繪西洋人早年位于廣州城外黃埔江邊十三行商館的建筑,廣場上旗桿自左至右懸掛法、美、英、荷蘭等國國旗。目前,盡管這類佚名民間畫工的作品國內收藏較少,但是當年并非以“外銷畫”概稱它們:一方面,晚明以來仿西洋筆法的風俗圖是外銷畫的最初來源,當西洋人訂購后才稱“外銷”;另一方面,當年裝訂的畫冊或單面圖像是在街面畫店中由中外游客自己選購,許多內容顯然是針對國內市場的。
在照相時代悄然到來之際,中國各地開埠城鎮中,許多民間畫工依然吸收西洋技法作畫,他們陸續使用不同材料、采用中西混合手法制作的繪畫取得了累累碩果,形成頗有特色、形象鮮明的畫種。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民間洋風畫逐步成為大眾的尚好。
二
誠然,中國民間畫工的畫風變革,是“西風東漸”的時代所趨,當外國人進入五口通商城市之后,“這些遠道航海來到廣州的外國人,多半都想買些異國情調的藝術品作紀念,聰明而又有寫實技巧的民間畫工依據這一市場上的新需求,開始創作一般商賈人士易于攜帶出國的紙本繪畫;內容當然要與東方中國的風物和文化有關,形式上自然也以中國的工筆細膩為上乘了”。《永泰興通畫店買賣場景》就展現了西洋人購買畫作的過程,學徒領著西方人來店鋪,學童拿出架上的各式畫冊,由店員與購買者商討、論價、挑選作品,畫工在一旁展示作畫方式。據說此畫店活躍于1860年至1890年,“外國客人踏進店鋪,店主會攜合伙人或伙計,以形形色色的問候來歡迎,有時候會迎上前來握手,竭盡其能地用有限的英語致意”。筆者認為,這類民間圖像具有“西方的眼鏡、東方的情趣”特征,“眼鏡”指西洋技法與觀察方法,“情趣”指傳統的中國風物。這些畫作充分體現了人們對近代商業發展的興趣,下面分四類敘述:
第一類是城鎮地志畫。這與鴉片戰爭之后開埠城市由南向北、由沿海向沿江發展有關,內容包括各種特色城市建筑風貌,及周邊的自然環境。組畫《澳門》《虎門》《黃埔》《廣州》解說了西方商人如何在華開展生意:澳門是外國商人不遠萬里、長途跋涉來到中國的第一個落腳點;虎門(Bocca Tigris)是通向珠江一條河的關口;黃埔是那些來中國做生意的商船停泊處;廣州則是最終的目的地。澳門是新興商埠城市,該地發生的新事物、新景觀受到國內外人士的關注,在城市組畫中首當其沖。《從東面眺望澳門南灣》以近距離、高視點描繪南灣水岸景觀,遠方天空中白云與群山簡潔柔和的線條,西望洋山教堂與葡萄牙人構筑襯托出南灣大街的繁華,懸掛大清國旗的紅色建筑為清政府南灣稅關,白色建筑是澳門市政機構,懸掛英國國旗的“漢口”號輪船在行駛。本圖對造型作了大膽變形,加強對固有色彩的夸張,畫面展現了裝飾性、民俗化油彩語言。葡萄牙人自15世紀開始海外擴張,在地理大發現過程中將自己長年積累的建筑樣式曼努埃爾風格帶到了各個新擴張的大陸及島嶼,澳門許多教堂即有明顯特征,如三巴寺“雕石、綺疏制珠瑰麗”,小三巴寺也“規制差約,軒豁過之”,板障廟“壯麗特甚”,這些均屬典型的西式宗教建筑,描繪這種東西洋文明交匯的景觀,讓人耳目一新。而流行于道光末年(1842—1850)的水粉風景畫,如《六榕花塔》《花棣舊跡》《園林美景》《芳園樓景》,均以真實地點的典型景物為對象,晚清人物服飾與中式花園建筑成為描繪的主體。雖然畫面中人與場景的比例、西洋色彩與焦點透視都還比較生澀,但它們趨向世俗化、寫實手法與融會中西的特征,體現了社會與時代的變遷。
第二類是世俗風情與中外人物肖像,尤其突出了街市百業或商業人士。《蒲呱水粉畫一百幅》是晚清市井各行各業的總匯圖像,色彩清新、主題鮮明,既有《繡花》《整扇骨》《撣棉花》《油漆》的傳統手工業場景,也有《賣扁食》《做箱》《剃頭》《釘屐》等小生意行為的寫照。其中《造酒》表現常豐酒行復雜的釀酒工藝,《寫畫》展示了中國人如何復制西方圖像,《山水梅湯》的賣者手握長勺子,正將楊梅湯注入小碗,畫家抓住了主人瞬間動態并精心營造出的商業氛圍,“翻閱這些藝術作品,廣州市井眾生相即刻呈現在我們眼前,豐富多采,栩栩如生”。此外,描繪以專營貨物為店面的作品有《瓷器鋪》《茶葉鋪》《煙絲鋪》等,《西式家具鋪》《洋表鋪》所描繪的店面,經營的應該是進口洋貨。現存一套展現社會節慶習俗的《元宵節舞燈》,共8幅,每圖描繪5人,提著各類工藝燈具做游戲,背景全無,近似京劇舞臺。此組畫題材、色彩、線條筆法及構圖處理大抵采用傳統筆墨,但是在立體陰影效果、人物動態方面吸收西洋畫法,屬于典型的民間風俗繪畫,用于懸掛裝飾是很好的。此外,學習西人油畫改繪水粉畫的“十三行行商”均為半身或全身肖像,雖然此前有伍浩官、潘啟官等名頭,但民間作品并不特別標明,只是重在表現他們的官商禮服而已。更多“達官貴人”“官宦人家”“戲劇角色”之類組畫,畫面五彩繽紛、場景復雜,人物眾多、姿態豐富。
第三類是對典型器具與事物的記錄,如車船、動物、植物的描繪,又如刑事事務場面的展示等。國內公私收藏的船舶圖像有數十種。一方面船舶是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和生產資料;另一方面它們的造型體現了東方民俗特色。如《賽龍舟》表現大大小小裝扮著節日氣氛的龍舟,大者有數十劃手,官船上貴族達人在一旁觀看,小龍舟劃手在鼓勁,場面壯觀。而形形色色的《養鴨船》體現了勞動者的智慧與勤勞。另外,《成利號店船》《太子太師船》《鄉科進士船》以及仿西洋的《洋船》,描繪的都是晚清特殊船舶。各種西洋船舶也成為地志畫中的主體。清代政治法律制度既是西洋人窺探中國的途徑,也是鄉官告誡懲治民眾的手段。對律令規定的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5種刑罰,許多作品有詳細描繪。現存數種冊頁《刑罰》,由12幅或8幅組成,展現審判、鞭刑、枷號、發號、監斬、驗棺整個過程。這些畫在今日南陽、淮安等地舊縣衙博物館中,與照片、道具同展,證實晚清刑律的殘酷。雖然畫中人體結構的描繪還不太成熟,但是器具、人物動勢和表情、悲慘的景況卻能清楚呈現。
第四類是表現行業生產的組畫,涵蓋了絲綢、茶葉、瓷器等物品的生產過程。清代絲茶成為中西貿易中交易額最大的商品,這些畫面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社會生產風俗的重要媒介。1870年吳俊創作的作品《制絲》,共16幅,其中有12幅圖與康熙時期御制《織圖》(共23幅)內容相近。如同樣題名的有《采桑》《上簇》《炙泊》《染色》等,均有照顧老小、娃娃玩耍的田園樂趣,康熙時期傳統風俗畫中最后為成衣細節,吳俊則以《裝運》《絲商》《入倉》《洋行》4幅傳達了蠶絲從絲廠到洋行的商業開展過程。《洋行》描繪了一幢似有南歐圍廊的二層建筑,門前有“如意洋行”牌子,有華人向樓內洋商通報,坐著轎子的買辦正好下轎。組畫出現社會變革中涌現的絲廠、絲行、洋房與中外商人等細節,這都是過去沒有的。另一套組畫《制瓷》共20幅,展現珠江海貿景象,以及為瓷器貿易專設的貨倉、店鋪,其中《陸路運輸》《水路運輸》展現了當時瓷器的生產與流通的規模。組畫《制茶》也有一幅描繪行商與外國人直接在裝箱倉庫前會面交涉的情景。康乾年間刻畫制茶、制瓷等商品具體生產程序的畫面較少,而那時外銷的民間繪畫則將世代相沿下來的特殊商品制作過程給予更加系統、精致的描繪。這類組畫常常細膩地描繪地方民俗、建筑、人物,畫作不僅滿足了中外人士對中國物產及其制作方法的好奇心理,同時也提供了具有實用價值的農業生產技術知識。
除了內容多為中外商品交易、近代開埠城市與生活習俗之外,這些畫的工具與形式還展現了中國情趣。畫工多利用傳統水墨工具,拓展工筆細膩畫法,體現了中國民間繪畫的實用性。當時流行一種繪制方便、價格便宜的草紙水彩畫(gouache on pith paper),多以墨線或褐色線條勾勒外形,并以半透明水彩畫法填色制作,也稱“通草紙畫”,這類畫確實稱不上高雅藝術,但它們具有明亮鮮麗的色彩并且非常有特色。畫在宣紙或通草紙上的獨幅畫或裝訂成冊的組畫,還常常在捆包或裝訂成冊后外銷歐美。另一種在玻璃背后用油彩或水彩繪制的作品,被稱為玻璃畫(glass painting)或背畫,有些題材是按照西洋原作臨摹的,有些則是土產的受人喜愛的民俗繪畫,如大多以大紅大綠為主的半身或全身女性肖像,有的畫面展現了臥床上的女性正在閑情讀書、母親哺育幼子等情景,有的則展現帶有歐式建筑的海岸風景。這種玻璃畫既是中國內壺畫的發展,也是傳統界畫的延伸,既銷售內地,也輸出海外。目前玻璃畫以廣東、山西二省流轉為多。
三
毋庸置疑,中國繪畫的洋風演變受到了西洋人的喜好,這不僅由于它們體現了與商品貿易或生產的直接聯系,更是因為在當時這種新畫種具有攝影記錄實景、實物的作用,是重要的信息媒介,為世界了解中國打開了一扇大門。它們以紀念品、裝飾品,或者官方贈品的方式,流向歐美,被攜至天涯海角。這些西洋人在華短暫居留,直接購買的畫作主要是依據訂單在對外商埠交易中的單件,數量之多甚至以捆包裝。這類繪畫借鑒了西洋科學知識,體現中西繪畫互補的新奇,因此也普遍受到本土民眾的歡迎。從近代中國民間繪畫的對象、手法、流通及市場的特殊性,可以窺視近代中國社會發生的急劇變化。
19世紀末人們評價中土西洋畫是匠藝之作,如畫家松年認為“西洋畫工細求酷肖,賦色真與天生無異,細細觀之,純以皴染烘托而成,所以分出陰陽,立見凹凸。不知底蘊,則喜其工妙,其實板板無奇,但能明乎陰陽起伏,則洋畫無余蘊矣”。但民間畫工卻大膽吸收西洋繪畫技法,他們以西洋明暗表現、焦點透視畫法為手段,來贊美民間風情、新生事物,達到吸引民眾、擴大市場的目的。這些借鑒西法的畫作具有洋風特色,如民間油畫《廣州》以近距離的俯瞰視點描繪珠江河岸景觀,包括街道、大碼頭商業區的繁華景色。全圖講究空間關系,又注重平面構成的效果,還大量運用原色,尤其遠去的馬路與紅色三層建筑像是為了專門介紹西方透視似的,使得畫面熱鬧非凡,很有感染力。在“茶葉”系列組畫中,《行商》描繪一個50余人的茶葉包裝工場,華商與洋人的交涉放在畫面最前方左側,所有場景統一在一個大屋子中,加上適度的明暗關系處理,景深效果非常好,栩栩如生的人物動態一目了然。這種民間洋風畫內容一般都簡明易懂,如有些畫面,風景場合幾乎雷同,只是人物穿著、建筑樣式略有變化。這類專門瞄準老百姓喜好的作品,不過是讓他們品嘗一下異國技法罷了。
至于模仿陰陽起伏的立體感覺,民間畫工在人物組畫中,有自己更多的主觀選擇。草紙畫《清代婦女與女仆》是較早的嘗試,圖中女仆取糕點佇立女主人一側,二者臉部皆以西洋明暗渲染,其余如桌子、花瓶等都有大體明暗,服飾與地面則完全以平涂繪出,畫法接近清宮廷借鑒西洋技法的重彩畫。而在蒲呱的《織布》《車煙桿》《車魚缸》等畫中,人物全身比例、道具透視效果、整體明暗關系,都較準確,證明畫家較為成熟地把握了西洋技法。流行于道光末年(1842—1850)的水粉風景畫《廣州西山》《香港遠眺》等,均以真實地點的典型景物為對象,目的就是引起人們的喜好。
民間畫工及洋風畫推動了文化下移、藝術大眾化的潮流。首先,制作時復制與模仿手法使稍加指點的廉價勞力都能參與,作坊主不必付重金招聘畫家。在《廷呱畫室》中可以見到,背景掛滿肖像畫與風景畫,靠窗戶的三位學徒正在一絲不茍地描寫畫作,畫面上方扁額書“靜觀自得”,這幅具有廣告性質的畫是想讓購買者知道這些畫是如何制作的。雖然外銷畫興盛之際,有許多畫工參與制作,但是他們留下的只是銷售作品時的店號名,如由英文名字譯過來的啉呱、庭呱、新呱、煜呱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民間繪畫的題材與內容,都具有教誨作用,這也使民間洋風畫能在民間迅速推廣。如近期發現的佚名《澳門內港》,畫中題字“讀可榮身書可富,勤能立業儉能豐”,顯然有鼓勵民眾好學勤勞的目的。這幅畫吸納了西洋明暗的方法,所有建筑、山體都有陽光的照耀,陰影合理,同時它又是一幅帶中國青綠山水特征的民俗繪畫。此時,廣東還出現了全新主題的組畫“新式救火”“勸戒鴉片”等。“家里的東西賣完了之后,鴉片鬼就完全依賴于妻子和孩子織布所掙來的微薄收入。圖中因犯鴉片癮而痛苦不堪的鴉片鬼正低聲下氣地懇求妻子和女兒給他買鴉片的錢。”這意味著,這些新聞性作品作為商品畫在國內流通時,也具有改善社會風俗的意義。
四
近代中國民間繪畫是隨著國門打開、商品外流發生變異的。這種變異與馮桂芬在晚清洋務運動中倡導的“采西學”“制洋器”主張一致,中國人期望利用各種西方技術來抑制殖民化,同時又通過學習西方文明來改造落后的風俗。在晚清大變局中,中國民間洋風畫跟上了“西風東漸”的時代潮流,具有積極意義。

另一方面,民間洋風繪畫為近代工藝設計的起步以及嶺南繪畫的突變,提供了一定的技術基礎。珠江口岸的城市因商品貿易的需求,出現了最早的商標設計、招貼海報,其中的繪畫部分是以民間洋風畫為范本的,有些甚至整個畫面直接采納了民間風景、人物、靜物等典型形象。早期設計的手稿則使用了水彩畫方法。筆者收藏的“益隆號”商標《鴛鴦荷花圖》,色彩濃烈、層次清晰,背景天空由冷色變暖,體現制作者對水彩技巧的有效把握。清末民初,學習西洋美術風氣興起,嶺南畫家最早開展了廣泛的中西融匯的傳統水墨畫創作,他們的作品從題材與內容、寫生的功力來看,留下了民間繪畫的痕跡,例如表現自然景色中日落晚霞的瞬間,表現開埠城鎮的市民社會生活,表現相對復雜的人物動態及其組合場面等。可以說,居廉、居巢對蔬果、花卉的精細刻畫,嶺南畫派高劍父、陳樹人等人對實景與場面的紀錄,方人定對人體骨骼的熟悉,甚至鄭錦(1883—1959)對寫實與意境的相互融合,都與近代民間繪畫的繁榮、變異有一定的聯系。

注釋:
[1]廣義而言,“晚清”實指乾隆、嘉慶以至宣統時期,而“近代”則指1840年至1911年期間。參見李鑄晉、萬青屴《中國現代繪畫史——晚清之部·導論》,文匯出版社,2003年。筆者在《晚清赴華西洋畫家與中國洋風藝術》文中提出此想法,載于《回憶與陳述》,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年。
[2]可以簡稱“中國洋風畫”,1995年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舉辦展覽并編印《中國洋風畫展——明末至清代的繪畫、版畫與插圖本》,通過圖文結合深入探討了此專題。近30年出現不少此類畫冊,參見筆者《澳門美術史》所附文獻。另見《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精華》(全8卷),王次澄等編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銀川當代美術館編《視覺的調適:中國早期洋風畫》,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中國西畫的起源——通草畫》,神暢畫廊,2016年。
[3] 莫小也.地志畫與澳門地志畫研究述要[J].文化雜志,2003(49):145—170.
[4]香港藝術館編.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M].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231—232.
[5]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M].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53.
[6]夏新德.奧古斯特·博爾杰[J].文化雜志,1993(10):75—81.
[7]Robin Hutcheow.Chinnery.Hongkong:Form Asia.Weatherhill,1989.P.27.
[8]普林塞普(Willian Prinsep)以油畫為材料繪制了《澳門媽閣廟》(1838),畫面中媽閣廟前的廣場上有漁民、商販及西洋人、貴婦,近處漁家女的紅圍巾將人們的目光吸引到水上生活的小船。屈臣《從大炮臺看澳門景》等速寫常常以鉛筆排線與棕色淡彩相結合,有雅拙之趣味。參見香港藝術館編《香港及澳門風貌》,1983年,第41頁。
[9]《倫敦畫報》的創刊號就有插圖32幅,發行26000份,到了1863年已經達到30萬份。據統計,該刊自1842年至1894年關于中國單幅圖像就多達400余幅。參見黃時鑒編著《維多利亞時代的中國圖像》,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第5頁、第18頁。但黃書中同一插圖秦風卻認為是銅版畫,需要進一步鑒定。參見其編《西洋版畫與北京城》,四川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102—103頁。
[10]此間還有英國《泰晤士畫報》(Illustrated Times)、美國《格利生畫報》(Gleason’s Pictorial)、法國《世界畫報》(Le Monde Illustre)等經常刊載中國圖像。參見沈弘編譯《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
[11]程存潔.19世紀中國外銷通草水彩畫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3.
[12]英文版原書名China:The Scenery,Architecture,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由賴特(G.H.Wright)撰文。李天綱編譯后名《大清帝國城市印象——19世紀銅版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3]中外學者統稱“中國外銷畫”或“貿易畫”,西方學者另以“中國沿海繪畫”“港口繪畫”“船舶繪畫”“中國貿易歷史畫”等稱呼它們。參見筆者論文《港澳地區歷史繪畫研究評述》,《藝術探索》,2008年第5期。
[14]外國商館區建筑主要是清代十三行(也稱公行)商人伍浩官及潘啟官的財產,由洋行租下來,因為正好十三家,故又稱“十三夷館”。在英國館前有商館區花園,種植大片樹木,其他館周圍有木柵。商館前邊有大片廣場伸展到珠江邊上,中央港灣有中國海關稅館。前景水面上大批船只,紅綠裝點似官員座船,后有英國小艇。數不盡的小船沿岸停靠,可以看出廣州作為清代對外貿易重要城市的繁忙景象。引圖現存澳門藝術博物館,見該館編《歷史繪畫》,2009年,第67頁。
[15][19]王樹村.廣東民間美術[M].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6:71,87—99.
[16]〔美〕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游記[M].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16.
[17]William Shang.Drawings from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1792—1794[J].Arts of Asia,May-June,1998:75.
[18]以上引用自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下《澳番篇》,清乾隆五十六年修,嘉慶五年重刊本。
[20]黃時鑒.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三百六十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11.
[21]澳門藝術博物館藏HP1998-281-288,佚名中國畫家,水彩并勾線,31.5cm ×19cm,約1880年,通草紙紙本。各畫題名為:1.出游;2.八卦轎;3.舞獅;4.點炮;5.魚蝦燈;6.鮮桃青蛙;7.舞鯉魚;8.放炮杖。
[22]程存潔.十九世紀中國外銷通草水彩畫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4—128.劉明倩等編.18—19世紀羊城風物: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廣州外銷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88—217.
[23]程存潔.十九世紀中國外銷通草水彩畫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57—280.
[24]劉明倩等編.18—19世紀羊城風物: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廣州外銷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0—131.
[25]Ifan Williams.Views From the West-Chinese Pith Paper Paintings[J].Arts of Asia,Sep-Des,2002:147.
[26]松年.頤園論畫[A].中國畫論輯要[C].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5:288.
[27]王樹村.廣東民間美術[M].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6:87—99.
[28]參考陳瀅《陳瀅美術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44頁。本人認為,就似啉呱的油畫作品不能被精確認定的情況一樣,許多庭呱風格的草紙畫畫作現在也不能確認是庭呱本人所作,大多數應當出于他畫室的學徒之手,甚至是后人以此風格作畫,也貼上“庭呱”商標,因為他的風格更適合復制與銷售。
[29]Carl Crossman.The Decorative Art of the China Trade[M].Suffolk: Antique Collector’s Club,1991:9.
[30]江瀅河認為民間洋風繪畫有“出口商品”“西洋風格”“身處社會低層的畫匠完成”要素,指出“在廣州,從18世紀中葉開始,出現了專門為西方市場創作的外銷畫。身處社會低層的畫家和畫匠們,能夠適應外貿的需要,臨摹和復制西洋繪畫,繪制出當時被人稱為‘洋畫’的廣州外銷畫”。見江瀅河《清代洋畫與廣州口岸》,中華書局,2007年,第2頁。
[31]本圖由澳門藝術博物館向本人提供,原圖紙面曾經嚴重損壞,目前已經修復并公開展示,圖上左側有題字,雖然無作者及日期,可認定是19世紀有繪畫功底者所作,在此向該館表示謝意。
[32]1858年12月18日《倫敦新聞畫報》刊印一組版畫《鴉片鬼的墮落歷程》共6幅,聲明是根據一位中國畫家的作品繪制的,這是第5幅的說明詞。參見《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倫敦新聞畫報〉記錄的晚清(1842—1873)》(中),沈弘編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第371—376頁。
[33]《說蠻》,《昭代叢書》已集,卷三十四。